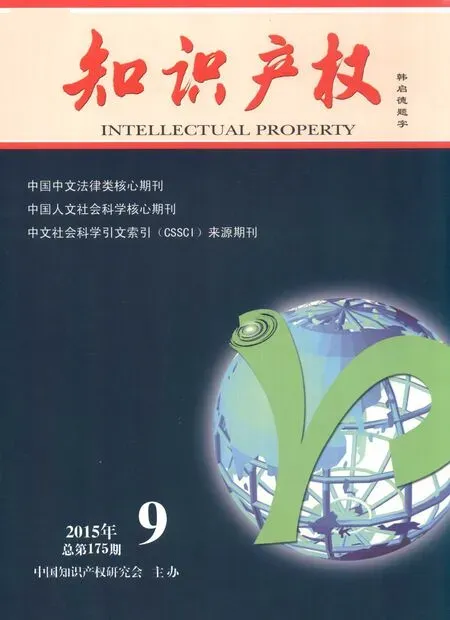《著作权法》修改中有关发表权存废的思考
2015-01-30赵宝华
曹 伟 赵宝华
《著作权法》修改中有关发表权存废的思考
曹伟 赵宝华
内容提要:伴随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逐步进行,发表权应否继续作为一项单独权利而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不同反响。发表权常常伴随着著作财产权的实现而实现,在司法实践中单独涉及发表权的案例也较少,但该权利亦存在经由其他著作权无法实现的独立权能以及作为著作人格权的独立价值。对发表权的片面把握将导致人们对该权利的忽视。本文旨在阐明发表权内涵及其实现途径,强调发表权存在的独立价值,参考比较国外发表权制度,并说明删除发表权的不可欲性。
著作权法 发表权 实现 价值
相比于其他著作权,发表权无论是在学者的著述中,还是在现实的案件中都呈现出比较“低调”的姿态。有关发表权的理论研究为数不多,涉及发表权的司法案例也屈指可数。这样的事实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即在整个著作权权利体系中,发表权似乎无足轻重。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有学者认为“当作者第一次行使自己经济权利的时候,例如复制、发行、表演、展览自己作品的时候,就同时行使了发表权”,①参见李明德、管育鹰、唐广良著:《〈著作权法〉专家建议稿说明》,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因而建议取消发表权。事实上,对于该权利的存废之争早已有之,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界对该权利的认识不够统一。为此,在论证发表权应否存续的问题之前,理应对发表权的内涵、价值等进行梳理,以构建论证之前提。
一、发表权与及其实现
(一)发表权含义的检视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而学界通说认为,是否发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表都是发表权的权能所及。如李明德所言,发表权“是指作者有权决定其作品是否发表,何时发表,以及以何种方式发表的权利”;②参见李明德著:《著作权法概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李雨峰亦指出“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公之于众的权利”③参见李雨峰、王迁、刘有东著:《著作权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等。诚然,这样的定义足以明确发表权的本质——从权利人主观方面考究,发表权就是一种发表决定权。是否发表由权利人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表亦由权利人决定。但客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现实中当权利人决定以发表作品的方式行使发表权时,作品能否真的公之于众仍存在不确定性。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作者以发表的意思将自己的作品交予报刊社,报刊社退回作者的作品而不予发表。这时作者的发表权仍未得到实现。因此,发表权有时并非权利人单方面行使决定权就可以实现的。既然如此,在对发表权进行定义时,如果只强调发表决定权就无法对现实当中发表权的真实状况作出总括。通说的这种定义方式突出了发表决定权,但这只强调了发表权行使的最初阶段,至于决定发表之后发表权如何走向实现,按照这种定义我们不得而知。
真实的情况是,在权利人作出发表的决定之后,发表权即进入行使发表的第二个环节——发表实施环节,在此环节,权利人会选择自己希望得到的发表模式,确定发表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为发表的实现设定条件并做好准备。作者将作品向报刊社投稿,拿去展览、播放、发行等都属这一环节的体现。当作者完成了前述两个环节之后,作品的发表接着进入第三个环节——发表实现环节。对于需要由期刊、报社、杂志社等媒介机构选择或审查才能公之于众的文学作品、学术文章等,发表的实现往往还需要这些机构的积极配合与推动。因而,发表权并非只包含对发表的决定环节,还囊括决定发表之后的实施环节、实现环节。詹启智在其《著作权论》一书中指出,“发表权是由发表的决定、行使和实现三个环节构成的”,④参见詹启智著:《著作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这种说法虽然混淆了发表的实现与发表权的实现,但其认识到了至为重要的发表三环节。
(二)发表权的实现途径
发表的实现往往意味着发表权的实现,然而,并不是只有当作品被发表时作者的发表权才会实现。如果作者决定不发表作品,那么将作品始终维持在不发表状态,也是作者发表权的实现途径之一。也即,发表的实现通常意味着发表权的实现,但发表权的实现并不一定通过发表的实现来完成。发表权的实现应当包括发表与维持不发表两种途径,这是发表权的应有之义。而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发表权实现途径,亦各有其特征和值得关注之处。
对于以发表的方式实现发表权,这是最常见的实现发表权的途径。通常的发表会依次存在决定发表、实施发表和实现发表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全部实现时才是实质意义上的以发表的方式实现了发表权,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意味着发表的失败和发表权的尚未实现。唯有当实现发表环节完成时才能以所谓的“发表权是一次性权利”⑤李雨峰认为,发表权是“一次性的权利”;吴汉东认为,发表权“只能行使一次”。参见李雨峰、王迁、刘有东著:《著作权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吴汉东著:《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的标准认为发表已经实现,作者权利已经用尽,从而不得再次主张发表权。也正是因为以发表的方式实现发表权时通常存在的三个环节,导致了在这其中的任一环节都有可能发生侵权。例如,作者完成一部作品后,基于隐私、秘密或是作品尚不成熟等方面的考虑暂不打算发表时,他人擅自对该作品进行披露,这构成在决定发表阶段对作者发表权的侵犯;当作者决定发表之后,选择了特定的发表机构并约定了特定的发表形式发表,但该机构擅自将作品转委托其他机构发表或改变约定的形式发表,这构成在实施发表阶段对发表权的侵犯;而在发表实现环节,侵犯发表权的主要表现是实施发表者未按照作者要求的期限、地域发表等。诚然,上述讨论是建立在作者以最常见的传统方式行使发表权的前提之下,而在网络环境下,倘若作者利用互联网平台,譬如博客、微信公众账号等对自己作品自行公开发表,由于这类情形中发表权被侵犯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并不在上述讨论之列。
对于以不发表的方式实现发表权,这种方式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其并不体现所谓的“发表权是一次性权利”的特征。发表权是一次性权利的说法仅在作者以发表的方式实现发表权的情形中成立,在作者选择以不发表的方式实现发表权的情形中,只要作品在法定期限之内尚未发表,作者随时可以进行发表、主张权利。因而,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发表权因作品的发表而用尽,发表是一次性行为,但发表权不是一次性权利。作者在作品完成之后直至进行发表之前,阻止他人对作品进行披露的行为都属于行使发表权,但发表权并不因此而用尽。
二、发表权的理论根基与独立价值
黑格尔有言,“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⑥[德]黑格尔著:《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3页。,也即所谓的“存在即合理”。当这一哲学上的伟大洞见引申于发表权存续的合理性问题时,同样经得起推敲。发表权之所以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所确认,正是由于其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和不可被替代的独立价值。
(一)发表权的理论根基
作品由作者创作产生,系“作者之子”,并体现作者人格,因而发表与否、如何发表的自由应当由作者享有;否则,不仅不能使作者对作品实施完整的控制,更有可能损害作者彰显于作品中的人格。当这种发表自由以作者权利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即成为发表权。因此,保障作者发表自由,并由此保护作者在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格,正是发表权正当性的基础。通过考究早期引起人们对发表权关注的一些案例,也可以发现,经由这些案例,公众最终达成了对作者发表自由的肯定和重视。例如在法国惠斯勒案中,画家惠斯勒与埃当勋爵约定,由惠斯勒为埃当勋爵创作一幅画像,并由后者向前者支付一定报酬。在惠斯勒创作完成之后便将画像作品向埃当勋爵展示,埃当勋爵给予惠斯勒一百金币作为报酬。惠斯勒因觉得报酬太低,于是在交付画像之前将其毁坏,并以该画像不能代表其创作水平为托词。该案经历了三级法院的审理之后,法院最终指出:“除非艺术家将油画交给对方当事人处置,并且对方当事人已经受领艺术家的给付,否则委托人就无法确定地取得油画的所有权。直到交付之前,画家都是其作品完全的‘主人’,先前的合同义务并不影响艺术家对其作品享有的正当权利”。⑦参见毕荣建:《论发表权》,吉林大学法学院2009年博士论文。同样,在另一起Dame Canal诉Jamin案中,法院也指出,“作者是其思想的唯一主人,他控制着思想披露的条件和程度。因而,他是决定其作品是否、何时、以何种条件发表,以及这种发表在何种程度上应该发生的唯一法官”⑧同注释⑦ ,毕荣建文。。类似的案件并不在少数,正是对这些案件的思考和讨论,使人们发现了发表自由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发表权正当性的基础。
与自由是每个社会成员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一样,发表自由乃是作者不可或缺的创作条件。更何况任何人都是潜在的创作者,只有为每一位创作者提供充分自由的创作条件,允许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实施完整的控制,创作事业之前景才会欣欣向荣,文学艺术之成果才会与日俱增。当然,在发表权未曾获得确认的时代,人类依然创造了丰厚的文化成果,但借用一位哲人的话来讲,“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⑨[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页。这也进一步说明,发表自由不仅关乎作者本人的人格利益及经济利益,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创造力。
(二)发表权的独立价值
1.发表权是行使其他著作权的前提和基础
作品创作完成之后,作者对作品的首要控制便是发表与否。没有发表便没有之后的复制、发行、展览、表演等作品的传播路径。发表权恰如连通作者私人领域与社会公共领域的一扇门,门开门闭都决定了作品的命运和流转。现实当中,作者或相关权利人通常会直接将作品用于发行、展览、广播、表演等,但前提必须是作者已经明示或默示同意进行发表;否则,发表之门不开,任何形式的作品传播都不得进行。尽管发表权较少被单独提出或主张,但这并不影响其在著作权体系中占据首要地位的事实。
2.发表权能够维护作者的人格利益
虽然,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作为著作人格权的发表权本身,天然地具有保护作者人格利益的权能。具体表现为:其一,发表与否的自主选择既是对作品的支配,也是作者对自己人格的支配。作者之所以能够构思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乃基于其对事物的细心观察和洞见,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和思考。更何况不同的创作者有着不同的阅历、思考力、想象力等,因而能够创作出风格不同、质量不同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风格迥异也恰恰是作者的独特人格在作品中映射的结果。作品寄托着作者的思想、情感,甚至包含作者隐私。当这些人格承载于作品中时,唯有作者才享有绝对正当的理由决定作品何时与公众见面、以何种条件呈现给公众。其二,一件作品何时创作成熟,其判断依据只能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想法。在外人看来已经很完美的作品,在作者看来也许并没有完整呈现其人格特质。因而,在作者认为作品达到成熟之前,任何人擅自披露作品的行为都是对作者人格利益的侵犯。其三,发表通常是作者追求社会好评的体现。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给作者带来良好的社会声誉,很多时候作者披露作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想获得“面包”,相比于并不丰厚的稿费而言,一本书的作者更希望得到的是“被作为艺术家或创造者受到尊重”。①参见李雨峰著:《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发表权所保护的何时发表、如何发表之自由无疑为作者追求这种人格利益提供了保障。
三、国外发表权制度的比较
(一)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发表权制度
大陆法系国家一贯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社会成员的各项权利义务。对于发表权而言,也大都直接在法律中单独明文规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当属法国。法国在其《知识产权法典》“精神权利”部分的第L.121-2条规定,“仅作者有权发表其作品……由作者确定发表的方式和条件”,②参见《十二国著作权法》翻译组编:《十二国著作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并详细规定了作者死后其发表权如何由他人进行保护和行使,此外还特别强调了发表权即使在法定期限届满后仍可行使。由此可见,法国对发表权的重视程度极高,全面充分地保护了作者的发表自由。
同为大陆法系国家典型代表的德国,在其《著作权法》著作人身权部分第12条明确以“发表权”的称谓进行规定。其内容不仅明确了著作人享有是否发表、如何发表的权利,而且在作品未被许可发表的情况下,公开报道和介绍作品内容的权利亦由著作人保留。③同注释⑪ ,《十二国著作权法》,第149页。相比之下,德国的发表权权利外延至少在法律规定上要多于我国,对发表权亦采取强保护。
对发表权规定最为详尽的国家是日本。日本《著作权法》不仅在“作者人格权”部分明确规定了作者对其作品“享有向公众提供或提示的权利”,更为值得借鉴的是,日本《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推定作者通过其他行为发表作品的各种情形,④同注释⑪ ,《十二国著作权法》,第370-372页。这样就避免了现实当中发表权权利状态不明确的问题。例如,在日本,作者转让尚未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时,按照法律规定,即推定其通过这种方式行使了发表权。我国虽然在实践中也如此操作,但在法律规定上未能做到如此明确。
(二)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的发表权制度
英国现行版权法并未明确规定关于发表的权利,这与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的传统有关。但这并不是说英国不承认或不重视发表权。相反,当发生纠纷时,法官通常会认为发表是作者的普通法权利,理应获得保护,进而以判例的形式对发表权益进行确认。例如在对近现代版权法产生深远影响的米勒诉泰勒案中,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 eld)曾指出,“作者应该获取其才能和劳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这是符合正义的,他人未经其同意,不应使用其姓名,这也是符合正义的。他应该决定作品何时出版,甚或是否出版,这是合适的”。⑤Millar v. Taylor,4 Burr. 2303,98 Eng. Rep. 201 (1769).由此可见,英国实际上在以判例法的方式践行着对发表权的保护。这种保护方式因其更符合判例法国家的司法环境,避免了因法律的明文规定可能造成的司法不便而受到偏爱。
美国对发表权的保护也类似于英国。现行美国《版权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发表权,但其亦借助司法判例承认发表自由为权利人的普通法权益。在哈珀与罗出版公司诉《国家》杂志案中,①Harper&Row v.NationEnterprises,471U.S.539(1985).法院认为,作者的“首次出版权”系其人身利益,因而给予保护。该做法大有同大陆法系国家长期坚持的发表权系著作人格权的主张相趋同之意。
综上,大陆法系国家长期以来注重人文关怀的著作权态度,导致其一直将发表权视为与作者人格相关的权利而加以明文规定,并提供了充分保护。英美法系国家因其在文学艺术保护方面走向了偏重于权利人经济利益的版权体系,虽未对发表权以成文法形式确立,但一旦发生纠纷,大都以判例法的方式对发表利益进行保护。发表自由尽管未能成为这些国家版权法中的成文法权利,但却长久地被视为普通法权利而对待。不容置疑的一点是,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发表之自由始终都被认为是作者的重要权益。
四、废除发表权的不可欲性
发表权既有其专门的实现途径,又是其他著作权的前提和基础,且能够维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并为许多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予以保护。尽管有学者提出了废除发表权的种种理由,但这些理由事实上经不起推敲。从结果来看,如此重要的一项权利倘若被废除,一方面会使作者的发表自由遭受侵害,另一方面会导致作者权利体系的不完整和激励功能的减损。这些学者主张废除发表权的建议诚然是为了实现重新整合著作权体系、完善我国著作权法之长远目的,但无论如何,发表权至少在现阶段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立法的改良终究应立足实际需求,在立法技术尚未成熟到取消发表权亦可保障作者发表自由的情况下,保留发表权依然是最恰当的选择。
(一)废除发表权并无切实充分的理由
主张废除发表权的学者指出,发表权不应成为一项精神权利的理由为:“其一,发表权的确立不利于作品的传播……保护不以发表为目的的创作不是《著作权法》的任务;其二,未经许可发表作品对作者真正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形不多;其三,发表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其权利状态有不确定性;其四,发表行为的人身专属性不强;其五,发表权有保护期与其他精神权利的规定不相符合”。②同注释①,《著作权法》专家建议稿说明书,第221-222页。
这些看起来言之凿凿的理由在面对客观现实和理性分析时却显得苍白无力。首先,发表权因为具有在法定期间内决定作品发表与否的权能,从这种意义上讲,该权利的存在似乎“不利于作品传播”。然而,发表与否本应是作者的自由,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自由的缺失会导致作者在创作完成之后无法控制其作品是否公开,这是对作者基本权利的忽视。因作者可能不公开其作品,不利于作品传播,即取消作者的发表权,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构成对作者创作的绑架,无异于把作者当成作品的生产机器来对待。而且这样的做法也与激励理论相背离——没有发表自由,作者进行创作的积极性反而可能受损。如此一来,以“不利于作品传播”为由取消作者的发表权,可能造成的却是更为严重的结果——不利于作品产生。更何况发表权是唯一有期限限制的著作人格权,法律之所以规定在经过50年期限后发表权不再受法律保护,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发表权对作品传播的阻碍。既然已经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立法技术,缘何又要以这一不再是问题的问题去主张废除发表权?
其次,“未经许可发表作品对作者真正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形不多”。的确,现实当中这样的案例较少,因为大部分作者会选择主动将作品进行发表。但是,“情形不多”并不代表没有发生过,更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例如,在何元农与江兴龙等著作权纠纷上诉案件中,上诉人何元农享有著作权,但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被上诉人江兴龙等剽窃并发表,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被诉侵权作品对被侵权作品造成的侵害是:“造成其发表困难,客观上影响了何元农的相关后续工作,对其造成一定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失)”,③参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黔高民二终字第9号。最终判令侵权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法院曾明确以“指导意见”的形式制定了相关法律文件,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第22条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一)未经原告许可,严重违背其意愿发表其作品,并给原告的信誉、社会评价带来负面影响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亦有类似的规定。①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渝高法[2007]89号)第20条。这些“指导意见”的存在,也充分说明未经许可发表作品对作者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形在实践中时有发生。因而,保留发表权也是立法前瞻性的必然要求,现实情形少决不能成为废除发表权的理由。
第三,“发表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其权利状态有不确定性”。针对这一理由,学者还进一步举例,如:“画家或书法家将作品赠与好友,好友或后人将作品拿去展览,按《著作权法》的规则,美术作品原件持有人是可以拿去展览的,此情形下就应当推断作者同意发表……”。②同注释①,《著作权法》专家建议稿说明书,第221页。诸如此类情形,《著作权法》在修订时可以进一步作出细化规定,换言之,发表权在不同发表方式之下的权利状态应当由法律不断加以明确,目前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由于法律的不完善造成的。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以完善著作权法在这些方面的规定为路径,而不是直接将发表权废除。
第四,“发表行为的人身专属性不强”。在作者去世后,发表确实可以由作者以外的人去着手实施和保护,并不像署名权和修改权。但只要作者在世,发表自由仍只能由作者享有,不得转让。虽然发表权的人身性质相比于其他著作人格权并不明显,但不能因此认为发表权应当被排除在著作人格权之外。仅凭这种在作者有生之年他人不得干涉其发表自由的属性,发表权也必须被划归著作人格权范畴,不可被剥夺。
第五,发表权具有期限性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该期限的必要性。著作权法之所以在一项著作人格权上附加期限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获得发表自由的作者长期不发表作品,从而妨碍作品传播。附加期限限制的本质是为了在作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在承认发表权为著作人格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限制,这非但没有不妥之处,反而是鼓励作品传播的恰当之举。
(二)废除发表权无法实现对发表自由的全面保护
发表自由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决定作品发表或不发表的自由;二是决定作品如何发表的自由。对于前者,其有时确实可以借助其他权利来实现,恰如主张废除发表权的学者们所言,“当作者第一次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利的时候,例如复制、发行、表演、展览自己作品的时候,就同时行使了发表权”。或者,在作者尚未决定发表作品的情况下,他人擅自将作品拿去发行、展览、放映、广播等,作者也可以以作品的发行权、展览权、放映权、广播权等受到侵犯为由主张保护。这些情形似乎使发表权的单独存在显得多余。其实不然,一种不容忽视的情形是:在作者基于作品不够成熟、隐私问题等方面的考虑决定暂不发表作品的情况下,他人擅自对作品进行了单纯的披露,譬如将作者尚未公开的诗歌在公共场所朗读,或将该诗歌上传至网络等,假使没有发表权,这种行为将无法得到规制。更何况,退一步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实施的不是单纯的披露行为,而确实是通过将作品发行、展览、放映、广播等方式进行公开,由此使得作者可以选择基于发表权主张保护或基于其他著作权主张保护,两者在保护效果上也是大相径庭的。发表权作为著作人格权,当其遭受侵犯且给作者造成精神损害时,以发表权被侵犯为由主张保护,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在高垒诉中国戏剧出版社财产损害纠纷一案中,③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4)海民初字第1927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高垒先后将自己的作品《大话日本漫画史》上、下两部交与被告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戏剧社由于疏忽将原告《大话日本漫画史》(下)的唯一稿件丢失。法院最终在判决中确认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发表权、署名权等著作人身权,并判决被告承担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
而对于决定作品如何发表的自由,其更是非发表权不能予以保障的作者权益。传统意义上的发表因为存在决定发表、实施发表与实现发表三个环节,导致从理论上讲,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侵权的可能性。如何发表的自由正是为了保障作者在实施发表与实现发表环节的自主,因为在这些阶段中发生的侵权,无法通过其他著作权获得救济,所以发表权在此独当一面、不容或缺。在王建华与安徽市场报社等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件中,法院即在判决中指出,“安徽市场报社未尽到注意的义务,未能按照王建华本人所决定作品‘公之于世’的通常方式将其作品公开”,因此认为报社侵犯了作者的发表权。
可见,经由其他著作权既无法实现对发表与否之自由的充分保护,也无法实现对如何发表之自由的保护。另外,我国一直以来在法律制度上对大陆法系国家承继较多,并没有类似英美法系国家遵循判例的传统,现阶段也不存在保护发表权的其他可替代途径。在此情况下,废除发表权必将使作者的发表自由遭受无理的侵害。
(三)废除发表权将导致著作权权能缺失与激励功能减损
不论是著作人格权还是著作财产权,其设立的共同目的皆是为了使作者在不影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充分控制其作品。因此,使作者能够在从作品问世到其传播的各个环节中实现自主,排除不应有的干涉,便是著作权的整体权能。为了保证这种权能的实现,著作权法根据作品的各种传播方式规定了各项著作财产权;并基于作者在作品中的人格彰显规定了必要的著作人格权。所有的这些具体权利都从不同方面保障了著作权整体权能的完整性。就发表权而言,它虽然有一部分权能与其他著作权重叠(即在决定公开作品方面的权能),但更多的是其独立的权能。维持作品不发表、选择作品发表方式、决定作品何时何地发表便是经由其他权利无法实现的权能。而这些权能于著作权整体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失去任何一项都会导致作者在某一环节丧失对作品的控制。
著作权权能完整的重要意义在于:只有权利体系合理、功能完整的著作权才能对作者产生良好的激励。通过赋予创造者合理的权利,鼓励他们不断创作,并将其创造性成果传播给社会公众,这是知识产权激励理论的要义。激励理论“是为知识产权提供正当性的一种重要理论。甚至在论证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上,建立在提供激励基础上的讨论被认为是最有力和最广泛适用的理论”。①参见冯晓青著:《知识产权法哲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该理论表明,作者获得创作激励的前提是他们针对自己的作品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一套不完整的著作权体系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仅仅是对作者自由的剥夺,更是对著作权激励功能的掣肘。发表权因其本身具有多项独立权能,它的废除也意味着对发表自由的禁锢以及著作权激励功能的减损。一个左右不了自己作品是否发表、如何发表的作者,其创作热情势必不会高涨。
结 语
法律的修改应当始终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一项不可或缺的权利在法典中的删除也应当以替代性机制的成熟为前提。发表权在现阶段的废除既无现实基础,也不存在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运用判例法提供保护的替代机制,这使得通过删除发表权以追求著作权权利体系更加合理的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法律对发表权的规定并非一纸具文,因为现实当中涉及发表权的案例确有发生;作者对发表权的需求毕竟不可忽略,因为作者需要像控制其他财产一样控制自己的作品;公众对发表权的尊重终究需要提倡,因为尊重作者的发表自由即是在鼓励创作。发表权不是某些国家的特设,有作者的地方即应当有发表自由;发表权不是财产权利,它确确实实体现着作者人格;发表权亦不是只在非常局限的境况下起作用,在发表的决定、实施、实现环节都功不可没。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比从前任何时期都崇尚知识与创造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方面人权都获得前所未有尊重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者理应获得最全面的保护和尊重。而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著作权法也应当顺应时代召唤,体现出法律对社会应有的人文关怀。发表权承载着作者的人格,维护着作者的自由,即便较少引起关注,于作者而言,其依然散发着金子般的光芒。
During the amendment of Copyright Law, someone argue that publication right is exercised when authors firstly exercised their property rights, such as reproduction, distribution, performance and exhibition right. Therefore, they propose to abolish publication right. However, it refl ects the differences among academics for publication right. Although publication right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property rights, there are also independent abilities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other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as an independent value. 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approaches of publication right and emphasize its independence value, in order to avoid wrong contempt and indicate that publication right cannot be abolished.
Copyright Law; publication right; realize; value
曹伟,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赵宝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