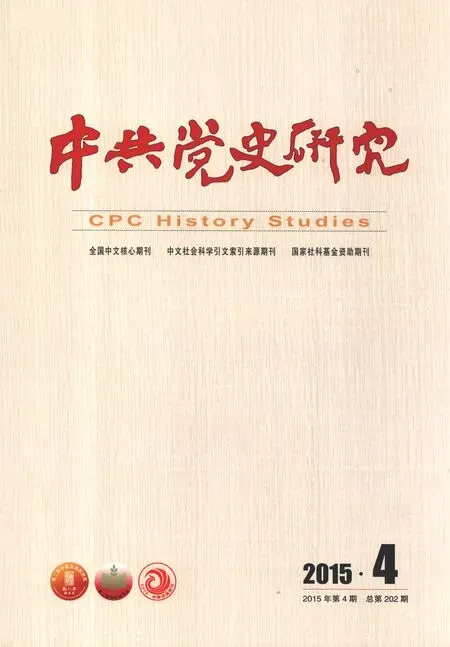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
2015-01-30金光耀
金 光 耀
·读史札记·
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
金 光 耀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而对这一段牵涉到1700多万人乃至更多人的历史书写也几乎同时开始。这一书写首先从文学发端,主要形式是有知青经历的作家写作的小说。知青历史的文学书写在8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高潮。当知青历史的文学书写在90年代开始退潮时,对知青历史的史学书写登台了,其实践者是有知青经历的史学工作者,并且在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个高潮。介于文学书写和史学书写之间的是知青回城后以各种形式发表的数量庞大的回忆录,相比较带有专业色彩的文学和史学书写,可称之为对知青历史的民间书写。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这三种书写的基本脉络,评析它们各自的特点,以使我们对知青历史的书写有一个总体把握,从而促进更清醒的认识和更自觉的作为。
一
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形成了当代文学中独特的“知青文学”。对于知青文学,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从思想内蕴、文学价值、美学意义、作家风格等诸多层面都已有详细、精到的评析。在知青文学最为辉煌的80年代,文学仍以宏大叙事作为自己的使命,知青作家也几乎都以展现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一代的命运作为自己写作的使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记录历史的责任。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知青文学作品看作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历史书写。虽然这种历史书写是以文学形式出现的,但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以知青作家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认识并叙述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的。
知青文学与“伤痕文学”是同时诞生的。小说《伤痕》*卢新华:《伤痕》(原载《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第1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2—292页。的主人公就是插队九年的知识青年。因此,文学对知青时代的历史书写的第一个特征是与“伤痕文学”相一致的,即紧扣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开展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和控诉,将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经受的苦难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极左路线。卢新华《伤痕》中的王晓华与“叛徒”母亲断绝关系而去插队落户,而当她醒悟时,母亲已经去世;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原载《作品》1979年第3期),钱乃荣主编:《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第4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1—537页。中的严凉姐弟,母亲被迫害致死,两人颠沛流离在农村历尽人间苦难;竹林《生活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中的谭娟娟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心灵创伤,导致最后赴水而死的悲剧;叶辛《蹉跎岁月》*叶辛:《蹉跎岁月》(原载《收获》1980年第5、6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中的柯碧舟因出身“反革命”家庭,下乡后备受折磨,杜见春的命运则随着干部父亲的打倒与复出而起伏,两个主人公间的爱情也因此波澜曲折。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知识青年在农村的遭遇几乎都与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父母具有的“反革命”“走资派”和“叛徒”等身份成为这些知青遭受苦难的根源,而所谓的“反革命”“走资派”和“叛徒”都是林彪、“四人帮”等政治势力诬陷所致。因此,这一类知青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和控诉色彩,宣泄了知青心中的悲愤之情,它们书写的是一代知青满身伤痕、历经苦难的蹉跎岁月,而这一切的根源都被归之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
文学对知青时代的历史书写的第二个特征是阐发知青岁月中充满青春气息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在那个荒唐年代里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所具有的悲壮性。完美表现这一书写特征的知青文学当然就是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原载《青春》1983年第1期),《梁晓声文集》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6—768页。。《今夜有暴风雪》中也有因家庭出身而受累的知识青年(裴晓云),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知青所受苦难的倾诉和对“唯成分论”的批判上,而是用更多的笔触展现在北大荒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知识青年的英雄主义气质和理想主义精神。暴风雪之夜裴晓云在冰雪中成为永恒的塑像,刘迈克在火场中英勇献身,还有在返城大潮中坚守北大荒的曹铁强,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那一代知青所具有的英雄主义气概。作者也通过郑亚茹这个人物以及暴风雪之夜抢银行的知青,对知识青年群体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严厉批评,显示出可贵的反思精神,也表现出知青群体的复杂性。总体而言,作者满腔热情地讴歌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知青,他通过老政委的嘴说道:“我相信,今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当社会评论到你们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青年时,会说到这样一句话:‘他们曾在北大荒生活过!’”这不只是梁晓声,而是相当一部分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和评价。
上述两个特征也就是文学对知青历史书写的两大主题。在第一种书写中,知青在农村经受的苦难成为倾诉或控诉的对象,苦难的根源则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而在第二种书写中,这种苦难成为磨炼知青并提升其精神境界的动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青作家都遵循这种泾渭分明的书写,这可以老鬼的《血色黄昏》(工人出版社,1987年)为例。这本类似自传的小说实录般地描述了林鹄及其周围知青的众生相。它既书写了主人公作为知青的“鬼一样的痛苦经历”,也通过林鹄的自省,深刻忏悔曾经在草原干过的坏事、荒唐事和傻事。作者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倾诉苦难或讴歌崇高,而是以平实粗犷的笔调直书自己的历史。类似的作品还有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花城出版社,1990年)和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第5期)。这类纪实性知青文学作品的出现表明,知青作家已不满足于仅仅用情感抒发、人物塑造、心理描写等文学擅长的手段来书写知青时代,而在追求更直接的方式直面这一段厚重的历史,而这一使命由史学来承担显然要比文学更为合适。
二
于是,当知青文学的高潮逐渐退去后,对知青时代的史学书写终于开始了。关于知青研究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出现在1987年,即张化撰写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谭宗级、郑谦等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41—155页。。从90年代开始,关于知青研究的史学论文逐渐增多,并且陆续出现概述性的史学著作,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前后,以刘小萌等合编的《中国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史卫民、何岚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以及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的相继出版为标志,形成了对知青时代史学书写的一个高潮。
通观这一时期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史学论著,对知青时代的史学书写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置于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探讨上山下乡政策的产生与动因,以及这一政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联。张化、刘小萌在他们的论述中都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专院校停止招生和工矿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不复存在而导致的全国1000多万中学生无法在城市中正常就业,作为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直接动因。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毛泽东推行这一政策,特别是他明确提出的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理论,源自于他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评估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安置无法正常升学和就业的青年学生这一点。如姜义华就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从农村招收进城的农民就达到1300万,因此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只是从经济上着眼,而是主要从政治上考虑的,反映出毛泽东对青年学生的失望和不满,以及对贫下中农的高度期待*姜义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369页。。虽然对于中学生无法正常升学和就业与上山下乡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等程度的关联有着不同解读,但研究者对上山下乡政策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之间的关系都有相同的评判,都认为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对知青时代史学书写的第二个层面是梳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潮起潮落,也就是这一运动进程的概貌。这主要是上述几本知青史著作以及也在90年代出版的其他几本知青史著作作出的贡献,尤以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最为突出,两部著作合起来完整、全面地叙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波澜初兴到大潮涌起再到戛然而止的整个历史进程。顾洪章主编的两部著作则是依据国务院知青办档案资料编写而成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些著作开启了立足历史资料书写知青上山下乡的史学之路。也有一些论文以省为单位,叙述上山下乡运动在一个省区的概况,但这种以区域为对象的研究还是不多。
对知青时代史学书写的第三个层面是从微观上展现和讨论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产劳动、恋爱婚姻、文化生活、医疗疾病等各方面的状况,这与第二个层面有交集,但在微观层面上的讨论更深入、更具体,也更聚焦。前面提到,在知青文学作品中,许多人物的下乡经历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相关,这一极具时代特征的“血统论”问题同样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比起文学作品中个人的坎坷命运,史学作品中那些看似冰冷的数据对“血统论”的批判更直接,也更深入。如1973年在贵州18个县的上海知青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占到19.9%,其中台江县甚至高达43%,几近半数的知青家庭出身有问题,当然也因此受到各种各样特别的“关照”*刘小萌:《“血统论”重压下的下乡知青》,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第119页。。与此相同的是对知青的婚姻、病退等问题的研究,对相关的政策、知青婚姻率、婚姻类型、病退中存在的问题等有细致而具体的探究*史卫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病退”、“困退”问题》、刘小萌:《下乡知识青年婚姻问题剖析》,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第144—149、164—187页。。而从事艺术史的学者则研究了包括美术和歌曲在内的知青文艺,展现了知青历史的丰富性*杨健:《历史勾勒:内蒙古与东北的知青文艺》、戴嘉枋:《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王洪义:《知青美术源流述略》,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第204—208、275—304、558—577页。。在一些具体问题如知青婚姻上,历史学之外的社会学研究者也介入进来,虽然在研究方法上与史学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也可看做是对知青时代的史学书写。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知青时代的史学书写主要是由有知青经历的历史学者完成的,这与文学书写由知青作家完成是相同的。这批学者是上山下乡的亲历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机会在高等院校接受正规的史学训练,并开始在史学研究的园地中崭露头角。他们对自己作为知青的经历有着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感,因此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和担待,摆脱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陈见,以史家之笔来书写这段特殊的历史。作为知青史的研究者,这些学者的优势是明显的,也是独特的。他们对知青生活有亲身的经历,对那个时代有切身感受,因此在阅读各种各样的史料时不仅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其主旨,而且还能更敏锐地察觉到字里行间或文字背后所隐藏的信息,从而能够更贴近事实地将历史书写出来。而专业的史学训练又使他们能够比他们的知青伙伴们更自觉地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置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当然他们的叙述也更专业。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涉及1000多万知识青年,整整一代青年在农村度过了生命中最难忘的青春时期。这些知青离开农村后都有倾诉的冲动和留下青春记忆的愿望,因此他们回城后以各种形式发表了难以计数的回忆文字。这些回忆文字是对知青时代的珍贵记录,也是历史书写的一种形式。相比较带有专业色彩的文学和史学书写,可称之为对知青历史的民间书写。
对知青历史的民间书写可以1990年出版的北大荒知青的集体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为开端。在这之后,知青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似乎成为一种时尚,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势不可当,至1998年上山下乡30周年形成一个高潮,与同时出现的史学书写高潮交相辉映。这些回忆录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回忆录,作者们是分散在各个领域的老知青,从事着不同工作,其中不少都是普通人。就编写方式和内容而言,这些回忆录有以下乡地区为主体的,如《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沈阳出版社,1992年)等;有以不同的知青群体为主体的,如《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重庆出版社,2006年)等。与文学书写和史学书写不同的是,民间书写在经历了高潮之后并没有冷落下来。进入21世纪,网络上出现了众多的知青网站,还有许多知青自己办的刊物,刊布出大量知青的回忆文字,对知青历史的民间书写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延续。从传统的纸本到网络,发表的门槛大大降低,又由于许多知青退休后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更多的普通人参与进来,因此在这些知青网站和知青刊物上发表的对知青时代的回忆更具有民间书写的性质。
民间书写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知青时代的方方面面,但其主题离不开文学书写的两大主题,即倾诉苦难与讴歌青春。就第一个主题而言,这些回忆录记叙了知青在农村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如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下的政治迫害,极左政策导致的事故和事件,包括许多知青辛苦劳动一年却无法养活自己等史实。在林林总总的回忆录中,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尤其值得一提。这是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因出身不好被剥夺升学资格而被强迫下乡的老知青,他们所回忆的苦难人生是对“血统论”的有力批判。但总体而言,知青回忆录的叙述更多地偏向于第二个主题。四川省知青1991年在成都举办赴云南20年回顾展时亮出的口号“青春无悔”,表达了许多知青的情感,喊出了他们的心声,也定下了他们回忆的基调。究其原因,首先,回忆录的撰写者虽不是知青作家那样的知青精英,但大多数还是后知青时代中的“成功者”,他们有能力更有意愿去回首往事,并且因为个人的经历往往会将昔日的苦难转换成今日成功的必要铺垫,在两者间建立起明确的因果关系。一位后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知青就这样写道:“在我们今天的成功中,都能看到当年兵团生活的痕迹。”*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这本书中的“老三届”讲述者大多数是在文化教育单位工作的老知青。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的回忆录中尤为突出。其次,随着已经或即将步入晚年,老知青更愿意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这是一种老人的情感和寄托,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他们对当今日益商品化时代的困惑和不满。这种情感在近些年的知青网站中更为明显。但是知青在追忆青春时不能没有自省和反思,因为他们的青春处在一个异常疯狂和荒唐的年代。已有不少知青对这种“无悔”式的追忆提出了尖锐批判,如知青作家张抗抗说:“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是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么?”*张抗抗:《张抗抗知青作品选》,西苑出版社,2000年,“自序”页。
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民间书写的最大价值在于其提供了浩瀚丰富的关于知青时代的独特而珍贵的史料。知青历史的书写要关注高层决策、政策演变、国家权力的强力推进,也要关注知青在农村的生存实态和生命经历。这不仅是顺应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取向,也因为知青历史的主体就是千百万知青。政府文件、档案资料、报刊文章等是研究者通常使用的基本史料,但民间书写中有大量知青在农村生存实态的鲜活素材,这是前一类资料所无法提供的。即使有些老知青们缺少自省和反思的青春追忆,也是知青一代生命经历的真实反映,为后人书写知青历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史料。
四
后知青时代对知青历史书写的三种形式在时序上呈现此起彼伏的状态。文学书写率先在80年代形成高潮,在其退潮后史学书写继之而起,并在90年代后期出现高潮。民间书写的高潮几乎与史学书写同时出现,并在文学书写和史学书写失去了当年的风头时,因为网络的兴起而得到延续,而结集出版的纸本也出现新的势头,从最初“北大荒”“黄土地”这样的大区域或“老三届”这样的大群体转向更为基层的知青群体,如一个县、一个公社或一个农场的知青回忆录。
对知青历史的文学书写在80年代出现高潮,是因为知识青年在经历了十年的精神压抑后需要精神上的释放和宣泄,他们要批判那个年代,也要证明自己的青春。而这又恰是文学最受大众尤其是青年人追捧的年代。精神宣泄如洪峰般过去后,因为缺少对知青历史更冷静、更深刻的反省和思考,对知青历史的文学书写再难出现曾经有过的辉煌和热闹,当然这也与整个文学相比新时期最初的十年相对冷落有关。
对知青历史的史学书写是在对那段历史乃至更长时段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后展开的。由于史学的功能不同于文学,因此它能更直接地探究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和推行,而它对知青生存实态的揭示也并不比文学逊色。以定宜庄和刘小萌撰写的两部《中国知青史》为代表的史学书写,为后来的知青历史研究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即尽可能地发掘包括官方文件和个人口述等在内的各种资料,在此基础上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去展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来面貌。但史学书写的第一波高潮已经过去十多年,其间虽有一些知青历史研究的成果问世,总体上却进展缓慢。从史学研究的一般发展来看,对于知青史这样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像《中国知青史》这样的通史类著作出现后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有专题史、区域史或其他成果出现,但迄今的状况却并非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知青史在史料搜集、整理和开发方面还有不少现实困难,史料整理的缓慢拖了研究的后腿。关于知青史料,迄今整理出版的只有寥寥数种。因此当务之急是做好史料整理工作,为对知青历史的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本文梳理的对知青历史三种书写形式的主体都是知识青年。这是目前知青历史书写的特点,也反映出它的不足。知青作家、知青学者以及撰写回忆文字的老知青,因为有过亲身的经历,所以书写那段历史有着非知青群体不可能具备的独特优势。但另一方面,正因为“身在此山”的经历和情感,他们也会比非知青群体更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看见自己眼前的树木,难以看见整片森林。发生在知青一代中“无悔”和“有悔”的争辩,就是一个例证。进而言之,如果知青历史的书写仅由知青一代本身来承担,那么其延续的时间至多不过再有二三十年,这能在充分利用目前尚未开发的史料的基础上深刻地书写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吗?因此,呼唤年轻人加入知青历史的书写势在必行。后知青时代对知青历史的书写要取得新突破,应该有“后知青”或曰“知青二代”“知青三代”参与进来,接力下去。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