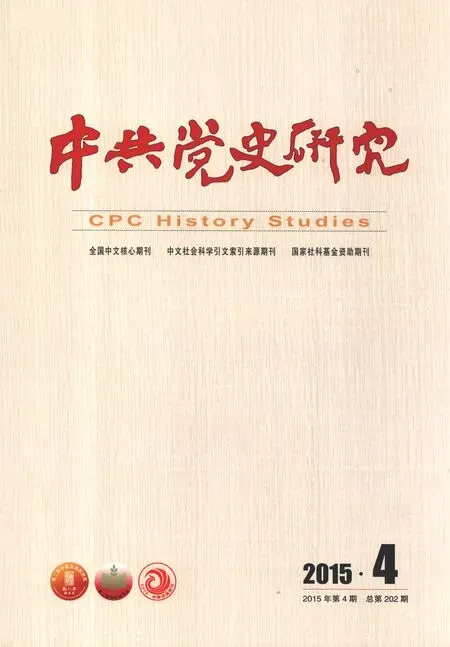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
2015-01-30谷继坤
谷 继 坤
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
谷 继 坤
1949年至1973年间,缘起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旅蒙华侨要求归国事件,经中方提议,在蒙古政府的要求下,超过26000名中国工人赴蒙援建。中国工人为蒙古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很大牺牲。而蒙古既迫切需要中国工人的援建,又对中国工人怀有戒心。同样,中国政府在派遣工人赴蒙援建一事上,也并非“一路绿灯”,同样设有“禁区”。最终,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在中蒙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赴蒙援建工人分批撤回中国。
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基本状况;政策变化
向国外派遣人员进行援助,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1949年至1973年间,在蒙古的要求下,中国政府累计派遣26000多名工人赴蒙援建,连同家属多达3万人。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探讨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和中蒙关系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中蒙关系的相关著述中对这一问题虽有涉及,但大多语焉不详。鉴于此,笔者利用近年来搜集的外交部档案和地方档案,同时借助于已出版的相关当事人的年谱、文稿、回忆录以及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一事进行专题研究①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中国工人”,包括中国派往蒙古的各种技术工人和青壮年劳动力工人,本文中提到的“蒙”“蒙古”,如无特别说明,均指“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整体上考察该问题的基本状况和政策变化。
一
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旅居蒙古的华侨总数约为1万人,多从事各种手工业和农业种植业以及采矿业。这些华侨大体分两批来蒙:第一批是1924年以前来蒙,这些人大多在蒙古定居下来;第二批是1945年8月苏蒙军队对日宣战后,因战乱等原因滞留于蒙古,且很多人来自内蒙古。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蒙古后,大批华侨纷纷要求回国,尤其是第二批来蒙的华侨。华侨要求回国,除因长时间与国内亲人音信隔绝外,主要是因为很难融入蒙古社会,这与蒙古政府的某些政策有关,如华侨不入蒙籍即不准入中学、大学读书,学习专门技术亦是如此;华侨购买物品与蒙人亦有差别,很多生活必需品不容易买到,有时为买一盒火柴要等数天。但蒙古当时仍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人口仅100余万人,劳动力本就不足,手工业、种植业等行业的技术工人更是缺乏,而华侨多为这些行业的技术工人或矿区工人,这些华侨一旦回国,势必影响蒙古生产,故蒙古方面不大同意大批华侨回国。*《外交部亚洲司关于在蒙华侨及蒙古的一般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025-03;《外交部办公厅关于在蒙华侨要求回国问题致吉雅泰的函》(1950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025-03。
这样,关于蒙古华侨要求回国之事就显得特别棘手:新中国已经成立,不能不顾及国外华侨的境况与诉求,但又不能不考虑蒙古方面的实际情况。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蒙大使吉雅泰离京赴任前,周恩来专门就此问题给予指示:可向蒙方提议,表示中方可动员一批工人赴蒙,以此替换要求回国的华侨,并据此征求蒙方意见*《外交部亚洲司关于驻蒙古大使吉雅泰于八月十六日及二十五日先后致电本部请示问题的报告》(1950年8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025-03。。吉雅泰到任后,于1950年8月10日同蒙古外交部部长拉姆苏伦就在蒙华侨等问题进行会谈。在会谈中,吉雅泰表示,对于1945年赴蒙的中国公民大多数想回国的情况,周总理提议“我们可以派遣其他工人来代替1945年8月份回来的同胞,如果蒙古还需要劳动力的话”。吉雅泰还提出,如果蒙古工厂缺少劳动力,可以将张家口的失业工人派往蒙古,中方“在劳动力方面助蒙方一臂之力”。*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11,оп.32,п.215,д.5。实际上,中方提出的派遣工人替换要求回国华侨的方案并未付诸实施。对于返国华侨,中方采取了区别对待和说服教育的方针:凡属年老病弱或国内有亲属需要返国者,经征求蒙方意见后办理返国签证;对于在国营企业工作的青壮年或技术工人以及已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内蒙古留学生,则尽量说服教育,并特别加强一般青壮年的说服教育工作,实际上就是动员这些“建设生力军”留在蒙古。通过上述方法,到1953年7月时,在蒙华侨剩余约7000余人,其中多数为建筑工人。*《驻蒙古使馆1953年侨务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8-00477-08。虽然此次中方派遣工人赴蒙的方案最终没能实行,但周恩来提出的派遣工人替换要求回国华侨的想法和吉雅泰在同拉姆苏伦会谈时中方可以在劳动力方面助蒙方一臂之力的表态,事实上可视为后来中国大规模派遣工人赴蒙援建的缘起。
1954年9月18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达姆巴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方派团出席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刘少奇指示中方代表团参加蒙方代表大会时“参观和了解一些情况,看是否可在某些轻工业和手工业方面给他们一些帮助”*《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11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率团访蒙。临行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时任中国驻蒙古第二任大使),除随同代表团参加蒙党代会外,“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蒙古方面对中国的提议表示感谢。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接见乌兰夫时表示:蒙古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非常缺乏,希望中国在轻工业、手工业、农业技术及劳动力方面给予帮助;大致需要1万工人,最好在1955年春耕前来一批,并携带家属,居留时间越长越好。蒙方还提出特别请求,要中国的翻译、医生、教员、政治工作人员也同时来,“工人的工资和汇款问题,因为我们财政薄弱,不客气地说,我们希望中国工人的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中国”。*《中央派乌兰夫副总理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12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电》(1954年11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2-00002-01(1);姚百慧:《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拖家带口援蒙古》,《世界新闻报》2007年5月18日。
乌兰夫回国后,将蒙方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中国方面很快答应了蒙方请求,并于12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答应“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并请蒙古方面早日提出所要求的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种类与数量。1955年1月14日,作为对中共中央1954年12月8日来信的正式答复,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致函中共中央,请求中方派遣12250名中国工人前往蒙古,并明确了各行业所需工人的具体数目。15日,蒙古副外长伊丹布来向何英递交了蒙古需要的劳动力总数以及工种详单:总计12250人,其中建筑工人9220人、农业工人2305人、工业工人725人。蒙方表示,这只是1955年所需要的数字,以后年份的数字将另行提出,并希望中国工人能随身携带手工工具及某些急需工具,最好4月1日就先行派遣4000人赴蒙。为此,从2月16日开始,蒙方派出代表团赴北京同中方就劳动力派遣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Гадаад хэргийн яамны архив(蒙古外交部档案馆),ф.05,ед.хр.406-409,转引自Батбаяр Ц. Монгол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р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Пекином//Россия и Монголия: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историю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в XX веке. М.,2001,с.154;姚百慧:《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拖家带口援蒙古》,《世界新闻报》2007年5月18日。
在谈判期间,中方根据蒙方提供的人数及工种详单,开始在国内先期进行传达动员工作。3月26日,习仲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签发国务院关于动员工人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指示的特急电报。电报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缺乏足够的人力和技术,我们应本着加强中蒙两国人民友好互助的精神,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困难给予同情和支持,我国政府决定派遣工人、技工和必要的干部,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生产建设。电报并对任务分配和赴蒙工人、干部条件以及工人工资待遇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第一,1955年初步决定派往蒙古的建筑工人、工业工人和农林水利工人总数为12347人,具体由建筑工程部、地方工业部和农业部分别负责,从内蒙古、吉林、河北、上海、北京等省、市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抽调,如不足则由当地劳动部门设法调配。第二,所有赴蒙工人均应是历史清楚、身体健康、年龄在18岁以上的公民,出国前须经当地政府审查批准;各省、市对赴蒙的干部和工人,在其出国之前,应采取开会、作报告等方法加以训练和教育;各类工人在技术上应符合蒙古的要求,并由原属企业发给工人技术等级的证件,其中手工业工人应随身携带自己经常使用的工具;工人按照工种组织起来,并配备必要的干部带领出国,带队干部大部将留在蒙古协助蒙方企业管理工人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干部条件要历史清楚,政治可靠,作风正派,最好能胜任技术指导工作。第三,工人在蒙古的工作期限为三年,期满后,可选择自愿回国或继续留居蒙古工作;工人在蒙期间工资待遇和蒙古的同等工人同工同酬,并享受蒙古政府现行法令所规定的一切社会福利待遇,每月可汇回不超过工资总额的30%以供养家属,工作期满回国时,可带回不超过一个月工资总额的钱款回国;工人家属,第一年除有生产技术可以做工的以外,一般不随同前往,但自第二年起可根据工人意愿及在蒙古居住条件的准备情况逐渐迁移到蒙古居住,各个员工的家属赴蒙之前,仍由原部门负责照料,工人及其家属去蒙古的旅费和工具运输费,凡属建筑工人和工业工人由各该员工原属部门或企业发给,农业工人由所在地政府发给,统一由中央财政部报销。*《习仲勋就国务院关于动员工人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指示给各地的特急电报》(1955年3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20-00738。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涉及工人切身利益的方面还是有诸多限制,尤其是赴蒙工人要随身携带工具以及每月只能汇回不超过工资总额的30%,即使工作期满回国时也只能带回一个月的工资,正如泽登巴尔所言,确实是要中国工人把挣到的工资“全部”用在蒙古。
与此同时,中蒙双方关于中国派遣工人赴蒙事宜的谈判仍在紧张进行,最终经过14轮会谈,于1955年4月7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协定》(以下简称“1955年《协定》”)。《协定》内容与3月26日电报基本相同,只是在工人人数和派遣方式方面有所改动,中方由原来的1955年一年派遣12347人改为分两年派遣12332人,其中1955年派遣8234人,1956年派遣4098人*姚百慧:《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拖家带口援蒙古》,《世界新闻报》2007年5月18日;《中国与蒙古关于中国派遣工人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的协定》,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017-02(1),转引自石绍湘:“中蒙关系分析(1949—1965)”,硕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10年,第22页。。至此,缘起于旅蒙华侨提出回国事件,经中方提议,在蒙古政府的要求下,关于中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一事开始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二
1955年《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蒙双方就中国派遣工人赴蒙援建事宜党际层次商谈的暂告结束,此后开始两国政府间的交涉办理阶段。为此,蒙古方面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工人事务局负责中国工人的接收工作;中方则先后由国务院下属的出国工人管理局和援蒙委员会以及劳动部统筹负责国内的动员派遣输送等工作,并在中国驻蒙大使馆设立工人事务处协助蒙方组织管理中国工人的工作。除此之外,中方还不定期派遣工作组赴蒙检查工人在蒙的工作生活状况。
1955年4月7日,也就是1955年《协定》签署当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向黑龙江等八省市组织部发出紧急通知,明确了赴蒙工人干部配置的相关问题。为配合1955年中国派往蒙古的8000余名工人,共需派随队出国干部73人,这73人均将留在蒙古协助蒙方各有关企业管理中国工人的组织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其中带领建筑工人的干部50人,均由各省建筑公司抽调;带领农、林、水利工人的干部10人,由各地抽调县级干部担任;带领工业工人的干部13人,均从各省市有关企业部门中抽调;蒙文翻译50人,由内蒙古负责动员,也将随同工人留在蒙古工作;临时护送的干部6人,由派出工人的地区和部门抽调。干部按前习仲勋3月26日电报的要求选派。出国干部由各派出地省市组织部审查同意后,填写出国工人审查登记表,连同档案材料,统一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最终审批。*《中组部关于抽调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人干部的通知》(1955年4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7-1-135。
12日,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也制定了遣送计划表,详细规定了1955年中国派往蒙古8000余人的具体工种和派出地区以及出发时间,其中包括建筑工人5282人,制砖、制瓦和烧石灰工人1283人;谷物和蔬菜种植、城市绿化以及捕鱼工人870人,厨师、面包师、西装裁缝及理发师,共175人;汽车喷漆、肥皂制造、纽扣制造、家具制造、制鞋、制桶、电话安装和瓷器制造工人,以及日用品工匠、手工艺品工匠、铁匠,共326人;洗衣、洗毛线和染布工人以及粉条挂面制造工人、肉品联合工厂安装工人,共223人;除此之外,由水利部和卫生部分别派遣水利灌溉工人99人、医生护士45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五年派遣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工人遣送计划》(1955年4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01-01-346。。可以看出,1955年派遣的中国工人涵盖农、林、渔、水利、手工制造、建筑安装、生活服务等各种行业和领域,也反映出蒙古当时的国民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各行各业工人和劳动力都缺,而与建筑工程相关的6000多名工人的派遣规模,则集中反映了当时蒙古正大力建设的经济侧面。
就在中央各部委制定和下发各种计划、通知的同时,接获中央的电报和指示后,有派出任务的地方各省市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动员工作。总体来看,地方各省市大致从分配任务、报名筛选、综合审查、集中训练、登车出国等五个方面来展开具体的动员工作。首先,根据分配的工种在相应企业或基层组织中进行宣传,动员工人进行报名,根据工人的报名情况进行“摸底排队”,通过“亲戚、邻居”访谈、“本人谈话”等方法,“由远及近”地全面了解报名工人的家庭情况和思想状况,并进行相应的技能考核,初步筛选出工人名单。随后,对初步筛选出的名单进行综合审查,尤其是政治审查;由卫生机构根据卫生部下发的检查防疫标准,对工人进行体格检查,剔除患有结核病等疾病的工人,并对体检合格的工人接种牛痘等疫苗;由公安部门负责政治审查,主要审查工人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综合审查后的合格工人开始进行集中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介绍蒙古的情况和出国注意事项。在出国注意事项方面,北京市要求工人树立“只许做好、不许做坏”的政治信念,并注意要尊重蒙古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学习国外礼节习惯。除此之外,训练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党、团骨干,成立临时党、团支部,并根据工人赴蒙的工作地点,编组分成若干中队和小队。集中训练之后,便按照出国工人管理局规定的出发日期,准备登车开赴集中地,集中赴蒙,各地在工人登车前,当地一般均组织欢送会,并由一些负责干部讲话。*《赴蒙工人、干部必须注意的事项》(1955年5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2-001-00188;《上海市劳动局关于赴蒙出国人员成立临时支部的问题》(1955年5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7-2-712;《关于动员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工人的工作总结报告》(1955年6月4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2-001-00188。
各地工人动员完成后,根据出国工人管理局的派遣计划,分别集中到沈阳、长春、北京等城市,然后统一乘车分批赴蒙。4月27日,中蒙双方最后商定,中国工人乘车经二连浩特进入蒙古,到乌兰巴托后再统一分配,每五日运送一次,每次运输900人至1000人;赴蒙工人的出国旅费在中国境内部分由铁道部负责支付,进入蒙古境内后的旅费由中共中央统一与蒙方接洽*《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关于我赴蒙工人遣送等有关问题给各地的特急电报》(1955年4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20-00738。。最终,中国工人从5月5日至6月6日分八批共计7451人抵达蒙古。第九批约1000名工人,因蒙方提出要求延期赴蒙,未能成行,直到1957年才最终赴蒙。其中,第一批中国工人于5月8日上午9时抵达乌兰巴托,蒙古方面为此组织了2000人的欢迎大会,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杜固苏伦等党政领导人出席大会,热烈欢迎中国工人的到来。而让部分中国工人感到不满的是,蒙方对中国工人的分配使用较为分散,几乎全部的蒙古国营农场和各省市合作社都分有中国工人,有的少至五人一处,甚至有一二人一处,最远的分在离乌兰巴托2000公里以外的地方,部分工人为此“闹情绪”,要求分在一处。除此之外,蒙方不同地区和企业部门执行的工资标准也不尽相同,有的按工人技术等级发工资,有的则不论工人技术等级高低,一律发放相同工资,再加上蒙方个别地区准备不足,工人伙食供应不上,有病无药治疗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而一部分中国工人到蒙古后不久就患重病,久治不愈,根本无法工作,还有部分中国工人犯了所谓“煽动罢工”等“严重错误”,蒙方为此向中国驻蒙使馆提出将这些工人送回中国。*《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关于赴蒙第一、二批工人情况给各地的电报》(1955年5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20-00738;《驻蒙使馆关于蒙方要求第九批赴蒙工人延期赴蒙电》(1955年7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048-05;《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关于赴蒙工人洪某某在蒙煽动罢工殴打干部等非法行为的处理报告》(1955年9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2-001-00188。
为解决上述问题,9月下旬,中方派出专门的工人事务工作组赴蒙,同蒙古方面进行会谈,对双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交涉,并达成了解决问题的初步意向,如制定统一的劳动定额与工资标准,以及设立一个专门管理定额工资的机构,在可能的情况下集中使用中国员工,中方将36名患有重病和犯有所谓“严重错误”的中国工人调回国内,并决定以后类似人员一律送回国内,由原派出企业单位或地区人民委员会予以安置处理。蒙古副总理锡林迪布向工作组介绍了蒙古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乌兰巴托市政建设方面的困难,并提出新的援助请求,希望得到中方的资金和人力支持。中方工作组则表示,除与7000余名中国工人有关的援助项目可以详谈外,蒙方如有其他援助要求,可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习仲勋就国务院关于从蒙古回国工人的安置问题给北京等地的电报》(1955年8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20-00738;《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接见我工人事务工作组情况简报》(1955年10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160-02。中方工作组的表态,让蒙方心里有了“底数”,为日后乌兰巴托不断向北京提出人力物力援助要求做了铺垫。
中国工人事务组的蒙古之行,使赴蒙工人初期遇到的各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蒙的7000多名工人开始安定下来,进入稳定的工作状态。而随着中蒙双方的不断接洽,中国工人最关心的家属赴蒙问题也得到逐步解决。
按照1955年3月26日习仲勋电报的指示,1955年除赴蒙后能直接从事生产的家属可以随队赴蒙外,其他工人家属要待蒙古方面准备好接收工人家属工作时才能赴蒙。随着中国工人在蒙工作的趋于稳定,蒙方的家属接待准备工作也逐步完备,中国工人家属赴蒙工作由此开始大规模启动。1955年10月12日,周恩来签发给吉林、山东、上海等省市的特急电报,布置各地工人家属的赴蒙工作。电报称,蒙古政府现已准备好接收763户、1431名在蒙中国工人家属的生活居住条件,要求最近将这批工人家属送到蒙古去,为此,要求各地动员有意向赴蒙的工人家属,并进行必要的健康和政治审查,按照计划,这批工人家属分两批乘专列前往蒙古*《周恩来就国务院关于遣送工人家属赴蒙问题给北京等地的特急电报》(1955年10月1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20-00738。。1956年4月和8月,根据蒙古方面的要求,中国政府分两次输送了2445户、共计6241名工人家属前往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遣送第二批中国工人家属赴蒙古的通知》(1956年3月2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01-3-478。。中方于1955年和1956年分两批共输送了7600余名工人家属赴蒙,与在蒙的7000多名工人人数基本持平。
如上所述,早在1955年9月中国工人工作事务组在蒙期间,蒙方就向工作组提出了新的援助请求,当时中方工作组建议蒙方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直接提出援助要求。有了中方工作组的建议,蒙古政府于12月21日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中国援建12个项目的请求。经过谈判,1956年8月29日,中蒙双方在乌兰巴托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56年到1959年内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在此款项内中方帮助在蒙方建设毛纺织厂、造纸厂、乌兰巴托市市内道路等厂房桥隧基础项目,中方为此将派遣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赴蒙援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5集,法律出版社,1958年,第144—148页。同年9月,中国国务院将乌兰巴托市内道路建设工程的六个项目交由城市建设部门负责筹建,此项工程议定由北京建筑工程局具体负责承建,同时由上海市负责设计工作并调配专门技术人员和干部予以支持,而具体建设的1000名工人则从河北省抽调。1957年4月,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从张家口、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抽调了1000名工人并于当年完成了赴蒙工作。*《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关于承建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市内道路工程给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956年12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08-00162;《国务院关于决定从河北省动员调遣1000名工人赴蒙古参加经济建设的通知》(1957年4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5-4-1241。
从1955年至1957年,中国共派往蒙古8000余名工人,其中1955年7451人,1957年1000余人,1955年和1956年中国还分别往蒙古派遣了1431名和6241名工人家属。到1957年时,中国在蒙古的工人及其家属达到15000余人。由此,中蒙关系与同时期的中苏关系一样进入“蜜月期”。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在同蒙党代表团会谈时就提到,300多年来中国人欠了蒙古很多债,中国有义务帮助蒙古,以偿还以前的“债务”,并表示“以后在农业方面,我们可以用人力援助你们,其数目可以是十万,也可以是二十万,甚至也可以达到三十万,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帮助你们搞牧畜业”。在中方公布的这份谈话记录中,蒙方代表团团长达姆巴对毛泽东的提议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明确表示接受,只是说“对,不过事先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和计划工作。不然,接到那些人后,住宅等各方面要发生困难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13—223页。但当时作为蒙方代表团成员并参与会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曾德,后来在同苏联驻蒙古大使莫洛托夫会谈时却有不一样的说法:“曾德和我(指莫洛托夫——笔者注)分享了他率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期间同毛泽东的谈话情况,毛说,300年来中国人欠了蒙古很多债。中国将满足蒙古的要求来偿还300年来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向蒙古提供20万名劳动力和10万名畜牧工人。我们那时请求,从内蒙古给我们提供15000名畜牧工人。但是,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后,这一建议被拒绝了。中方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能从内蒙古提供畜牧业工人,(作为替代方案)中方愿意以任意数目的中国工人作为交换。”*АВПРФ,ф.111,оп.40,пап.252,д.5。另外,苏联驻华大使馆向国内提交的1956年工作报告所提到的一点也很能说明问题:“使馆了解到中国同志具有向蒙古迁移很大一批中国公民的计划,但由于蒙古人采取的含糊立场,他们原则上不反对,但又不准备与中国同志就该问题讨论具体建议,因此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与之相反,蒙古方面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中方从内蒙古地区派人的努力。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在给达姆巴的复信中提到:“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9—160页。显然,达姆巴在来信中提出了从内蒙古迁移蒙古族人前往蒙古定居的要求,而毛泽东对此予以拒绝。
可以看出,中蒙双方高层领导人在是否从内蒙古地区派遣蒙古族工人赴蒙这一问题上有着明显分歧,即蒙古领导人一直致力于要求中方从内蒙古地区派遣蒙古族工人赴蒙,而中共高层始终没有答应这一要求,中蒙领导人似乎都在“担心”什么。虽然有如此分歧,但一方面中蒙关系与同时期的中苏关系一样整体上处于上升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蒙古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正逐步加快,需要大量外部资金和人员援助,以至蒙古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直接将中国援助尤其是中国工人援建的因素考虑进去,因此中蒙双方的上述分歧并未影响中国工人赴蒙援建一事的整体进程。
三
1958年至1961年可以说是中蒙关系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工人在蒙古援建趋于成熟的时期。一方面,蒙古政府先后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三年计划(1958—1960)和五年计划(1961—1965),都将中国政府的援助和中国工人的援建纳入经济发展规划,尤其是中国政府对蒙古的各方面援助不断增加,中蒙关系在1960年达到顶峰,而中国工人的援建工作经过1955年至1957年三年的实践,不论是从国内动员还是在蒙古建设,都积累了不少经验,整体工作逐步成熟起来。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里,中苏双方在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歧和矛盾开始显现,中苏关系也由“蜜月”逐步走向“分歧”。受此影响,中、苏、蒙三角关系也趋向微妙,蒙古一度成为中苏“争取”的对象。
1957年8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六中全会讨论并公布了1958年至1960年三年计划草案,其中工业方面的计划除蒙古自己投资外,还加入了苏联、中国等国家的援助,而最突出的是城市住宅建设比重,占投资总额的20.8%*新华社:《蒙古三年计划草案内容》,《内部参考》1957年8月17日,第2286期。。显然,这些城市住宅主要靠中国工人来建设完成。时任蒙古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曾德表示:“蒙古党、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指望中国在劳力上帮助。”*新华社:《曾德对中国工人帮助蒙古建设的评价》,《内部参考》1957年11月6日,第2352期。同年8月,蒙古政府委托何英向中国政府提出新的援助问题,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无偿援助,并列出了要求中方援建的具体建设项目清单*АВПРФ,ф.111,оп.39,пап.248,пор.5。。可以看出,蒙古政府仍然致力于继续得到中国的经济和人力援助。
与此同时,1955年派往蒙古的7000余名中国工人的三年工作时间已近期满。在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工人为蒙古的生产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方面,中国工人不仅帮助蒙古建设了大批工厂、住宅,还提出了很多经济建设中的合理化建议,使蒙方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而且不少中国工人受到了蒙方的表彰和奖励*新华社:《曾德对中国工人帮助蒙古建设的评价》,《内部参考》1957年11月6日,第2352期;《蒙古驻中国大使鲁布桑在蒙古驻华大使纪念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1957年10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657-04。。另一方面,在三年建设过程中,有的工人怕影响工资收入,不愿带蒙古徒弟,有的甚至不择手段做投机买卖,赌博行贿,虚报工作量,盗窃企业的材料和到外面包私活等,以致发生了多次中国工人罢工、拒绝分配工作等不良事件*新华社:《在蒙古企业中曾发生中国工人停工事件》,《内部参考》1958年4月22日,第2462期。。因此,对中国工人在蒙古的表现,应全面认识和看待。面对中国工人即将期满回国的情况,蒙古方面除挽留中国工人继续留蒙工作外,向中方提出了1958年增派2370名中国工人的要求*《蒙古外交部就增派员工问题致我驻蒙古使馆的照会》(1958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432-01;《关于向蒙古增派2370名员工问题》(1958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206-02。。最终,经过中蒙双方的动员,1955年赴蒙的7000多名工人中有5000人选择继续留在蒙古工作,其余人员按期回国。同时,中方同意了蒙方的请求,决定于1958年增派2370名工人赴蒙,由山东、河北、北京三省市动员完成。*《国务院关于由山东省、河北省、北京市动员2369名工人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通知》(1958年5月1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34-0-23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复关于期满回国工人安排中几个问题的请示》(1958年7月5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401206800-X0084-C-000625。1958年6月16日至7月2日,2370名中国工人分乘三列火车顺利到达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关于1958年赴蒙工人的遣送计划》(1958年6月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932-2-101。。此后不久,经过中蒙双方协商,1958年9月,中方完成了1958年度赴蒙工人家属1710户,共计3453人的遣送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关于1958年遣送赴蒙工人家属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的有关事项的通知》(1958年8月2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32-2-101。。这样,虽然一部分援蒙工人回国,但在蒙古工作的中国工人仍然保持在7000人至8000人左右,为援助蒙古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和人力支持。
而1957年8月蒙古政府委托何英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援助请求,此时也有了重大进展。1958年7月,中国政府正式答复同意了蒙古政府提出的援助要求。不过,中国方面并未按蒙方要求的那样无偿援建,而是采取了有偿信贷的方式,即中方将向蒙方提供1亿卢布的贷款*АВПРФ,ф.0111,оп.40,д.5,пап.252。。为此,1958年12月,蒙古方面派出以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扎木茨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赴北京同中国政府商谈给予蒙古新的经济援助和1亿卢布贷款的具体问题*《关于接待蒙古政府代表团的请示报告》(1958年12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706-01。。12月29日,中蒙双方代表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及其议定书,规定中国政府将向蒙古政府提供1亿卢布的长期贷款,用于帮助蒙古建设两座发电厂、三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梁、一个养鸡场、一个淀粉糖心厂、一个酒精厂、一个小五金工厂和5万平方米的住宅*《我国援助蒙古一亿卢布》,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81期,1959年1月6日,第1—2页。。显然,如同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项目一样,这些工程从勘察设计、材料供应以及施工的组织技术等工作要由中方来负责,具体由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建筑工程部和交通部负责承建,而建设施工工作则要靠中国工人来完成。
1959年2月3日,国务院下发专门通知,从上海等省市抽调壮工5100人、土建技工和机械技术工人275人,补充支援建筑工程部和交通部,以确保1959年内援蒙的道路、桥梁等项目的工程建设。所有工人要求在1959年第一季度内分批赴蒙,并根据工程任务分别签订两年或三年的合同。*《国务院关于解决援蒙工程处所需劳动力问题的通知》(1959年2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7-1-833-1。3月2日,劳动部也下发通知,在1959年内由山东等省市动员1200名工人赴蒙援建,要求为经体检和政审合格的年满18岁至45岁青壮年,工种包括钢筋、水暖、养路、电话安装等近20个工种,且要在蒙古工作三年。蒙方接收单位为运输邮电部、商业采购部、生产合作总社、建委会、工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关于1959年动员工人赴蒙工作的通知》(1959年3月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01-1-680;《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1959年度赴蒙员工工种技术等级明细表》(1959年3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27-1-833-11。这样,1959年中国分两批向蒙古派遣了6300多名工人。相较而言,2月3日由国务院抽调支援建筑工程部和交通部的工人,以基建类的工种为主,主要负责中国援蒙的具体工程项目建设,属于专业建设队伍,在蒙古也是集中使用;而劳动部动员的1200名工人,则涵盖了生产建设和生活服务方面的各个领域,这点从蒙方的接收单位和中国工人的工种均可以看出,到了蒙古也不是集中使用,而是由蒙古统一再分配,其使用方式如同1955年派遣的工人一样。由此可以判定,随着援建规模的扩大,中方有两套动员派遣体系:一是由国务院下属的建筑工程类各部委,负责组织筹建援蒙的具体工程,并为此调配壮工和技术工人;二是由劳动部组织动员派遣,派遣的工种涵盖各个经济部门,服务于整个蒙古的国民经济。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苏双方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开始显现,并在1959年10月爆发了高层之间的争论,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更停止了对华经济援助并召回苏联专家。在这种背景下,为增强在蒙古的政治影响力优势,中苏双方对乌兰巴托的经济援助不断升级。蒙古方面得益于这种形势,从中苏双方均获取了大量援助。继1958年至1960年三年计划之后,1960年蒙古方面开始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草案,泽登巴尔为此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实现五年计划要依靠苏、中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蒙古正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内部参考》(国际版)1960年5月21日,第22期。据苏联驻蒙大使莫洛托夫向孟英(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临时代办)的通报,蒙古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用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援助请求总金额达7亿卢布*АВПРФ,ф.0111,оп.40,д.5,пап.252。。同时,蒙古方面也向中方提出了新的援助请求。1960年3月31日,泽登巴尔交给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一份要求中国援助的项目清单,共计19项,约需2亿卢布。对于这些援助项目,泽登巴尔“一再表示所提项目考虑得还不周到,有的可能不合适,不一定完全按照他们的意见,但也表示变动不宜太大”,同时指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援蒙项目仍采取由中国包建的办法,并指责某些蒙古同志想自己搞是说空话”。*《蒙古提出要我援助十九个项目》,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201期,1960年4月13日,第3—4页。泽登巴尔的口吻看似客气诚恳,却传递着不容拒绝的信息,而事实上后来中方基本“照单全收”,按照蒙方的要求给予了援助。
1960年5月,周恩来率团访问蒙古期间,除答应贷款2亿卢布给蒙古外,对于蒙方关心的劳动力援助问题,周恩来表示,中方认为可以由现有工人延期,不回去,不必换人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可以减少一部分人。对于周恩来“可以减少一部分”中国工人的提议,泽登巴尔则表示:“我们还有困难,不能完全同意,现在技术人员需要量很大,还要增加1000多工人。”周恩来最后表示:“关于劳动力问题,有关部门可以具体商谈,交换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会谈记录》(1960年5月28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20-853。可以看出,蒙方仍在坚持要求中国继续派遣劳动力。5月31日,中蒙双方在乌兰巴托签订“协定书”和“互助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写道:“(中蒙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会谈中双方对讨论到的各项问题观点完全一致。”中国《人民日报》和蒙古《真理报》纷纷刊文发表社论予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9集,法律出版社,1961年,第37—44页;社论:《蒙古和中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谊与合作的新阶》,Yнэн, 2 июня 1960 г(蒙古《真理报》)1960年6月2日,转引自Батбаяр Ц. Монгол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р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Пекином,с.127。正如蒙古《真理报》社论的报道,周恩来1960年的赴蒙之行开启了“中蒙关系的新阶段”。
1960年6月14日,为了进一步做好援蒙项目的建设工作,国务院决定由交通部专门成立援蒙工程处,重点负责援蒙的基建类工程项目,并在1960年抽调派遣67名干部和639名工人赴蒙援建,具体由河北、山东等省市完成,而组织派遣方面的实施工作则由交通部负责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交通部成立援蒙工程处和抽调各类援蒙人员的通知》(1960年6月14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04-1-142。。这批工人由交通部负责统一调配,以完成工程项目建设为目标,因而工人的工作年限在通知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周恩来访蒙期间关于由有关部门进一步协商解决中国派遣劳动力赴蒙的表态,中蒙双方开始就中方继续派遣工人赴蒙援建问题进行商谈。1960年8月16日至9月19日,中蒙双方就中国继续派遣工人援建蒙古一事进行了21次专门会谈,最终于9月20日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协定》(以下简称“1960年《协定》”)。《协定》规定从1961年1月1日起至1965年12月,中国向蒙古派遣的工人总数每年保持在12000人。*《中蒙两国政府劳动力谈判代表团第1-21次会谈记录》(1960年8月16日至9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259-01、106-00259-0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协定》(1960年9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6-00151-03(1),转引自石绍湘:“中蒙关系分析(1949—1965)”,第25页。如此,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基本形成了“苏联出钱、中国出人”的基本格局,当然,中国也为蒙古提供了2亿卢布的贷款。
1961年2月23日,1958年到蒙工作的7000余名中国工人工作期满,其中有3369名工人选择回国,连同回国家属,计有1359户4450人,按照计划这批工人及其家属将于1961年的四五月份分批回国。回国工人基本按照由原派出单位和企业或基层单位负责接收的原则进行安置。*《关于接收在蒙古工作期满回国工人的通知》(1962年2月23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07-5-230。为了执行1960年《协定》,同时填补1961年回国工人的空缺,1961年3月23日,国务院下发通知,决定1961年抽调职工3796人继续赴蒙援建,要求各地按照政治任务的要求标准“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工人干部的抽调工作。抽调的援蒙职工,必须是政治历史清楚、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至45岁的青壮年,并应配备25%的党、团员作为骨干。带队干部必须是中共正式党员,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能够担负领导工作人员。相较于以往的派出工人,此次对工人的要求和审查明显严格了许多,凡是地、富、反、坏、右等所谓“五类分子”,“反革命嫌疑分子”,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抱有不满情绪的人员以及患有严重疾病或一般慢性病的人员都不得派遣出国,并规定工人在蒙古工作的三年期间内不准携带家属。因此,要求各省市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体格审查。按照中国劳动部制定的遣送计划,1961年抽调援蒙的3796名中国工人将于4月30日至5月30日,分乘六列火车前往蒙古。*《国务院关于抽调职工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通知》(1931年3月23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57-4-262;《劳动部关于1961年赴蒙工人遣送计划表》(1961年3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7-1-837。由此,1961年中国在蒙工人仍保持在7000人至8000人
综上所述,1958年至1961年中国政府共计派遣13000余名工人赴蒙援建。1960年5月周恩来的蒙古之行,使中蒙关系发展至顶峰。但此后不久,中苏双方的分歧日趋严重,以致公开论战。随着蒙古日趋明显地站在苏联一方,中蒙关系开始走向“下坡路”。这一切都影响了在蒙工作的中国工人的命运。
四
1960年5月周恩来的蒙古之行,中蒙双方可谓“各取所需”:中方至少使蒙古在中苏争论的一系列问题上暂时没有倒向苏联,而蒙方则获得了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和人力援助保证。但就在周恩来离开蒙古后不久,蒙古政府便邀请赫鲁晓夫访问乌兰巴托*《赫鲁晓夫将访蒙古》,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200期,1960年4月8日,第11页。,泽登巴尔更在1960年一年之内访问莫斯科至少三次,并成功从苏方获得新的经济援助。1960年9月,苏联同意向蒙古提供总额为6.15亿卢布的长期贷款,用于蒙古1961年至196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Батбаяр Ц. Монгол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р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Пекином,с.157-158.,远超中国政府提供的2亿卢布贷款。同时,蒙古日趋向苏联靠拢的情况在周恩来1960年访蒙后不久开始表现出来。据新华社驻乌兰巴托分社反映,1960年8月前后,蒙方在列举向外国专家学习取得成绩的企业单位时,只列举了苏、捷援助的工厂,没有列出中国援建的工厂,“这是过去少有的现象”*《最近蒙古提兄弟国家援助不提我国》,中宣部编:《宣教动态》总第682期,1960年9月2日,第6页。。8月27日,蒙古代表团过境中国访问越南时,“一直避免谈论政治性的问题”,只谈“两国友好关系和文化艺术交流”*《外交部礼宾司关于蒙古党政代表团情况简报》(1960年8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7-00607-01。。显然,蒙方一直刻意回避中方所“关心的问题”。
进入1961年后,中蒙之间在工人问题上的摩擦开始不断增多。1961年9月,乌兰巴托市联合加工厂里一辆蒙古汽车压伤一名骑车的中国工人,导致双方100多名工人群殴,中国员工有20多人受伤。11月21日,蒙古外交部部长沙格达苏仁在谈话中指出,中蒙在工人问题上一直以来就存在一些细小摩擦,但当前的问题是,中方想利用这些细小的摩擦来制造所谓蒙古对中国不友好的证据。近来中蒙在援蒙工人问题上的矛盾其实是中方想竭力制造一个事件,以证明蒙古对中方不友好。去年来,中方的这种态度体现得尤为明显。中方还向外界公开表示,中国工人在蒙古的工作条件非常不好。而蒙方希望这些问题都通过党际高层交流来解决,但中方对这样的建议不予回复。受上述情形影响,中国工人及其家属思想情绪开始出现波动。在蒙古的中国部分员工表示,“在蒙古中国员工不敢出去,不小心就要吃亏,特别是晚上,弄的人提心吊胆”,有的中国员工开始提出要提前回国,部分家属“一个月没有接到信就愁的哭”,在中国国内休假的部分员工更是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不回蒙古工作。*PAAA,MfAA,C247/74, “Aktenvermerk über die Unterredung mit dem Minister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MVR,Gen.Schagdarsuren,am 21.11.1961”,Ulan-Bator 22.11.1961,转引自陈弢:《中苏分裂背景下的六十年代中蒙关系:基于中国和前东德双边档案材料的考察》,中国当代史高级研修班研讨论文,美国·华盛顿,2014年8月,第9页;《山东省劳动厅关于援蒙工人回国情况的思想情况和一些问题的请示》(1962年3月14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04-1-166。
到1962年,在蒙古工作期满的中国工人大部分都没有选择留蒙继续工作,而是选择回国。6月27日的蒙古外交部备忘录显示,5月至6月间,2719名合同到期的中国工人返回中国。后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指责中国方面说,中国工人有超过500次在工作地点暗中破坏和干扰正常工作进程的企图。中国工人只完成了1958年至1960年开始的32个建设项目中的12个。另据蒙古外交部解密的档案显示,1962年12月泽登巴尔为签署中蒙边界条约访问北京,在同周恩来会谈期间,泽登巴尔对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工人罢工事件次数的增多表示遗憾,但仍表示蒙古方面准备继续招收包括来自内蒙古在内的中国工人。周恩来则批评泽登巴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片面立场,并使他相信中国的立场是正确的,还表达了自己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开发表意大利、捷克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文章的不满。泽登巴尔和周恩来还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很多争论。*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Гадаад хэргийн яамны архив, ф. 05, ед. хр. 765.,хр. 816.,转引自Батбаяр Ц. Монгол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р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Пекином,с.159-160.与此同时,中方在对蒙古援助问题上,也一改往日的“有求必应”,开始持谨慎态度。1962年5月18日,周恩来就对蒙古经济援助谈判一事作出批示,提出关于援助蒙古“量力而行,凡无把握者概不承担”等八条原则*《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78页。。显然,中国派往蒙古援建的工人问题已经和背后的中苏关系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了。
1963年1月,泽登巴尔在公开讲话中“指名攻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泽登巴尔在蒙思想工作者会议上攻击中阿》,《内部参考》1963年1月15日,第3455期。。7月至9月间,蒙古《真理报》发表多篇社论,公开指责中共,表示蒙古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中共领导人“百般歪曲”和“攻击”苏联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立场。12月22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挑起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指责中共“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妄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取得统率地位”,以党内决议的形式表明了自己在中苏分歧中的立场。*《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华言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1—20、88—89页。在中蒙关系恶化的同时,中蒙双方围绕中国工人援蒙问题的谈判也在同步进行。1963年4月至12月,中蒙两国就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问题进行了47次会谈,都无果而终*PAAA,MfAA, A7568,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Sekretä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Gen.Naidanjav,und Gen.Jarck am 25.9.1964 in der Zeit von 15.00-16.30 Uhr”,Hanoi,转引自陈弢:《中苏分裂背景下的六十年代中蒙关系:基于中国和前东德双边档案材料的考察》,第13页。。蒙古方面转而寻求苏联在人力援助上的支持。1963年9月13日,泽登巴尔在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洛马科会谈时提出:蒙古现在劳动力紧缺,因为中国缩减了在蒙古的工人数量,近两年来中国工人的数量从12000人减少到7000人,1964年第二季度将撤走全体工人。因此,泽登巴尔请求苏方派遣苏联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接替中国工人工作,并要求苏联第一批工人最迟于1964年第一季度到达。*АВПРФ,ф.0111,оп.45,п.278,д.2。与此同时,中国在蒙古援建工人的处境日趋险恶。1964年3月21日,中国一援蒙工人被蒙方人员用刀刺进背部;29日,中国工人的三个宿舍被蒙古人破窗而入,许多物品被捣毁*《东欧各国和蒙古对赫修反华新行动的初步反应》(1964年5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2705-04。。6月11日更发生了严重的“于深水、窦海玉事件”*事件最初起因于1964年2月20日。因工作分配问题,中国援蒙工人窦玉海小队与蒙方发生争执,中国工人刘成先被打。事后,蒙方以中国工人聚众闹事为由,于3月6日将窦玉海和大队长于深水带走“调查”,窦玉海、于深水二人随即被扣押。5月8日,蒙方判处二人各四年徒刑,但6月11日于深水在监狱中被杀,蒙方向中国通报说是窦玉海杀死了于深水。《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关于青岛市房管局援蒙工人于深水同志被蒙古政府杀害、请给予烈士称呼及对其家属抚恤的报告》(1964年7月17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04-2-144。。显然,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工人撤出蒙古已经不可避免。
最终,根据蒙古政府的提议,从4月24日至7月8日,中国在蒙工人约6000余人分28批离开蒙古回国*《根据蒙古政府的提议 我国援蒙员工已有三千五百人回国 第十八批援蒙员工已于前天离开乌兰巴托》,《人民日报》1964年6月5日;《根据蒙古政府的提议 我援蒙员工最后一批离蒙回国 我员工九年来为蒙古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人民日报》1964年7月10日。。而中蒙双方在为何送这批中国工人回国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中方认为,这些工人回国并非由于其在蒙劳动合同期满,而是由于蒙古政府的主动要求;蒙古不要中国的劳力,是因为想接收苏联的劳力。而蒙方则认为,将这批人送回国是因为他们在蒙古的期限到当年5月份即到期;蒙古向苏联求援,乃因中方先撤回援蒙劳动力。*PAAA,MfAA,C247/74,“Erläuterung durch die Monzame”,12.5.1964;PAAA,MfAA, A7568,“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Sekretä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Gen.Naidanjav,und Gen.Jarck am 25.9.1964 in der Zeit von 15.00-16.30 Uhr”,Hanoi,转引自陈弢:《中苏分裂背景下的六十年代中蒙关系:基于中国和前东德双边档案材料的考察》,第14页。
事实上,中方1964年撤出的主要是根据1960年《协定》派往蒙古的工人,仍有大批中国工人留在蒙古负责继续完成未竣工的工程。为完成这些工程,中国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又派往蒙古3700余名工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第4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页。。当然,“于深水、窦海玉事件”发生后,中方加强了在蒙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工作。1964年8月31日,中方专门将仍在蒙古负责中国援蒙养鸡场试生产的14名女工调回国内,另派相应政治可靠、年轻健壮的男工予以替换,以免发生针对中国女工的意外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商调养鸡男工出国赴蒙换回在蒙女工事》(1964年8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1-01605。。此后,直到1967年初,蒙古方面拒发在中国国内休假工人的返蒙签证,原先在蒙古留下工作的约5000名中国工人无法返蒙。至此,中国赴蒙援建的工人只剩下300余名在蒙留守的职工,受到蒙古方面的严密监视,中国在蒙古遗留的尚未完成的工程主要由15000名苏联工兵予以继续施工。*PAAA,MfAA, G-A 350,“Die Entwicklung der MVR nach dem XV.Parteitag der MRVP(vom Juni 1966 bis Marz 1968)”, Ulan Bator,29.3.1968,参见陈弢:《中苏分裂背景下的六十年代中蒙关系:基于中国和前东德双边档案材料的考察》,第24页;《首都一万五千革命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 愤怒声讨蒙修当局追随苏修反华暴行 坚决支持我驻蒙人员和爱国华侨的正义斗争热烈欢迎三位华侨反修战士归来》,《人民日报》1967年5月27日。
这样,与中国工人赴蒙援建一事相关的只剩下在蒙留守员工和这些员工负责看守的未完成工程以及仍被关押的中国工人窦玉海了。而这些问题因中蒙关系的持续恶化,一度被搁置起来。1970年4月底,中国外交部派吕子波任驻蒙使馆临时代办,负责解决同蒙古间的遗留问题,并寻求缓和中蒙关系。8月5日前后,根据中国外交部指示,吕子波向蒙方提出建议,以因在中国杀人被收监的蒙古留学生那松扎布交换被蒙古判刑关押的中国工人窦玉海。17日,蒙方同意这一建议,并于9月2日在二连浩特附近中蒙边界上的双方边防会晤点进行了交换。而中国留守员工问题和未完成工程的移交问题直到1973年才得以解决。1973年3月23日,历经半年多谈判,中蒙双方就中国在蒙未完成工程的移交问题达成最后协议,中建驻蒙古公司将留守员工看守的已完成和未完成的工程项目作价移交给蒙方。1973年5月,最后负责留守的中国员工总共80多人返回中国。*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56—160页。孙一先,原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二等秘书、临时代办。至此,中国工人赴蒙援建一事最终落下帷幕。
五
中国工人赴蒙援建一事,缘起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旅蒙华侨要求回国事件,后经中方提议,在蒙方要求下,中国政府于1955年正式开始派遣工人赴蒙援建。据笔者考察,中国政府累计共派遣26000多名工人赴蒙援建,其中1955年7451人、1957年1000人、1958年2370人、1959年6575人、1960年639人、1961年3796人、1964年3700余人。综合考察中国工人赴蒙援建一事的基本状况和政策变化,可以简要作出如下分析。
第一,中国工人赴蒙援建,为蒙古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牺牲。不可否认,中国工人在蒙期间存在打架斗殴、投机倒把甚至是违法乱纪等情况。但中国累计派往蒙古援建的工人达到26000多人,连同家属则多达30000多人,而当时蒙古全国人口才100万人左右。很多中国工人在蒙古工作了六年以上,建筑了270余万平方米的各种建筑物,铺设了数十公里铁路,建造了190多座桥梁,修筑了200多公里公路,架设了900多公里的电线,建造完成了中国政府援助的发电厂、养鸡场、毛纺厂、玻璃厂等各种工厂企业。很多工人因公、因私死在了蒙古。因此,置身于冷战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间交往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和境遇也是一个值得详细探讨的问题。
第二,如前文所述,中蒙双方领导人在对待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上,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一方面,蒙古缺乏劳动力和技术工人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后来中国工人撤出时仍然缺乏,不然不会让苏联工兵接手中国工人未完成的工程,因此迫切需要中国工人帮助援建,以发展其国民经济;另一方面,蒙古方面始终对中国工人怀有戒心,这点从早期中国工人的分配使用以及后来极力要求从内蒙古派遣蒙古族工人等现象中可以看出。蒙古领导人这种“既要用而又不敢放手去用”的矛盾心态,贯穿了中国工人援蒙的始终。中国领导人在派遣工人赴蒙援建问题上,也并非“一路绿灯”,同样也设有“禁区”,即绝不答应蒙古方面关于从内蒙古地区大量派遣蒙古族工人赴蒙的要求,中蒙双方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和矛盾也贯穿了整个事件的始终。而仔细梳理中国工人赴蒙援建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后期中国工人的撤出,可以发现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的命运,从根本上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因为中苏矛盾和分歧的公开化,导致夹在中苏之间的蒙古地位渐趋重要,一度成为中苏争取的对象。而随着泽登巴尔的全面掌权,蒙古日趋倒向苏联,最终公开追随苏联反对中国,中蒙关系不断恶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工人最终撤离蒙古。那么如何理解中蒙双方此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国工人最终撤离蒙古呢?这就要从社会主义国家间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不一致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特点加以分析。
第三,从蒙古方面来说,作为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急缺技术性工人和劳动力工人,中国工人的援助对发展其国民经济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从中国方面来讲,派遣人员赴蒙,可以提升自身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力。这对中蒙双方本是互利共赢的事情,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中蒙双方围绕是否派遣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工人赴蒙等问题发生分歧,主要受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也比较容易理解。问题的关键是中蒙双方在发生分歧后,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的“不一致性”,即中蒙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彼此党际关系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掩盖双方
在国家利益中的分歧与矛盾。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结构失衡”问题,即“在冷战时代,共产党之间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他们掌权后的国家关系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党际关系的结构和政治范式与现代意义的国家关系完全不同。在这种结构中,作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同一性和唯一性,无视并抹杀了阵营内部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利益诉求”*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50页。。当中苏关系破裂后,蒙古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并完全倒向苏联,中国在蒙援建工人的撤离便无法避免。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吴志军)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Chinese Workers’to the Mongolia for Aid (1949—1973)
Gu Jikun
During 1949—1973, Chinese government sent more than 26000 Chinese workers to the Mongolia to aid its construction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request of going back to China by Mongolia Chinese ear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These Chinese worker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as well as sacrifices. However, Mongolia on the one hand was of urgent need on the Chinese aids, whereas on the other hand kept wary of Chinese workers. Likewi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give “green light” all the way in terms of dispatching workers to Mongolia. Instead, it set up some “restricted zone”. At last, influenced by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China-Mongolia relations, these Chinese workers returned to China in batches.
* 本文是2012年度北京东方历史学会基金(研究类)“中国工人‘赴苏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54—1964)——以河北省清苑县为中心”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D232;K27
A
1003-3815(2015)-04-004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