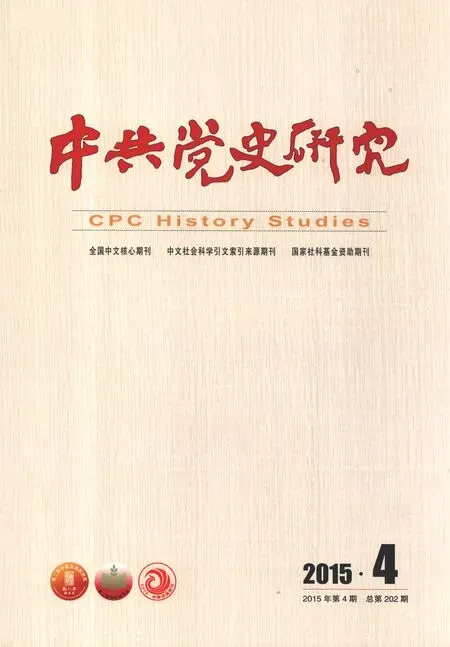“新兴社会科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2015-01-30阎书钦
阎 书 钦
“新兴社会科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阎 书 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新兴社会科学”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思潮。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通过编撰大量社会科学论著,在次递传承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诸多重要理论原则的同时,构建起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他们系统阐述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基本方法论,构建起以经济基础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社会阐释体系,并自觉将其与美国以社会心理行为为中心的社会理论相区别。马克思主义论者的理论阐述与宣传表明,迄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体系已大致形成,并受到中国学术与思想界的极大关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兴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时人称作“新兴社会科学”或“新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日渐兴盛,至30年代臻于壮大,形成一个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流派。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辅相成,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者群体不限于中共人士,亦包括曾经与中共有组织瓜葛但后脱离中共的人士,甚至包括虽与中共无联系但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进而在中国形成一个颇具社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群体。他们大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理论撰述与宣传,构建起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系统考察与梳理这一论者群体及其话语体系,并分析其以何种论述方式与阐述策略,以何为阐述重点,向中国学界乃至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基本知识,目前学界所论并不充分,确为学界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论者群体与文本承续
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既是中共理论宣传的结果,亦与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自发学术努力有关。随之,以上海地区为中心,涌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群体与大量相关论著。同时,各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著之间的文本传承颇为明显,通过梳理这种文本传承,可以呈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的传播脉络。
瞿秋白于1924年10月出版的《社会科学概论》和柯柏年于1930年3月出版的《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成为中共努力宣传的文本。瞿秋白此书系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在该校夏令讲学会上的讲稿。1930年6月,中共中央创办的上海华兴书局将此书以德国人“布庄德耳”著、“杨霞青”译《社会科学研究初步》的名义印行。中共以“霞青”名义评介此书可以给青年提供认识社会的门径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现在许许多多的青年,时常苦于摸不着寻找认识和理解社会的门径,以致更无法找到改造社会的方案”,“德国布庄德耳的这本短短的著作,虽然不是什么包罗万象的大作,但它却能够给现代青年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门径”*霞青:《译者序》(1929年双十节),〔德〕布庄德耳著,杨霞青译:《社会科学研究初步》,上海华兴书局,1931年,第1—2页。。柯柏年于30年代初参加中共上海左翼文化领导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组成员。柯柏年此书旨在以通俗读物的形式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其所谓“新兴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他在“自序”中表示:“它告诉了青年们:新兴社会科学是什么?新兴社会科学为什么比旧社会科学优越?它又告诉了青年们:自己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时应该怎样自修,应该读哪一本?”*柯柏年:《自序》(1930年3月6日),柯柏年:《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增订本),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第1页。此书一度流传很广,其再版“自序”称:“这本书出版了四个多月,就卖去了二千本。”*柯柏年:《再版自序》(1930年8月4日),柯柏年:《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增订本),第4页。30年代初,瞿秋白、柯柏年两书被中共理论宣传机构作为基本学习材料推广。1932年8月,具有中共背景的北平科学研究会编《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即介绍,《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初步》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参考书*《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北平科学研究会,1932年,第8页。。两书均遭到国民党当局查禁。1931年1月,中共以“杨霞青译”名义出版的瞿秋白此书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理由查禁;柯柏年此书在1930年3月出版后不久,即于同年11月遭国民党当局查禁,缘由为“宣传共产”*《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第15、11页。。
萧楚女于1926年11月出版的《社会科学概论》,对杨剑秀于1929年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概论》影响极大,而顾凤城于1930年5月出版的《社会科学问答》又大量引述杨剑秀所撰内容。萧楚女此书是他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期间的讲稿。杨剑秀系中共重要理论宣传工作者。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加入创造社,并任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组织部书记。杨剑秀所撰多有引述萧楚女所论之处。例如,萧楚女在阐述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抽象性时说:“此等科学之对象,大都是抽象的,虽显著如一国之政治组织,巨册之法典条文,乃至买卖、征兵、罢工、战争等明明白白之事实,然要皆只可以脑系中之思索与表现思想之语言文字,以推求说明其理性质素之所在,却终不能如自然科学,可以视听嗅触诸觉及精微之仪器,以求得其香臭、甜苦、软硬、轻重、大小、黑白、高低等之具体的形质。”*萧楚女:《社会科学概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1926年,第1—2页。杨剑秀亦称:“此等科学的对象,大都是抽象的,虽显著如一国的政治组织、巨册的法典条文,乃至买卖、征兵、罢工、战争等明明白白的事实,然都只可以用思想与文字来推求说明其因果关系的法则性,却终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用视听触嗅诸觉及精微的仪器,以求得其香臭、甜苦、软硬、大小、轻重、黑白、高低等具体的形质。”*杨剑秀:《社会科学概论》,上海现代书局, 1934年,第5页。20年代末30年代初,顾凤城曾任共青团嘉定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光华书局编辑,所撰的《社会科学问答》旨在向民众普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顾凤城在“自序”中介绍:“这本书的编著,是专门供给一般初学社会科学的青年看的,也可以说是一本社会科学的入门书。”*顾凤城:《序》(1930年5月25日),顾凤城:《社会科学问答》,上海文艺书局,1930年,第1页。他引述杨剑秀所论之处也不少。例如,杨剑秀在说明人类生产活动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联系的纽带时说:“人类所组成的社会是生长在自然界之中,人必须以自己的劳力通过技术以达自然界而摄取其物质的营养,人类社会才能存在。这种以劳力摄取自然界的物质的过程便是所谓生产。”*杨剑秀:《社会科学概论》,第11—12页。顾凤城亦称:“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生长在自然界之中,必须以劳力采制自然界的物质以为营养,人类社会方能存在,这种‘以劳力采制自然界的物质’之过程,便是所谓生产。”*顾凤城:《社会科学问答》,第11页。杨剑秀、顾凤城两书在当时社会似亦极有影响。杨剑秀此书至1934年9月出版至第七版,于1935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共产主义”理由查禁;顾凤城此书也于1931年7月被国民党当局以“鼓吹阶级斗争”理由查禁*《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第56、22页。。
陈端志于1934年3月出版的《现代社会科学讲话》多有引述陈豹隐于1932年10月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内容之处。陈豹隐原名陈启修,曾于1924年加入中共,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流亡日本,与中共失去联系。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1934年改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的讲义,不少内容取材于日本相关书籍。他申明:“这个讲义虽然取材于各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大半取材于最新颖、最正确、最能将辩证法具体化了的广岛定吉、直井武夫共译西罗科夫等所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教程》,但是,我自己却也有许多独特的主张。”*陈豹隐:《序》(1932年9月18日),陈豹隐讲述,徐万钧、雷季尚笔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北平好望书店,1932年,第2页。30年代,陈端志任职于上海博物馆,以左派史家和博物馆学家闻名,所撰的《现代社会科学讲话》包含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由此看来,他即便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亦可说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他表示,此书以倡导“新兴社会科学”自任,“本书的编辑,就是要想使那沉湎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群众和中国青年,给与正确的新兴社会科学的一个指标”*陈端志:《卷头语》(1934年3月12日),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第2—3页。。陈端志似对陈豹隐相关论点颇为赞同。陈豹隐在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唯物的社会观”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科学成熟的标志时说:“这种社会观的代表者,不消说,是马克司……一方面,他在方法上克服了旧来的唯心的、唯物的、实证的、实践的、机械的、辩证的等等不正确或不完全的方法,建设了辩证的唯物的方法——真正的唯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因为有正确的方法的缘故,他打破了一切不正确的不完全的社会观,抓住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生物现象并精神现象等等的区别和关联,发见了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对象。”*陈豹隐讲述,徐万钧、雷季尚笔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第48—49页。陈端志亦称:“这种社会观的代表者,便是完成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一方面他在方法上克服了旧来的唯心的、唯物的、实证的、实践的、机械的、辩证的等等不正确或不完全的方法,建设了辩证的唯物的方法——真正唯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因为有正确方法的缘故,他打破了一切不正确的不完全的社会观,抓住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生物现象和精神现象等等的区别和关联,发见了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对象。”*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第25页。
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宣传与介绍方面极具代表性。高尔松笔名高希圣、高振清、高圯书,而高尔柏则长期以郭真为笔名*关于二人的笔名情况,《社会科学大纲》于1929年11月由上海平凡书局出版时署名高希圣、郭真。上海解放后,《社会科学大纲》于1949年6月由平凡书局再版时,则署名高尔松、高尔柏。可见,高希圣应为高尔松,郭真应为高尔柏。另外,1930年4月与郭真合撰《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的高圯书,应为高尔松。《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于1930年4月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时,署名郭真、高圯书,而1931年6月再版时,封面则将印行者标为上海新文艺书店,将著者标为郭真、高希圣,而封二仍将印行者标为乐华图书公司,将著者标为郭真、高圯书。参见郭真、高圯书:《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1年,封面、封二。另外,高尔松亦曾以高振清为笔名。高尔松曾于1930年12月由平凡书局出版《新政治学大纲》。1932年10月,他又以高振清为笔名将此书由上海社会经济学会再版。。高尔松于1923年10月加入中共,翌年进入上海大学听课。四一二政变后,他流亡日本,与中共失去联系。他于1929年6月回上海后,与高尔柏创办平凡书局等出版机构,合作出版《社会科学大词典》。他们在“刊行之辞”中注意到:“现代的社会科学,已分成为有产者的和劳动者两方面的学说了。所以,同是一个社会科学名词,就有不同的解说。”*《刊行之辞》(1929年3月),高希圣等编辑:《社会科学大词典》,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5—6页。同年11月,两人合作出版《社会科学大纲》。1930年4月,他们又合编《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此书第一章“社会科学”由《社会科学大纲》缩写而成,全书大部分编写工作由高尔松完成。高尔柏称:“在二月前,乐华图书公司约我编辑这本书,并且要我很快编成。可是,我为了有其他的事,不能赶编,乃由圯书担任编著。只因要紧完稿,我也帮他写了一些,自然,成分是非常少的。”*郭真:《序》(1930年3月4日),郭真、高圯书:《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第4页。
显然,至30年代初,中国学界初步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群体。此群体大致包括三类论者:中共理论宣传工作者、曾参加中共后脱党但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员、虽与中共无组织瓜葛但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员。除上面提到者外,第一类论者还包括祝伯英、曹伯韩等,第二类论者还包括沈志远、李平心、胡伊默等,第三类论者尚有柳辰夫等。祝伯英在3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参加社联工作,于1933年12月出版《社会科学讲话》。曹伯韩于1924年加入中共,1936年任李公朴、柳湜、艾思奇等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于1937年1月出版《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沈志远于1925年加入中共,30年代初任社联常委,并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他在1933年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后,于1936年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并于9月出版《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李平心曾于1927年加入中共,虽于30年代初脱党,但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于1936年5月出版《社会科学研究法》。胡伊默亦曾于20年代加入中共,30年代脱党后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于1937年4月出版《社会科学读本》。柳辰夫为30年代活跃于上海地区的左翼知识分子,于1934年5月出版的《怎样自学社会科学》,旨在向民众普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此外,从1939年9月出版的《新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所具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撰写此书的王明之、林哲人、卢宁夫、萧达四人可能也具有中共身份。此书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此书目的即为“对于实践工作者建立了正确的立场,免得受伪科学的理论的氛围所欺骗,所迷惑”*三户编辑部:《代序》(1939年4月1日),王明之等:《新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上海三户书店,1939年,第3页。。刘剑横、李季达等亦是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论者。刘剑横于1932年9月出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反对统治阶级的“歪邪的社会科学”,提倡“新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刘剑横:《序言》(1929年4月6日),刘剑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第2页。。李季达于1937年6月出版的《怎样研究社会科学》,系上海一心书店万有小丛书之一种。此丛书编撰大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其“刊行缘起”称:“本小丛书所编译的范围取材于多方面,立论全以唯物史观为根据。”*《万有小丛书刊行缘起》,李季达:《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上海一心书店,1937年,第2页。
日本学者杉山荣的论著对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影响很大。1930年10月,张栗原、温盛光将杉山荣所论分别以《社会科学理论之体系》(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社会科学十二讲》为题,译为中文出版。杉山荣在此书“自序”中表示,他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提炼为统一的理论体系,“马克斯和恩格斯之社会的理论,散见于他们遗著的无数之文献中,一部分是为统一的形式,但一部分又是为断章的形式”,他“试为了统一他们之散于许多文献中之他们底社会的理论,加之补缀和为体系的,使构成为容易理解他们底社会科学之形式”*杉山荣:《原序》(1929年12月),〔日〕杉山荣著,温盛光译:《社会科学十二讲》,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0年,第1页。。温盛光对杉山荣此书评价极高:“在混沌的中国社会中,现实社会之种种的矛盾,非应用马克斯与恩格斯之全部的社会学说之后,才有解决的可能”,“著者杉山荣先生是日本社会学专家。他关于社会科学是有深刻的观察、透辟的议论、精确的文字和丰富的著述”*温盛光:《译序》(1930年6月13日),〔日〕杉山荣著,温盛光译:《社会科学十二讲》,第1—2页。。杉山荣另一部著作《社会科学概论》关于科学与因果关系及其法则的阐释,对民国学界影响尤其巨大。1929年3月,李达、钱铁如将杉山荣《社会科学概论》译为中文出版。杉山荣所论被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论者频繁引述。例如,杉山荣称:“不可把因果关系当做已成停滞状态的孤立两现象间的依存关系来考察。向来世人把因果关系当作死物看待,以为在一定的瞬间,有已成停滞的A现象,他一瞬间,同样有已成停滞的B现象,在两者之间有依存关系存在时,这就叫做因果关系。这种见解是错误的。一切的现象,都要当做生成、流动的过程来把握。”*〔日〕杉山荣著,李达、钱铁如译:《社会科学概论》,上海昆仑书店,1935年,第2页。杉山荣此论首先被高尔松、高尔柏《社会科学大纲》全面引述。高尔松、高尔柏亦称:“不要把因果关系认为既成停滞状态下两个孤立现象间的依存关系。向来,世人往往把因果关系当作死物看待,以为在一定的瞬间有既存停滞的甲现象,在另一瞬间有既存停滞的乙现象,在两者间,有因果关系的存在时,便称为因果关系,但这样的解释是差误的。一切的现象须依生成、流动的过程而加以把持。”*高希圣、郭真:《社会科学大纲》,上海平凡书局,1929年,第一章“绪论”第2—3页。经高尔松、高尔柏宣传,杉山荣的相关论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界中广泛流传。例如,1930年5月,顾凤城即称:“不可把因果关系当做已成停滞状态的孤立两现象间的依存关系来考察。一切的现象都要当做生成流动的过程来把握。我们往往把因果关系当作死物看待,以为在一定的瞬间有已成停滞的甲现象,他一瞬间,同样有已成停滞的乙现象,在两者间有依存关系存在时,就叫做因果关系。这是不对的。”*顾凤城:《社会科学问答》,第3—4页。此外,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胡伊默《社会科学读本》、李季达《怎样研究社会科学》、王明之等《新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均几乎原封不动地转引杉山荣的论述。由杉山荣相关论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影响来看,日本学界对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不容小觑。
在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受到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论者的关注和诘问。一些论者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应站在纯客观立场,指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有理论预设、先入为主之嫌。1928年7月,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心理学家郭任远声称,社会科学研究应注重实际观察,不应成为“任何主义”的“宣传品”,“我主张社会科学也应当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须极力注重实际上的观察的”。他注意到,实证立场在当时中国理论界左右分裂的境况下难免陷于窘境,“因为我极力批评现有的社会制度的缘故,一般头脑守旧的先生们,看这书后,一定要骂我‘赤化’了。但是,我恐怕C.P.先生们反要怪我旗帜不显明哩!”*郭任远:《序》(1928年7月1日),郭任远:《社会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3页。1929年10月,时任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孙寒冰则批评一些研究者没有以“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仅“凭着些由‘信仰’、‘成见’、‘感情’、‘常识’等组成的空洞的理想,来妄事揣摩”。他强调:“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人,勿论对于资本主义的观察也好,对于共产主义的观察也好,不拘你喜欢这个或不喜欢那个,都应该用冷静的头脑去研究,如同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一样。”*孙寒冰:《社会科学是什么?》,孙寒冰主编:《社会科学大纲》,上海黎明书局,1929年,第26、28页。在孙寒冰指责的先入为主的“信仰”“成见”“感情”“常识”中,马克思主义显为其重要所指。1935年2月,青年党理论家常乃惪则从国家主义立场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称作“伪社会科学”,声称:“在现今浅薄孤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情形之下,所有的社会科学著作,不属于支离破碎的英美派个人主义社会学,即属于牵强附会的马克司派伪社会科学,真正有价值的著作非常缺少。”*常乃惪:《参考书》,常乃惪:《社会科学通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1页。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招致的批评与指责,反证出其在当时社会影响力的扩展,在时人眼中已成为一支不能不重视的思想与理论流派。
显然,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被冠以“新兴社会科学”或“新社会科学”之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兴起,不仅涌现出大批相关著作,亦形成马克思主义论者群体,进而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流派。诸论者写作动机相当不同,中共及其理论宣传工作者多出于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需求,而一些与中共曾有组织关系或从无组织联系的论者,则多出于自身的思想信仰。同时,通过对二三十年代各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著的文本对比,可见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在各种文本之间的次递传承,由此可窥见诸多马克思主义论点有一个学术乃至社会传播的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谱系。
二、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论者在各种社会科学论著中反复申明,唯物辩证法是“新兴社会科学”或“新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他们均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作为阐述重点,向读者大力推荐。这方面的系统论述说明唯物辩证法在二三十年代即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大力传承,学术与思想影响亦日益扩大。
马克思主义论者为论证唯物辩证法是社会科学的总方法论,构建起这样的思维理路:哲学具有科学性,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的总方法论,而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哲学理论,因而唯物辩证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总方法论。他们首先指明,哲学是各种科学法则的综合与概括,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科学。1937年4月,胡伊默强调,哲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哲学所研究出的法则与理论,是一切科学的法则与理论的综合”,反过来,“哲学是一切科学研究之总的方法论”*胡伊默:《社会科学读本》,上海一般书店,1937年,第26—27页。。他们进而指出,哲学是社会科学的总方法论。1933年12月,祝伯英在《社会科学讲话》中以“哲学与社会科学”开篇,将社会科学总论视作一种哲学。他强调,哲学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同样有方法上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比任何科学都容易被宗教、传说、流俗观念所俘虏,所以,哲学的介绍更其重要”*祝伯英:《社会科学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5页。。1936年9月,沈志远亦申明,哲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和总方法论,社会科学受“领导人类一切知识部门”的哲学的指导,“社会科学跟一切其他的知识部门有着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沈志远:《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第5—6页。。他们接着肯定,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科学的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1932年8月,北平科学研究会编印的《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强调:“彻底的唯物论是马克斯、恩格斯的,他们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成为辩证法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唯物论是数千年人类思维发展最高的成果”*《新兴社会科学研究大纲》,第67页。。陈豹隐也于1932年10月称,唯物辩证法“是科学方法中最高级的方法,所以,也可称为科学的方法论”*陈豹隐讲述,徐万钧、雷季尚笔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第59页。。1936年9月,沈志远将辩证唯物论称为“新唯物论”,强调这是“最科学的宇宙观”*沈志远:《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第32—33页。。由上述逻辑,他们得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正确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论。顾凤城于1930年5月强调,研究社会科学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辩证法的唯物论是每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所首先应当把握的。这是马克斯主义的哲学基础”*顾凤城:《社会科学问答》,第71页。。1934年3月,陈端志表示,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应该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现代社会科学既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真正运动过程中的一页,那么,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无疑的,应从辩证法的唯物论做出发点。它不仅奠定了社会发展学说的基础,并且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至高无上的法则”*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第41页。。1936年5月,李平心把唯物辩证法称作“唯物的动的逻辑”,认为此种方法包括“辩正法或动的逻辑”、唯物论等两方面,是研究社会科学的真正科学方法*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第44—45页。。显然,唯物辩证法是最正确、最根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被马克思主义论者反复申述。这构成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并成为其向社会说明的重要知识点。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野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着重阐明的核心话题。马克思主义论者竭力向读者说明,这个问题是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最基本问题。1933年12月,祝伯英指出:“思惟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中基本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就决定哲学的基本分派。”*祝伯英:《社会科学讲话》,第5—6页。沈志远亦于1936年9月称,世界是由物质构成,还是由精神构成,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便是一切哲学底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唯一的关键问题”*沈志远:《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第7页。。他们进一步指出,唯物论与唯心论问题是决定社会科学性质的关键要素、划分某种社会科学属于何种阵营的分水岭。1929年6月,杨剑秀申明,唯物论问题是“关于社会科学内的最根本的先解问题”*杨剑秀:《社会科学概论》,第19—20页。。陈端志亦于1934年4月更明确地注意到,社会科学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主张物质占优势,精神为从属的,即所谓唯物论派。另一派是主张精神为根本,物质是副本,即所谓唯心论派。这两个对立的阵容,斗争得非常激烈,那些名目上彼此不相同的学派,实际上都划分到两个阵营里。”*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第39页。
在唯物论与唯心论问题上,诸论者一致强调唯物论的正确性。1933年12月,祝伯英指出:“大致说来,唯物论是进步的,因为它承认客观的存在,而去逐步认识它。观念论是退化的,因为它违反事实,结果是阻碍进步。”*祝伯英:《社会科学讲话》,第8页。1936年9月,沈志远亦强调:“对于两大哲学阵营的考察底结果,我们认为,正确的是唯物论,而不是唯心论。而且,哲学所以能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它也必须是唯物论的。”*沈志远:《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第15页。不少论者进而分析了将唯物论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问题,指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野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就是到底应以精神、心理、意识还是应以物质的社会生产为基础来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1937年4月,胡伊默分析,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出发点的不同与社会科学研究有“重大的关系”,“把它们应用到人类社会科学的构成,就发生这样的问题,即社会的基础,究竟是精神抑是物质呢?两种哲学对这问题的答覆是完全相反的”,唯心论主张社会“是由人类的思想、意志、感情、欲望等等结合而成的东西”,“人类意识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唯物论则认为“物质的生产及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社会的精神生活,是依存于物质的生产状态,且随后者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社会科学便“因此出发点的不同,而分成两个对抗的派别”*胡伊默:《社会科学读本》,第31—32页。。在胡伊默看来,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分野在社会科学中表现为是否以社会生产为基础分析社会问题。显然,在马克思主义论者看来,唯物论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就是以社会物质要素为本位认知社会问题,而这种社会物质要素的核心即为社会生产。这就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日益兴盛的唯物史观的基础命题。
马克思主义论者将社会科学话语与辩证法直接联系起来。他们强调,辩证法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采用的根本思维方法。1929年6月,杨剑秀指出,辩证法是对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现象的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如果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懂不得辩证法的几个公律,对于一切的社会现象,他将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观察方法”*杨剑秀:《社会科学概论》,第31页。。此言得到陈端志的认可,他于1934年3月引述杨剑秀的话说:“非但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依辩证法的公律而发展,就是人类社会也同样的依辩证法的公律而演进。如果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能了解,那就对于社会现象,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观察方法。”陈端志接着强调,只有运用辩证法,才能确切了解“社会关系的运动法则”。*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第60、75页。马克思主义论者大力宣传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他们看来,辩证法主要包括三大定律,即事物的运动与普遍联系定律、矛盾的对立统一及否定之否定定律、由量变到质变的定律。诸论者重点阐释了事物的运动与普遍联系定律。杨剑秀于1929年6月将此定律称作“物质永动及现象互系的公律”*杨剑秀:《社会科学概论》,第31页。。同年11月,高尔松、高尔柏又将此定律称为“诸现象间的关联之动力观”*高希圣、郭真:《社会科学大纲》,第四章“唯物论”第5页。。他们均申明,必须以发展的眼光,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观察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及否定之否定定律,诸论者强调,必须从事物的内在矛盾与否定之否定中认知事物发展的原因。顾凤城于1930年5月表示:“一切的运动和变化都由于内部的不断的矛盾、内部的不断的斗争所造成的……这里要说的,便是一切变化、运动或发展,都在对立或矛盾中发见,即因一事物的否定而实现。由否定一事实而生否定,再否定,此否定又生肯定。”*顾凤城:《社会科学问答》,第60页。同时,他们将此定律与阶级斗争理论联系起来,强调阶级斗争是此定律在社会发展上的最明显表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高尔松、高尔柏即称:“社会之中常常有许多矛盾,阶级斗争是社会矛盾之最显明的表现。”*高希圣、郭真:《社会科学大纲》,第四章“唯物论”第19页。马克思主义论者系统阐明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定律。1937年4月,胡伊默分析说:“一切变化均由质变与量变交织而成。量的变化总是逐渐的,是以量变的过程,是渐变的过程;质的变化总是飞跃的,是以质变的过程,是突变的过程。”*胡伊默:《社会科学读本》,第37页。他们进而申明,事物的质变或突变表现在社会发展上就是社会革命。顾凤城即认为,社会革命就是事物的突变性在社会问题上的表现,“社会内的进化(渐进的发达)要引到革命(飞跃)”*顾凤城:《社会科学问答》,第70页。。从其将辩证法三大定律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相联系的思路,可见推动现实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是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阐扬辩证法理论的重要现实关怀。
综上所述,在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论者看来,唯物辩证法是“新兴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他们在各种社会科学论著中勾勒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大体轮廓和基本原理,并向中国学术与思想界大力推广。这说明,至3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阐述已大致成熟,并具备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的基本论题。经过马克思主义论者的宣扬,唯物辩证法亦在诸非马克思主义论者中产生了极大影响。1936年7月,作为国民党人的郭海清(字湛波)称,他撰写《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即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方法:“本书自有一种观点和方法,所用的方法是新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辩证法唯物论。作者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并非有什么成见和信仰什么主义,只是相信在今日只有这种方法能解决问题,较为妥当,不得不用它。”*郭湛波:《再版自序》(1936年7月4日),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第9页。
三、唯物史观之社会论:以经济基础为中心的阐述策略
在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论者看来,所谓社会科学,即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瞿秋白于1924年10月即谓,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是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譬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天津联合出版社,1949年,第1页。。如果说唯物辩证法是用以研究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那么,以何种角度或立场认知社会现象则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论题。马克思主义论者提出,研究社会现象必须立足唯物史观,只有唯物史观才是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1930年6月,中共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吴黎平即表示:“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理论。在马克思以前,并没有科学的关于社会的理论。”*吴黎平:《唯物史观》,社会科学讲座社编:《社会科学讲座》第1卷,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第38页。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他们构建起一套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为框架的社会阐释体系,并竭力强调经济基础在各种社会要素中的关键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论者的大力宣扬,这种阐述体系被民国学界极度关注,成为各派论者相互辩驳的热门话题。
马克思主义论者反复强调,对“社会”概念的阐释必须立足生产问题,正是生产将人类社会与“动物群”区别开来。1933年12月,祝伯英分析,人们运用工具获取“自然资料”,是“改制自然以供自己应用的过程”,亦即“人类的生产”,这与“动物的劳动”完全不同,因为动物只能“用爪牙直接攫取食物”,所以“人类社会与动物群的区别,就在这个‘生产’,而社会的特质也就是生产”*祝伯英:《社会科学讲话》,第14页。。1936年5月,李平心亦称:“在正确的社会科学看来,任何社会要维持并且往前发展,最不可缺少而且成为基本的决定要素的,就是物质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生产。”*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第140—141页。因而,沈志远于1936年9月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是生产,“人类社会底一切要求是靠物质的生产来满足的”*沈志远:《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第78页。。所以,他们阐释的“社会”概念,完全立足于社会生产。他们提出,社会就是人类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的总和。1924年10月,瞿秋白如此定义“社会”概念:“社会者,能制造工具的人类之劳动结合也。此劳动结合——‘经济体’之演化,乃生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风俗、艺术、科学等现象,以应组织劳动之需。”*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第17页。他们进而阐释了由“生产——人与人间的关系——社会”构成的社会话语体系。1929年11月,高尔松、高尔柏申明,人类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必须进行社会生产,“在这生产过程中,不能不共同劳动或互相工作,而直接、间接地发生种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错综复合,形成社会之经济的构造。加入这种生产关系中的一切个人遂构成一社会”*高希圣、郭真:《社会科学大纲》,第二章“社会论”第1—2页。。高尔松、高尔柏此说于1930年5月被顾凤城引用。顾凤城引用高尔松、高尔柏所言称:“在这生产过程中,不能不共同劳动或互相工作,而直接间接地发生种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错综复合,形成社会之经济的构造。加入这种生产关系的一切个人遂构成一社会。”*顾凤城:《社会科学问答》,第74—75页。
由于立足社会生产阐释“社会”概念,所以马克思主义论者将其社会观与美国社会学界从心理行为角度对“社会”概念的阐释完全区别开来。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社会学教授爱尔乌德(C.A.Ellwood)在出版于1910年的《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SociologyandModernSocialProblems)中提出社会心理交互论。赵作雄于1920年12月将此书在中国迻译出版,其理论在中国学界影响极大。1929年6月,杨剑秀注意到,爱尔乌德称“社会是从各人‘心的相感作用’(Mental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s)而成。两三个人,如果在意识上能有相感的关系,即可以成为社会。若是仅止因为有同样的经济环境或是住的地点接近,还不能成社会。必定是因为心性相感,或者说是因为‘内我(Inner self)相联络’,才能成作一种共同的生活,是之谓社会”。他断然否定此论,表示“爱尔乌德这话对不对呢?社会真是所谓‘心的相感作用’或‘内我相联络’而成的吗?”“事实上,恐怕不是这样的吧”*杨剑秀:《社会科学概论》,第47—48页。。同年11月,高尔松、高尔柏亦认为,从“心性相感”角度解释“社会”概念,“此说太重视心理的要素,要知心理的要素完全是跟着物质生活而变更的”*高希圣、郭真:《社会科学大纲》,第二章“社会论”第4页。。
立足于社会生产阐释“社会”概念,马克思主义论者将经济基础决定论作为理论宣传的重点。他们指出,经济基础决定论是唯物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表现,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1929年6月,杨剑秀介绍,社会科学的唯物论认为,个人与社会的“意识”“精神”“意志”均受“客观存在”的限制,而这种决定个人与社会意识、精神、意志的“客观存在”就是社会生产及其导致的生产关系,“人类在用生产这个方法去摄取自然中的有用物的过程中,便形成了种种的物质的经济生产关系,由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奠定了社会的基础,没有这基础,所谓‘社会意识’、‘精神文化’等精神生产都不会发生”*杨剑秀:《社会科学概论》,第26—27页。。同年11月,高尔松、高尔柏也表示:“唯物论以物质的生产及物质的生产力为全社会的基础……没有这些物质的东西,什么‘社会的意识’、‘精神文化’,都不会有的。”*高希圣、郭真:《社会科学大纲》,第四章“唯物论”第3—4页。1930年5月,顾凤城也指出,“社会科学内唯物论者的见地”是指“物质的生产及其手段(物质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底基础。没有它们便不会有‘社会意识’、‘精神文化’”*顾凤城:《社会科学问答》,第35—36页。。
马克思主义论者在各种论著中频繁阐述了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并力图向社会大众进行推广。他们申明,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要素构成的。1924年10月,瞿秋白将经济基础称作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某种“物质关系”,将上层建筑称为人们基于这种“物质关系”而结成的各种“精神关系(政治、道德等)”*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第3—4页。。1936年5月,李平心指出,社会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生产关系的总和就形成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这就是社会的真实基础”,“有了某种的社会经济形式,就有和它相适应的上层的社会现象,如政治、法律、社会心理、道德、宗教、宇宙观(它的发展形态就是哲学)、科学、艺术、习俗等等,这些关系在新的社会科学学说上称为上层建筑”*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第150—151、151—152页。。他们又强调上层建筑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发展。1926年11月,萧楚女表示,“生产方式(合工具性质、技术程度、生产量、生产性质而言)”是社会变化的“原动力”,而政治、法律等“文物制度”只是“某个时代的经济关系之反映”,“所以说,一切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表层建筑物,经济才是社会的真实基础”*萧楚女:《社会科学概论》,第15—16页。。祝伯英亦于1933年12月称,政治、法律、科学、艺术、宗教、习俗、道德等之所以被称为上层建筑,“因为它们是建筑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任何上层建筑都是依据基础而演进的”*祝伯英:《社会科学讲话》,第17、18页。。一些论者试图运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这种社会结构理论。时任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的中共理论宣传者曹伯韩于1937年1月出版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颇具代表性。他在此书“前言”中称,自己只想“在通俗化运动上获得一点抛砖引玉的结果”,“至于内容方面,所谈到的原不过是社会科学里面几个最基本而浅近的原则”*曹伯韩:《前言》(1936年10月19日),曹伯韩:《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第3—4页。。他生动地将社会比喻为一栋房子:“社会好比一栋房子,下层的基础是经济关系,那些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等的关系,是上层的建筑物”,“社会的上层构造不能不和下层基础相适应,正和房子一样,要建造二十层的大厦,就不能不把基础弄得异常坚固”*曹伯韩:《好比一栋房子(社会的结构)》,曹伯韩:《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第21页。。
由于马克思主义论者的宣传,以经济基础决定论为导向的唯物史观受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的日益关注。在非马克思主义论者中,表示赞同者有之,表示反对者亦有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论甚至成为中国学界辩驳的焦点论题。1927年5月,时任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的国民党籍学者何思源,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讲稿《社会科学研究法》中表示一定程度地认可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论,认为:“这种思想是否完全周密,是否全体贯彻,我们暂不论他。但就现社会上各种关系说来,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确是此社会的政治法律的基础。政治及法律是他的表面,经济实情是他的真体。”*何思源:《社会科学研究法》,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宣传部,1927年,第15—16页。另一些论者则质疑经济基础决定论。1930年7月,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兼编辑部主任的国民党学者胡一贯注意到,马克思主张“物质”为“精神”的因子,而在社会问题上,“经济”又是“物质”的“代表”,故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建筑”,“依生产工具而存在”的“生产力”又是“经济”的“实在”,“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知道马氏的唯物史观,其以经济为社会组织之基础,以生产力为经济现象之实在”。他声称,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应以基于民生史观的“唯生论”为基准。马克思主义论者将孙中山所言“民生”解释为“经济”,将“民生史观”解释为“经济史观”是错误的,“所谓民生实包生命、生计、生活、生存四者之言,决不仅限于经济,换言之,即民生史观决非经济史观”。*胡一贯:《社会科学概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30年,第42、52—53页。1935年2月,青年党人常乃惪则试图从理论上推翻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论。他分析,唯物史观以“经济”为“人类的唯一原始本能”,“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实际,无不从经济史观出发,而经济史观的学说则建立于经济欲望为人类唯一欲望的错误学说上”。但这个“出发点”是错误的,“经济欲望”并非“人类唯一的欲望”,人类还有性、求智、爱美、权力等本能,这些本能导致社会组织产生种种区别。社会组织的演变“决非单纯的经济原因所能包括,而经济欲望也不见得比其他欲望有独占的专利权”。他甚至认为,攻破了经济基础决定论,就攻破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整体,“这个根本的错误一经攻破,则一切由此错误出发点而建设的空中楼阁的理论系统自一齐倒塌下来,不足一驳”。*常乃惪:《社会科学通论》,第93—94页。
由上所论,可见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运用唯物史观,系统阐释了与同时期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完全相异的社会理论。他们对“社会”概念的阐释,立足社会生产,认为所谓社会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的总和。他们依据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基于经济基础决定论,他们系统勾勒出人类社会的构成结构。他们的这些阐述说明,迄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论者已经形成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理论,并向学术、思想界乃至社会民众大力宣传这种理论,使这种理论体系成为一种被时人瞩目的理论模式。
综上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新兴社会科学”或“新社会科学”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思潮。一批马克思主义论者撰写并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论著,系统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由此在中国学界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群体。在他们看来,所谓社会科学亦即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是最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他们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问题的大致理论轮廓,认为唯物辩证法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采用的基本方法,而唯物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核心。从其出版的各类社会科学论著中,可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相关基本观点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乃至社会民众中传播的大致路径与谱系。由此亦可知,由中共引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中共领导武装斗争的努力和正确,同时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巨大学术与思想需求。这或许是我们认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所值得重视的另一个视角。
(本文作者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天津 300387)
(责任编辑 吴志军)
The Rising of New Soci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ng of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m Social Science in 1920s and 1930s
Yan Shuqin
There is a huge current of Marxist social scientific theory behind the new social science rising in 1920s and 1930s. Many social scientific scholars believing Marxism have written a large number of social scientific books so as to hand down the many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Marxist social science, and construct whol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social science. They hav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basic social scientific methodology, whose kernel i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on the other hand, 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society-explaining system, whose kernel is economic base, and then consciously distinguished this society-explaining system from the American social theory, whose research center is soci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he theoretical exposition and propaganda of the Marxist scholars denote tha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ts about social problem has formed roughly, and has gotten a lot of attention of Chinese academia and ideological sphere until 1920s and 1930s.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研究”(09YJA770049)的阶段性成果。
D618;K26
A
1003-3815(2015)-04-002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