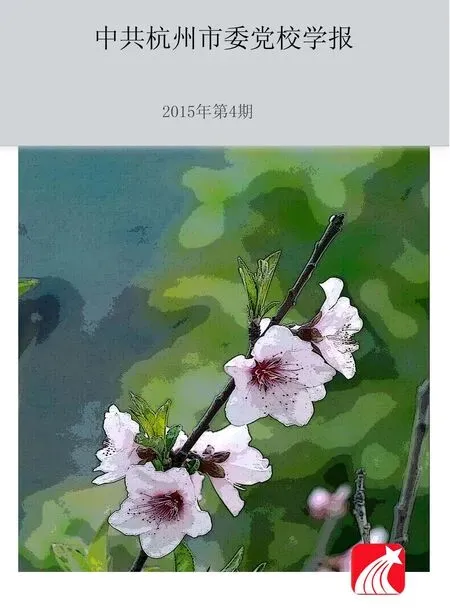狭窄空间内的政治构想和实践——关于古希腊政治的思考
2015-01-30李黄骏
□ 李黄骏
在古希腊时期,政治的基本含义就是参与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但这种公共生活的参与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城邦中的大部分人是没有资格参与到这种政治生活中去的。享有这种资格的人被称为公民,他们因为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实现了生活的完整性,而城邦也因为有了公民而具有了政治性,成为了一个政治共同体。简而言之,政治的含义与公民的政治身份紧密相关,没有了这种政治身份,也就没有了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这就是身份政治的基本含义。
古希腊政治的另一个范畴就是城邦,与身份政治不同,这是一种利用国家规模的解释政治的维度。在希腊人的思维中,政治不仅等同于公民,也等同于城邦这个狭小的国家规模。“在希腊人的思想里,政治范畴的概念已被等同于城邦确定的空间维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理想城邦的规模和人口所做的严格限制,以及他们对节育、财富和商业、殖民地与军事扩张所给予的详尽关注,是他们如下信念的一部分,亦即他们认为与其政治特性同义的城邦生活,只能在小型城市国家的狭窄范围内得到系统的安排。”[1](P75)
一、身份政治与城邦政治的依存关系
在古希腊的政治思维中,公民身份与城邦是政治范畴的两个维度,而且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维度。如果没有城邦的规模限制,公民身份就会失去它所承载的价值;而如果没有公民身份对政治含义的限制,城邦的规模限制也会失去它的意义。
首先,在古希腊,公民身份意味着政治认同,意味着你与其他人分享同一个政治空间,融入一个共同的生活,分享着同样的利益。而疆域狭小、人口有限、与外界隔绝的城邦自然成了公民们分享同一身份的最好空间。而且,根据法律史专家梅因的说法,城邦的公共生活是法律史上“最早最广泛的法律拟制”,即在法律上假定这些人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古希腊城邦为什么带有那么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将公民群体局限在一个同宗同源的小型群体中无疑也是会极大地加强这种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除了来源于对同一空间和同一利益的分享之外,更来自于将自己与其他类型的集体的成员相区分。“将某人和其他相似的类型的人结合起来,并相应地与其他类型集体的成员区分开来,这是社会认同所要求的相辅相成的过程。”[2](P258)在古希腊,公民的政治身份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这些公民们垄断了城邦的共同生活。与城邦中奴隶相比,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没有主人,或许他们也同奴隶一样受雇于人,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是自由的公民;与野蛮人相比,他们是文明人,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意志统治自己的城邦,他所服从的只是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君主的奴役;与外邦人相比,他们是城邦共同生活的参与者,他们的生活与城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是城邦的主人而不是客人。
公民就是通过将自己与奴隶、野蛮人以及外邦人区分来完成自己的政治认同。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民身份的特殊性需要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因为“一个城邦的公民,为了要解决权利的纠纷并按照各人的功能分配行政职司,就必须互相熟悉各人的品性。”而如果国家规模过大、人口过多的话,人与人之间就无法互相了解,那么在分配职司的时候就会出现纰漏和不公,而且,“在人口过多的城邦中,外侨或客民如果混杂在群众之间,便不易查明,这样,他们就不难冒用公民而混用政治权利。”[3](P361)这也就解释了他固执地将公民限制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城邦之中的原因。
其次,公民身份意味着相同的政治品质,意味着相同的政治生活,而这一切也与城邦的狭小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希腊人认为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是一种人人相同的天赋,而且这种天赋不会因为后天的学习和经验而有所改变。“有关人人都可以积极参与共同生活的这一理想,实是以这样一种乐观的估计为前提的,即一般人都具有天赋的政治才能。从否定的角度看,它并不认为惟有经过严格训练和拥有强化的专门知识才能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做出智慧的判断。”[4](P42)在那篇著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中,伯里克利对这种天赋的才能充满了自豪。“我们所依靠的并不是阴谋诡计,而是我们自己的满腔热情。在教育问题上,他们(斯巴达人)从孩提时代就一直在接受刻苦的训练,使之变得勇敢,而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却同样愿意去直面他们所面临的那些危险。”[5](P43)这段话表面上是在讽刺斯巴达后天的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在表扬雅典人的天赋。在他看来,这种天赋既可以取代后天的军事训练,也可以取代后天的政治训练。
公民相同的政治才能要求他们在政治实践中也要有相同的参与机会。与现代政治形态不同,古希腊的公民是可以直接参与统治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分的。举雅典为例,伯里克利改革以后,城邦的政治权力转移到了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那里。前者由全体公民组成,它有权讨论、制定和修改法律,订立条约、决定和战。它不仅制定一般性政策,还经常就政府工作的具体细节做出决定。它选举将军等部分公职人员,监督、罢免和制裁各种公职人员。至于后者,其地位与公民大会相当,被认为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拱顶石”。陪审员每年选举产生,年满30 岁以上,不曾欠国库的债和不曾失去公民权的人,都可通过抽签选举进入陪审法庭。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估计,每年在六个公民中就有一人可能要担任某种公职,而如果他不担任公职的话,那么他仍然要出席每年定期举行的十次公民大会,参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绝对的政治平等,是一种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为了赋予更多的公民以参与政治的机会,雅典采用了轮流担任公职、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任职人选以及把一些统治机构扩大到甚至难以运转的程度等做法,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雅典政治的危害是巨大的,即使雅典公民愿意承受这种危害,这种做法的效果也是有极限的①关于这些做法的极限问题,最好的例证就是古代雅典的公民大会,虽然它是古雅典理论上最核心也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但是因为其6000 人的规模过于庞大,在政治实践中难以实际发挥作用,而不得不用一个500 人的评议会代行其职权。具体参见[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最新修订版)[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pp.21-22.。如果我们把每个公民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用分数来表示的话,公民总数就是分母,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就是分子,那么要想使这个分数尽可能大的话,除了增加分子以外,还必须限制分母,即限制公民的总数。无怪乎区区两万公民的雅典已经被当时人们认为是过于庞大了。
最后,公民身份意味个人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影响,这是公民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这也与狭小的城邦规模有着密切的联系。拥有公民身份、参与公共政治生活都是古希腊人的光荣和梦想,但如果将我们送回那个遥远的时代,就会发现这种公民的身份并不像一种权利而更像是一种义务。“真正的自治,正如古希腊人实践过的那样,要求公民完全致力于公务。自我统治意味着用毕生的时间去统治。”[6](P285)库朗热在其《古代城邦》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评价:“由此可见,在民主国家中,公民身上的担子极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城邦事务上,留给个人事务或私人的生活时间很少。……这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战时准备牺牲生命,平时又要准备牺牲时间。他们不能置公事于不顾,去理自己的私务。正确的做法应是,牺牲私利以便致力于城邦公益。”[7](P312)既然作为公民的代价这么巨大,那么为什么古希腊人还对这种身份和活动如此热衷呢?除了古希腊城邦时代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外,公民们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也获得了巨大的快乐,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就像贡斯当指出的那样,“在古代,每个人分享国家主权决不仅仅像我们今天那样是一个抽象的假定。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有真正的影响:行使这种意志是一种真实的、不断重复的乐趣。惟其如此,古代人随时都会准备作出许多牺牲,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8](P39)
对于古希腊公民来说,他们生活的乐趣以及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不停重复地对城邦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大小却是与城邦的规模有着紧密的关系。“由于公民集团的人数有限,个人与城邦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可见、距离非常近的。如果把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用分数来表示,公民总数是分母,每个公民是分子,那么,分数越大,个人与城邦的距离越近,个人与城邦一体化的感觉就越强。”[9](P175)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公民数量与公民个人在城邦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成反比的,公民数量越多,公民个人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就越少,那么为了扩大每个公民的影响,就必须首先限制公民的数量,控制城邦的规模。除此之外,限制国家的规模,塑造一个同质化社会也十分重要。人们的意见往往会因为种族、风俗、财富等因素产生分歧,如果一个个体的意见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屡屡没有被采纳,那么他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的政治认同感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乐趣从何而来?他的人生价值又将寄于何处?
二、身份政治与城邦政治的危机
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将身份政治和城邦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也确实在实践着这样紧密的结合。但历史中的城邦政治生活却远没有“伯里克利”们歌颂的那么美好,正如谢尔顿·S.沃林(Sheldons.Wolin)评价的那样,“在希腊哲学中高度发达的政治空间意识,是一个实际政治世界的直接反映,在这个世界里,众多小型的独立城邦,为野心的原动力、阶级斗争、人口压力和经济不平衡所驱使,不断互相撞击并发现已很难无碰撞地行动。”[1](P75)城邦狭小的国家规模虽然使得身份政治在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了现实,但同时也放大了身份政治的弊端,甚至使得这种弊端超过了该种政治形态本身可以承受的极限,并最终使得城邦政治和身份政治一起走向了死亡。
首先,狭小的国家规模加剧了古希腊政治生活的动荡,并使其成为城邦最大的“疾病”。古希腊人将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乐趣都寄于城邦的政治生活必然会导致过度的政治动员和社会过分的政治化,一旦政治体系出现危机,社会便没有缓冲和回旋的余地,容易失衡或瘫痪,这便是现代政治学家所称的“参与内爆”。而城邦狭小的国家规模更是加剧了这种冲突,“由于公民集团人数少,其内部的分化显得很刺目,任何利益与权力的冲突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公民内部的对立往往没有缓冲余地,内部的党争动辄采取极端的形式。”[9](P217)
其次,过度的政治参与导致了古希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失衡,而狭小的国家规模则放大了这种失衡带给城邦的危机。充分的政治生活需要全体公民全身心的投入,对于一个古希腊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事务就是他的政治生活,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事务都首先应该服从于它,这其中就包括经济事务。正如萨托利所评价的那样,“这套公式所要求的卷入政治的程度如此之深,它造成了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衡。”他把这种政治活动的过分膨胀称为“政治肥大”。政治的过分膨胀,压缩了城邦其他事务的空间,经济也不例外。“政治的肥大造成经济的萎缩:民主愈完美,公民愈贫穷。”城邦政治制度的这种功能性失衡导致希腊社会长期维持着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这种“政治肥大”对社会的影响还远远不限于此,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需要大量的财富,但萎缩的经济此时却无能为力。“因此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为了弥补财富生产之不足,就不得不去没收财富。”[6](P285)萨托利认为,正是由于古希腊社会的功能性失衡,富人和穷人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古代经济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和手工业一直受到古希腊大部分思想家的鄙视和排斥。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就认为农业人口和畜牧业人口的情操最为高尚、体格最为健壮,而“其他品种的平民政体作为基础的它类人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比农牧为卑下。工匠、商贩和佣工这些群众,各操贱业以糊口,他们的种种劳作都无可称尚。”在他看来,商业和手工业既不足取,也不足道,一个城邦的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于它的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倘若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太少,这在生活上就无法自给自足。一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而且,“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说,应当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上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富裕但仍需节制。”[3](P325,360,362)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的财富是与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直接挂钩的,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直接决定着城邦的经济水平。而限制国家规模的基本外延就是土地和人口,所以限制城邦的规模实际上就是限制城邦的经济水平,其必然后果便是扩大了政治和经济失衡所导致的危机。
最后,将政治思维局限于狭小城邦的做法限制了古希腊结成一个大型共同体的可能,使得古希腊城邦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方面,在古希腊世界内,由于无法实现统一,各城邦之间发生了无休止的纠纷和战争,并最终导致了波及整个古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场战争之后,古希腊城邦便纷纷走向了衰弱。另一方面,由于狭小城邦难以结成一个整体,这就分散了整个古希腊世界的实力,在面对强敌时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古希腊城邦最后被马其顿帝国所征服的重要原因。
三、小结:古希腊人的反思
与后来出现的斯多葛主义相比,古希腊的政治思想显得紧张和强烈。在沃林看来,古希腊政治思想的力量或许正是来源于狭小政治空间与充分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的紧张,“古希腊政治思想之所以强烈,是由于它接受了针对曾一度拥挤不堪而又极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所规定的挑战。”[1](P75)在这样的分析中,城邦狭小的政治空间与充分的政治参与在希腊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是存在强烈紧张的。既然两者存在的紧张造成了希腊政治实践和思想的困难,那么解决的方法也很明显,要么继续拥挤,要么继续参与,两者只能取其一,而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也确实是那么设想的,并由此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尝试。
第一种尝试是柏拉图式的。他拒绝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的适当规模,并转而求助于限制公民的政治生活。在他的世界里,国家的规模还是城邦式的,甚至还小。这种对于扩张国家规模的恐惧也体现在他很少谈论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并对战争和扩张所带来的后果持一种警告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古希腊城邦政治所表现出来的无序性的原因就在于民主政治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在沃林看来,“柏拉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计划克服在拥挤的政治环境中不可容忍的摩肩接踵的无政府状态。依靠明确规定每个阶级应履行的职能,依靠阻拦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流动,新的政治空间的结构将得到保护,不会再有随机的流动出现。”[1](P75)可见,柏拉图由于拒绝重新界定政治所适用的国家规模,使得他只能通过限制政治生活生命力的方式来谋取城邦政治失序的出路,而这又与古希腊政治所带有的身份特征是严重冲突的,这也注定了其思想从一开始便是紧张的。
而另一种更为有意义的尝试便是突破古希腊政治的规模限制,通过重新定义政治共同体规模的方法来寻求古希腊政治的出路,这突出地体现在通过组织和其他方式协调若干结盟城邦关系的实验中。其中一种尝试就是在所谓“市民平等权”的约定下,一个城邦的公民在所有的别的约定的城邦中都拥有公民身份;而在另一种联盟形式“联邦制的国家”中,个别城邦的公民则同时拥有整个联邦的公民身份。例如伊索克拉底,他意识到特定城邦的公民身份是阻挡构建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主要障碍,提出了一个关于希腊统一体的理念——“希腊人”的概念。[10]从这两种突破政治共同体规模束缚的尝试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破除公民身份与城邦的紧密关系。在一些不那么著名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我们都能找到这些尝试的印记,但就如他们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一样,他们的这些尝试也没有在历史中留下太多的影响。诚如上文所述,在古希腊的政治生活中,公民身份是与城邦这一拥挤的政治空间紧密相连的,只要政治的范畴仍然等同于公民身份、等同于广泛的政治参与,那么希腊人对政治的理解就很难超出城邦的这一狭窄的范围。正如沃林指出的那样,“只要政治的范畴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等同于深入细致地参与有关共同事务的生活,那么对于人的政治忠诚而言,伊索克拉底和狄摩西尼关于在希腊城邦间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建议以及对于联邦制国家的实验就不能臻于完美。”[1](P78)
可见,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对于他们的城邦并不是没有反思,但是由于他们对政治范畴的理解限制了他们的反思,使得这种对于古希腊政治实践的反思一直就没有挣脱城邦那个狭小空间的束缚,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身份政治与城邦政治的互为依存的关系。无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是伊索克拉底和狄摩西尼,他们的政治思想都停留在了理想的层面上,从来没有对古希腊的政治实践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古希腊人对于政治范畴的理解一直没有跳出身份和城邦的限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 世纪马其顿帝国的征服之前。随着古希腊各个分散的联邦被马其顿的强权所征服,古希腊世界开始了由城邦向帝国的时代转变,希腊人也不得不开始对原有的身份政治和城邦政治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
[1][美]谢尔顿·S.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M].辛亨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英]德里克·希特.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M].郭台辉、余慧元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邓正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古希腊]伯里克利.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词.转引自[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邓正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英]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7][法]库朗热.古代城邦[M].谭立铸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0]Ernest Barker,Greek Political Theory,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Methuen,1918,pp.100- 105.T.A.Sinclair,A History of Greek Political Thought,Routledge,1952,pp.13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