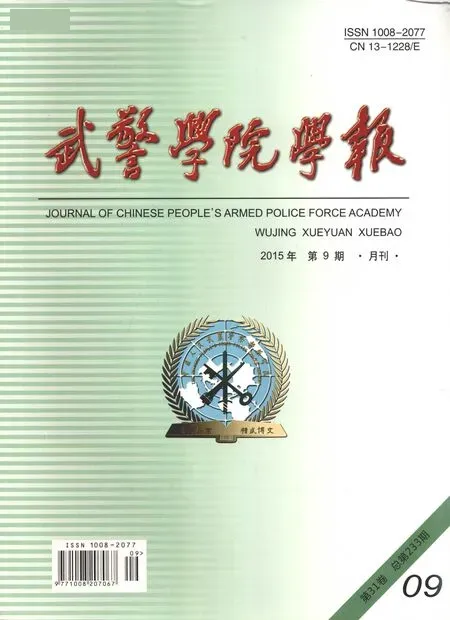我国公安情报工作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2015-01-30张秋波郭永良
张秋波,郭永良
(1.武警学院 边防系, 河北 廊坊 065000;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我国公安情报工作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张秋波1,郭永良2
(1.武警学院 边防系, 河北 廊坊 065000;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对公安情报工作进行立法,需重点考察和分析四个基本论域,即:明确法典化的“立法模式”、确立权利与效率兼顾的“立法目的”、选择以纵向情报工作流程为主体的“立法主线”和构建以核心型和保障型为主体的“主要制度”,以澄清可能出现的误区,推进立法实践的开展。
公安情报;立法;金盾工程;总体国家安全观
近年来,随着金盾工程的推进、社区警务模式的开展以及情报引导警务理念的倡导,我国公安情报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这是一种法律保障缺失之下的制度实践,关涉情报工作的相关规定游离于内部工作守则和外部线索奖励通告之间,位阶低、内容杂、效用小,法律上有关公安情报工作的条款数量少且难以统揽全局。①以《刑法》第111条为例,该条涉及“情报”用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4号),该条的“情报”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根据第111条的规定,情报的涵义只用作界定为境外窃取、刺探、售卖、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适用,可见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不能包含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广泛开展的情报工作。而且,公安情报工作极具秘密性,稍有不慎极易导致公民合法权益的侵损,这种侵损又很难得到司法机关的审查和救济,因此,有对它立法规制之必要。尤其是在2015年7月1日施行的《国家安全法》设专节以五个条款对“情报信息”进行顶层设计之背景下,如何基于该法的统领,制定符合公安情报工作特点的、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和规则指南,弥补公安机关执行《人民警察法》第2条②《人民警察法》第2条规定了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并对其职责范围进行了列举。时存在的制度空白,成为了公安情报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欲就某一领域进行立法,需先对该领域的重点进行考察,以释清理念上可能存在的分歧。就公安情报工作进行立法,需重点考虑立法模式、立法目的、立法主线和主要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对上述四个基本问题的理论探讨将有利于立法实践的开展。
一、立法模式之选择
对公安情报工作进行立法,首当其冲的就是选择一个既适合《国家安全法》立法宗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安情报立法体例模式(以下简称立法模式),对公安情报工作进行法制化。所谓立法模式,既是特定法律规范的载体所体现出来的总体表征,亦是立法者表达立法观念的方法和途径,还是一般公众认知法律规范的媒介。[1]从立法形式考查,法的体例主要有两种模式,即法典模式和分散模式,前者是指把调整公安情报工作领域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一个专门的法律文本之中,称之为法典;后者没有这样一个处于统领地位的公安情报工作法典,而是通过零星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分别调整情报工作某一领域(比如情报收集)的法律关系。[2]当然,法典模式下的公安情报工作法律文本也会给其他层级较低的单行行政法规、规章留有一定余地,而不是包揽所有规范公安情报工作的行政法规。
就目前而言,没有专司规定公安情报工作的法律。根据学理解释,可以合理推断出包含有规范公安情报工作意涵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刑法》《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事件应对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城市人民警察巡逻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航空情报工作特情处置管理办法》等,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关于公安情报工作的内部规定,可以说该领域的相关规范十分庞杂。缺失了起统领作用的法典式公安情报法律文本,导致各个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效力冲突、内容重复等情形经常发生。而且由于公安情报工作并非由公安部门独立进行,也涉及到国家安全部门、民航部门、外交部门、运输部门等的协助和共同开展,现行部门之间的条条关系极有可能因为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而导致关键情报流失、不能发挥情报的先导作用。因此,亟需统一法典的出台,以协调并固化部门之间涉及公安情报时的工作关系,并指导公安情报实践的具体开展。*事实上,考察各国情报体制的历史轨迹(大都萌芽于军事情报体制时期,发展于松散的社会情报体制时期,而成熟于整体的国家情报体制时期),不难发现,也都是遵循着统一化、聚合化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情报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有统一立法之必要。参见郭永良:《国家情报体制的历史沿革》,载于《情报资料工作》2008年第1期。统一的公安情报法典应就情报工作的一般性、共同性、基本性问题进行规定,既能避免各部门之间工作的低效和重复,又能缓解不同层级规范性文件的冲突;既保障公安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又为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提供明确的指引。鉴于现行立法机关专门就公安情报工作立法的时机并不成熟,可以先通过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公安情报工作的行政立法。待行政法规经过实践后,相关的各部门在该法规的指导下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层次分明的情报法制体系后,再由立法机关整体统筹规划。
二、立法目的之厘定
目标是设计任何一项制度的前提,是设计者赋予该项制度所欲实现之价值状态。[3]科学界定公安情报工作行政法规的目标模式,既是对公安情报工作理想目标的法律化阐释,又是理性架构该法整体内容的逻辑起点。在厘定目标模式时,难免会遇到不同制度的价值冲突,例如,公开与保密、秩序与自由、公正与效率、公权与私权等。由于公安情报工作所具有的隐蔽性、对抗性、谋略性、时效性等特征,要求公安情报工作者采取特情、耳目、线人、卧底以及各类监听技术获取并分析情报,而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特定人员的自由和权利。显而易见,让立法者陷入困境的莫过于如何在最大程度提高各部门公安情报工作能力和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权利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即究竟应选择效率模式还是权利模式?各国立法机关根据本国情势需要,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不同答案。以美国为例,2001年“9·11”事件后,国会为了便于国家打击恐怖主义通过了《爱国者法》,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此谓效率模式;然而时间延至2015年6月,美国政府意识到公民权利在庞大的国家监听权力面前日趋孱弱,国会议员之间存在广泛的意见分歧,导致《爱国者法》失效,行政部门不再有权大量搜集情报信息,效率模式向权利模式发生了偏移。
对于我国来讲,在情报立法时如选择权利模式,极其强调个人权利的保障可能导致无法有效开展公安情报工作,最终无法保障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若选择效率模式则可能由于片面强调公安情报工作的时效性,导致公民合法权益的不必要牺牲,不利于保护特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由此可见,在对公安情报工作进行立法时,应尽可能做到权利和效率二者兼顾,既要有利于控制情报工作滥用情报权力和保护公民权益,又要有利于提高开展情报工作的效率。在某些情况下,公安情报工作的法制设计可能难以兼顾二者:控权即难于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即难于控权,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在获取暴恐情报时,赋予公安机关搜集线索和临时限制特定公民权利是可以的也是可行的,这时就要偏向于效率模式;在广泛获取社区情报时,公安机关搜集的线索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就需要注意防范滥用情报权力的可能,这时就要注重权利模式。总体而言,就公安情报工作进行立法时,其立法目的既不能是完全的效率模式,也不能是完全的权利模式,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混合模式,“为了规范公安情报工作,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表述可以比较明确地概括这种模式的立法宗旨。
三、立法主线之明确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世界上针对特定工作进行立法的国家,一般都遵循两条基本立法主线,即在横向上依据调整对象的类型进行立法,在纵向上根据调整对象的工作程序进行立法。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侧重于横向主线,有的国家侧重于纵向主线,而有的国家则是平分秋色。[4]如果在横向上进行立法的话,就要区分公安情报的种类。一般而言,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公安情报有多种类型。按照部门管辖的不同,公安情报有公安刑事情报、公安行政(治安)情报、安全保卫情报、反恐情报以及其他部门情报(比如航空特情情报、边防情报等)之分。如果以类型来设计立法主线,则有可能出现将各部门出台的内部规范性文件混杂在一起的法律文本。这样一来,不仅起不到法典化的统一性,而且还可能出现法律内部结构的交织错位,因为多数部门涉及的公安情报的基本流程都大体类似,只是在特定情报技术和特有人财力资源上有所不同。因此,以这种立法主线为主进行立法不足取。
在纵向上根据公安情报的工作程序进行立法,就要明确情报的流程。根据信息的产生、组织、传递、吸收的生命周期理论,如要在信息中萃取情报,情报工作就需要有针对性地遵循情报收集、分析研判、及时报送、有效使用及分享的程序。那么,对公安情报工作进行规范的法律文本就应该对上述四个环节安排篇章结构和条文体系。依笔者之见,公安情报工作的法律文本除了第一章的总则和第六章的法律责任之外,第二章至第五章应依次为公安情报收集、分析研判、报送、使用及分享。这样,章的编排就会结构完整,可以涵盖公安情报工作的整个过程。而在章内的条文规定上,则可以根据公安情报的种类和某个环节所特有的方法进行设置,例如情报收集环节,可能涉及到其它行政部门公安情报的归口汇入,这时就应设置相应的衔接条款。简言之,明确公安情报立法主线时,可在特定环节中设横向主线,但是法律全文的格局应是纵向主线。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公安情报工作并非线性,也并非必须是前一个环节完成后方可进行下一个环节,这也是之所以《国家安全法》第52条规定“应当及时上报信息”的同时,又在第58条规定“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的原因所在。对公安情报工作四个环节的设计,是为了解读理解和开展工作的方便,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理想类型”分析方法是马克斯·韦伯所创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意指研究者为了对对象进行分类和比较分析时的一种价值中立式的主观建构,无论哪种类型都与其他类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包含其他类型之因素,在现实中,实际上任何一种类型都不可能以纯粹形态出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在具体情报实践中,各个环节有可能是在时间上并行开展,或者说同时发生,相互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先后顺序。[5]这需要在公安情报立法中予以察觉,并合理配置各个章节的逻辑关系。
四、主要制度之设计
对公安情报工作进行立法,意味着要将法治原则渗透进公安情报工作的具体制度中去,为解决“有法可依”提供法律逻辑,同时也为现行的情报工作实践提供制度框架,以提升公安情报工作质量。在设计法律文本的主要制度时,应主要考虑核心型制度和保障型制度。
核心型制度是指,直接用以规范或调整情报主体在公安情报工作中之行为的规则体系。核心型制度主要是指四个情报工作环节的制度:情报搜集制度、分析研判制度、报送制度以及使用和分享制度。鉴于情报搜集制度、使用和分享制度主要涉及到外部行政行为,与公民的联系比较紧密,因此在立法中应该对这部分的情报行为进行细密规定,尤其是有可能侵害到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以及必要的知情权利时,必须进行权利义务关系的配置。例如对于人力情报手段的适用范围,对于秘密监控的审批流程,对于情报分享的程序以及公民行使知情权的过程,都应进行规定,避免外部行政行为给公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或者一旦造成损失,公民有明确的救济路线可循。对于分析研判制度和报送制度而言,主要涉及到内部行政行为,这些制度的运作一般包含指派经办人员、审查审核、分析研判、请示汇报、专家讨论、领导决定等一系列“内部行政程序”制度。对于外界而言,它并不影响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因此,对于这些制度,公安情报立法时可就必要的制度框架进行原则性规定,对于制度的具体内容,可授权各个行政机关以行政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做进一步细化。
保障型制度是指,用以支撑核心型制度顺利推进和有效运行的规则体系,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制度、情报资金制度、队伍建设制度和保密制度。对于信息技术制度而言,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已经建立了以“金盾”工程为依托的现代警务情报信息机制,增强了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打击犯罪的能力,但是它的依据是2003年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金盾”工程初步设计方案和资金概算》,并没有立法层面的合法来源。以反恐为例,我国拟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立法机关正在审议的《反恐法(草案)》草案将把它纳入法治化轨道。未来在公安情报工作立法中,“金盾”工程的运作应当纳入法律的框架下,避免无法无据造成情报工作的被动。对于情报资金制度而言,目前我国以预算“申请——批复”的形式进行专款专用,但是这种方式没有法律的硬性规定,导致情报资金的供给跟不上情报工作的发展,尤其当前公安机关“非警务工作”繁重,很多本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也通过当地领导的决策纳入公安工作范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情报工作的开展自然难以为继。在公安情报立法中,可参考韩国《灾难和安全管理法》第67条第2款规定,“每年度向第一款规定的灾难管理基金投入的最低金额是最近三年间《地方税法》中的普通税的收入决算额的年平均额的1/100”。公安情报资金应随着政府税收岁入的变化而有固定的比例,而非每年都是固定的额度。同时,杜绝在经费使用中,经费用途或随领导意图发生变化、或被其他工作借用情形的发生。队伍建设制度是公安情报工作人员的准入、培养和管理制度,它是公安情报工作开展的人力上的保障,在法律文本中应有明确的表达,对违法管理队伍的情况要追究法律责任。保密制度是情报工作的特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安情报都必须保密,“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或“以保密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保密理念将形成完全不同的公安情报立法观念。在信息化的今天,必须对核心情报加大保密力度,而对不甚关键的情报则可以适当公开,这就需要在立法中体现出相应的解密程序规定。
[1] 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06.
[2] 胡建淼.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模式与结构[J].政法论坛,2004,(9).
[3] 郭永良.应急行政立法目的之重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5,(3):58-60.
[4] 戚建刚,郭永良.《武汉市突发事件实施办法(草案)》若干问题研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12.
[5] Gregory F Treverton. Reshaping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an Age of Inform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9-22.
(责任编辑 杜 彬)
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Issues of Police Intelligence Legislation
ZHANG Qiubo1, GUO Yongliang2
(1.DepartmentofBorder-controlandImmigration,TheArmedPoliceAcademy,Langfang,HebeiProvince065000,China; 2.LawSchool,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HubeiProvince430073,China)
In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four basic domains should be focused on, namely: the confirmation of explicit codification in “legislative model”,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rights-protection and efficiency in “legislative purpose”, the assurance of longitudinal process of intelligence in “main legislative lin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uclear and supportive systems in “basic frameworks”. Based on the studies above, possible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practice of legislation can be clarified and the quality of law can be promoted.
police intelligence; legislation; golden shield project;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5-07-02
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公安情报法制建设理论体系与立法探索”(2015030313)
张秋波(1965— ),女,黑龙江绥化人,教授;郭永良(1984— ),男,河南许昌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
D920.0
A
1008-2077(2015)09-0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