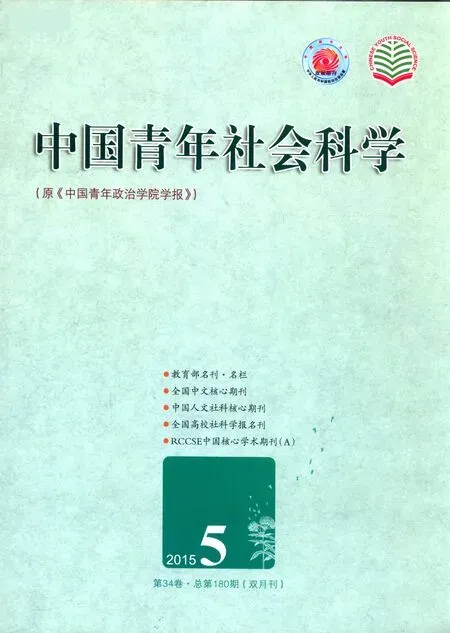青年文化发展规律研究
2015-01-29邓希泉
■ 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所,北京 100089)
青年文化发展规律研究
■ 邓希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所,北京 100089)
青年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规律。从生成角度看,青年文化主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生成并借此嵌入社会结构。从发展角度看,青年文化呈现为具体文化之间的非关联性与整体文化内在逻辑的统一。从功能角度看,青年文化主要以抗争的方式凝聚青年认同和确认群体价值。从传播角度看,青年文化主要在同辈群体互动中进行传播并实现青年文化的再次建构。
青年文化 发展规律 抗争性 同辈群体
亚文化纳入学科化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芝加哥学派。青年文化是亚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种成熟的青年文化已经成为现实”,以至于文化史学家“喜欢用各种基于青年的术语——诸如嬉皮时代、迪斯科时代、朋克时代、嘻哈时代等等——来描述时代特征”[1]。从美国芝加哥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到后伯明翰时期的亚文化研究理论,以及我国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亚文化和青年文化的本质、内涵、功能、特征、历史、结局、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等方面,较少研究亚文化和青年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或者用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发展规律来替代青年文化生成发展规律的研究。青年文化规律研究的滞后,正日益制约着青年文化的本质探讨与青年文化的建设进程。从整体上看,青年文化具有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特殊的内部逻辑和外在特征。青年文化建设不只是一种大众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建设,而且是基于青年群体特性和青年文化特性的大众文化建设。深入研究青年文化发展规律,是做好青年文化引导和建设的基础及前提,也是青年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和紧迫任务。
一、青年文化主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生成并借此嵌入社会结构
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于社会成员而存在的社会结构要素。主流文化是承载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精神现象,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深层次方面影响社会成员。社会成员的生活空间可以分为日常生活领域和非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主要是指经常重复的以衣食住行为主要内容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非日常生活领域则是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专业性、创造性相关的社会行动或集体行为。区别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或文化的价值体系,青年文化主要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以非专业性的方式生成,并以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等为载体全面嵌入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青年文化的日常性、具体性、非专业性和非知识精英性,凸显了青年文化生成的特殊性。
首先,青年文化一般在日常领域和生活方式中产生并依托日常行为、生活方式和日常用具表现出来。青年尤其是处于青年前期的青年,主要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这决定了青年的活动空间集中在日常领域,青年的社会行为聚焦于生活方式。青年往往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穿着、外表、谈吐、用具等发现和表现自己的身份,也可作为青年反抗或偏离成人世界的载体或媒介。因此,青年文化往往是从青年的衣着打扮、休闲娱乐、人际交往、时尚生活和日常话语等众多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中产生、体现和发展的。承载和凸显青年文化的日常领域和生活方式,也必然成为凸显青年文化理念、推动青年文化实践的辨别性标志。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社会群体对现行占据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抵制与偏离,青年文化则更明显地通过创造新的行为方式来抵制、偏离或反对原有的生活方式而表现出来。
其次,青年文化主要是满足青年的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同辈交往、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亚文化具有的“风格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审美领域、休闲、消费等领域”[2]。青年文化经常表现为时尚文化,直接体现为生活风格的凸显,以生活风格的差异化作为青年文化的载体。青年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也表现为激烈的政治行为,形成以青年运动为主要内核的青年文化,似乎形成了青年文化日常生活化与政治的非日常生活化之间的矛盾。应该说,政治生活确实属于非日常生活领域。但是,青年政治文化的出现和兴起,或者是因为政治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导内容,由此也就主导着青年的日常生活;或者是青年主动地把政治诉求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政治诉求与日常领域的结合来实现青年文化的发展和青年群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主流文化倾向于用政治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日常生活,进而在文化文本中否定‘日常生活’存在的意义,或根据‘非日常生活’的价值准则来组合拼贴‘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也并不因此就被主流文化所屏蔽,“‘日常生活’也一直以‘民间’的形式隐蔽地存在于主流文化文本中,赋予文本真正的生命力”[3]。 青年文化总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围绕时尚文化和政治文化进行权衡和抉择。当前,我国政治生活日益回归非日常生活领域,青年文化的日常风格特征更加凸显,更多地依托物质文化与行为文化表现出来。
青年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满足于成为一种边缘的社会现象,而是要在既存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求更好的制度安排和更大的发展空间。青年文化嵌入社会结构的一般路径,是从具体到抽象,由部分群体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日常领域和生活方式就成为青年文化全面有效嵌入社会结构的通道和载体,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成为一种国家力量和民众的自觉力量。与主流文化相比,青年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要淡一些,娱乐性、成长性和学习性的色彩要浓一些。青年文化建设不能过度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性,否则会偏离青年文化建设的轨道,成为青年不喜欢的教化型的政治文化。要借助新媒体和同辈群体,更多地将主流文化融入青年的日常生活,成为青年的生活习惯,以青年文化的常识化与风俗化路径来推动青年文化的发展。同时,青年文化建设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否则,青年文化就偏离甚至消解主流文化,由亚文化滑向边缘文化甚至是反文化。
二、青年文化呈现为具体文化间的非关联性与整体文化内在逻辑的统一
从文化发展史看,文化一般是人类不同世代传承创造的结果,呈现为连续的线性或曲线型的文化演进轨迹;文化创新总是在新兴文化与现有文化进行对话的基础上,在文化要素、文化形式或文化方式等方面实现发展或突破。从青年文化的发展规律看,青年文化的跳跃性、非规则性非常明显,其自身内部的承继性、关联性和连续性较弱。“后起的青年文化与此前的青年文化,两者之间没有或很少有内在的关联性,后起的青年文化既不是对此前的青年文化的继承或深化,也不是对它的反叛或改造。”[4]无论是20世纪西方国家的嬉皮士、光头仔、朋克、无赖青年、足球流氓、摩登族,还是我国的潘晓讨论、流行音乐、痞子文学、大话文艺、恶搞文化、超级女声、身体写作、网络思潮等,各种具体的青年文化之间大相径庭,彼此间关联度不大。
青年文化是生产方式变革导致青年群体在上层建筑中的新的精神需要而引发的文化现象。青年文化传播范围广、变化速度快,内容不断变化、形式不断更新,往往具有多方面发生、多领域涌现、多地域纷起的特点。处于同时态下的青年文化,或相互竞争,或相互支撑,或互不干涉,或我行我素,呈现为一种非紧密关联的松散状态。处于历时态下先后继起的具体的青年文化,彼此之间的理论渊源、内在逻辑、内容依存或形式沿袭等相关性和延续性更为薄弱。时尚和热点往往是青年文化的重要方面,时尚和热点也往往是纷然杂呈的,并不遵循一种必然的逻辑和理论体系。从整体上看,青年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青年群体是青年文化的创造主体和使用主体,并不是因为青年文化的文化传承或内在逻辑。非关联性地呈现跳跃性发展的青年文化,一般总是发生在青年群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冲突表征最为明显的地带、领域、事件或群体之中。从其根源上看,青年文化的发展变化与青年自我认同的变化关系密切。青年时期的认同正在进行,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很有可能持续发展或发生变异,实现自我认同性转变。青年群体自我认同决定了青年文化的类型与走向,青年文化则体现和反映了青年自我认同的状况与问题。这是青年文化跳跃性变化的内在根源。
青年文化非关联性的跳跃性发展,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即使在时空上具有相邻性的青年文化,也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青年文化的发展光谱是以跳跃的方式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约翰·克拉克和斯图亚特·霍尔等指出,青年和新的青年文化最能反映社会变迁的本质特征[5]。青年文化是在非连续性的不同点上非同时态的出现,体现连续发展的社会变化的过程。在单个的青年文化之间,很难找寻青年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另一方面,非关联性的跳跃性发展的青年文化,并不就意味着青年文化在整体上缺乏承继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如果将不同时期的青年文化置于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时间轴上,就能发现青年文化跟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断发展前进的内在规律。同时,青年文化总是青年需求的集中反映,青年文化的发展总是青年需求发展的结果,必然体现出青年需求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青年发展需求的变化,作为青年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贯穿于青年文化发展的始终。更重要的是,青年文化的承继性和关联性主要体现为新兴青年文化对已有青年文化的抛弃式或否定式创新,从而实现青年文化的自我超越创新。青年文化绝不是自我欣赏的内部摸索,也不是此起彼伏的雷同或相互继起的重复,一般总是在已有青年文化基础上的超越创新,总是建基于已有青年文化的风格、式样、内容、形式、途径、载体等之上,新兴青年文化总是要与以往的青年文化产生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差异。
从青年文化的发展视角看,青年文化呈现为具体文化之间的非关联性与整体文化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正因为具体的青年文化之间缺乏先后继起的连续性或因果性,青年群体在认识事物和处理事务时更多地采用横向比较思维而非纵向历史思维,青年文化一般是对成人世界和既有文化的抗争与偏离甚至反叛,本土文化基因并不容易纳入青年文化的视野,优秀传统文化难以天然地作为青年文化的内核元素;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青年文化的叛逆与反抗,会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故意批判甚至摒弃来宣告和展现。与此相反,外来文化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有可能成为青年文化反对本土文化的工具。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越激烈,矛盾越尖锐,青年群体和青年文化就越有可能接受和吸纳外来文化。因此,把握青年文化的本土基因与外来元素的对立统一,要使青年文化从对本土文化基因的叛逆性否认转到主动性濡化,青年文化建设必须真正体现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精华及价值取向。从文化更替看,要对青年文化保持应有的持续关注,准确把握青年文化的非关联性、多样性和突变性,以及宏观上的继承性和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以跳跃性思维跟上青年文化的突变发展,在青年文化的断裂地带推动青年文化的平稳发展。
三、青年文化主要以抗争方式凝聚青年认同确认群体价值
文化的认同功能是文化功能的标志性内容。文化是“一个为符号商品争取社会承认的动态化斗争”[6],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流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或现行文化的新的文化形式,抵抗性是亚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从文化功能视角看,青年文化是“指青年人将他们自身从他们通过符号体系、语言、服饰和音乐所感受到的成人文化当中分离出来的种种方式”[7],这是青年群体努力区别于成人世界、社会结构和主流文化的种种方式,体现出青年对父母、教师和其他权威角色的反叛[8]。也就是说,青年文化主要以抗争方式来确认青年群体的价值并争取青年群体的社会地位,这是青年文化功能的明显表征,是青年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青年文化区别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其他社会群体或社会文化的本质方面。
青年群体在社会结构中进行的价值确认与主体地位的争取,集中反映了青年文化的抗争性。青年文化是一种以集体认同的力量来改变群体地位的努力,既体现为青年文化整体上与社会主流文化、成年人文化争夺话语权与社会资源的斗争,即青年文化作为青年群体社会地位提升需求的外在表现而进行的社会博弈,又体现为青年文化内部的抗争性,即青年亚群体创造的青年亚文化之间对青年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以及争取尽可能多的青年对象作为本文化的群众基础。青年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努力,则是青年文化抗争性的另一种体现。青年文化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本国、本民族和本地区主导价值理念的元素,总是在意识形态指导下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只是这种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或是合作,或是疏离,或是对抗。青年文化总是置身于社会主流文化之中,也或多或少地来源于社会主流文化。因此,青年文化对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偏离或斗争总是相对的、有限的,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总是独立存在的。
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以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和收编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是以商品的形式,即“把亚文化符号(服装、音乐等)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即转化为商品的形式)”,第二种则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即“统治集团(如警方、媒体、司法系统)对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和重新界定(即意识形态的形式)”[9]。当代青年作为“压力一代”,教育压力、经济压力、就业压力与社会适应压力引发了青年文化中的压力效应。面对社会不公及青年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青年文化的叛逆和偏离属性会相对较强地显现出来。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加强对青年文化的吸纳和纠偏,市场经济对青年文化的商品进行转化和市场化运作,使青年文化更迅速地被消费意识形态所收编改造。从政治视角看,主导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看待和处理青年文化,是其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明确反映,更直接影响和决定着青年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必须明确,抗争性是青年文化的一种本质属性,是青年文化之为青年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因此,必须保持青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抗争性、抵抗性和偏离性,这是保持青年文化创新性的必然要求。即使青年文化的偏离和对抗有可能或正在威胁主流文化,也不能对青年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青年文化的反叛与对立,其实质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在青年问题上的文化反映。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是由经济社会主要矛盾引发的,是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映射,而不是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经济社会矛盾。当然,青年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对抗和冲突,很有可能会加速或加重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青年文化抗争性的实现,必然要经由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有效引导和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青年文化作为文化创新持续动力和来源的积极作用。
青年文化主要以抗争方式来实现青年群体的认同功能,但并不否认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一致性与和谐性。“青年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文化偏离的非对应性上表现较明显。这就是在某些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主文化吻合或基本一致,某些方面则表现出程度不等的偏离倾向,而不是在任何文化内容上都发生偏离。”青年“不可能组成一个闭合性的独立社会来接纳与主流文化全方位偏离以保持完全独立形态的青年文化”[10]。一方面,青年文化以抗争方式来实现渗入、融入或介入主流文化之中;另一方面,青年文化日益体现出其作为主流文化面向未来、面向创新的一个主要源头的特点,体现出青年文化的和谐性。因此,任何忽视或否认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和谐性与一致性的做法,都只会危害主流文化建设和青年文化建设。只有既正视青年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抗争性,又充分认识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一致性,才能发挥青年文化对青年群体和主流文化的正效应,推动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
四、青年文化主要在同辈群体互动中实现传播与再建构
主流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可以借助社会结构的强制力,通过层级传播、平行传播和人际传播等方式,实现文化的传播、认同和内化。青年文化是青年群体中存在的或通过青年群体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集中表现出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青年文化必然是以青年群体为主体的文化,脱离青年群体的青年文化,就不再具有青年文化的本质属性,青年文化的归宿要么纳入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或大众文化之中,要么成为被更新、被替换或被抛弃的文化内容。因此,青年文化首要的和基本的规律就是在青年群体内部的生成、传播和发展,由此形成了青年文化构建和传播的特殊性规律,其主要表现是,通过青年群体之间的模仿、从众、示范、认同等互动方式,以非强制性的力量来推动青年文化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平行传播,并且在青年同辈群体中进行动态构建,参与青年文化传播过程的青年群体又以自身的参与对青年文化进行再构建和创新发展。
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群体的意识与观念,借此作为区别于成人世界的显著标志。青年文化既是同辈群体中的共同话题,可以增进同辈群体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增强群体之间的内聚力,又是结识和区分朋友群体的途径和载体,青年文化承担着大众场合或多人在场的情境下吸引或排斥互动对象的作用。青年文化使青年既能够获得身份、角色和群体的认同,构建起青年群体共同的价值和认知体系,又能够构建起通向成人世界的桥梁,在同辈群体在互动中获得代入感。青年群体内部虽有分化与分层,但青年群体内部的分层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分层,不同于以科层制、阶级阶层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结构分层。青年文化的传播并不必然地因循社会阶层从高到低、社会地位从强到弱的传播规律,而是类似平等主体的平行传播,是非权力型和非强制型的主动接收和认同。同时,青年文化的接收主体又能够主动参与该文化的传播过程并进行再次构建,青年文化是青年同辈群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不断参与构建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青年阶层和青年群体会因人际互动的差异,对原来的青年文化文本进行新解读和新创造,创造和构建带有本阶层或本社群特征的青年文化。这种青年文化文本的传承和构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具体环境和同辈群体互动中进行的,由此形成了同一种青年文化在不同时空和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变异或嬗变。可以说,青年文化的传播过程是经常性的、可反复的,是一种在传播参与中实现不断构建的持续性的文化创造。
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由媒体主宰的文化世界中,青年文化既是人际互动非常强的亚文化,也是更为媒体化和网络化的亚文化。青年文化的生成、发展和传播的角色,不依赖市场化的大众传播,也不依赖以信息控制为主导的层级传播。青年文化可以通过大众传播或层级传播来实现,但更多地是通过人际互动、行为模仿、语言应用、服饰从众、身临其境等方式实现传播。也就是说,青年文化的生成和传播,必然离不开大众传播和层级传播,只是大众传播和层级传播服从和服务于青年群体内部的人际互动传播。“青年在同辈群体交往和虚拟交往中都会使用特殊的词汇、符号和言说方式,而在与成人群体的交往中基本不使用或很少使用流行词语。”[11]青年文化在同辈群体的人际互动中产生和发展,即使是新媒体介入青年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也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加速、拓宽和延展青年群体内部的人际互动和平行传播的角色。青年文化的同辈群体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传播模式,使青年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呈现为一种发散性的多维多点影响模式,决定了青年文化的广泛传播很难依靠类似主流文化的层级传播等方式来实现。
当前,大众文化与媒体文化合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媒体文化的作用下相互融合,导致青年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日渐模糊。青年文化建设的动力和主体是青年,外在力量不应对青年文化建设有过多的干涉。层级传播对青年文化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宜过多地、生硬地介入青年文化的生成与传播,为青年文化的自我组织、自我发展和自我传播保留一定的空间。引导和规范青年文化建设,要充分借助新媒体和青年同辈群体,更多地将主流文化融入青年的日常生活,成为青年的生活习惯,以青年文化的常识化与风俗化路径来推动青年文化发展。
[1][7]达内西:《酷:青春期的符号和意义》,孟登迎 王行坤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1页。
[2]陶东风 胡疆锋:《亚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页。
[3]张 贞:《“日常生活”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4]本书编写组:《青年文化: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5]John Clarke,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In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3,P.27.
[6]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邓文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8]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 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9]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 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117页。
[10]董敏志:《接受与超越:青年文化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11]陆玉林:《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
2015-06-18
邓希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本体和青年现象。
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个人课题“青年文化研究”(课题编号:2014GR0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