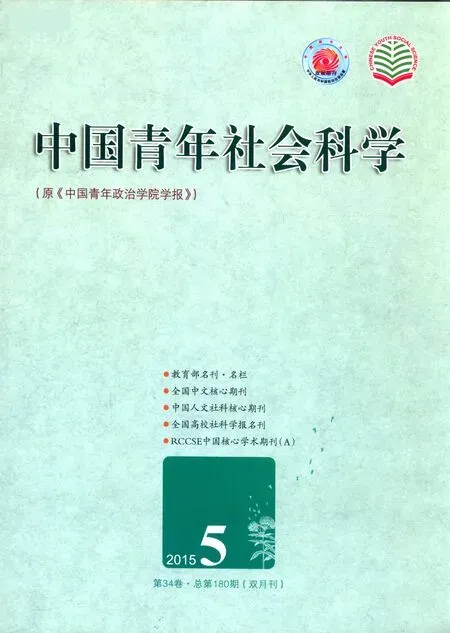“青年学”:百年青年研究的里程碑
——中国青年研究走向世界的若干史实
2015-01-29苏颂兴
■ 苏颂兴
(上海东亚研究所 台港澳青年研究室,上海200070)
“青年学”:百年青年研究的里程碑
——中国青年研究走向世界的若干史实
■ 苏颂兴
(上海东亚研究所 台港澳青年研究室,上海200070)
中国青年研究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中国青年研究的丰硕成果在于几代学人的孜孜以求,而其学科化的建设则更得益于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在学术前沿的互动和思考中与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青年研究百年,代际交替紧迫,唯薪火相传,才能建立并发展好“青年学”,青年研究者要加倍努力,不懈地加强学科建设,让中国青年研究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青年学” 百年青年研究 里程碑 国际交流
一
在中国青年研究走过百年之际,探讨当代中国青年发展与“青年学”学科的建设,不仅具有学术积淀的历史内涵,而且展现了未来创新的时代意义。1915年,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新青年》杂志(首刊名《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至今整一百年。当时,中国正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政治的、文化的现实引起了一批先进人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深思。他们认为要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广泛开展“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说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新青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青年》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创办。在这份刊物上,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倡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号召年轻人做“新青年”,提出“新青年”的六大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某种程度上,《新青年》的创刊也被视为中国青年研究的起点。这不只是因其刊名和办刊的宗旨,也不只是因其内容已经初显对青年的观察、分析和研究,而是《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这个时间节点,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正是西方青年研究开始进入学科化建设的初创期。横空出世的《新青年》杂志顺应了这一现代青年研究学科化趋势的世界潮流!我们知道,在英国工业革命后,劳动者进入职业岗位前出现了不断延长的传习期,就是这个传习期,后来把儿童和青年(青少年)之间原本没有的区分凸现了出来。诚如国际社会学学会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ISA-RC34) 前主席、挪威学者奥拉·斯塔芬森(Ola Stafseng)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利用对青年一般了解上的发展——不再把青年仅仅看作是学童,与此同时,来重构教育和青年研究的关系。”[1]因而许多欧美学者研究了青年(青少年)概念的形成过程,从1904年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的《青春期》到1916年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的“进入汉堡”及其对儿童成长环境系统考察后创作的《发展心理学》为转折点*参见奥拉·斯塔芬森:《从青年概念的角度看青年和福利国家》,王寅通译,载《当代青年研究》,1999年第2期。,集中涌现出一批专著,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学科。
其实,青年研究学科建设更早的奠基人应该是瑞典学者爱伦·凯伊(Ellen Key),1900年她的《儿童的世纪》出版,更早地将普通心理学与儿童、青年研究联系了起来。书名告示读者,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至1990年这本书(今译《儿童与青年》)已有13种文字的版本,仅德国就出了37个版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因此称之为“使她闻名于世”的作品*③④ 参见苏颂兴:《要重视青年社会学史的研究》,载《当代青年研究》,1997年第1期。此文发表时,还未发现《儿童的世纪》20世纪20年代已有中文节译本。,被学界公认为“儿童学”的奠基之作。顺便指出,从青年研究学科化建设的另一个角度来看,Ellen还是欧洲建立第一个青年问题研究机构的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上述研究成果,既深刻反映了社会历史的经验性,阐明了青年是“成长中的人”的基本含义③,同时也标志着现代青年研究学科建设在那个年代的蓬勃兴起。认识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百年青年研究”历史起点的理解。
二
198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建立,使上海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研究的重镇之一。建所初期开展的三项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的青年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一是1983年10月罗马尼亚青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马赫列尔(Fred Mahler)和同事米哈伊(Mihai)在访问北京后顺访上海。Mahler作了青年研究方法论的讲演。他的观点是,既然有“老年学”就应该有“青年学”;但“老年学”研究老年病,而青年人没有病,“青年学”的构建就要完全不同于“老年学”。他还指出,青年研究是跨学科的,“青年学”是一门整合青年问题,即研究其“具体的普遍性”的学科。虽然他的青年研究理论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过多引用西方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在罗马尼亚曾被视为“西化”的典型而受到批判),但不管怎么说,它为我国青年基础理论的研究展现了来自域外以相同意识形态分析问题的新视角。
从学科角度看,黄志坚教授1988年的专著《青年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算得上是第一本专著。因为黄研究的是“青年(Youth)”,而文献检索显示,Key、Hall、Stern及其他西方学者,还包括Mahler,他们论述的是“儿童(Child)”、“青春期(Adolescent)”和“青少年(Juvenile)”。至于Mahler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原著名实为《少年学(Juventologie)导论》,现名使用“青年学”则是译者陆象淦的主意④。即便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在研究中也使用了Youth 一词,也把青年视为一种社会力量,但其基本含义指的还是“青少年期”或“青年前期”;虽然有西方学者也提出了“青年学”的概念,但并没有从学科角度真正为“青年”提供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论据。因此,Ola认为,有别于“青少年期”概念而真正从学科角度提出“理论青年”概念的代表人物,是杜德克(Dudek)教授(1990)*Fred Mahler,An Introduction to Juveniles,Bucharest,Romania,1883.,但其提出的时间要晚于黄志坚教授两年。
二是1984年6月日本青少年研究所代表团(团长千石保、顾问尾中郁夫)的到访。千石先生作了“日本与世界青少年比较”的报告、中村英郎教授作了“日本青年的社会规范意识”的报告,让所有与会学者耳目一新:当代日本青年是“新人类”(言下之意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外星人”)!这是患了“劳动中毒症”的日本老一代人对“追求享乐”青年一代的评价。确实,这一带有强烈“代沟”痕迹的评价,不仅获得了我们的共鸣,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青年研究和社会舆论。作为交流的成果,千石先生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合作项目:当年实施的“中日美三国初中生生活意识”研究,之后通过对“初中生母亲”等历经7年的系列调查,将上述合作拓展为“三国中学生价值观比较研究”大型课题,等等。在合作中,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边干边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一次完整地运用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
三是1988年10月,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瑞典学者尤根·哈特曼(Jurgen Hartmann)的来访。如果说我们以往的对外学术交流都建立在“双边”基础上,那么Jurgen的来访则为中国青年研究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我们第一次与国际青年研究专业机构建立了联系。正是由于Jurgen的来访,1989年5月,黄志坚教授等得以应邀参加在保加利亚瓦尔纳举行的“青年与社会变动”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近三十个东西方国家百余名学者参加,主办方保加利亚青年科学研究所所长安德莱·拉切夫在开幕致词中一再表达了对中国学者到来的热烈而由衷的欢迎。也正是由于Jurgen的这次访问,我们还获邀参加了于199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社会学学会大会。Jurgen表示:“要研究世界青年的问题,有这么多青年的中国不应排除在外。中国的青年研究做得好,必然有益于整个世界。”鉴于我国台湾是国际社会学学会的团体会员,为避免“两个中国”的政治问题,他睿智地建议我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
三
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与中国青年研究学者们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首先,该会为中国青年研究学者开辟了走出国门到国际论坛上进行广泛交流的渠道。1994年7月,第十三届国际社会学学会大会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召开。中国青年研究的老前辈魏久明、黄志坚、谢昌逵、金志堃等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这次会议,分别递交了论文。他们代表中国青年研究学者走进了世界级的学术殿堂。
此前,时任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的Sibylle Hubner-Funk已经和同事们讨论过下届理事会候选人事宜,郑重希望中国学者出来参选,并认为这是推动中国青年研究进入国际青年研究论坛的好机会,中国学者应该在这一国际学术机构内发挥作用。由于Sibylle的力荐,笔者有幸在这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为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副主席(1994-1998),成为Ola Stafeng主席的助手,负责亚洲地区的青年研究。四年后连任,笔者又成为Lynne Chisolm 主席的助手(1998-2002),并在卸任后再任顾问(2002-2010)。除笔者外,曾当选过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副主席的中国学者还有金志堃(上海)、魏雁滨(香港)和沈杰(北京)。更可喜的是,魏雁滨教授还担任过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主席(2006-2010)。这一切体现了各国同行对中国学者所寄予的厚望。此后,来自北京、上海、山东、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广西等省市自治区的青少年研究机构的学者,相继加入了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中国会员达15名之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1998)、澳大利亚布里斯班(2002)、南非约翰内斯堡(2006)、瑞典哥德堡(2010)、日本横滨(2014)举行的国际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大会上,都有中国学者参加并发表论文。
其次,该会为中国举办开放性的青年研究国际研讨会创造条件并给予巨大支持。中国青年研究为亚洲、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离不开国内同行的鼎力协作。我们在上海、北京、澳门先后主办了6届亚洲地区青年问题国际研讨会。每次会议的与会学者除来自亚洲外,更有来自欧美等其他地区的,完全称得上是“国际”的规模,其中有3次研讨会由澳门基金会资助、澳门青年暨教育部门承办。而且每一次亚洲研讨会,国际青年社会学学会的历届主席或带领庞大的代表团与会,或派代表参加,或写信致电祝贺。他们亲自给大会递交论文,给予亚洲学术会议特殊的关注和奉献。
最后,该会积极推动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建设与国际学术发展方向的“接轨”。1993年3月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亚洲青年研究学术研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借国内外学者云集之际,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在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的悉心指导和支持下,于3月29日在上海成立。Jurgen和Sibylle为研究会的成立写来贺信。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作为中国社会学学会下属分会的成立,无疑是百年中国青年研究及其学科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闻此盛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先生也致电表示祝贺;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同志不仅在会后听取了魏久明等学者关于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成立的汇报,而且提出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要积极配合、协调和对相关课题进行分工研究的要求。此后,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先后在北京、上海、江西共青城和浙江舟山等地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
四
国际青年社会学学会的历届主席在上世纪90年代,带给我们许多具有学术前沿性的思考。
高新技术对青年实现社会参与影响巨大。Jurgen Hartmann认为,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结构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只有能够运用蕴藏在与时俱进中的生产力的人或阶级才是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新兴的信息技术打破了国界,青年得以有机会选择个性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其影响必将涉及未来的社会结构。试想现实教育制度仍然让青年在学校里学习过时的东西,试想没有广大青年的积极参与,将不可避免地延缓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因此,青年的动员和投入,将产生创造性的思想和改善生活的机会,由此老一代人将失去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参见尤根·哈特曼:《新技术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谈谷铮译,载《当代青年研究》,1993年第3、4期合刊。。
青年社会参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始终如一的机会。Sibylle Hubner-Funk认为,必须改变社会对青年的认识。“青年”一词在欧洲,具有“国家的青年”和“跨国家的青年”双重身份的含义,性别、阶级、种族、代际矛盾是现代青年的特征。青年作为工业化社会中正在缩小的人口次群体,政府在制订青年政策时,既不要将他们只界定为人力资源,也不能认为他们是危险的因素,而应动员、开发其潜力,真正让他们参与重要的决策*参见西比尔·芬克:《欧洲青年面临的欧洲一体化》,王寅通译,载《当代青年研究》,1999年第1期。。当今社会发展离开了青年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福利的含义必须包容青年这一新贫穷主体。Ola Stafeng认为,欧洲国家的福利思想是二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和平社会要与疾病、贫穷、愚蠢、无家可归、失业这五种社会“罪恶”作斗争。福利思想提出时,“贫穷”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主要是老年人问题,因此,福利的内容仅限于健康、社会保险和养老金,但实际上福利还应包括教育、住房和就业。现在青年首次在统计中成了贫穷的主体,凸现其学业、职业和置业的困境。后者对青年人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对青年不平等的影响更大。机会不平等与缺乏平等机会都包含着经济的、文化的因素。Lynne Chisholm认为,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起着协调社会的作用,但似乎前者有助于决定发展的进程,后者总是维持相对的独立性。因此,要特别注意文化因素比经济因素对青年造成更大不平等的严重性。计算机改变了社会、青年,也改变了人类。Lynne Chisholm认为,在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知识与青年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代青年被迫承受了全球化的沉重代价。Helena Helve认为,全球化(包括网络化)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儿童和青年的安全带来了威胁,如环境隐患、艾滋病、毒品、违反人权、不平等、网络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都有全球化因素的存在。未来我们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变化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世界各地的儿童和青年*参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第六届亚洲地区青年问题研讨会文集》,2004年。。 因此,需要采取各种行动,呼吁各国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保护人权、倡导性别平等、促进安全和发展的社会,把全球化带来的沉重的社会代价尽可能地降到最低水平。
五
作为社会科学院系统的青少年研究所,青少年研究的学科化建设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其建立和存在的价值所在。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给予了我们十分具体的支持和帮助。1993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研究”课题在上海立项,Sibylle 为此专门去慕尼黑大学图书馆找来了德国学者奈特(E·Neter)发表于1906年的世界上第一本研究独生子女的专著《独生子女及其教育》;Lynne主动寄来了其同事的相关研究成果。1996年,“青年社会学”课题在上海立项,Ola 邀请我们访问奥斯陆大学,在那里我们读到了《青年的历史》一书;Ola 还赠送了新版的Ellen Key的《儿童的世纪》。
非常遗憾的是,对中国青年研究怀有极大热情和深厚感情、在1986-2002年间先后担任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的四位学者,因病相继离开了我们。我们缅怀他们对推进中国青年研究及其学科化建设的付出,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学生运动的亲历者,正是那场改变世界的学生运动让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也献给了青年研究事业。他们的离世,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青年研究领域代际交替的紧迫感。
令人欣慰的是,百年青年研究,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薪火相传。世界各国年轻的青年研究学者不断涌现,现任主席、澳大利亚学者Ani Wierenga 正是这一群体中具有创新精神和活力的代表。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今天依然是国际社会学学会内学术活动最活跃、会员队伍最壮大的研究会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曾经为中国青年研究留下深刻足迹的、在社会科学院系统内分别位于北京和上海的两个青少年研究所,相隔近三十年先后被撤销了建制而并入其他研究所。特别是上海青少年研究所,这个两代人为之奋斗的研究机构(在笔者看来终究是因其学科建设的滞后而被淘汰出局),2014年已不复存在。面对在国际青年研究领域至今仍然十分活跃的德国慕尼黑青年研究中心、韩国青少年研究院、日本青少年研究所、伦敦大学Thomas Cram研究所等独立于实际工作部门的青年研究机构,我们感到惋惜和心痛。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众多共青团系统的青年研究机构和学者,仍在青年研究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无论是问题研究还是学科建设都做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已成为中国青年研究领域无可替代的主力。
[1]奥拉·斯塔芬森:《欧洲教育与社会中关于青年研究的历史》,王寅通译,载《当代青年研究》,1997年第6期。
(责任编辑:任天成)
2015-07-09
苏颂兴,上海东亚研究所台港澳青年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原所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原副会长,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原副主席、顾问,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