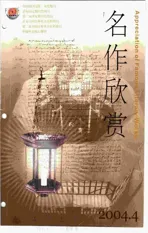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文明”的唯一性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序言
2015-01-28山西林鹏
山西 林鹏
“文明”的唯一性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序言
山西 林鹏
林鹏先生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唯一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林鹏先生在此提出了“文明”的三大标准: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需要“文以载道”,未能“载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唯有“中华文明”曾经照亮历史,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中华文明是“唯一的文明”。
中华文明 文字 文以载道 唯一性
西方在海外扩张的历史大约经历了五百年。由起初欧洲列强轮番兴起的时代,到英、法、德争霸,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超级大国间冷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时期。其间,从大约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的一百年间,逐渐形成了西方扩张主义的理论基础——“欧洲中心主义”,而“欧洲中心主义”则建立在西方的“古典历史观”即“希腊主义”基础之上。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承受来自西方扩张主义的压力,外部世界的侵入,引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震荡。其间,中国文化逐渐从抵御西学的“夷夏之辨”,退守到“中体西用”,最终被“全盘西化”。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向西运动”。“西”者“西学”也,无论“民主”还是“科学”,都是“西学”的表现形式。而“西学”实际上也植根于“希腊主义”。
我们发现,“西学”在起源过程中大量引进了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内容。例如,最初出现于法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概念就来源于中国文化。
现代学术界将“文字”的出现,作为衡量“文明”产生的核心标准。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天下文明”是其用例。“文”指“文字”,指“斯文”。“斯文”者,自尧、舜、禹,经汤、文王、周公至孔子的文化传统之谓也。“明”指“昌明”,“斯文”因“文字”而“昌明”于“天下”就是“天下文明”的含义。这也是“文明”一词的本来意义。
在欧洲,“文明”一词出现于18世纪中期的法语中,最早由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财政部长阿内·罗贝尔·杜尔哥(Anne Robert Turgot)使用。法国在17世纪、18世纪是欧洲传播 “中国文化”的中心,路易十五被称为“中国的皇帝”,法国自诩为“文明”的传教士。
杜尔哥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与源于中国的法国经济学“重农学派”的成员广泛接触,可以说“文明”一词最早由杜尔哥使用,绝非偶然。
欧洲“文明”概念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的是孔子的“斯文”照亮了历史。孔子的斯文传统不仅照亮了中国历史,孔子的理性观念也照亮了欧洲大陆,所谓欧洲“启蒙运动”是也。“启蒙运动”者,以孔子“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神权欧洲”之谓也。
“文字”指书面语言系统,完整的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汉字就是这样一种“文字”,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种起源于上古的、原生的,至今依然在使用的“文字”。西方诸语言的书面记录是一种被称为“拼音字母”的形式,不具备“字形”要素,在“音声”中寻“意义”,算不上是完整形态的“文字”。加以欧洲历史上使用纸张时间甚晚,之前缺乏书面语言的载体,因而到18世纪末才有了“文明”的概念。
此外,我认为“文明”还有另一个标准。
“文明”的“文”是“文字”的“文”,这个毫无疑问。另外,中国还有一个概念,叫作“文以载道”,光有“文字”没有“载道”不行。除了有“文字”,还必须看使用该“文字”记载了怎样的“文献”。
举例来说,埃及“象形文字”其实是图画文字,里面“载”了什么“道”没有呢?西方学者说发现了古埃及的《死者之书》。然而,遗憾的是《死者之书》不仅没有“载道”,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死者之书》这样一本书——该书是19世纪德国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编造出来的。再如西亚地区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等,这类“文书”中根本没有类似中国古代群经、诸子、史籍等各类文献的内容。换句话说,用“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衡量,找不到“道”的影子。没有“载道”就谈不上“文明”。
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是西方学者们在19世纪开始的。与其说是“释读”,不如说是“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而“找到”破译这些文字“钥匙”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愣头青。
法国人商博良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当时三十二岁(1822年),“破译”方法为“猜谜”;首位“破译”西亚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国人,名叫格罗特芬德,当时二十七岁(1802年);而英国人罗林森在二十五岁(1835年)时又一次独立“破译”了楔形文字。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据说是年仅十一岁的儿童。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位法国小伙子“猜谜”的基础之上。格罗特芬德是德国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据传有一次打赌说他能够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琢磨一下就“破译”出来了。罗林森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教授,当时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国年轻军官,出于一时的兴趣就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古波斯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并将其译文及论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世纪这两位欧洲青年,在文字学“形、音、义”三要素中,只顾及字音,模拟假定“音值”,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中若干人名的发音进行比对,用“破译”或“猜谜”的方法,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准确无误”地完全揭示出来,形成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基础。然而,以中国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东方学”可信度甚低;同时,《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是西方早期“东方主义”的刊物,是为英国殖民政策服务的工具,缺乏学术性,不足为凭。其实,在17世纪也曾有过类似方法,不过“破译”对象为“神秘”的汉字。如柏林一位学者缪勒(Andreas Müller)声称于1667年11月18日发明了所谓的“中文之钥”(Clauis Sinica),运用他的“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掌握汉字。当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相信他的大有人在,包括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假设汉字是一种灭绝了的文字,想来一定可以通过“中文之钥”完全“破译”出来。缪勒生前对其“发现”秘不示人,想卖个好价钱;据说临死前将“中文之钥”及其他手稿都销毁了……
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国人于20世纪初(1901年12月)“发现”了一件“世界级文物”,即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该法典碑刻为楔形文字(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体),据说距今约三千七百年,使用语言为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释读方法也是“破译”(而非考释),可“释读”比例达百分之百,现代人能够毫无障碍地释读几千年前语言完全不同并且久已失传了的残碑,其中文字三千五百行,法律条文二百八十二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其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竟然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而且该石碑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领略所谓“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及西亚楔形文字的性质。以考古学常识来说,普通人一看也知道《汉谟拉比法典》是假古董,欧洲学者们硬要将其说成国宝,实在匪夷所思。当代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东方历史”在欧洲原来可以被“如此这般”猜谜、破译、杜撰出来……
15世纪以前欧洲没有文明。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就有这类作品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欧洲的基督教不是原生的“文明”。近代欧洲“文明”是在纸张及印刷术传到欧洲之后才开始的。只有不断更替的不同族群及其所操的不同语言,没有纸张,不能将语言记录下来,如何可能积累文化?没有文化积累的过程,也就不可能有“文明”。
从天下文献源流来说,属于原生的、达到了“文以载道”标准的文明有两支:一支是中华文明,以儒学为代表;另一支是印度文明,以佛教为代表。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原生的中国典籍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而作为印度文明的代表,以1193年最后一座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被伊斯兰军队焚毁为标志,佛教从印度历史上永久消失了。古印度没有统一的民族与语言,佛陀说法使用摩揭陀土语,佛经结集为文字是在佛陀身后,据说最初结集使用巴利文,而汉译佛经则大多来自梵文。古印度原文典籍贝叶书很少流传下来;现存佛教典籍,除少量梵文、巴利文残卷外,大部分以汉文译本及藏文译本的形式被完整保存下来。
有人会说,在佛教之前不是有“吠陀文明”吗?事实上,所谓古印度“吠陀文明”是19世纪初前后出现的概念,也属于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欧洲人在经营印度殖民地过程中,鉴于“古希腊文明”根基浅薄,出于为自己寻觅古老优种“祖先”的需要,虚构“雅利安人入侵”的故事,编造了“印-欧语系”的学术谎言。《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的年代无法确定。据说这类文献起初以“口传”方式流传,形成“文字”的历史甚晚。现存《梨俱吠陀》由“天成体”写成,而“天成体”出现于13世纪初。说梵文在三千余年前一经出现就非常完备,至今没有多少变化,显然违反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将《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断定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的说法出自殖民主义学者马克斯·缪勒的猜测,并无科学依据;后来找出了土耳其波加兹科易(Boghaz Keui)等地据说是公元前14世纪的某些“泥板文书”,说这些“泥板文书”上有“雅利安”君王的名字,用以支撑马克斯·缪勒的立论。由上文所述欧洲人对西亚“泥板文书”楔形文字的“释读”建立在“猜谜”的基础上,可知其对土耳其“泥板文书”内容的“释读”亦缺乏严肃性,不足凭信。
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试举明代文献数端为例,如由皇家所编《永乐大典》(汇集文献七八千种,正文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佛家的官、私刻《大藏经》(少者6300余卷,多者达12600余卷),道教的《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计5485卷)等皇皇巨典,不一而足。其他经、史、子、集四部各类文献,各种典章制度,各家诗词、文集,各州道府县地方志,等等,数不胜数。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大宗遗产。同时期的欧洲,除了写在羊皮上与《圣经》相关的几页“书册”之外,没见到有什么可称“文献”的东西。
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相接触,表现出来的是像“鉴真渡东海,郑和下西洋”那样传播文化、传播和平的“王道思想”;而以“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打着“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旗号的扩张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是“霸道主义”。今天以“西方扩张主义”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表面看来,如今单极世界、一国独大的“霸道主义”横行天下,不可一世;但历史表明,“霸道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可以横行一时,但都好景不长。而以“仁者无敌”理念为基础的“王道思想”则根本不同。“王道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中庸、民本、孝道、仁德、礼让(修养、怀柔、文化)、义利之辨、和而不同、成人之美、扶危济困等核心价值观念。
我认为,与“王道思想”相较量,“霸道主义”终将败下阵来,历史的天平终将向以“仁者无敌”为核心理念的“王道思想”倾斜。换句话说,可以制衡“西方扩张主义”的唯有“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
山西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具有特殊意义。从新文化“西向运动”,到传统文化“向东回归”,到2015年恰好是一百周年。经过百年轮回,人们看到一个古老文明从救亡图存到文化上自我否定,从追逐“四个现代化”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轮回过程。
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本书作者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提出“古希腊文明虚构论”,从源头上系统地揭穿了“西方文化”的假面,揭示出“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者们虚构“古希腊文明”过程的大致轮廓,揭露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作者提出,欧洲近代“文明”来源于中国。无论是西方的“科学”,还是“哲学”“艺术”,其源头都在中国。欧洲在近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为了隐瞒其真实来源,虚构了“古希腊文明”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杜撰了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为其“欧洲中心主义”服务。
本书考述内容尚属初步成果,所提出的论点未必全部成为定论,或者毋宁说本书考述内容是对18世纪下半叶以来“古希腊文明”定论的全面质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人们反思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及五百余年的欧洲历史,彻底解构三百年来的“欧洲中心论”,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使命,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全世界二十六种“文明”的生灭,提出了“中华文明救世论”,近年有人据此提出“中国文明的独一性”。
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文明的独一性”,不如说是“文明的唯一性”,而这唯一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概而言之,“文明”的标准应当是: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需要“文以载道”,未能“载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唯有“中华文明”曾经照亮历史,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西方的“东方主义”与“希腊主义”相表里,一并构成“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核与幔帐。常言道“去伪存真”,佛教云“破邪显正”;在破除虚构的“希腊主义”之际连同邪恶的“东方主义”一并剪除,才能廓清迷雾,彻底解构“欧洲中心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完全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现在应该到了正本清源,以中华文明“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为圭臬,为人类和平乃至“天下太平”(平天下)做出贡献的时候了。这正是“中华文明唯一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4年12月于太原东花园
作 者: 林鹏,生于1928年。学者,书法家,篆刻家。出版有随笔集《蒙斋读书记》《平旦札》《东园公记》,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书法、篆刻专著《丹崖书论》《林鹏书法》《蒙斋印话》《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等。
编 辑:张勇耀 zyy_197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