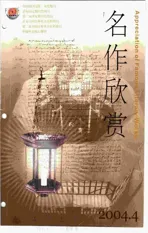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诗经·关雎》解读
2015-01-28山西
山西
刘毓庆 夏展宏
经典重读
《诗经·关雎》解读
山西
刘毓庆 夏展宏
《关雎》一诗,虽然文辞易通,却内涵丰富。解读经文时必须结合当时文化背景,才能读懂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信息。如诗中提到的“河洲”,实际上是古代水隔离制度的反映。“河洲”环之以水,应为如辟雍、泮宫之类的女性学宫,是周代贵族女子进行婚前性隔离教育的地方。“琴瑟友之”是恋爱方式,“钟鼓乐之”是成婚方式,然皆为幻境,非实境。此诗为乐新婚之歌,寓有教化意义,应从“诗”和“经”两方面进行解读,方得其正。
《关雎》 性隔离 新婚乐歌 两种读法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因此备受人们关注,历代对它的解释歧说之多,也超过了其他篇。这首诗被选入了中学与大学教材中,所以原来被忽略的诸多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必要。虽然诗篇没有什么难懂的词语,但要彻底读懂却不容易。比如:为什么说“在河之洲”?这与《蒹葭》之“宛在水中央”,《汉广》之“汉之广矣”“江之永矣”,《竹竿》之“淇水在右,泉源在左”等,有无关系?为什么这些诗写男女之思,总要写到隔水相望?“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什么意思?难道真如今之时髦男女弹琴击鼓欢乐起舞吗?要解决这些问题,须费一番周折。
关于“在河之洲”
要弄清背景,必须在获得大量上古文化信息的前提下进行。近世学者,特别是20世纪的《诗》学研究者,往往对《毛传》及汉儒有极大的偏见,故对他们的解释弃而不用,敢于另创新说,以惊世骇俗。汉儒之说,确有比附、牵强之处,但同时应该注意到,《毛传》及汉代人对于周代民俗生活的了解,远比我们多。关于上古的信息,他们可从三个渠道获得:一是文献,他们所见到的上古文献远比我们多;二是上古传闻,他们毕竟去古未远,上古传闻还大量存在;三是原始礼俗,有一些较原始的礼俗在汉时还残存着。而我们现在却只有一个渠道:文献,最多加上残篇断简的出土文献。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有较多的发言权。尽管有时他们对上古历史只是如雾中看花一样,并不十分清楚,但毕竟能看到雾中有花。因而对于汉儒之说,我们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无论是对是错,尽量找到他们立说的理由,从而从根本上肯定或否定他们。就此诗而言,《毛传》及汉儒之说主要有四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是他们把“淑女”与后妃联系起来,即《诗序》所谓“后妃之德也”;二是将河洲与“淑女”居处联系起来,即《毛传》所谓“水中可居者曰洲”,《韩诗章句》所谓“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洲隐蔽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①;三是将诗与男女之别的礼俗联系起来,即《毛传》所谓“若雎鸠之有别焉”;四是将“左右芼之”与祭祀联系起来,即《毛传》所谓“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解释?显然这里携带着一些远古流传下来的信息。
“河洲”“有别”“事宗庙”等,我们把这些关键词联系起来,便会发现,诗篇是与周代的性隔离教育和婚礼仪式相关联的。据文献记载,贵族女子成年期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婚前教育,时间短则三个月,长则不定。《礼记·内则》说:“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这是说,女子十岁前不出家门,在家学习妇德、妇功及礼仪之事。十岁之后是否可以出门就教呢?没有说。妇师被称作“姆”,字又写作“娒”。《说文》:“娒,女师也。”《仪礼·士昏礼》注:“姆,妇人年五十无子,出而不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妇师又称妿,《说文》:“妿,女师也。”又称师氏,《毛传》云:“师氏,女师也。”姆、妿与师氏,是否是不同性质、不同时段女师的名称呢?这不敢说。但《仪礼·士昏礼》的一段记载,则颇值得注意:“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若祖庙已毁,则教于宗室。”《礼记·昏义》也有同说。这里所特指的是士的女儿的婚前教育,而不是《内则》所说的十岁前的教育。这种教育,自然是要与男性隔离的。士的女儿受教育的地方是“公宫”或“宗室”。公宫、宗室何指?孔颖达有如下一段考证:“‘祖庙未毁,教于公宫三月,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昏礼》文也。彼注云:‘祖庙,女高祖为君者之庙,以有缌麻之亲,就尊者之宫教之。’则祖庙未毁,与天子诸侯共高祖者,则在天子诸侯女宫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宫者,以庄元年《公羊传》曰:‘群公子之舍(何注:女公子也),则以卑矣。’是诸侯之女有别宫矣。明五属之内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则大宗者继别为大宗,百世不迁者,其族虽五属外,与之同承别子者,皆临嫁三月就宗子女宫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宫者,《内则》云:‘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则女子亦别宫。故《曲礼》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门’是也。”②所谓“女宫”,就是指贵族女子的“别宫”。这种“别宫”形制,今天我们已全然不知了。据《礼记·文王世子》,“公宫”包括了太庙在内的所有王侯宫室。故陈澔《礼记·昏义集说》云:“公宫,祖庙也。”③以为女性教育在祖庙中进行。方苞亦云:“宗室即别子庙也……如宗子为庶人而无祖庙,则卿大夫之女当教者,其家可久舍乎?又或有同时而教者,其家能兼容乎?惟大宗之庙未毁,然后可各止于旁舍,而并教于宗室耳。”④方苞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将女子受教之地固着在祖庙,也未必为是。根据《仪礼》所言,诸侯大夫之女当有学宫或固定的性隔离教育之所,这样士的女儿才有可能在出嫁前就其地而教之。这种属于“公宫”“宗室”的地方,或许就是辟雍、泮宫之类。
关于辟雍、泮宫,《礼记·王制》中有一段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这是说在周代,大学分两级,“国家”级的叫辟雍,地方级的叫泮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学”的形式,周围都有水环绕。杨宽先生《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一文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他认为,辟雍所以称辟,就是表明其形状如璧。“雍”和“邕”音同通用。“邕”是环于水中的高地及其建筑。“雍”字在古文字中,从巛、从邑、从隹。从巛,象四周环绕有水;从邑,象水中高地上的宫室建筑;从隹,象有鸟集居其上,因为辟雍和泮宫的附近有广大园林,为鸟兽所集。泮宫的结构也和辟雍差不多。⑤从杨宽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出,辟雍是很大的,周围有水环绕,附近有广大的园林,有鸟兽居集,水中有鱼。这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湖泊中间有洲的形式了。班固《辟雍》诗有“造舟为梁”之说,这样大的规模,它的水泊很难说纯粹是由人工开掘的。从《大雅·灵台》的描写看,辟雍显然是选择水泽之地而构成的建筑。吕思勉先生云:“盖我国古者,亦尝湖居,如欧洲之瑞士然,故称人居之处曰州,与洲殊文,实一语也(洲岛同音,后来又造岛字)。以四面环水言之则曰辟,以中央积高言之则曰雍。斯时自卫之力尚微,非日方中及初昃犹明朗时,不敢出湖外,故其门必西南入。”⑥这是说环水建构的“学宫”形式,乃是古老的居住模式的沿袭。问题在于:为什么作为学宫的辟雍、泮宫,却要环之以水呢?而且这样的学宫,究竟只是男校,还是同时也有女校呢?
从杨宽、吕思勉先生的考证可知,辟雍、泮宫皆在水畔河洲之地。《关雎》中的“河洲”,正是这样的地方。汉儒解“辟”为“璧”,以为是像璧玉一样的圆形水池;解“泮”为“半”,认为是璧之一半,因半边有水,故谓“泮”。其实“辟”与“泮”都当是分别、僻远的意义。《淮南子·修务训》注:“辟,远也。”《楚辞·离骚》王注:“辟,幽也。”“幽也”“远也”,皆有僻远、与世分离的意义在内。从“辟”之字亦多有分离意,如劈,从刀,意为用刀将物分开;避,从辶,意为回避;壁,从土,意指墙壁,为隔离物,可避开风雨;幦,从巾,意指覆盖在车上,以遮避日晒雨淋之物;擘,从手,意为用手剖开物;僻,从人,意为远离人在之所,即偏僻;闢,从门,意为将合着的门分开。半,《说文》云:“物中分也。”从“半”之字,亦每每有分开之意。如判,从刀,意为分开;畔,从田,意为将田地分开的田界;姅,从女,指女人月经,须与男人分开。由此观之,“辟雍”“泮宫”意即“别宫”,实际上就是性隔离教育的地方。既然是性隔离,必然是兼男女两性言之的。虽然我们不敢说辟雍、泮宫就是女性学宫,但有理由猜测三代时存在过的女性学宫,应当就是辟雍、泮宫之类的地方。或男女两性的学宫,皆可以辟雍、泮宫名之。《白虎通·辟雍》说:“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恐渎也。又授之道当说极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所谓“阴阳夫妇变化”,实即性的问题,故父子不能相授,且男女只能分开进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辟雍与原始性隔离的关系。“在河之洲”,所指正是河洲之上的女性学宫。故下言“窈窕淑女”,“窈窕”所状正是女宫之貌。苏辙释《关雎》云:“在河之洲,言未用也。”⑦“未用”即指未嫁。苏辙的解释虽未必有什么根据,但他却以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了诗中的奥秘。
关于上古的女性隔离,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民族的习俗中获得旁证,这似乎是人类早期普遍存在过的一种制度。根据人类学的调查,许多原始民族女性成年期要举行成年礼,且伴着性隔离进行。中非地区性成熟的女孩,在隔离期间,就有人教给她们将来该干些什么。⑧赞比亚女子的成年教育,是被隔离在丛林隐蔽之处的小屋里进行的,隔离期有的长达十个月。⑨利比里亚的尼格罗人,在结婚之前,少男少女们要分隔为两个“咒森”,这可以看作一种准备结婚的寄宿塾。少女的咒森设在部落附近的森林里,女塾中的教师由年老妇女担任。少女十岁入塾,一直在里面寄宿到结婚。女咒森中,绝对不许男人入内。少女在这里学唱歌、游戏、舞蹈、咏诗。男咒森性质与之相当。⑩新几内亚的基米人,凡满婚龄的姑娘,往往聚集在一间圆形茅屋内,接受婚恋教育,由已婚的中老年妇女任教。⑪在民族志中我们看到了不少女性成年期隔离教育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女子隔离教育时间的长短,是与她的家庭地位、经济条件相随的。越是大户人家,女子隔离教育期就越长,越讲究礼节仪式。根据这种情况推测,士的女儿婚前教育是三个月,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女的教育期,恐怕要远长于此。
总之,女子婚前教育是完全与男性隔离开来的,隔离的地方一般在水洲或二水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古列女传》言简狄浴于“玄丘之水”,或作“旋丘之水”,即古代类似辟雍的地方。因此,在此期间,即使男子爱上了女子,也只能是隔水相望,而不能渡水求爱,因为那是违反礼的。诗中所言的“河洲”就是这样的地方,所以汉儒说是“隐蔽乎无人之处”。因为是隔离生活,所以秦汉儒者将此与男女之别的礼俗联系了起来;又因为在周代只有大贵族之女(即王妃或诸侯夫人之类人物)才能严格地遵循性隔离的古礼,而且“窈窕”深宫,也只有贵族才有条件居住,琴瑟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所以《诗序》将“淑女”与后妃联系了起来。女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教育之后,要举行成年礼,进行祭祀。像《汉广》《蒹葭》《竹竿》等都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⑫据此,《关雎》乃是基于这个背景而产生的情歌。歌中的故事内核是写一位贵族男子(或即王子)对“窈窕淑女”之爱,故而抒写其单思、相爱、成欢的情怀。此即其本事。所谓“关关雎鸠”,乃是以雎鸠的求鱼,以象征男子的求爱,并非是以雎鸠和鸣比喻男女之爱,因为雎鸠是鹗鸟,凶猛异常,比喻温柔之爱,实在不类。
关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关于“琴瑟友之”,郑玄以为此与以下的“钟鼓”皆言祭祀用乐,似不甚妥。日本冢田虎《冢注毛诗》曰:“求淑女而得之,则如琴瑟相和,将以友之也。”⑬又言下章曰:“得而友之,则如钟鼓相和,将以乐之也。”⑭以琴瑟、钟鼓为比喻,恐亦非。此当指“琴挑”。胡适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言及《关雎》篇时说:“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有什么稀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至今中国的苗民还保存这种风俗。”⑮此说颇有见地。《风俗通义·声音》篇曰:“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非必陈设于宗庙乡党,非若钟鼓罗列于虡悬也。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文选·长门赋》注引《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太平御览》卷五七七引扬雄《琴清英》曰:“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嬖,去邪欲,反其真者也。”《白虎通·礼乐》篇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乐府诗集》卷五七《琴曲歌辞》:“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白虎通·礼乐》篇引《诗传》曰:“大夫士琴瑟御。”又曰:“瑟者,啬也,闲也,所以惩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据此可注意者有二:一、琴瑟为上古贵族男子携带之物,特别是琴,无故不去其身,可能这本身就是其高贵地位与有教养的标志;二、琴瑟皆有禁邪防淫的功能。所谓禁邪防淫,当是指禁防不合于礼的行为,特别是爱情行为。此当是上古人的观念,君子御琴瑟与禁邪防淫是相联系的。在初民社会,男女之间的求爱方式多种多样,《诗经·将仲子》所言越墙幽会私通者,即孟子所谴责的“越东墙而抱其处子”,是一种野蛮的方式。而以琴瑟传递爱情信息,则是一种文雅的恋爱方式,且合于当时的礼俗即道德规范,流行于上流社会中。《白虎通·礼乐》篇曰:“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周礼·大司徒》注曰:“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乐所以荡正民之情思,而使其心应和也。”男女相思,发之于琴瑟之声,不为鲁莽之行,此即礼乐防淫之谓。《拾遗记》卷一记神话中少昊、皇娥之恋曰:“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依瑟而清歌……”《郑风·女曰鸡鸣》篇言男女之相亲昵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小雅·常棣》篇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皆可证琴瑟之意义所在。当今一些民族中,也时可见到以音乐传情相爱的习俗。如布依族青年,常用弹月琴的方式邀请姑娘“囊哨”(谈情说爱)。林谦光《台湾纪略》记土人风俗:“男在外吹口琴,女出与合,当意者告于父母,置酒席邀饮同社之人,即成配偶。”⑯《苗族调查报告》说:“苗族之婚姻,为自由结婚,男子于所恋女子之屋外吹笙,发美妙而有趣之音节,如能使女感动,则为夫妇。又于踏月吹笙之夜亦行之。”⑰此外,菲律宾不少男青年在月光下用吉他向他倾心的姑娘求爱;缅甸钦人中,小伙子们常用竹笛向姑娘求爱。在汉族中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张生琴挑崔莺莺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小说《万锦情林·张于湖记》《西湖二集·邢瑞君弹琴遇水仙》《春莺柳》《刘生觅莲记》《意外缘》《梅兰佳话》等,戏剧《竹坞听琴》《东墙记》《玉簪记》等,皆以琴为爱情使者,将相爱的男女结合在一起。此皆可为“琴瑟友之”的注脚。只不过琴瑟之恋,在上古为守礼节情之行,而在后世则为风流佳话。此自然是观念变化的结果。总之,“琴瑟友之”乃是指恋爱方式,与上“采”之相呼应,“采”表示采到了手,“友”表示求到了手。
“钟鼓乐之”则大不相同了。古钟用青铜制成,钟悬挂于架上,以槌叩击发音,西周时主要用于庙堂祭祀。从今人所发现的两周钟铭可知,西周钟多为乐神所用,不用于乐人,西周晚期以后始有“以乐嘉宾”之类的钟铭。此诗所说的“钟鼓乐之”,应当是成婚时在宗庙祭祀的情景。古婚礼,妇入夫家,三月后要到家庙中祭祀先人。《白虎通·嫁娶》篇说:“妇入三月,然后祭行。舅姑既没,亦妇入三月奠采于庙。三月一时,物有成者,人之善恶,可得知也。然后可得事宗庙之礼。曾子曰: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也就是说:三月祭庙之后,婚礼才算完成。如果不到三月,新妇意外死亡,还须把她的尸体运回娘家,因为她还不算是夫家的人。
从内容看,这也应当是乐新婚的乐歌。今湖北一些地方婚礼仪式中仍有活用此诗者,如云:“关关雎鸠进新房,在河之洲看新娘。窈窕淑女生贵子,君子好逑状元郎。”“关关雎鸠一块屏,在河之洲两个人。巧言令色真好看,君子好逑做夫人。”“关关雎鸠在两旁,在河之洲陪新郎。窈窕淑女容貌好,君子好逑为新郎。”“关关雎鸠进房来,在河之洲两帐开。窈窕淑女床上坐,君子好逑撒起来。”⑱陈戍国先生有《说〈关雎〉》一文,举十六证,力主古时婚礼不用乐,《关雎》非贺新婚诗,其说甚辩。但《礼记·曲礼》有“贺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之文,又曰婚礼“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说明婚礼还是可以贺的。我们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嫁娶的诗,如《桃夭》《鹊巢》《绸缪》《何彼矣》《车舝》等,以及《大明》篇写文王之迎娶,所表现出的都是一片欢乐气氛。如果说因“思相离”“思嗣亲”,而以乐事为丧事,这无论如何也是于理不通、于情不顺的。我们认为所谓婚礼不用乐,应该是有时间规定的,并不是一直不用乐。《礼记·曾子问》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这就是说,在迎娶的三天内不用乐,三天过后是完全可以庆贺的。因此,以此为贺新婚之诗歌未尝不可。
《关雎》的两种读法
《诗经》既是诗,又是经,故当从“诗”与“经”的两个不同角度来解读。今人重在解诗,古人重在解经。从诗的角度看,这是一首爱情诗,首章写“艳遇”,二章写“求爱”,三章写未得之苦,四章写相恋之欢,五章写既得之乐。主题即如《诗序》所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为了表现君子淑女相得之乐,诗中虚设了一种情景,即在美丽的河洲水畔,一位贵公子隔水望见了一位端庄娴雅的小姐。他一见钟情,于是害了相思,但又无法马上得到她。刻骨铭心的思念,使他“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终于在幻境(或梦境)中得到了满足。他以弹奏琴瑟,传递他对女子的爱,如同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一样,最终得到了对方的爱情。他们完婚了,举行了庙见礼,在庙见礼上钟鼓齐鸣,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后两章即是对幻境的描述。此诗之妙在于入“山穷水尽”之地,忽逢“柳暗花明”之景。既感“求之不得”之苦,忽又现琴瑟钟鼓之乐。转悲为喜,化忧为乐,于幻境中完成了恋爱、结婚的乐事,可谓绝处逢生。但这“生”,绝不是一般的“生”,而是对苦闷现实的超脱,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戴君恩《读风臆评》说:“诗之妙全在翻空见奇。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作实境,便是梦中说梦。”⑲可谓善会诗义。人或不明,故疑为错简。
前人对此诗有诸妙评,今摘录几则于下:
明贺贻孙《诗触》卷一:“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四句,乃诗中波澜。无此四句,则不独全诗平叠直叙,无复曲折,抑且音节短促,急弦紧调,何以被诸管弦乎?忽于“窈窕淑女”前后四叠之间插此四句,遂觉满篇悠衍生动矣。此即后人所谓诗中活句也。⑳
明陈元亮《鉴湖诗说》卷一:二章。“流之”,是未遇荇菜时,景象无定。“寤寐思服”“悠悠”是未得淑女时,意象无定。“寤寐求之”,总括下“求之不得”四句。“求之不得”四句,只足上“寤寐求之”一句。寤寐中如何求?只是想象其“得”之意。“不得”,谓洽阳谓涘已有其人,而“文定”未行时也。“辗转”句正形容一“悠”字,“悠哉”句正形容一“思”字。
又:盖荇菜则“采”之而又“芼”,淑女则“友”之而又“乐”。喜乐尊奉之意有加无已,自不觉其言之再耳。“友之”“乐之”,只自家友乐淑女之情,借琴瑟钟鼓以写之,非真对其人以奏之也。㉑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一:(三章)前后四章,章四句,辞义悉协,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遽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着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故此当自为一章,若缀于“寤寐求之”之下,共为一章,未免沓拖矣。且因此其一章为八句,亦以下两章四句者为一章八句,更未协。㉒
清高侪鹤《诗经图谱慧解》卷一:通诗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尽之,然言不尽意,故二章写出未得时忧思宜如是,三章、四章写出既得时喜乐尊奉又如此。二章形容忧思处,千回百转写出;三四章欲形容“乐”字,不轻易递过,作两层写出,情致深长。㉓
清李诒经《诗经蠹简》卷一:以“辗转反侧”四字形容彻夜不寐,极编凑,却极工妙,后人再不会如此写法,亦再不会如此炼法。㉔
清邓翔《诗经绎参》卷一:“流之”“求之”,文气游衍和平,至第五句,紧顶“求”字,忽反笔云“求之不得”,乃作诗者着意布势,翻起波澜,令读者知一篇用意在此。得此一折,文势便不平衍。下文“友之”“乐之”乃更沉至有味。㉕
《关雎》一诗真实地表现了先民的生活情趣、性格及心灵。诗中的男子,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古代男性青年的形象。他执着地追求“窈窕淑女”,为之神魂颠倒,“寤寐思服”;但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他苦闷,他悲伤,可他没有消沉,没有堕落,也没有像希腊神话中的山林大神那样,不顾女神绪任克斯的拒绝,追逐着去拥抱她,而是用美好的幻想,解脱失恋的苦闷,求得心理上的满足。即使在幻想中也是那样有分寸,只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已,表现得那样有修养、有风度。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就是这种精神。在中国度过二十多年传教士生涯的美国人史密斯曾经这样说过:“纵然他们的环境明显无望,也不显得失望,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似乎是在做无望的挣扎,时常反对抱有希望。特别是19世纪末叶,大多数其他民族都有一种躁动不安的特性,在中国人当中却没有觉察这种特性。”㉖是的,中国人不浮躁,不失望,他们富于理想,富于感情。这感情受着理性的制约,这理想受着感情的驱使。对于现实,他们不是在激情的冲动下奋斗、竞争,而是在希望的岸边,呼唤并等待着彼岸船只的到来。他们的心地太善良了,不愿意把现实想得太糟,总是以美好的愿景安慰创伤的灵魂。他们能够忍受一切痛苦,很少想着去发泄。感情、精神上的折磨尽管是猛烈的,但只要想到“窈窕淑女”,想到“钟鼓乐之”,便一切都坦然了。这便是《关雎》对待人生的态度,也是民族性格最充分的表现。这性格,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在苦难中顽强地生存、挣扎,在世界性的狂热中保持冷静与稳定。有悲怨,但少愤怒;有牢骚,但少批判;有欢乐,但少狂欢。每个人都有一身“克己复礼”的硬功夫。这既是我们的优点,也是我们在世界性大竞争中处于落后位置的一个原因。这种克制,有利于和平环境的维持,而不利于物质利益的获取和科技的高速发展。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价值判断是以经济发展为尺度的,而中国人的这种文化性格,自然影响了民族的经济发展。于是在20世纪,这种文化遭到了来自本国青年的攻击和批判,认为民族是处于不冷不热的“温吞水”状态中,“温柔敦厚”不客气点说,就是“半死不活”,是要不得的。但要清楚,中国民族文化,能在世界上成为唯一一种延续数千年而不间断的文化,其中是否有更多的合理性存在呢?人类的发展并不只是科技的进步,甚至科技进步只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是外在于人的工具的发展。真正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性的发展,是人类野性的消解与善性的增益,是人类精神向道德之域的不断提升。人类需要和平,需要安定,需要从性格中彻底消除争斗与暴行的因子。而“温柔敦厚”,不正是人类和平存在的依据、人类精神提升的良药吗?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本诗以雎鸠起兴的问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此诗是以雎鸠鸟雌雄和鸣象征温柔的爱情,可是《尔雅》《毛传》以及早期的文献都说得很清楚,雎鸠就是王雎,王雎是食鱼的鸟,很凶猛,用来象征爱情实在不相类。同时在《诗经》的时代,我们没有发现以鸟喻夫妻的证据。日本著名的《诗经》研究专家松元雅明先生就曾说过:就《诗经》来看,在所有的鸟的表现中,以鸟的匹偶象征男女爱情的思维模式是不存在的。㉗不仅在古籍中没有,在春秋前的古器物图案中,也难找到雌雄匹配的鸟纹饰。在良渚文化遗物及金铭图饰中,出现有连体鸟型器物与双鸟纹饰,但那多是为对称而设计的,并看不出雌雄相和的意义来。自从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诗经》中的鱼及食鱼的鸟做出男女求爱隐语的解释后,学者们才开始有了新的考虑。孙作云先生在《诗经恋歌发微》中,提出了《关雎》以鱼鹰求鱼象征男子向女子求爱的观点。赵国华先生《生殖崇拜文化论》在此基础上,对上古时代诗歌及器物图案中的鱼、鸟做了全面考察,认为鸟与鱼有分别象征男女两性的意义,并进一步认为雎鸠在河洲求鱼,乃是君子执着求爱的象征。这一解释可以说是基本正确的,从而改变了《关雎》雎鸠喻夫妻的单一诠释方向。
从经学的角度读诗,关注的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关雎》作为《诗经》的第一篇,而且自古即把此篇的内容与后妃之德联系起来,编诗者自然有特殊的考虑。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把此篇居首的意义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他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韩诗外传》卷五记孔子与子夏的对话说:“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像这样巨大的意义,我们今天已很难感受到了,但敢肯定,古人的这种领悟一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古今大略相同的认识有两点:第一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得“性情之正”。这也是《诗经》作为经学所十分强调的一点。男女之情乃人道之常,如果没有了这种情,人类就有可能绝种,因而绝对不可没有。但人与动物之别在于人的这种情是有道德制约的,不能放荡不羁,这就是所谓止乎礼义。《诗序》说:“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先王之泽”,就是指先王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制约着人的行为,使人把握着爱情的尺度。《关雎》篇所表现的爱情故事,就是非常有分寸、合于情礼的恋爱进行曲。孔子对《关雎》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评价,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乐”,是指君子淑女相得之乐,“不淫”,是指虽欢乐但不过度(淫者,过也)。“哀”,是指未得淑女时的忧思,“不伤”是指不为过度忧思而伤神。人在恋爱过程中,“乐”与“哀”都是很正常的,《关雎》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正常的情感,所以说是“得性情之正”。有相当多的年轻人,为了爱情,要死要活,背弃父母,背弃家庭,乐则相吻于闹市,哀则自杀于密室,这则是“乐而淫,哀而伤”,大背人道之正。对此而言,《关雎》自然是有表率意义的。
第二是正夫妇的意义。《关雎》表现出的是一种和谐的爱情关系,《毛传》说“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虽然“后妃”“君子”之说不见其是,但那种“无不和谐”的气氛却是可以感受到的。《诗序》所谓“风天下而正夫妇”,就是希望化此成俗,让天下夫妇皆能如《关雎》之人。“夫妇正”,这是根本。《毛传》说:“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这是古人的逻辑。日本学者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说:“龚遂曰:《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是也。然举其要,则《二南》为之本。举《二南》之要,则《关雎》一篇为之本。其所以为本者何?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推及于国,及于天下,莫不被熙皞之化者,由此道也。”㉘夫妇正了家道就可以兴,家兴了国就可以治,天下也就可以安。风俗归于淳厚,民皆敦于孝敬,这无疑是人所共盼的,也是《关雎》作为经要承担的文化责任。
①〔清〕陈乔枞:《韩诗遗说考》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页。
②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③〔元〕陈澔:《礼记集说》,《四书五经》中册,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325页。
④〔清〕方苞:《仪礼析义》 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
⑤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页。
⑥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47页。
⑦〔宋〕苏辙:《诗集传》卷一、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6页。
⑧〔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0页。
⑨任巍、刘冰主编:《风俗奇观》(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⑩朱云影:《人类性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8—90页。
⑪刘玉学:《世界礼俗手册·亚太地区卷》,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⑫刘毓庆:《中国文学中水之神话意象的考察》,《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
⑬⑭〔日〕冢田虎:《冢注毛诗》卷一,无穷会图书馆藏宽政十年写本,山西大学国学院资料室复印本。
⑮胡适:《谈谈〈诗经〉》,顾颉刚等编著:《古史辨》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页。
⑯〔清〕林谦光:《台湾纪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1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8页。
⑰〔日〕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1926年译。
⑱方培元:《楚俗研究》,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⑲〔明〕戴君恩原本,〔清〕陈继揆补辑:《读风臆补》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⑳〔明〕贺贻孙:《诗触》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
㉑〔明〕陈元亮:《鉴湖诗说》卷一,万明刻本,山西大学国学院资料室复印本。
㉒〔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㉓〔清〕高侪鹤:《诗经图谱慧解》卷一,清康熙间著者第三次手稿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㉔〔清〕李诒经:《诗经蠹简》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叁辑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页。
㉕〔清〕邓翔:《诗经绎参》卷一,同治丁卯孔氏藏版,山西大学国学院资料室复印本。
㉖〔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㉗〔日〕松本雅明:《诗经诸篇の成立た关する研究》,日本东京东洋文库昭和33年版,第55页。
㉘〔日〕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卷十一,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刊本,山西大学国学院资料室复印本。
作 者: 刘毓庆,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先秦文学、诗经学、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夏展宏,山西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编 辑:张勇耀 zyy_197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