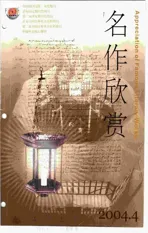素描,最有力量——读雷达散文《黄河远上》
2015-01-28甘肃杨光祖
甘肃 杨光祖
作 者: 杨光祖,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文化学教研室主任。
从事文学批评十多年,读了很多作品,也读了很多文学理论著作,越来越服膺老子的四个字:道法自然。我认为,自然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我很反感那种炫技的文字。朋友春生说,马原、格非1980年代的那些先锋之作,现在看还是很轻飘。我喜欢杨显惠的三个“纪事”,就是因为它的自然、朴素,而大力量、大艺术正来自这种自然、朴素。
雷达是从甘肃走出去的大批评家,他文字里的那种风骨、那种硬朗,就是这片土地给予他的。他早期的散文大气、雄浑,真有《史记》那样泥沙俱下的气概。众所周知,雷达是以评论立身扬名,其实,他的散文也很优秀,而且他的很多评论本身就是美文。通读他以前的全部散文,我还是感觉到一丝遗憾,总是感觉在语言上略有生硬,写作之中藏藏掖掖,不是很过瘾,比如《还乡》《皋兰夜语》。不过,隐隐之中觉得他散文创作的空间还很大,应该还能写出更好的散文来。多年前,我给他写信,建议他应该减少评论的写作,而专力于散文创作,尤其是自传体的散文。他回信说,兹事体大,容慢慢考虑。
去年,他说,他要写一组西北往事的散文,在《作家》连载,希望我关注。我的单位没有订这份杂志,无法看到文章。后来从他的博客,还有别的地方,看到了他写妈妈的一篇《多年以前》,文章前半部分真情写来,动人心魄,其中写到母亲和自己的痛苦经历,让人泪下。父亲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日子极其艰难,备受他人的欺凌。“每当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姐姐到兰州农校后面的旷野地里,面对黄昏时苍茫的皋兰山时,我就害怕极了,我预感到母亲又要哭了。果然不一会儿母亲大放悲声。对她,也许是生活重压下的一种宣泄吧。那是我童年最恐惧的时刻,父亲离开的那个傍晚的恐惧也在这时一并袭来,我不由浑身颤抖。”
但是,我感觉《多年以前》依然没有完全放开,很多东西藏了。他似乎还是有点怕,不敢碰似的,文章后半就躲避了,开始引用了别人的文字,仓促结束。《新阳镇》写的是他的老家和老家的人,《新华文摘》也转载了,粗读之下,略觉琐碎,仍然觉得无法代表他的最高水平。不过,其中大嫂的形象极为感人。
2014年7月26日夜,在微信上偶然读到了他的新作《黄河远上》,写他少年时在兰州的日子,很长,万字吧。我细细地读完了,唯一感觉是:无语,隐隐之中有一种大力量穿透了我。给雷达老师发了一个短信:这是一篇杰作,其水平可能在您的《皋兰夜语》之上。我认为,在这篇散文里,他终于打开了自己,没有顾虑,没有忌讳,真实地书写了一个少年成长中的内外压力、隐痛以及受到的伤害。雷达给我短信说:“也想还原西部历史人心的真实。全真实的,包括每个细节。”
《黄河远上》不仅是雷达的散文代表作,也是当下中国散文界难得一见的有风骨的文字,既有历史的苍茫感,也渗透着个体的生命体验。文字较之雷达以前的散文,更加精练,更加丰富,更加有一种人世沧桑。读这样的文字,我不由想起了一个古语:人书俱老。也想起了杜甫的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雷达以前有一篇写兰州的名文《皋兰夜语》,我觉得《黄河远上》一文,不下于《皋兰夜语》,甚或超之。
鲁迅说,中国多的是瞒和骗的文学。此话虽然刻薄,但却极有道理。这也就是中国很难产生大师级作家的一个原因,因为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做不到坦诚,都在假声写作,都在装腔作势。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就有这个毛病,猛一读,似乎很有文化,文词也颇华丽,但经不起反复阅读。因为,他不真实。《黄河远上》,可以说是一篇“将内心呈现出来”的散文。这是中国作家很难做到的。鲁迅、张爱玲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敢于揭开自己的内心。鲁迅说,我严厉地解剖别人,但我更严厉地解剖自己。他的《呐喊·自序》就是一篇解剖自己的散文,每次读之,都心魂几惊。我曾在《雷达论》里说过,雷达写评论,就好像走钢丝,极其小心。其实,他写散文,也很小心,他内心的很多隐痛,不敢深度去碰。但这次他开始撕开写了,越写越好。他敢于直视自己早年的创伤,这是散文的最高品质:真实。
《黄河远上》开篇就是1949年的兰州战役:“我六岁那年,1949年8月,亲历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最著名的恶战与决战——兰州战役,其时我只是一个孩童,却始终没有远离火光硝烟的现场,亲见了尸横街头,血流如注,这也算我人生的一大奇遇吧。与我经历相似者恐怕少有。”甚至,他在农校的操场上玩,差点被国民党的飞机扫射而死。“我在路边,望着 ‘垛’满人肉的卡车,一路滴血而来,缠满绷带的血头颅和断了手脚的白骨一起撑在车外,血红撕拉地赫人。接着的几天,马步芳最精锐的骑兵日夜不息地绕皋兰山转移,不时有马匹与人从高山上滚落下来。”对一个六岁的孩童来说,这样的遭遇太过酷烈。
兰州战役,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出来,既残酷,又真实,这是我第一次阅读真实的兰州战役的回忆文字。“8月26日清晨,天亮了,红旗插上皋兰山主峰,从山顶到城里,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口音多是外地的,有点侉。我胆子不小,曾偷偷跟着大人们溜进城里看热闹。沿途可见沟壑里倒着死马和马军士兵尸体,血水沿着沟渠潜流着。没有枪栓的枪、未爆炸的手榴弹、各式刺刀、榴弹炮的炮弹、子弹袋、军用水壶,满街都是,要捡多少有多少。在水北门的城边,我看见一个年轻的马家军伤兵面色苍白,浑身筛糠似的抖,极痛苦的样子,抬头欲起复又趴下。其时,解放军虽控制了全城,但一切还来不及清理。这就是我亲见的兰州之战。”
十多年前,我在兰州某医院住院时,同病室有一位老革命,参加过兰州战役,说起狗娃山战役,那个死人,一团一团的,老人叹口气,太惨了。然后就望着窗外,不说话了。《黄河远上》如此说:“我的一个朋友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偶遇马继援,席间,马说:‘我们实在是打不过,我们机枪的枪口都打红了,人还是一层一层往上冲。’”
“那年我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记忆中天总是黑的,人总是冷得打颤。”《黄河远上》第二部分开始写他兰州附小的经历,主要写了解放前血洗邱宅的灭门大血案,邱氏乃新疆盛世才的老丈人;详细描写了听来的血洗过程,让人零距离感触了那个时代变化之际的血与火。还有那个天主教堂,在镇反中的遭遇,“只是大门关得更紧了”的描写,也颇有力量。
第三部分,回忆自己在兰师附小时的游戏,踢毛旦,叠罗汉。叠罗汉也是我儿时熟悉的游戏,但踢毛旦,我却不知道。此外,还写了自己被同学欺辱,以及他单斗的经历:“当晚在空操场上我们打得天昏地暗,没有观众,双方衣服都撕破了,脸上都挂了彩,他眼窝开了花,我鼻子大量流血——多年后诊断鼻梁骨骨折过。为此我鼻窦炎了一生。我耗尽了所有力气,他略胜一筹。他走了,不再趾高气扬,我垂头坐在台阶上。月亮上来了,有一人气咻咻找来,是姐姐。她带着哭腔说,有一天你叫人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我至今记着姐姐眼角的泪。”这段文字,写尽了在那个时代,一个孤独少年为尊严而战的惨烈。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模糊的影子。
至于斯大林逝世纪念大会上,他的不由自主的大笑,写来真实,但也让人无法理解。这可能是人的一种奇怪的生命现象,也可能是压抑过多的缘故吧?“早有同学提醒我,说我在上学路上,也经常自言自语,嘴唇动得飞快,有时还笑,看上去怪怪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笑,突如其来的笑,以前也有过。”“我实在无法解释自己的这些行为,我只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我在渐渐丧失笑的能力,我能完全控制住自己了。像这种无意义的笑,永远也不会再有了。”
第四部分,文字较少,写自己的附小生活,还有那次彻底考砸了的中考。“我承认我愚顽、敏感、淘气、怪诞,但我也有小孩子的天真、透明、可爱和不时恶作剧的念头,我是既单纯又不单纯,我的心头似总有隐隐压力,我无法做到彻底放松地纵声大笑,我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自负感,还有一种自卫感。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是因为我过早失去了父亲的保护和爱,还是母亲的忧郁传染了我?我多么希望我能和别的孩子一样。”这段文字,让我感动,雷达终于可以直面自己了。“我的心头似总有隐隐压力”,“我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自负感,还有一种自卫感”,这在我阅读雷达以前散文时,就可以感觉出来,但藏得很深,我只是隐隐感觉到,在一篇评论《雷达散文的青春气象》里也曾论及。后来,我一再说,你应该撕开写,你可以写写你的母亲,但雷达总是摇头。这几年,他终于在访谈里可以涉及了,这次的“西北往事”系列散文里,他终于可以直面了。在写《多年以前》的时候,他虽然还有遮掩,但基本上写出了自己真实的母亲。他终于可以直接写他的母亲了,这对雷达来说,太艰难了,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的母亲对我影响最大。我三岁父亲去世,母亲守寡一生把我抚养成人。上小学前,她逼我每天认三个字,记不住不准吃饭。她是音乐教员,性格忧郁敏感甚至暴躁,但她对古典文学和书法都有很好的感悟力。她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性格、气质、爱好上的。”
第五部分,写自己没有考上母亲希望中的兰州一中,被划拨到兰州西北中学。这段文字的幽怨,我能清楚地感知。我也能感觉到雷达母亲的失望,这种失望对少年的他影响至巨。“西北中学位于兰州西郊七里河,又称回民中学,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兰州东部的学生来说,那近乎兰州的西伯利亚;意味着必须住校,必须适应与回族师生打交道,必须只能一周回一次家,有点流放的味道。我只有十一岁。我并非回族,何必要把我‘拨’到那里去?难道管分配的人特意要治一治我吗?”这可能是雷达人生选择的第一次挫折。这段文字主要写了班主任女老师R:“小矮个,南方人,声音尖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没有同学不怕她的。当时她也就二十来岁吧。她有绝招。”那种特务式的管理方式,和阶级斗争式的揭发方式,在“果子事件”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和露骨。雷达他们去黄河游泳,然后摘吃了农民的梨。于是,被批斗,痛哭流涕地检讨,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要果农来声讨。果农却说:“娃们吃几个果子是多大的事嘛,那就不叫个事嘛,你们做撒哩沙,家算劳沙!”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孩子们吃几个果子是多大的事嘛,那就不是个事嘛。你们做什么吗?算了吧!”可是学校有人依然不依不饶,检讨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时,回族同学安映魁帮助了他,给他温暖。但是,那种人生的荒凉感、失败感,却从此烙印到他的心里。“在我消沉之时,我常一个人到学校四周去转,有一天中午我翻过几座土山,来到现在大约是兰州西站附近的位置,向南望去,眼前猛然显现出上千个甚至上万个坟墓,丘墓间还建有门楼,罩在一层雾霭中,一直铺向天边;四野岑寂,无一人,无一声,时间仿佛凝固了,但坟场本身似乎又在动,在发出一种声音或信息,好不瘆人!我在想,每个土馒头下必有一人,他们是谁,是男是女,他们都有些什么故事。大约从明清以来兰州的逝者都埋葬于此吧。十二岁的我,有一种莫名的悲悼与伤感之情涌上心头。它是什么,我不明白。我至今也不能忘怀当时的震惊。”
当然,生活并不都是痛苦,老师里面也有善良的。第六部分写了M老师,M老师也是回族,美丽,颇有艺术素养,她在课堂上公开表扬了雷达的作文。“这件事情极大地改变了我,我开始对语文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这个时期,也是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最初体味自由的时期。我家住小西湖,房子紧贴着黄河边,能听到黄河的涛声。春天‘开河’时,能听见河冰爆裂的砰砰声。三初中是所新建学校,新调来的老师和家属,互相都很生疏,没人跟我玩,我很孤单。我烦了闷了,就到黄河里游泳。假期有时一天游好几回。当时的黄河非常宽,水流湍急,十多岁的孩子游泳是很危险的,每年夏天都出事,但我不怕。我天生对水有一种亲近感,从没感到危险,只是体会游泳的快乐,和人在水中无法言说的自由感。黄河是我最亲近、最不会背弃的亲人。 我家旁边,有一条支流,游过去,就能上到一个河心小岛,岛上一个人也没有,沙滩质地细腻,小树林幽美,小鸟儿格磔其间。我把它当成我的鲁滨逊小岛,流连忘返。”
这段文字内涵丰富,既写了他的幸福、自由,终于找到了自信,也无意中依然渗透着那种让人难受的寂寞、绝望。“黄河是我最亲近、最不会背弃的亲人。” 但这位美丽的M老师最后也被打成了右派,不知所终。
从雷达在西北回民中学的经历中可以看到许多隐痛,这种少年的创伤给了他毕生的影响。我们从他以后的文字里,还是可以感觉到那种痛的。文章结尾写到那个女孩J,字数不多,信息量很大,其实可以扩充写成一篇长文。但在此文作为结尾,颇有力量,意味悠长。“她小我两岁,性格腼腆,说话声音细弱,她的身姿和面相在我看来都非常美丽。我们的家长都是教师,我家在小西湖南坡上面,J的家在坡下的一处独院内。那时候兰州人生炉灶要用柴火,J常常去河边帮母亲拣柴,我就帮她拣,两个人都不说一句话。秋天湖上刮大风,树上摇下来好多干枝,我们仿佛约好了一样,一起到湖边拾柴,捡了的都归她,但她还是只笑一笑,不说一句话。有一次我去她家,她看见后赶快藏起来。”
“秋天湖上刮大风”,这段文字非常富有画面感,是这篇散文里难得的温暖之笔。“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当面交给了她。经过好多天忐忑不安的等待,她仍无任何表示。我绝望了。她却用邮寄方式把回信寄到了西中。让我惊奇的是,她的字写得竟那么好。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年龄,信中除了表达友谊,就是鼓励好好学习。我珍藏她的信,一直装在棉裤的口袋里,晚上睡觉时都不脱棉裤。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母亲和姐姐的怀疑,她们在我熟睡后终于发现了秘密。但母亲并没有发怒,似乎连母亲也是喜欢J的。”这里把一个小男孩的情感萌动,写得那么真切动人,而母亲的慈爱,也活现笔下。
《黄河远上》最后一段文字:“当时,我没想到,她成了我此后十年间的挚友,最亲的人,更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才貌超群、善良温柔的女孩,在那个年代的狂风暴雨的摧残下,像一颗流星过早地陨落了。”这样的结尾,让人遗憾,令人痛惋,却又无言无语,这就是那个时代。在时代的洪流里,个人算得了什么呢?但为什么老是美丽善良的遭殃,而假恶丑却可以纵横驰骋?当然,雷达的《黄河远上》没有这么直接的追问,它只是描写,却从不发问,也不抒情,亦不议论,就那么素描下来。
其实,素描最有力量。
2014年7月30日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11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