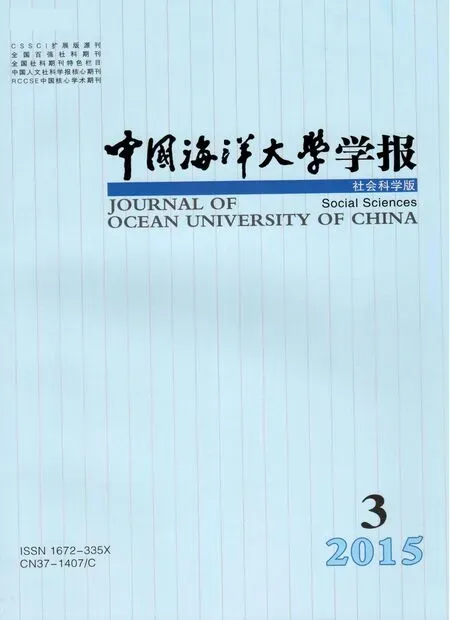宋代海盗成员的构成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 *
2015-01-22唐春生
宋代海盗成员的构成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
唐春生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宋代的海盗,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地痞无赖、不法商人、普通百姓,甚至还有违法的官兵。宋政府治理海盗主要采取招抚的政策,辅以一些具体的措施,如建立沿海各区域的协同配合机制,实施保伍法,改革地方的军政体制,强化铜盐之禁。由于海盗的收益远大于其违法成本,且得到了沿海地区百姓的支持及胥吏、官兵的庇护,政策很难奏效。
关键词:宋代;海盗;治理制度;治理失效
收稿日期:*2014-11-09
作者简介:唐春生(1964-),男,湖南武冈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两宋文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3-0030-06
Abstract:During Song Dynasty, the pirates came from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including rogues, unscrupulous businessmen, ordinary people, and even illegal soldiers. The government chiefly took pacification policy to deal with pirates, and supplemented it with some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in coastal reg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owu system, the reform of loc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ystems, and the strict control of copper and salt. These measures proved to be ineffective because pirates' gains were far greater than the cost they paid, and they usually got supports from common people in coastal areas, petty officials, soldiers and officers.
中国历史上的海盗问题,明清史时期最为突出,学界对此关注较多,而对其他朝代的海盗研究则关注较少,宋代海盗研究的成果也很有限。郑广南先生《中国海盗史》辟有专章论“宋元时期海盗活动的发展与特点”,对宋代海盗的成因、活动的具体情况、亦商亦盗的特点,以及南宋末期海盗抗击蒙(元)等方面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1]专论宋代海盗的论文并不多见,惟丁辉硕士论文《南宋福建路的海盗与海防》分析了福建路海盗的具体活动、特点、出路及其与海防的关系等内容。[2]本文主要从宋代海盗成员的构成、宋廷对海盗的治理、治理失效的原因三方面加以探讨。
一、海盗成员的构成
海盗的基本特征是“暴力戮掠”。[1](P8)宋代海盗成员,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
(一)纯粹的暴力犯罪集团。这一群体的成员较为复杂,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地痞流氓和作奸犯科的刑事犯。在宋代,沿海地区“多恶少亡命”,[3]( P97)为逃避打击,基于生存的需要,这些人便纠集起来,成为暴力犯罪集团,劫掠于海洋之上,成了职业海盗。南宋高宗朝活跃于莆田、福州地区的海盗郑广麾下不乏以一当百的“亡命”徒。[4](卷4《郑广文武诗》,P41)孝宗淳熙年中,兴化、漳、泉等州也有“逋逃之人”剽劫往来海上的商旅。[5](刑法2,P121)至于宋末的著名海盗朱清,本为雇工,杀害雇主并劫其钱财后,逃亡至海岛,与同党张瑄做起了海盗。[6](卷5《朱张》,P64)不仅是沿海地区犯罪的无赖,就连亡命军人也加入到海盗中来,他们与“沿海州县犯罪小民”一样,“畏避刑宪,因而啸聚,在海作过”。[5](兵13,P28)
二是演变为海盗的普通百姓。这一群体因生计困难而铤而走险的最为常见。四明(今宁波)近海边一叫砂岸的地方,是渔民打鱼的谋生地,当地豪强向官府交租后便经营于此,失去谋生之地的百姓便沦为海盗。[7](卷8《蠲放砂岸》,P6008)[3](卷3《奏禁私置团场……》,P89)如果说渔民打鱼的地是公共用地,他们失去其使用权尚可理解,而沿海地区拥有财产权的百姓的利益被政府强行侵蚀,则属明火执仗的强盗行为。理宗端平年间,温、台二州征用民船以增强镇江府一带的江防力量,民众因此“破家绝产,流离死亡”,不堪其扰的部分百姓被迫为海盗。[3](卷3《奏行周燮义船之策……》,P85)至于沿海地区那些缺粮少食的百姓,也只得“在海啸聚”而为海盗。[5](兵13,P27)此外,还有两种不为多见的情况,一是被海盗胁迫而入的伙。孝宗隆兴初,活跃于两广地区容、雷、高、藤四州的海盗,有一部分便是被驱胁的良民。[5](兵13,P23)又如,流窜于泉州海面的海盗抢劫船只,并强迫那些强壮者入伙,力量迅速壮大,由最初的三两只船增至二三十只船;由三五十人发展至数百以至上千人。[8](真德秀《申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第312册,P441)二是贪图海盗行为的利益而为海盗。泉州城外的围头澚的村民,与常停泊于此的海盗交通,经不起诱惑,“因而为盗”。[8](真德秀《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第312册,P379)
三是来自境外的海盗。从文献来看,宋时这类海盗并不多见,后世所称的倭寇,本时期并不存在。境外的海盗主要来自交州(越南境)与毗舍耶国(菲律宾)。太宗朝,交州潮阳镇的卜文勇杀人后率全家逃至广西钦州如昔镇,成为海盗,“连年剽掠”,有男女老小130口。[5](蕃夷4,P25)交州刺史黎桓,“负阻山海,屡为寇害”。至道元年(995),“交趾战船百余艘寇如洪镇(今广西钦州境内),掠居民,劫廪实而去”。[9](卷330《四裔考七》,P9095)至于毗舍耶国的海盗,则始于南宋时期。孝宗乾道年间,毗舍耶国的海盗入寇泉州,杀害居民。[8](真德秀《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第312册,P379)淳熙中,毗舍耶“酋豪常率数百辈猝至泉之水澳、围头等村,恣行凶暴,戕人无数,淫其妇女,已而杀之”,[10](卷上《毗舍耶》,P149)对福建地区的海防安全构成了极大危险。
(二)从事非法贸易的经济犯罪集团,其成员主要为商人和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人群。在宋代,某些商人“因商贩折本,无路得食”,为求生存,无奈而为海盗。[8](洪适《招安海贼札子》(一),第213册,P36)但这并不是两宋海盗产生的主要原因。两宋时期,政府严禁铜钱外流与食盐走私,这两个领域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福建、广东地区海盗形成的重要原因。[11](韩维《曾巩神道碑》,P803)商人为海盗主要有两类:一是盐商。宋政府对盐实行国有专营,垄断了市场供给,控制了市场价格,以获取暴利。这一政策,曾引发过沿海地区以食盐生产、销售为生的居民之变乱。如东筦大奚山列岛“居民不事农业”,赖盐业为生,宁宗庆元三年(1197),当地政府强夺其食盐经营权,岛民便“啸聚为乱”。[12](《广东备录下》,P3346)一些有实力的盐商武装贩私,甚至发展到劫掠商船的地步,亦商亦盗。孝宗淳熙年间,福建兴化、漳、泉等州的海盗“易置大船,创造兵器,般贩私盐,剽劫商旅”,[5](刑法2,P121)贩销私盐似乎成为海盗海上劫掠的一种掩护。商人的海盗行为还与职业海盗的劫掠互为倚靠,结成利益联盟,如高宗绍兴年间,福建“多桨船商贩”与南海海盗一同“劫掠海道”。[8](胡宏《向中郎行状》,第198册,P388)
另一类为海盗的商人,是与域外国家进行海上贸易的生意人。宋代的货币体系是铜本位制。宋代尤其是南宋,铜钱几成一种国际通用货币。境外诸国得宋代铜钱,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5](刑法2,P144)当时,金、日本、高丽有大量的宋代铜钱流入。此外,越南、马来亚、爪哇、印度、甚至阿拉伯、非洲都吸收过宋的铜钱。[13](P353-354)铜钱作为商品走私贸易,“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蕃货百贯之物;每百贯之数,可以易蕃货千贯之物”,[8](包恢《禁铜钱申省状》,第319册,P283)利润丰厚。但对宋朝,尤其是南宋的政治、经济影响很大,使得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楮价更加低落,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了极大危险,所以宋政府屡屡颁布严禁铜钱外泄的禁令,那些与域外国家进行铜钱交易的商人也被视为海盗加以打击。淳祐九年(1249),吴潜就称捕捉到与日本人经商的数百海寇,起获铜钱二万余贯,对于倭船只是驱逐出境而已。[3](卷4《条奏海道备御六事》,P94)
总之,宋代海盗成员的构成复杂,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全是作奸犯科的桀黠无赖,普通百姓、商人、士兵等因各种原因也参与其中,当然也有少数境外国家的杀人越货者。两宋海外贸易发达,巨大的人流物流是不可抵挡的诱惑,违法犯罪难以避免。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成的海盗,也不论是境内还是境外的海盗,都会提高商品的贸易成本,贸易空间自然受限,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例如,由于漳州、潮州、惠州一带海盗的猖獗,严重影响到了国外商船前来贸易而致宋政府的财政税收受损,也使得依赖广米的福、兴、漳、泉四地因海上交通阻梗而出现粮食供应安全的问题。[8](真德秀《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第312册,P442-443)海盗杀人越货极其残忍,庆元三年(1197年)夏,大奚山岛的海盗劫“掠商旅”,杀害平民一百三十余人。[14](卷5,P81)海盗的商业行为也奉行着强盗逻辑,宁宗时,温、台、明州海盗前往广东肇庆府贩私盐,“强买村民”,并劫掠其财产。[5](方域19,P35)
二、治理海盗的制度安排
对海盗的治理,除了必须加强武备,包括在要冲地带设立军寨,充实军兵外,宋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应对措施。
(一)抚主剿辅的政策。宋人治理海盗主要用招抚的手段,实则是无奈之举。因为海盗是跨区域作案,行踪飘忽不定,围剿的成本相当高,很难彻底根治,且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其武装力量主要用于应对外来的军事威胁。因此,政府希望海盗“开其自新之路”,待境内安定后,以便“专意外攘”。[15](《论广海二寇札子》,P621)对海盗施以安抚政策可追溯至太宗时期,太宗曾赦免捕获的海盗四十九名,将其收编为一支名为“平河”的军队。[16](《后集》卷45,P751)此后,宋王朝虽捕杀过海盗,但主要还是以招安为主。高宗绍兴年中,张浚为福建安抚大使,招降海寇,得兵将二千五百人。[8](韩元吉《李公墓志铭》,第216册,P258)那些招抚过来的海盗,大多补充至水军中。例如,即位不久的孝宗采纳了臣僚“将海贼贷命人互配诸处水军”的建议,[5](刑法4,P50)隆兴元年(1163)被捕获的海盗朱百五麾下的八百余人便被收编为水军。[8](袁燮《冯公行状》,第281册,P343)海盗的首领,甚至被用为水军将领,如高宗时的海盗朱聪投降后担任了水军统领。[17](卷28《高宗纪五》),P521)
(二)区域联动机制。海盗活动空间范围广,从浙江至两广地区达五六千里,[3](卷3《第二札论国家变故……》,P82)行为流动性强。因此,进剿海盗时,必须区域之间协调、合作,才能进一步压缩其生存空间。这种联动机制,一是州县之间的合作。隆兴元年,有臣僚建议在海盗盛行地区,相邻州县“互相追捕,使无所止”,这一建议得到了孝宗的认可。[5](兵13,P22)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三月,知庆元军府(治宁波)兼沿海制置司公事的韩元礼说:温、台、明、越四郡“各顾其私,不相统一”,以致海盗“出彼入此,无由捕获”。因此应设沿海制置司,“假以刺举之权”,统一协调剿捕海盗事宜,沿海州县因此“不敢私自纵容,盗贼无所隐庇”。[5](兵13,P47)在福建路的沿海地带,漳州、泉州居首,福州、兴化军居中,其余地带为其尾,福建提刑包恢要求各州、县采取措施,做到“首尾中相应”,[8](包恢《防海寇申省状》,第319册,P281)以应对海盗的袭扰。二是跨地区的合作。北宋真宗时,地方政府清剿福州长溪县的海盗,“盗贼多窜入温、处等州”;进剿两浙州军的海盗时,他们便窜犯至长溪县界。[18](卷19《兵防》,P7940)浙东与福建如不携手,是难以清剿海盗的。至南宋,海盗也时常出没于广东沿海地区。理宗时的福建提刑包恢认为福建北邻浙东,南接广东,“须一体严行措置”,“合三路为一家”。[8](包恢《防海寇申省状》,第319册,P281)跨区域的协调与合作,当时已为惩治海盗的地方官员所实践。知福建泉州的真德秀将海盗击溃,海盗退至广东,真氏通报给了广州方面,以便“疾速措置”。[8](真德秀《申左翼军正将贝旺乞推赏》,第312册,P438)方大琮知广州、任广东经略安抚使时,派兵追击沿恩平江而下的海盗,海盗被迫进入福建的漳州,方氏也将此讯息通报给福建,两个地域的联合进剿海盗,海盗“遂衰且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8](方大琮《与袁侍郎书》(七),第321册,P243)
(三)州县统摄军政。在宋代,文武分为二途,地方也是如此。这种体制在治理地方盗贼方面多有不便,宋人对此作了制度上的变革。上文已提及,真宗朝,两浙州军的海盗因遭围剿便逃窜福建至长溪县界。长溪县负责捉拿海盗的都同巡检,没能按时会合,错过了打击海盗的有利时机。于是援用建州浦城例,以武职兵马监押兼知长溪县事,以更好地协调围剿海盗所涉及到的军民事务。至仁宗庆历年间后,复以文职知县兼兵马监押。哲宗时,福州宁德宝瑞、宝丰场新增人户千余家,二地距县治较远,为有效加以管控,元祐七年(1092)五月,即以峰火澳巡检兼知长溪、宁德两县,“巡捉私煎贩盐兼管当两县盗贼公事”。[18](卷19《兵防》,P7940)地方州县统摄军政,即便在海盗猖獗的沿海地区也没能成常态。宁宗时,真德秀又提到了州郡综理军政的必要性。当时,驻扎泉州的左翼军,其“月粮衣赐”等物资均由当地提供,征兵也要由州郡审验,因此,州郡与军队事务关系密切。但州郡对军队的兵籍、战舰、器械、训练、升迁等问题全然不知。地方军将“肆意掊克”,士兵“教阅尽废,纪律荡然”,州郡对军中这些积弊虽然十分了解,由于不相统摄,不敢过问。知泉州的真德秀认为,一遇紧急事态,州郡与军队不能“同心协力”,自然难以收到好的成效。如果州郡节制军队,“缓急或有调发,不至乖违”。[8](真德秀《申枢密院乞节制左翼军状》,第312册,P384-385)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原受殿司节制的左翼军因此改受泉州地方统辖。[14](卷16,P296)
(四)实施团结保伍法。得到了一部分普通民众的支持,这是海盗存在的社会基础。为加强社会面的管控,宋政府实施团结保伍法。哲宗元祐六年(1091)七月,广南恩、端、潮等州县沿海船户每二十户被编为一甲,每甲选二人充任大小甲头,“县置籍,录姓名、年甲并船橹棹数”;如有违法行为,“同甲人及甲头知而不纠,与同罪。”[19](卷461元祐六年七月戊辰,P11025)同甲互相监督、责任连带。至绍兴二年(1132)七月,广东福建帅司建言:将沿海地区大小桨船家登记姓名,每三家或五家结为一保,保伍互相监督,[5](兵13,P11)保甲的范围大为缩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百姓为海盗。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朝廷对那些庇护海盗的民户除断罪外,还拆毁其房屋,迁移其家属,以切断与海盗的关系。[5](兵13,P34)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上,一度还推出了结社制度。绍兴五年四月,宝文阁直学士连南夫建议“团结濒海居民,五百人结为一社”,推举社首,并“给帖差捕”海盗。朝廷因此诏令福建、广东帅臣措置团结濒海居民为社。[20](卷88绍兴五年四月戊午,P1702)
宋人试图通过保伍团结法,将增强地方武备的问题融入到社会治安的制度建设中。孝宗乾道年间,郑兴裔提出:“澚置一长,择地方之习知武艺者而任之;仍令结为保伍,旦夕训练。”如此,国家有武力可供驱遣,同时也没给财政增加负担,而海盗的气焰可以渐息。[8](郑兴裔《请置澚长御海寇疏》,第225册,P72-73)理宗时,包恢也认为,解决海盗问题,可用“保伍民兵澳长为将,深防固守,使不得近岸,近则聚众擒捕”,配合官军的攻击,海盗的来犯不过是“送死而已”。[8](包恢《防海寇申省状》,第319册,P279)吴潜认为团结法的实施,可令“本境之盗无所容,外境之盗不可入”。[7](卷8《蠲放砂岸》,P6010)
(五)有限度的海禁。两宋时期,推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希望形成“外藩辐辏中国”的局面。[21](卷5熙宁二年九月壬午,P239-240)至南宋,国土日蹙,更加重视航海贸易。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5](职官44,P20)他主张“招徕远人”以助国用。[5](职官44,P24)
宋政府为了国家财政的需要对盐业经营实行管控,出于货币体系的安全又实行铜禁。宋代海禁主要也是这两个易于产生海盗的经济领域。宋代禁绝商人自由贸易食盐。在实施钞盐新法后,沿海某些地方对此也曾有所放松,如山东半岛的莱州,其商人可由海道往淮南等州军贩销盐货,但担心盐商有可能“夹带奸细及隐藏海贼”,崇宁五年(1106)三月,朝廷“依旧权行禁绝百姓船”。[5](刑法2,P46)至于铜禁,绍兴三十年(1160),宋政府规定走私铜钱五贯即为死罪。[8](范成大《论透漏铜钱札子》,第224册,P311)乾道七年(1171)三月,有人建议严禁“官司铜钱”载入海船,否则必须严惩,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5](刑法2,P158)私载铜钱下海,一经查实,常常是罚没充公。这类法规,时常见诸文献。例如,嘉定十年(1217)十一月,对那些私载铜钱入海的船户,“不问缗钱之多寡,船货悉与拘没”。[5](刑法2,P142)
三、治理制度失效的经济学解读
尽管宋政府采取了以上的措施以防控海盗,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海盗问题,两宋时期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海盗行为的收益远大于成本。海盗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盐铜之利。即以政府控制盐利而言,孙觌曾称走私之盐一斤五十钱,而官盐高达百余钱一斤,差价如此之大,私盐价格优势明显,百姓纷纷购买,甚至连官兵也消费私盐,[8](孙觌《上沈相书》(二),第159册,P67)为海盗的贩售私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又如广东的海盗就通过东、西二江,将“所贩私盐”向东销售至潮、惠二州,向西至梧、横二州,甚至更广的地区。[5](食货26,P21)在价格低廉的地下市场面前,价高的官盐无法与之竞争,需求受到严重的影响,官盐甚至滞销。宋朝地方政府便强行推销——“计口敷盐”,高盐价令老百苦不堪言,真德秀认为这是海“寇之源”。[8](真德秀《论闽中弭寇事宜白札子》,第312册,P445)这一做法,福建地区早在绍兴末期就已实行过,弄得家家“钱谷空虚”,“人甚苦之”。[20](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甲子,P3322)
再看铜禁。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大量的铜钱流入金、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吸收过宋的铜钱,[13](P353-354)铜钱几乎成了一种国际货币,具有了商品属性,且有着广阔的海外市场。既为商品,铜钱自然会往财富生产最有效的地方流动,在与域外国家的铜钱贸易中,“利源孔厚,趋者日众”。[5](刑法2,P144)虽然宋代严禁贩销私盐和交易铜钱,但由于冒禁的收益大于成本,冒禁成为海盗的理性行为。李纲说广南福建路的海盗劫掠“所得动以巨万计”,而海盗“重得官爵,小民歆艳,皆有仿效之意”。[22](卷82《论福建海寇札子》,P829)海盗行为的风险小,成本低,获利大,招抚难以收到解决海盗问题的实效。殿中侍御史郑刚中也指出:“海盗非招安所能尽也。往年招朱聪矣,其徒聚而为刘广;后又招广矣,其徒聚而为李元。盖招致其魁,其徒必纵以归业;魁得官,其徒谓可取以为准也,什百啸聚,又作一头。”[8](郑刚中《论弭海贼奏》,第178册,P98-99)他认为招安海盗首领并予以重用的做法并不可取,只会形成“羊群效应”,徒众群起效尤,继续为海盗,然后再希望获致招安,形成恶性循环。对招安的海盗来说,无风险无成本可言,反而有较大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招安政策为海盗行为提供了激励。一遇官兵围剿便再次招安,这手段某些海盗屡用不爽。日人桑原隲藏指出:官府“于山贼海贼之猖獗者,每以招安为先务,贼之应招安者曰归顺,实则招安者意在藏弱,归顺者意在利禄,于实际无补。”[23](P123)宋政府治理海盗的制度设计既然存在问题,加之食盐与铜钱供求机制的作用,政府的禁令自然无可奈何地失灵。
(二)海盗的生存基础:权力的寻租与百姓的庇护。宁宗嘉泰四年(1204),宋人就指出:“(海盗)盖缘濒海豪户利在窝赃,巡尉、水军与为表里,洎其败获,狱吏又阴与为市。”正是得益于豪户、官兵、胥吏的“多方全护”,海盗才难以肃清。[5](兵13,P43)
首先,海盗之所以难以根除,是因为沿海地区的官吏与官兵和海盗存在着利益交易的权力市场,有着肮脏的利益输送。如高宗时南海海盗暗地里与贵州(今广西贵港)地方胥吏相勾结,“兵将动息,贼皆先知”。[8](胡宏《向侍郎行状》,第198册,P388)孝宗时,明州“海寇以赂通郡胥吏,吏反为之用,匿其踪迹,贼遂大炽。”[17](卷247《赵子□传》,P8747)那些负有剿捕之责的官兵竟然也与海盗相勾结,如宁宗嘉定年间镇江府下辖的圌山寨的士兵“素与海盗为地”。[17](卷415《傅伯成传》,P12443)广南地区、两浙东路温州、台州等地的海盗也得到了官兵的关照,所谓“沿海官兵皆相为囊橐”,他们不仅不尽力剿捕,即便捕获了海盗也大多以予释放。[5](刑法2,P141-142)官兵这种不法的失职行为较为普遍,宁宗时的监察御史郑昭先说:“水军寨兵、弓级不即殄灭(海盗),或养寇以自丰,或玩寇而不捕,阴受其赂,反与交通。”[5](兵13,P45)剿捕海盗的官兵与海盗结成利益共同体,已成为他们的保护伞。
其次,海盗行为是离不开陆地的,海盗的日用饮食之类的生活用品,得靠岸上补给。福建泉州有一较大的围头澚,为交通要道,海盗船常停泊于此,既可以避风,又可以补给淡水,还可将劫掠所得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购置所需的物品。[8](真德秀《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第312册,P376,380)岸上之民,为海盗带来的“动以万计”的巨大利益所诱惑,“富者为之停藏,贫者为之役使,甚至多起酒楼,多设妓馆以诱之,惟恐其不来”。[8](包恢《防海寇申省状》,第319册,P279)围头澚成了贸易中心与海盗的补给基地。与海盗关系密切的百姓不只是窝藏海盗货物,甚至成为其货物销售的代理人。如绍兴初期,广东贩私盐的海盗就将货物交由“停藏之家”代为保管,并由他们“或就某处出卖”,所得的报酬便是“贼赂”。[5](食货26,P21)虽然政府实行了团结保伍法,但效用并不高。海盗的到来,人们得到了工作的机会,增加了收入,其利益诱惑远大于保伍连坐的成本。所以,海盗拥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使得他们能较为从容地应对来自官府的压力。“官司动静,贼未尝不知其详;贼船动息,官司反逻不得其实。”[8](包恢《防海寇申省状》,第319册,P278)在信息情报方面,部分受惠于海盗的民众乐为其耳目,大大增加了官军剿捕的难度。
(三)造船技术水平的提高,降低了海盗行为的风险,增强了他们与政府抗衡的资本。宋朝的海盗拥有了较为先进的海船,船只来源除抢夺、购买外,还能自造。绍兴初期,广东的海盗已能建造大棹船只,“大船至三十棹”,利于海上劫掠。[5](食货26,P21)宁宗嘉定时,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四地沿海的民众拥有了造船所需的资金与技术,造船用来“兴贩牟利”。[5](刑法2,P137)这里有必要说说多桨船。这种船本系南宋水军所用,“其船系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通长八丈三尺,阔二丈,并准尺,计八百料,用桨四十二枝,江海、淮河无往不可。载甲军二百人,往来极轻便。”[5](食货50,P22)是一种平底快速江海两用船。[24](P89)至迟在绍兴前期,海盗已开始使用多桨船。例如绍兴十年张浚招降海盗时,缴获多桨船五十三艘。[8](韩元吉《李公墓志铭》,第216册,P257)技术较为先进的多桨船,极便于海盗快速劫掠、撤退。正因为此,绍兴年间的南海大海盗大棹与福建商贩利用多桨船劫掠海道,“兵将疲于奔命,讨不能得”。[8](胡宏《向中郎行状》,第198册,P388)宁宗嘉定年间,也有人说:“海多寇盗,剽掠平民。如广之多浆船,温、台之捕鱼船,所至为害。”[5](刑法2,P141)官兵的船甚至不及海盗船。在泉州,海盗船“高大如山”,官兵之船“不及其半”。[8](真德秀《申左翼军正将贝旺乞推赏》,第312册,P438)在福州,围剿海盗的船只多为小船,而海盗甚至拥有巨舰数千。[8](包恢《防海寇申省状》,第319册,P277)海盗拥有的舰船技术的先进程度为官府所不及,与官府舰船较量于汪洋大海上不处下风,甚至还强大些;海盗的比较优势明显,剿捕就成了一句空话。对于宋政府来说,要对付海盗自然要打造新舰。真德秀在泉州任上为对付海盗,造左翼军甲乙丙战船三艘,“系是鼎新创造,木植坚壮”,虽然作战效果不错,但“所费不赀”,[8](真德秀《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第312册,P378)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四、余论
治理海盗,须抚与剿相济。海盗的治理如只重招抚而失之于惩处,是难以收到实效的,尤其是对那些屡剿屡抚的海盗;只有严惩重处,让其重为海盗的代价足够大到他们没法承受,才能止盗。高宗绍兴中期,陈康伯知泉州时,“海盗间作”,他按照“上意招怀”了海盗,并编入兵籍。一段时间后,有人图谋作乱,存在着重为海盗的可能,陈康伯果断严惩了“不逞者”,威服了余众,“州以无事”。[17](卷384《陈康伯传》,P11808)
宋朝治理海盗制度的某些方面,如加强社会面的管控,其实是可收到实效的,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得到落实。绍兴初期,海盗周聪、陈旺等窜犯高、化、雷三州,在陆地被严控的情况下,无法获得补给,致“无水可饮,而食且尽”,二人最终降于宋廷。[24](卷78《胡待制舜陟传》,P1897)孝宗时,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赵子□在严厉打击海盗的同时,“凡豪猾为贼囊槖者,穷治之”,海道也得以安宁。[17](卷247《赵子□传》,P8748)成效的取得,势必要求职掌剿捕海盗的地方官吏与官兵竭诚效命,切断海盗与那些贪图利益的地方豪猾、普通民众的联系。
海盗的产生,与求利的奸民相关。这类人既惰于务农,也缺乏生存之良技,[8](王质《论镇盗疏》,第258册,P243)贪图海上劫掠之厚利,他们构成了海盗成员的重要来源。当然,海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个民生问题。理宗时,曾任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的吴潜认为彻底解决海盗,须“安百姓”,“遂生理”,要让百姓拥有“衣食之源”。[3](卷3《第二札论国家变故……》,P82)他在任上免除两税钱三百三十余万贯文,也尽量不扰民,减轻百姓的负担。[3](卷3《奏晓谕海寇复为良民……》,P87)宋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即使是对招安的海盗也予以生存的出路。绍兴四年四月,高宗下诏对招抚的海盗予以经济政策的扶持:置田产与免两年税役。[5](兵13,P15)这一问题日后处理得并不好。高宗朝后期的海盗王先在招安后因生计所迫重为海盗,至再次招安时,规模有所壮大,发展至八百余人。[8](洪适《招安海贼札子》,第213册,P35)再如孝宗朝安置于大奚山(今香港西南的大豪岛)的海盗,由于“无所廪给,遇岁饥,或间出掠鱼盐之利”。[8](韩元吉《周公墓志铭》,第216册,P328)
宋朝政府尤其是南宋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铜盐之禁不可能放开,商人难免为海盗,借用明人语,所谓“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25](P33)加之民生的安定也很难保证,虽有个别官员在这方面做了些努力,有时政府也有些善政,但毕竟当时的大势是如何巧取于民以渡过财政危机(晚宋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海盗问题只能做到可控,而难以彻底解决——即便是当今时代,要想彻底根治海盗也绝非易事。
参考文献:
[1] 郑广南.中国海盗史[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2] 丁辉.南宋福建路的海盗与海防[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3] 吴潜.许国公奏议[M].丛书集成初编本.
[4] 岳珂.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徐松.宋会要辑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 吴潜.开庆四明续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 全宋文[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9]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 赵汝适.诸蕃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 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4] 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5]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6] 章如愚.群书考索[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17]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0.
[1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1]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2] 李纲.李纲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3] (日)桑原隲藏.蒲寿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4] 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25]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Z].合肥:黄山书社,2004.
[26] 梁小民.走马看商帮[M].上海:上海书店,2011.
The Compositions of Pirates and the Arrangement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Tang Chuns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Work,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Key words: Song Dynasty; pirates; the governance system; the failure of governance
责任编辑: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