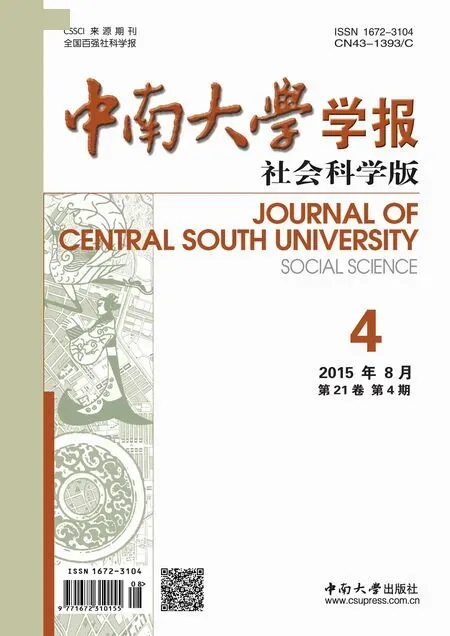论《魔幻玩具铺》中的自我身份认同
2015-01-21程毅
程毅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论《魔幻玩具铺》中的自我身份认同
程毅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魔幻玩具铺》是英国当代作家安吉拉•卡特早年以思考身份认同为核心的作品。小说主人公梅拉尼用镜像与易装术作为身份建构的策略,但对这两种策略的认知偏差导致她陷入身份断裂与缺失的困境。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指出无论镜像还是易装术,都建立在庞大的文化话语系统中,梅拉尼的自我身份认同并非先验主体的产物,而是不同符码、话语体系、象征系统以及日常习俗构成的文化模式共同塑造起来的,是交往过程中不同文化话语协商建构的结果。
《魔幻玩具铺》;自我身份认同;镜像;易装术;文化协商
《魔幻玩具铺》是英国当代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创作的第二部小说,作为一部形式上将“童话与成长小说相结合”的作品[1],这部小说因书写方式的多样化与文本意指的复杂性成为当代英国文学中被文学评论界关注最多的小说之一。众多批评家将其视作结合了童话、神话、哥特元素等多种“通俗小说形式上的多层重写”[2],认为小说抹去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3]此外,基于女性主义理论及卡特的女性主义创作背景,长期以来批评家多将研究重点放在探讨小说中父权暴力对女性的宰制以及女性对父权等级的颠覆上,认为小说“解构了性别偏见及其宏大话语”[4],“反抗并抛弃了传统的性别对立”[5],是一部“青春期女性欲望觉醒的赞歌”[4]。但事实上青年卡特的女性主义意识仅处于萌芽状态,她曾声称自己在写作之初“并未发现女性主义的意图”[6],而是试图通过小说的形式“提出问题”“认识自己”[7]。可见卡特早年创作重点并未集中于批判父权等级制以及两性性别冲突问题,而是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下集中思考自我身份问题。
身份是人们与他人交往并对自己进行定位进而确认自身归属的关键元素,思考身份问题就是思考我是谁,思考个人在社会或群体中的角色问题。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从主体角度曾将身份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启蒙主体、社会学主体以及后现代主体三个阶段。其中,启蒙主体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思想的影响下强调自我是建构身份的核心;社会学主体则强调身份建立在自我隶属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后现代主体则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为身份是外在于自我的各种话语建构的产物①。在此基础上,身份研究在当代进一步衍生出性别身份、文化身份、种族身份等纷繁各异的研究领域。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卡特《魔幻玩具铺》中主人公梅拉尼在身份认同上面临的困境,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检视其建构自我身份的主要方式,从而把握卡特创作早期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思想历程。
一、自我身份的焦虑
所谓文化身份,在霍尔看来是指在“共同历史经验与共有的文化符码”基础上确立的稳定不变的身份。同时由于受后殖民理论影响,他认为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文化、权力”的合力下不断发生变化。[8]尽管表面看来霍尔对文化身份的界定自相矛盾,但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符码建构了模式化的文化话语,才导致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必然发生冲突,从而造成原本看似稳定整一的身份在不同文化影响下趋于多样性和碎片化。显然,这种身份问题也出现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著名批评家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曾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女性作家一直处于本质主义身份与作家自我身份的双重焦虑之中,这使得她们在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我是谁”的问题[9](197),作品也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9](200)。如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就是一部讨论女性特质的建构方式,“注解自身的作品”[10]。同样,青春期的卡特也一直被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所困扰,由于备受神经性厌食症②的折磨以及父母的过度宠爱,青春期的卡特认为自己只是父母“游戏中的棋子”[7](22)。在早年文学创作中。卡特思考的问题也多围绕自我身份展开,尤其体现在小说《魔幻玩具铺》中。
自我身份的焦虑或者说“我是谁”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小说主人公梅拉尼的核心问题,但在梅拉尼进行身份认知之初,文化因素并非她建构身份的关键。在她看来,主体性是其身份建构的核心。小说以她对自我身份的崭新认知开始:“这年夏天,十五岁的梅拉尼发现了自己的血肉之躯。哦,我的美利坚,我的新大陆。”[11]她痴迷而满足地凝视自己在镜子前摆出的姿势及假扮的各种身份。对她而言,伴随身体成长的是随之而来的恋爱与结婚,这是她把握“自己自主性身份”[3](72)的关键。也就是说,梅拉尼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最初建立在先验主体的“人”的基础之上,将作为主体的“人”视作建构自我身份的关键,这里作为主体的“自我”是“整一,受自己控制,不受制于外在力量”[12]的主体,对包括身份在内的外部世界具有支配权,在此基础上自我身份始终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13],不存在身份的缺失或者断裂。
然而梅拉尼稳定连续的身份幻想却因父母遭遇的一场空难而化为乌有,作为孤儿她不得不与弟弟乔纳森、妹妹维多利亚搬去与舅舅菲利普同住。在玩具铺,梅拉尼不断面临自我身份缺失的窘境:她要照顾未成年的弟妹,不能继续读书,只能做家务、贩卖玩具。此外,还要在周末观看菲利普舅舅的木偶戏,去崇拜真人大小的木偶。这一切让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梅拉尼感到自己“不再是行动自由的人”[11](35),只是“一个影子”[11](81)。在主体性遭到遮蔽时,她开始自我怀疑:“我永远不会这样,不是真的我。”[11](95)
自我身份的焦虑在梅拉尼以木偶的身份表演菲利普的木偶戏《琳达与天鹅》的过程中达到顶峰,扮演木偶彻底剥夺了梅拉尼的主体性,将她彻底降格为物,于是在舞台上,“她的自我痛苦地分裂了”[11](177)。扮演木偶使梅拉尼意识到自己在玩具铺只是被提线掌控的被动客体,因此在木偶戏结束后的当天夜里梅拉尼梦见自己变成弟弟乔纳森。小说里的乔纳森对制作模型船异常狂热,以至于“看不见现实世界”[11](55),他的手艺受到菲利普舅舅的赏识,得以继续专心制作模型船。尽管评论家们认为乔纳森对模型制作的专注“象征了退化的混沌心灵”[4](337),但小说中他的自我身份始终是稳定的,不受外在环境变化的影响,其身份认同始终寓于其内在主体性中,而这种稳定的自我身份正是梅拉尼所渴望的。与乔纳森相比,梅拉尼的自我身份不断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外界环境的变化令她不得不频繁转换身份,变成乔纳森的梦境便是梅拉尼身份焦虑的潜意识再现。
二、自我镜像与身份易装术
面对身份缺失的焦虑,梅拉尼分别通过镜像与易装术完成自我身份认同。这两种方式均建立在她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基础之上,强调自我身份的同一性,将自我视作身份建构的主导力量,并拥有控制、转换身份的主动权,是实现内在自我与外在身份统一的关键。
首先,镜像既是梅拉尼自我身份焦虑的再现,也是她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装置。她在镜子前摆出各种姿势,将自己想象成拉斐尔派画作中陷入沉思的女子,或图卢兹—罗特列克风格的浪荡女,并借镜像假想自己未来的生活。显然,梅拉尼试图通过镜像在自我身份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正如拉康(Jacques Lacon)所言,镜像是在“有机体与它的现实”“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某种关联”[14]。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镜像并不仅仅是身份的简单复制,镜中之象与镜外之人是相互指涉的,一方面,镜中之物是镜外之人欲望的投射,另一方面,镜中之物反过来塑造了镜外之人。在梅拉尼看来,镜像任由镜外的自己随意塑造表现,是自身意志的体现,于是通过镜像建构起来的自我身份才具备稳定性,不存在与主体的背离。然而,玩具铺里没有镜子,这使梅拉尼失去了建构自我身份的装置,镜子的缺失使她无比惶恐,她感到自己不再完美,自己拥有的只是笨拙的手和“两条怎么摆弄都显得不优雅的长腿”[11](65)。她在菲利普的地下工作室见到酷似真人的玩偶时蓦然意识到自己与这些玩偶没有任何区别,都在菲利普的宰制下过着丧失自我意志的生活。
但她并未就此放弃建构自我镜像。在城郊公园,梅拉尼第一次与费因接吻,整个过程梅拉尼一直出离于接吻事件之外。在强烈的自我意识驱动下,她通过费因的瞳孔寻找到自己的镜像,同时,她假想自己站在远处观看这貌似浪漫的一幕,通过费因的瞳孔获得自我认同。显然,在镜像认同开始的瞬间,梅拉尼便被瞳孔镜像建构成自身的对手,在镜像认同过程中“被客体化”[14](76),梅拉尼正是通过与“客体化”的镜像之间的想象关系建构她的自我身份,从而补充和调整在玩具铺由于镜像缺失而不再稳定的主体身份。在一篇颇具自传意味的随笔《肉体与镜》中,卡特曾着力阐释了自我与镜像之间关系的暧昧不清:
魔镜让我看见在此之前不曾思索过的、关于我自己之为我的一种意念。无意间,我被镜中映照的动作所定义。我围困了我。我是镜中所写的句子的主词,而不是在观看镜子。镜面之外毫无他物。[15]
也就是说,镜像的功能是促使“我”得以思考我何以为我的问题。一方面,镜外的“我”拥有一个独立的视野,“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自己”并“控制我自己这具木偶”。另一方面,这种认同实则是以镜像为依托,镜像定义或者塑造了“我”的身份。小说中梅拉尼的自我认知便开始于她在镜子前的顾影自怜。镜像使她有机会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镜像中,并制造了她控制“镜中之我”假象,同时又反过来塑造了梅拉尼的自我身份。事实上,在镜像认同的过程中,自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作为主体,自我通过欲望幻想整合现实中碎片化的身份并将其投射为镜像;作为客体,此处的身份实则是外部世界的大镜像自我幻想中的投射,自我在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外部世界。由于这个塑造过程只是自我幻想以及外在世界建构出来的假象,所以实际上梅拉尼并未真正将碎片化的自我整合为完整的统一体。
除镜像外,易装术在小说中也是梅拉尼展示或建构其外部身份与内在自我的重要方式。所谓易装术是指通过更换服饰的方式来实现包括社会、性别等层面的身份变换,它是易装者对自己身份的声明,涉及身份的本质、真相、稳定性以及假想身份与表象身份之间的关系。[16]罗兰•巴特曾指出:“透过衣服的穿着,我们每个人互相交换许多很基本的资讯,代表各种不同职业身份,……服饰会努力配合我们所想要表达我们自己的样子,我们在社会上所扮演的复杂角色。”[17]由此可见,服饰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小说中梅拉尼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中产阶级作家,常穿袖子上贴了皮革衬垫的毛料夹克,她的母亲则拥有许多款式各异的服饰,以至于她认为“母亲一定是衣冠整齐地生出来的”[11](11);玩具商菲利普舅舅常穿一身呆板的黑色西装,打理店务的玛格丽特舅妈穿不合身的黑毛衣与破洞的黑袜,费因那身消防夹克和灯芯绒长裤则是当时英国青年展示其反叛特质的典型装束[18]。
对梅拉尼来说易装术是她获得稳定而完整身份的重要方式。一方面,梅拉尼通过幻想、虚拟层面的身份易装术,将自己想象成歌剧演员或职业模特,这些女性均是梅拉尼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或静若处子或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她决定穿上母亲的婚纱。沙朗•伯顿(Sharon Boden)曾指出,婚纱在从少女到新娘的身份转换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被视作婚礼服饰中“最神圣的人工制品”,新娘穿上婚纱的瞬间便意味着“婚礼的开始”和“新娘身份的转化”。[19]梅拉尼用窗纱为自己做新娘睡袍,用窗纱包扎头顶假扮德国画家克拉赫勒笔下的维纳斯,并趁父母外出旅行于深夜溜进母亲房间,在镜子前穿起母亲的婚纱,虚构出一场假想的婚礼。对梅拉尼而言,婚礼确立了她的女性身份,正像卡特所指出的那样,婚礼是“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只有在这一刻,她才被允许成为任何存在”[20]。也就是说,尽管掩盖了父权等级下女性身份的他者性,但婚礼在传统意义上仍然是女性完成其身份建构的重要标志。
然而,梅拉尼对自己的易装行为并非毫无疑虑。在决定穿起母亲的婚纱之前,她的内心其实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面对婚纱她不停自问,“它适合我吗?”“能吗,我能吗?”[11](16)尽管母亲在她心里一直是幸福完美的代名词,但她也敏锐意识到母亲的生活过于沉默、刻板——小说中梅拉尼的母亲始终是以回忆或相片的形式出现——她一直生活在自己各种华丽服饰中,像“蝴蝶标本”[11](14)般成为房间的装饰品,而梅拉尼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应该是热情并且充满生命活力,因此自由热情的理想女性与刻板优雅的现实母亲之间的差异造成了梅拉尼在女性身份认知问题上的困惑,从而导致她易装行为前的摇摆不定。
伴随这种悖谬的身份认知困惑,梅拉尼的易装行为也是一场身份灾难的隐喻:巨大、沉重、光滑、冰凉的礼服使梅拉尼不得不“爬进”去才能穿起它,渔网般的面纱将她罩住绊倒,经过与面纱的一番“撕扯”搏斗才好不容易得以脱身,但此时身着婚纱的梅拉尼却感觉自己“迷失在永生里”[11](19)。凯瑟琳•克拉夫特−菲尔柴尔德(Catherine Craft-Fairchild)在《易装与性别》(Masquerade and Gender)中曾指出,易装在性别角色问题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易装能够使女性获得“独立身份”,另一方面,易装也会“加强或再次刻写性别化的假定与角色”[21]。显然,易装行为在身份建构上存在一个预想模式,即希望通过易装来表达的某种身份,易装术使梅拉尼完成了由女孩向女人身份的转变,但她的这种自我身份是建立在易装之前对女性身份的想象基础之上。易装术使梅拉尼完成了想象中的婚礼,获得了假想中的女性身份,但婚纱同时将妻子的身份强行刻写在梅拉尼身上。于是,易装成为束缚梅拉尼原本自由并充满生命活力肉体的隐喻,它非但没有实现梅拉尼成为理想女性的愿望,相反,自由女儿与刻板妻子之间的冲突导致梅拉尼的女性身份发生紊乱,现实与想象身份之间的落差使梅拉尼的身份建构发生了灾难性的迷失。
此外在梅拉尼看来,在易装过程中自我是操控易装术的主体,服饰是易装行为的工具。她身着婚纱兴奋地在花园中对果树和月亮发号指令,将自己视作某种超验主宰者。然而实际上,自我在易装术中并不是易装行为的主体,而是由服饰塑造的被动客体。安吉拉•卡特早年非常关注服饰与身份之间的关系,在一篇发表于1967年的随笔《六十年代时尚理论札记》(Notes for a Theory of Sixties Style)中她指出,“服装的本质是非常复杂的。衣服同时可以是许多事物。我们社会化的表面人格,将我们的意图广而告之的符号体系,我们对自己幻想的投影。”[22]通过服饰,“自我作为一个三维的艺术品被展示出来,被思考和操控”[22](87)。一方面,卡特将服饰视作主体欲望的投射,这种投射以自我对身份的幻想为前提。另一方面,卡特也注意到在该过程中自我实际上是被服饰操控、展示的,也就是说自我是被服饰建构塑造而成,并不是掌控服饰的主体。于是,婚纱在小说中已然幻化为试图吞噬、占有梅拉尼的恶魔隐喻,主体性受到威胁的梅拉尼为此“惊慌失措”[11](19)。可见,身份幻想的落差与主体性的缺失导致梅拉尼在易装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发生断裂。
可以说,梅拉尼的镜像与易装术这两种身份建构策略之所以都令她陷入身份困境,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她对自我身份既定的想象之上,在此基础上建构而出的自我身份其实只是梅拉尼“理想中的自己”,是她虚构的身份幻象和对自我身份的“误
认”[14](80)。另一方面,梅拉尼坚信自己是身份建构的主体,其身份在主体意识的控制下成为内在自我与外在身份协调一致的统一体,在此意义上,其身份认同实则只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恋式认同,然而在身份建构过程中,无论易装术还是镜像其实都僭越了自我,窃取了自我在身份建构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使梅拉尼实际上成为由服饰和镜像塑造的被动客体。
三、自我身份的文化协商
通过梅拉尼在身份认同上采取的镜像与易装术两种策略,卡特反思了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对易装术与镜像的认知误区,但卡特对身份认同的思考显然并未停留在反思这两种认同误区的层面。实际上,她在小说中敏锐地注意到了易装术与镜像背后蕴含的文化机制,并进而指出这两种身份建构策略其实都建基于特定文化话语之上,寓于庞大的文化系统中,梅拉尼成长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实际上是不同文化话语之间交锋、协商的产物。
在这里笔者借用了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al Focault)的“话语”概念,所谓话语在福柯看来是指脱离了抽象文字和语言符号的“系统化地组织人们言说之物的运作”[23](80),是被还原到具体语境中实际应用的言语行为,是人们进行交流、沟通和理解、认知的单位,是被某种社会目的所决定的交际行为。在此基础上福柯进一步扩展了话语的内涵,将话语视作“所有陈述的普遍领域”,并将话语的性质重新界定为“陈述的独立集合”和“用于解释某些陈述的规则化运作”[34]。福柯在并未放弃话语独特性的前提下将所有得以言说于现实世界的陈述都称作话语,并强调正是话语的独特性使一种话语能够与其他话语区分开来。他认为话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规训本质,一种话语就是一套系统性行为规范或思维方式,整个世界都处在交织错杂的话语网络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被话语标记、交织的世界,包括人们说的话,关于事物的描述,关于肯定、疑问,关于已经发生的一切言语。”[24]
在此意义上,我们发现从最初自我身份建构开始,梅拉尼便已然身处不同文化话语中。她生于一个典型布尔乔亚式家庭,父亲是成功的作家,母亲优雅而多愁善感,他们强调着装,恪守礼节,居住在爱德华七世风格的房子里,并在成为有钱人后有意疏远了与贫穷亲戚之间的关系。他们重视宗教对个人道德的规约,追求“体面的生活”,其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依靠“与对立面的对比而产生”,他们歧视“商人与制造业者”,并将家庭的幸福视作其“床边的座右铭”。[25]
正如S•皮尔(S. Pile)所言:“家庭不仅是个人身份的表达,它还是个人身份的建构。”[26]显然,家庭就是一个小型文化圈,家庭成员的个性、心理、言谈举止无不受到这个文化圈的影响。梅拉尼的家庭环境使她看待外部世界的视野被烙上了深深的布尔乔亚文化印记,她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充满了布尔乔亚式的文学、历史与文化意象:她在镜前对自我肉体的开掘来自诗人约翰•邓恩歌颂女性肉体之美的《哀歌22:至他床上的情妇》,她对自身情欲的探索来自劳伦斯张扬自由与性爱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她对爱情的认识来自布莱克莫尔书写浪漫爱情的小说《罗娜•杜恩》,她阅读妇女杂志,认为女人应当在新婚之夜身穿象征纯洁的白色婚纱,她的玩具是极具布尔乔亚风格的爱德华熊,这一系列文本或文化符号使梅拉尼成为“一个布尔乔亚少女”[27]。在她看来,作为一个女人首先要成为母亲那样的端庄淑女,还要会施展各种手段取悦男性,因此她在镜子前才摆出妩媚甚至放荡的姿态,才在夜里穿上母亲的婚纱伪装成新娘。镜像与易装术使梅拉尼得以进入女性身份的象征秩序,并借助文化话语下符号媒介完成她的身份建构。正如林顿•佩奇(Linden Peach)所言,小说中梅拉尼的身份始终是由“外在于她自己的话语界定出来的”[3](75),其身份策略并非如她所认为的以自我为核心,建立在稳固的主体性基础上,而是受制于她身处的历史、文学和文化场域,被她所生活的布尔乔亚文化话语所塑造。
因此,小说中梅拉尼的自我身份建构实则是不同文化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父母空难后,失去镜像认同的梅拉尼不得不通过调整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来界定自我身份。正如安娜•M•桑切斯−埃尔切(Ana María Sánchez-Arce)所言,身份是自我“与外界世界社会交往的结果”,不仅包含“我们/别人认为我们是谁”,还包含“我们/他人是如何塑造我们关于自我的看法以及如何塑造我们思想所追随的话语”[28]。梅拉尼在小说里分别通过与菲利普舅舅以及与玛格丽特姐弟之间的交往行为来检视自我身份,在这些交往行为中包含着不同文化话语之间的博弈,它们分别是以梅拉尼父亲为代表的布尔乔亚文化话语,以菲利普为代表的传统维多利亚文化话语以及以玛格丽特姐弟为代表的英国60年代青年文化话语,梅拉尼的自我身份认同便是这些不同文化话语之间交锋的场域,其自我身份也是不同文化话语之间互相碰撞、协商的结果。
首先,菲利普是传统维多利亚文化话语的代表。他刻板保守,是旧时代的小手工业者和往昔帝国文明的怀旧客,体现了维多利亚社会最显著持久的元素——帝国意识、阶级意识和性压制,他经营的玩具铺因古老的装饰风格而被美国游客视作“狄更斯风格的商店”。他拒绝现代文明,家中没有任何电子产品,他视支票为“不自然”的东西而在买卖行为中拒绝使用,并因“圣诞节太商业化”而禁止家人过圣诞。他视女性为自己的附属品,给妻子的新婚礼物是象征奴役的哥特式项圈,并在生活中对妻子姐弟异常暴虐。此外,他憎恨新兴的布尔乔亚文化,曾将一名来玩具铺采访的杂志摄像师的摄像机摔烂,还逼迫梅拉尼以木偶的身份表演《琳达与天鹅》,试图通过操控梅拉尼实现自己对布尔乔亚阶层的报复,“我永远不能容忍你父亲,……不中用的杂种,他的两只手就从没弄脏过。”[11](54)因此,梅拉尼与菲利普的关系相当微妙,一方面,布尔乔亚文化背景使她对菲利普充满厌恶与鄙视,但另一方面,布尔乔亚的出身又使她在对待玛格丽特姐弟的态度上与菲利普保持一致,但同时,菲利普对家庭成员的暴虐又使她对其满怀恐惧和反抗心理。
尽管在梅拉尼看来对菲利普呆板空虚无聊,他居住的玩具铺简陋寒酸,浴室冰冷肮脏,这在梅拉尼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但从住进玩具铺那天开始,梅拉尼便试图主动努力融入新环境。清晨,她为舅舅一家煮茶,当费因告诉她菲利普不能容忍女人穿长裤后,她赶忙回房间将长裤换成裙子。可见,虽然并不情愿,但梅拉尼依然开始按照维多利亚文化话语来进行自我塑造,希望以此获得菲利普舅舅的认同。在对待玛格丽特姐弟的态度上,梅拉尼起初与菲利普出奇相似,她将他们视作低贱的人,不愿与他们交往,并开始将那些装扮时尚华贵的女性顾客称作“小气的贱女人”[11](101),而她的母亲显然也曾是这些女性中的一员。她不断告诉自己“以往奢侈的生活是不可靠的,是幻想出来的”,只有当下苛刻艰难的生活才是真正“所谓的生活”[11](99),用这种心理暗示擦抹自己的布尔乔亚文化印记。由此可见,在住进玩具铺之后,梅拉尼一直试图与菲利普代表的传统维多利亚的文化话语达成妥协,并通过这种文化协商塑造新的身份从而获得身份认同。
其次,玛格丽特姐弟——尤其是弟弟费因——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话语的代表。尽管有学者将费因与梅拉尼的感情视作“中产阶层女孩”与“工人阶层男孩”之间的爱情,并将其与菲利普之间的矛盾解读为工人阶层与手工业商人之间的矛盾[4](344),但小说中的费因并不是D•H•劳伦斯笔下粗野肮脏充满原始欲望的传统工人形象,他身上承载更多的是英国60年代兴起的青年文化元素。在穿着打扮上他既不像菲利普那般古板寒酸,也不像梅拉尼父亲那般时尚高雅,而是灯芯绒长裤加消防夹克,这也正是当时英国青年流行的穿戴扮相,此外,他还拥有绘画天分,其画作充斥离经叛道的恶魔、裸女和杀戮,并经常用怪诞的行走方式与歪斜戏谑的笑脸来激怒菲利普。在音乐、生活方式以及休闲消费等方面的姿态使费因成为与以菲利普为代表的“父辈文化”的反叛者,是“社会变革的隐喻”[29],在此意义上,与其说费因代表工人阶层不如说他实则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的代言人。
正因为此,梅拉尼对玛格丽特姐弟的感情也非常复杂。一方面,在布尔乔亚文化塑造下的梅拉尼对他们的种族身份、青年亚文化身份满含歧视与排斥心理。在伦敦初次见到费因与弗朗辛时,她便因其爱尔兰人的身份和他们的怪异扮相以及身上发出的浓烈体臭而对兄弟俩充满厌恶;同时,玛格丽特的苍白、憔悴、刻板、病态与自己母亲的优雅美丽完全是天壤之别。在梅拉尼看来,“他们很脏,是普通人”“他们活的像猪”[11](81)。可以说,起初梅拉尼对玛格丽特姐弟没有任何认同,她始终都以布尔乔亚式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们,通过保持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彰显自我身份。
但玩具铺孤独疏离的生活使她又异常渴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在目睹玛格丽特姐弟的晚间音乐会后,他们之间的亲密让她感到家的温暖,而家庭正是梅拉尼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场域,因此她愈发渴望融入这个团体。随着对玛格丽特姐弟日益深入的了解,梅拉尼开始接纳他们,并开始认同他们所代表的青年文化话语。首先,菲利普在家中的暴虐行径使梅拉尼产生了可怕的幻觉,她幻想自己住在蓝胡子的城堡,并被幻觉吓得晕厥过去。在玛格丽特姐弟的悉心照顾下,梅拉尼逐渐摆脱菲利普舅舅的阴影和自己恐怖的幻觉,开始将“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连在一起”[11](130)。其次,梅拉尼演出《琳达与天鹅》之后的当天夜里,费因偷偷毁掉并埋葬了菲利普的天鹅,有学者认为费因埋葬天鹅是其内心“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5](28),是父权等级的真正颠覆者[30]。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人造天鹅也是传统维多利亚文化话语的隐喻,象征着规训宰制下丧失自由的个体,因此,费因毁掉天鹅也具有了英国青年文化反抗传统维多利亚文化的意味。
费因对菲利普舅舅的反抗给了梅拉尼莫大的勇气,也令她对费因的感情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开始想象自己与费因未来的生活:
她知道有一天他们会结婚的……他们的家会一直是无法驱散的贫穷、肮脏、杂乱和寒酸……她所有的生活就是一群哭喊的孩子,要洗的衣服和马上要烤焦的吐司。永远不会有什么陶醉、浪漫和魅力。[11](189)
尽管梅拉尼依然本能地试图拒绝这种身份塑造,但无疑潜意识里她已经开始认同费因的生活。她违抗菲利普不许过圣诞的规定,为玛格丽特买了香水做礼物,并将自己珍藏的绿色礼服和珍珠项链全部送给她,“她要把她们彻底送出去,即使母亲在房顶某个地方看着……她觉得自己年轻、坚韧、勇敢,送走了她昔日的残迹”。[11](199−202)显然,这一切意味着她对以菲利普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文化和以父母为代表的布尔乔亚文化话语的背叛,在不同文化话语的碰撞下,梅拉尼逐渐成长起来,并开始认同以费因为代表的青年文化话语,“我们已经一起经历了所有这些,我们再也不会跟别人一样了。我们只能像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会互相相像。”[11](212)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梅拉尼的自我身份自始至终都处于不同文化话语的协商、塑造与交锋中,是未完成的。尽管幻想与费因的未来生活,但清晨起床后梅拉尼仍希望与费因同在一张床上的事实只是一场梦境;她仍会模仿妇女杂志中女性矫揉造作的口吻与费因交谈;当再次看到费因的瞳孔中自己的影子时,浮现在她脑海中的依然是约翰•邓恩歌颂爱情的诗歌;当目睹弗朗辛与姐姐乱伦之爱时,她在无比震惊之余表示了对乱伦行为的否定:“没有乱伦,我们家里没有。”[11](208)显然,在不同文化话语交织下梅拉尼的自我身份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与建构中,尽管她背叛了布尔乔亚文化与维多利亚文化对自我身份的塑造,但这两种文化话语仍会不时影响着她的言行及思考方式。小说结尾,伴随菲利普的狂怒与玩具铺的熊熊烈焰,梅拉尼与费因站在黑暗中“在慌乱的揣测里彼此凝望”[11](214)。无论这个结局意味着梅拉尼和费因最终抛弃旧有的性别对抗秩序,建立新的平等关系,还是意味着他们只是逃进了另一场等级秩序的花园[5](3−32),在卡特看来,玩具铺只是“一个世俗的伊甸园”[32],她仅仅给了梅拉尼走出伊甸园的勇气,而没有设定她的未来。正如伊莱恩•乔丹(Elaine Jordan)所言,卡特的小说从来不指向“结论或解决方法”,通过小说略显开放的结局,卡特似乎想告诉读者甚至连她本人也无法在当时为梅拉尼找到自我身份型构的最终答案。
乔安妮•崔维娜(Joanne Trevenna)曾经指出,在卡特的文本中存在一个“前性别主体状况”,也就是先验主体,但她并没有假定个人主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而是认为“前性别主体是不稳定和碎片化的”[33],因此卡特在对身份的处理上更加具有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特征。在小说中,小说主人公梅拉尼以易装术与镜像为身份建构策略,但对这两种策略的认知偏差导致她陷入身份断裂与缺失的困境。卡特不仅反思了身份建构过程中对易装术与镜像的认知误区,更重要的是,她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入手,深入考察了身份建构中的文化机制,指出身份并不是建立在先验主体基础之上,而是不同符码、话语体系、象征系统以及日常习俗构成的文化模式共同塑造起来的,是不同文化话语之间交锋、协商的产物。
注释:
① 关于斯图亚特•霍尔对身份问题的具体探讨可参见,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 Stuart Hall.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596-632.
② 神经性厌食症是一种进食障碍性疾病, 患者症状多为拒绝进食并伴随对自我身份的扭曲性认同, 如身体的发育导致患者对自我身份感知的陌生化和客体化, 厌食则能使其保持稳定的身体状态, 从而获得对身份意识的控制力. see Malson Helen. The Thin Woman: Femin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norexia Nervosa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3-5.
[1] Bristow, Joseph, Trev Lynn Broughton. The Infernal Desires of Angela Carter: Fiction Femininity, Feminism [M].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1997: 76.
[2] Wisker, Gina. At Home All Was Blood and Feathers: The Werewolf in the Kitchen—Angela Carter and Horror [C]// Jessica Bomarito. Gothic Literature: A Gale Critical Companion (Vol. 2). Farmington Hills: Gale, 2006: 184.
[3] Peach, Linden. Angela Carter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66.
[4] Smith, Patricia Juliana. “The Queen of the Waste Land”: The Endgames of Modernism in Angela Carter’s Magic Toyshop [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06(67:3): 338.
[5] Day, Aidan. Angela Carter: The Rational Glass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
[6] Fruchart, Anna Watz. Convulsive Beauty and Compulsive Desire: The Surrealist Pattern of Shadow Dance [C]// Rebecca Munford. Re-visiting Angela Carter: Texts, Contexts, Intertex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32.
[7] Carter, Angela. Note from the Front Line [C]// Angela Carter. Shaking a Leg. London: Penguin, 1997: 37.
[8]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 罗钢, 刘向愚.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09−211.
[9] Waugh, Patricia.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Continuities of Feminism [C]// James F. English. A Concise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197.
[10] 多丽丝•莱辛. 金色笔记[M]. 陈才宇, 刘新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8.
[11] 安吉拉•卡特. 魔幻玩具铺[M]. 张静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12] Myers, Tony. Slavoj Zizek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33.
[13]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 Stuart Hall.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603.
[14] Lacan, Jacques.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I Function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C]// Écrits. trans. Bruce Fink.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78.
[15] 安吉拉•卡特. 肉体与镜[C]// 严韵译. 烟火.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85.
[16] Tseelon, Efrat. Introduction: Masquerade and Identities [C]// Efrat Tseelon. Masquerade and Identities: Essays on gender, sexuality and margin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3.
[17] 罗兰•巴特. 谈《流行体系》[C]// 刘森尧译. 罗兰•巴特访谈录. 台北: 桂冠图书, 2004: 71.
[18] Goulding, Simon. Seeing the City, Reading the City, Mapping the City: Angela Carter’s The Magic Toyshop and the Sixties [C]// Sonya Andermahr. Angela Carter: New Critical Readings.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ePub ISBN: 978-1-4411-7776-6.
[19] Boden, Sharon. Consuming Pleasure on the Wedding Day: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being a Bride [C]// Emma Casey and Lydia Martens. Gender and Consumption: Domestic Cultures and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veryday Life. Aldershot: Ashgate, 2007: 114.
[20] Bedford, William and Angela Carter. Connoisseur of Unreality [J]. London Magazine, 1992, (Oct/Nov): 52.
[21] Craft-Fairchild, Catherine. Masquerade and Gender: Disguise and Female Iden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s by Women [M].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3: 52.
[22] Carter, Angela. Notes for a Theory of Sixties Style [C]// Angela Carter. Nothing Sacred: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Virago, 2012: 85.
[23]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M].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0: 49.
[24] Ruas, Charles.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C]// Michel Foucault, trans. Charles Ruas. Death and the Labyrinth: 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l.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uum, 2004: 179.
[25] 彼德•盖伊. 施尼兹勒的世纪: 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 1815—1914[M]. 梁永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4− 41.
[26] Pile S. The Body and the City: Psychoanalysis, Space and Subjectivi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55.
[27] Gamble, Sarah. The Fiction of Angela Carter: 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 [M]. Cambridge: Icon, 2001: 32.
[28] Sánchez-Arce, Ana María. Identity and Form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C]// Ana María Sánchez-Arce. Identity and Form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5.
[29] Hall, Stuart and John Clarke, Tony Jefferson,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C]//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4−11.
[30] Wyatt, Jean. The Violence of Gendering: Castration Images in Angela Carter’s The Magic Toyshop, The Passion of New Eve, and Peter and the Wolf [C]// Alison Easton. Angela Cart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73.
[31] Haffenden, John. Novelists in Interview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80.
[32] Jordan, Elaine. The Dangers of Angela Carter [C]// Lindsey Tucker. Critical Essays on Angela Carter. New York: Hall G K, 1998: 37.
[33] Trevenna, Joanne. Gender As Performance Questioning the Butlerification of Angela Carter’s Fiction [J].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002, 11(3): 274.
Mirror, masquerade and cultural negotiation: self-identity ofThe Magic Toyshop
CHENG Y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The Magic Toyshopis a novel of Angela Carter’s early creations which focused on self-identity. Its heroine Melanie considers mirror and masquerade as the strategies for identity construction, but her cognitive deviation of the two strategies lead her to the plight of breakage and loss of identity. The essay,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puts forward that both mirror and masquerade are built on the enormous cultural discourse system. Melanie’s identity is not the product of transcendental subject. Fashioned instead by the cultural model composed of different symbols, discourse system, symbol system and routine customs, Melanie’s self-identity is the product of the negoti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interaction.
The Magic Toyshop; self-identity; mirror; masquerade; cultual negotiation
I106.4
A
1672-3104(2015)04−0175−08
[编辑: 胡兴华]
2015−04−12;
2015−06−30
程毅(1983−),男,山东烟台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国当代文学,西方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