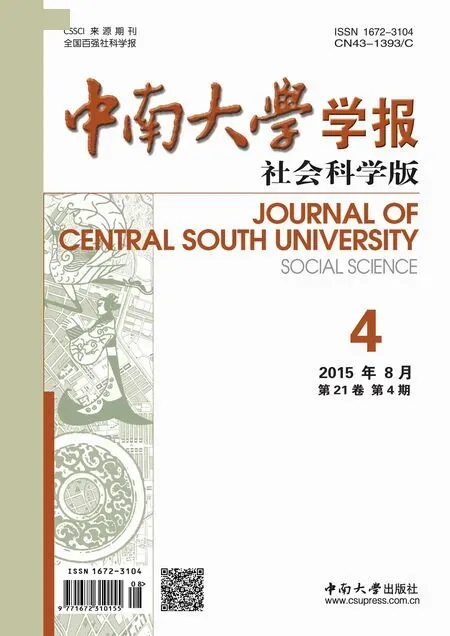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包容性人文主义”的生态向度
——杜维明生态伦理思想初探
2015-01-21林雄洲
林雄洲
(汕头大学社科部,广东汕头,515063)
“包容性人文主义”的生态向度
——杜维明生态伦理思想初探
林雄洲
(汕头大学社科部,广东汕头,515063)
杜维明“包容性人文主义”论以儒家思想为底模,以涵容自然与宗教为方向,以范导社会发展与生活信念为宗旨,是一种契合时代精神、具有明确生态向度的新型人文主义;其理论视域主要源自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揭示问题的根源在于由启蒙心态引发的“去精神”与“去自然”的世俗人文取向;其理论根基立足于传统天人合一观,力图通过重新改造使之同时涵纳自然与宗教;其理论旨归意在重塑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一种系于宗教情怀的儒家生态伦理。
杜维明;人文主义;启蒙心态;生态意识;天人合一;儒家生态伦理
“包容性人文主义”(Inclusive Humanism)①一词早在20世纪前半期就已出现,但缺乏对其细致深入的讨论。②较早予之以系统阐述特别是立足儒家思想进行理论建构的应推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在杜氏那里,所谓“包容性人文主义”,就是在高举理性旗帜的同时,注意自然情感与宗教情怀的培护,强调对理性暴力的约束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涵纳。概而言之,“包容性人文主义”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底模,以涵容自然与宗教为方向,以范导社会发展与生活信念为宗旨,契合时代精神的新型人文主义。这一理论在建构的过程中,无论就其视域、根基还是宗旨而言,都充分体现了对宇宙自然深沉的情感认同与道德关怀,因而具有明确的生态向度,较集中地体现了杜维明的生态伦理思想。系统梳理与客观评析“包容性人文主义”的生态向度,既有助于杜维明哲学思想的完整把握,也能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理论视域:生态危机的自觉反思
“人文主义”(humanism)的界定向来被视为难事,原因主要在于概念生成演变的时空跨度较大,意涵亦随之复杂多变。“人文”一词在古罗马时指文明与教养(humanus),与野蛮的外族相对;文艺复兴时期则强调人的尊严,与扼杀人性的教会相对;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一词(humanismus)直到启蒙运动时才首次出现,其含义既指接受文明的熏陶,也指人的价值与尊严。启蒙运动奠立的人文主义强调理性的力量与人的崇高地位,发展出了统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工具理性为主),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大量问题。这一困局逐渐引发学界反思,并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兴起了一股“新人文主义”思潮。“新人文主义”虽然仍以人为中心,仍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和理性,但开始批判启蒙以来人文主义所片面追求的物质性、工具性、技术性和实用性。然而,尽管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传统人文主义仍旧是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进一步反思、批判乃至超越它,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杜维明的“包容性人文主义”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着的恐怖主义、社会解体、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杜维明强调建立一种新的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的迫切性;同时指出,尽管现成的文明传统都不具备统合其他文明的一枝独秀地位,但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新人文主义思潮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契合的,“儒家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看来比启蒙时代以人类为中心的世俗人文主义更加切合当前的时代精神。”[1](632)基于这种认识,杜维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以儒家思想为底模的“包容性人文主义”概念,其意图“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儒家心目中的人文主义概念的广泛性或包容性,另一方面又为了使之同大家所熟悉的排他的世俗的人文主义区别开来”[2]。此后二三十年间,杜氏一直没有停止对此理论的诠释与发扬,并视之为21世纪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无论是明确地以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为思考起点,还是主动地与导致生态危机的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划清界线,都表明了杜维明拥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其关于世俗人文主义弊端的深入反思,尤其显示了“包容性人文主义”旗帜鲜明的生态视域。
所谓“世俗人文主义”,笼统而言,即上文所说的由启蒙运动奠立的人文主义;准确地说,则是以启蒙心态为核心的现代性意识。何谓“启蒙心态”?杜维明将“启蒙”区分为三类:一为启蒙运动,即17、18世纪发生于西方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二为启蒙理念,是一种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普遍性的观念意识,它主导了西方现代文明发展;三为启蒙心态,是一种固执于启蒙理念的心理积习或思维模式,对中国影响犹深。[3]在杜氏看来,启蒙心态虽然为人类社会开辟了许多利益领域和普世价值,但它作为近三百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弊端——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这是引发生态危机的主要思想根源。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将被高科技所笼罩的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认为它源自于现代观念的两种根本转化:“自然的终结”(人类对自然界的全面干涉)与“传统的终结”(人们对传统文化与习俗的弃绝)。尽管并未完全否定“风险社会”,吉氏仍认为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或多或少与此有关。[4]杜维明非常赞赏吉登斯的研究,指出其关于现代性特色的认识主要包含两点:“去精神”(或“去宗教”)(de-spirited)与“去自然”(de-natured),并认为这也是启蒙心态一直存在的两大盲点。[5]“去精神”即对宗教的排斥。启蒙运动从基督教传统蜕变而来,一开始就反对基督教的权威,要求去神圣化;此后,孔德又提出了影响很大的人类理智发展三阶段说,神学阶段被看作是未被理性光芒普照的蒙昧时刻。受此影响,韦伯也提出了“祛魅”(deenchanted)概念,将宗教视为迷信而祛除之。由此,人类理性精神得到空前高扬,并发展为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对敬畏力量的完全祛除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信奉落实又势必会导致对自然的征服与宰制,所以杜氏慨叹:“这个人类中心主义的致命伤就是没有办法了解生态环境对人类的重大意义,没有办法把人摆在更宽广的自然环境中,从而导致了非常大的混乱。”[5]这种对自然的宰制即是“去自然”。启蒙以来,人们在排斥宗教的同时也致力于发展经验科学,秉持“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相信自然可以被人所了解、认识乃至改变。杜维明认为这一观念背后携带着一种“浮士德精神”,“即为了追求知识,可以放弃自己的灵魂,跟魔鬼打交道。也就是说,只要追求真理、追求新的经验,就是人之为人的最高理想。这种思想是有侵略性的,所以就形成了两种结果,一个是边缘化精神世界,另一个是宰制自然。”[6]所以,“去自然”的观念表现出了强烈的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从工具和目的的角度来理解理性,以有无实用性、有无价值、对人类是否有益为衡量标准,实为一种闭塞、专断、傲慢的意识形态——科学主义,乃由偏激的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所铸成。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有本质不同,后者的特征是严格、开放、谦虚、多元,正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
可见,“去精神”与“去自然”是一事之两面,不仅“去精神”必会导致宰制自然,“去自然”也往往走向排斥宗教;而其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主义便是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主导理念。面对生态问题的挑战,杜维明断言,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启蒙心态“对现在复杂的多元世界、生态环保的要求所带来的问题没办法处理”[5]。这就表明,超越启蒙、走出世俗人文主义、重建新的人文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的必然要求与重要任务。
二、理论根基:立足于天人合一观
目前对世俗人文主义展开批判的力量主要来自西方学界,如环保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多元主义等思潮都对启蒙所造成的困境作出了重要的回应。这些回应虽然均以工具理性为反思焦点,立场却可分为截然不同之两种:一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理性解构立场。启蒙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极度张扬,造就了理性的狂妄,将世界的复杂多样性化约为简单的符号与原则,相信人类凭借理性所创造的程序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解构主义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将人类推入“观念符号暴力”的困境之中,只有将之彻底消解,才能使人的精神世界摆脱牢笼、重获自由。所以,德里达深挖理性主义的根,一直挖到语言本身,挖到了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逻各斯的出现就是理性的出现,只有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才能真正解构理性。然而,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解构主义尽管对启蒙的缺失有深刻洞识,其否定理性的极端立场却是破而不立的,“有堕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陷阱的危险”[7]。不仅解构主义,环保主义等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也都有此弊病。对此,西方学界(包括后现代主义内部)早有警觉,发出了不同于理性解构的其他声音,此即回应启蒙困境的另一种立场:理性重建,以哈贝马斯最为知名。哈氏承认启蒙理性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近代意识哲学的产物,它由于强调主体的自我保存与发展,走向了对外的征服、控制与攫取,变成了工具理性。但哈氏反对彻底否定工具理性,认为启蒙的任务仍未完成,还应继续发展,现在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过少,必须进一步扩大理性的层面。因此,他在工具理性之外,又提出了着眼于主体间性的“沟通理性”,以此应对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尽管更认可哈贝马斯将理性重新带回生活世界的道路,杜维明也指出了其理论在自然与宗教两方面的重要缺失:“(哈贝马斯的研究)着眼于人类世界,特别是重视个人之间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自然和宗教于无意中,甚至有意地被贬为无关宏旨的背景。”[8]可见,无论哪一种立场,其自身都存在固有的困难,不足以独力承担超越世俗人文主义、重建新人文主义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儒学具有独特的价值:“面对21世纪,如果有一种比较涵盖性、整合性的人类思想,儒家无疑是非常杰出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可以涵盖一切。……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宗教都是涵盖性的,但儒家的涵盖性是多元的,还有很多不同的涵盖性。”[9]
那么,与世俗人文主义及其他思潮相比,儒家人文主义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其多元的涵盖性(涵盖性即包容性)具体表现在哪里?杜维明给出的回答是:“儒家人文主义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它既不反精神,也不反自然;既是自然的,又是精神的。”[10]这恰好映照、弥补了世俗人文主义的两个盲点。进一步的追问是,儒家人文主义为什么具有这种包容性?能够涵纳自然与精神的到底是什么观念?杜氏接着指出,正是天人合一观赋予了儒家人文主义以包容性:“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包容的,它基于一种‘anthropocosmic’观念,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1](19)在此,“anthropocosmic”是杜维明指称天人合一观的新造术语,意在强调新轴心时代人文主义的无所不包性质。在杜氏看来,天人合一观不仅是儒家人文主义的依据,也是构建新人文主义(“包容性人文主义”)的理论根基。关于天人合一观的包容性,杜氏常引用王阳明《大学问》中“大人者……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一段予以说明。阳明把“心之仁”视为连接人与宇宙世界的根本所在,等于“做出了一个本体论的断言:与天地万物同情共感的能力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12]。立基于此的儒家人文主义于是具有了极广泛的包容性:一是对自然的包容。人有仁心而能与天地万物一体,不仅包括同类的孺子、有知觉的鸟兽、有生意的草木,甚至包括无生命的瓦石,爱护自然是人之为人的必然要求。二是对天道的包容。仁心并非后天所有,也不因大人、小人而有别,而是每个人类个体禀自天命所共有;一方面人之生命意义植根于天,另一方面天道的彰显也有待于人,天人从本体上即是合一的。
当然,儒家人文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它经历了一个从神圣到世俗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受到现代西方启蒙思想冲击以前,儒家本是一种神圣的人文主义。这在古典时期的《大学》《中庸》中已展露无遗。《大学》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修行进路,体现的就是一种从宇宙背景看待人类处境的世界观,将人类视为宇宙进程的积极参与者,肩负着关怀自然环境的责任。《中庸》则明确了人类“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使命,更加开拓了儒家涵纳整个宇宙自然的博大胸怀,宋明儒学的“万物一体”观即由此发展而来。然而,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积贫积弱,引发了儒家人文主义的世俗化进程。肩负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中国主流知识界在实用主义精神的指导下反思批判儒学,以是否符合西方定义的现代化为标准来衡量并改造古典儒家的神圣人文主义。其结果是,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等观念大行其道,在儒家传统的内、外部同时发力,将之改造为与启蒙精神接轨的世俗人文主义。这种启蒙心态在中国大陆是压倒性的,在当前西方深入反思启蒙弊端的情况下依旧被奉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圭臬。在此情况下,自然与精神不可能有其位置。所以,尽管西方“生态环保发展了,中国现在生态环保的情况非常糟糕”[13];之所以生态环保主义的建构者都是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处于缺席状态,原因主要在于“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当做遥远的回响”[13]。这个失落的传统,就是作为“包容性人文主义”根基的儒家天人合一观。杜维明相信,这种天人合一观与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学有相通之处,甚至可被视为“深度生态学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典范”[14],具有不言而喻的生态意蕴。
三、理论宗旨:系于宗教情怀的生态伦理
天人合一观不言而喻的生态意蕴指的就是:“它拥有无尽的可资发展更全面的环境伦理学的伦理资源,包括典籍文献、礼仪习俗、社会规范和政治政策等。从古代起,儒家就注意与自然保持和谐,接受自然的适当限度和范围。这种关注表现在他们用大量的方式培养被认为是同属个人与宇宙的美德。他们的关注还包括用生物的形象来描绘修身的过程。在人与宇宙之间实现深层多样的对应,是儒家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观念,对于救治当前的生态危机也有现实意义。”[11](19)然而,杜维明强调指出,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并不可行,因为近代以来儒学的价值理念已被启蒙心态所消解,异化的观念和事实已然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想回到大自然的亲子关系,回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事实上是一个倒退”[15]。对传统的真正回归,必须走出世俗化的儒家人文主义,并进一步深入发掘天人合一观的思想资源,以此重建一种切合时代精神的新人文主义。
对于世俗儒家人文主义的批判早在20世纪后半期就已开始,大陆、香港、台湾三位新儒家代表冯友兰、钱穆、唐君毅都不约而同地重提了天人合一观,并视之为儒学传统对人类最有意义的贡献。对此,杜维明评价道:“标志着一个回归儒家并重估儒家思想的运动”,“就回归而言,人类-宇宙统一的世界观通过强调天人之间的互动共感唱出了不同于当代中国世俗人文主义的曲调。就重估儒家思想而言,这种世界观通过强调人与天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标志着儒学的生态转向。”[12]尽管三位学者未必意识到其论断所隐含的重要生态意义,但他们对人类仁爱之心与天人和合观念的弘扬,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乃至排斥性二分思维模式的新视野,从而也为杜维明的“包容性人文主义”理论提供了资源与灵感。当然,代表时代精神的“包容性人文主义”又要求继续发掘天人合一观的潜在用途,找寻更多的与现实相应的思想资源。那么,具体应如何掘寻呢?
较之德里达的理性解构立场,杜维明更认可哈贝马斯的理性重构道路。尽管哈氏的理路存在着重大的缺失,但人类问题的解决除理性之外别无他途。据此,“包容性人文主义”的理论定位主要是以儒学为中心,通过拓宽启蒙方案的界域,扫除启蒙的主要盲点,最后实现对启蒙心态的超越。这首先需要摒弃笛卡尔以来的排斥性二分思维,代之以一种对话式(dialogic)的思维模式,即与轴心文明展开对话,为进一步挖掘天人合一资源、超越世俗人文主义确立思想的参照系。其中,杜氏尤其强调以印度文明为参照,因为“印度最有价值的财产就是它层次分明的丰富精神景观”,如果认真以之为参照,中国本土的大乘佛教、道教以及儒家人文主义都将大行于世。[12]杜氏虽然强调新人文主义必须同时整合自然与宗教两个层面,但其整合理念主要是以宗教包纳自然,在儒学人文主义不排斥自然与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其宗教性,由此更好地将自然层面整合进儒学之中,“儒家的一个趋向,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那么现在更要增加一点,就是对宗教有敏感”[15];“虽然还难以确证宗教和生态为了共同的关怀将会走到一起,但是宗教的宽容通常具有生态的情怀。”[12]基于此认识,杜维明相信一种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的新观念必然需要宗教的意识,要求为自然注入超越的意义,“生态问题促使所有宗教传统重新检讨它们关于地球的预先设定,只做有限的调整以便容纳生态的层面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把自然神圣化。这可能需要在基本理论上进行重建工作,把地球的神圣性视为天授。……有必要在更阔大的人-神关系中思考有关自然的理论。”[12]当然,强调宗教层面的整合并不是想把儒家改造成为基督教式有神的宗教组织,因为儒家传统中完全没有此类资源,将外来的解释模式强加进儒学的作法并不可取。然而,也不能简单地说儒学就必然不是宗教,因为儒学虽然入世却也有向往天道的维度,此即人伦日用间体现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相信人可以通过“尽心知性”而“知天”乃至“赞天地之化育”。所以,宗教层面的发掘不是要为儒学融入上帝、未来天国、彼岸世界等观念,而是重在阐发儒学不离人伦日用的天道维度,把终极关怀的焦点集中到人类居住的地球和生存的世界上。杜维明之所以特别赞赏印度哲人巴拉苏布拉马连(Balasubramanian)将儒家界定为“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的作法,并多次借此指称“包容性人文主义”,原因即在于此。
“精神人文主义”即指向天人和谐的终极关怀,而和谐的最终达成往往需要经过四邻、朋友、民族、国家、世界、地球以及宇宙等各种中间组织的多重协调,所以和谐的本质就决定了“包容性人文主义”须照顾到四个不可分割的维度:自我、群体、自然与天道,以及由此四维相互联系形成的三层关系:自我与群体的依存,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心与天道的合一。四维关系的调谐不仅寓示了儒学的宗教性,也彰显了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构成了杜维明儒家生态伦理的一套认识论与方法论。首先,自我转化要求走出个人主义。通过不断地修身,人能够为自我实现创造出内在的价值源泉,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独立的道德行为者。但是,一个独立的道德行为者不能只满足于“成己”,更应追求“成物”,自我转化必然要求从小体到大体的突破,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自我超越过程。因此,“一种开放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必须基于超越自私自利与自我主义的能力。”[16]其次,自我与群体的依存要求超越工具理性。走向群体的自我不是只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它绝非离群索居的孤立个体,而是一个经验中的和实践着的人际关系的中心。在此情况下,“正如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论证的,使我们能够在社会中进行持续的、有成效的交流的,无疑是沟通理性而非工具理性。”[17]融入群体,不仅意味着对个人主义的超越,同时也是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再次,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要求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儒家对人类繁荣的强调不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它绝不因人类利益而罔顾其他非人类的存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对应的只是作为利益主体、价值主体的人类,而非作为德性主体的人类,儒家正是通过后者来调谐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其基于德性修养的“参赞天地之化育”表现了一种摒弃狭隘人类中心主义、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最高理想。最后,人心与天道的合一必然导向对宇宙自然的终极关怀。鉴于启蒙心态排斥自然与宗教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单纯基于德性的天人合一并不足以充分唤起人类的生态关怀意识,必须“强调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层面”[12],借宗教情怀以激发生态意识。这就需要预设对自然界的敬畏,为自然界注入超越的意义,从而也就寓含了一种终极的自然关怀。
四、简要评论
杜维明虽然不是“包容性人文主义”的最早提出者,但他立基比较文化理念、以儒学为底模的“包容性人文主义”理论建构,无论是对启蒙人文主义的反思批判,还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阐发重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就其生态向度而言,可以简要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包容性人文主义”的生态向度体现了异于前辈新儒家的理论进境。首先,杜维明将儒学重塑为一种“天人调谐”(anthropocosmic)的型态,它以自我转化为核心,追求成为宇宙自然参与者、保护者以及共同创造者的君子人格,并以此为儒家生态伦理的根基,这种与时俱进的诠释有力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华裔学者李晨阳先生对此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杜氏的生态伦理构想“如果成功,将能帮助儒学应对环境的挑战”[18]。其次,杜维明所提出的生态伦理构想立基于儒学的宗教性,正是对天道神圣性的信仰推动了自我在四维关系中的终极转化。这种“终极的自我转化”作为处于关系中的公共行为以及回应天道的信仰对话,不仅迥异于康德作为自律主体的自我,而且也有别于牟宗三作为超越主体的真我,显示了杜氏的理论创造性,是其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19]
第二,与西方生态哲学相比,杜维明基于“包容性人文主义”的生态思考具有独特的价值。环境保护主义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作法尽管有其深刻性,却存在着破而不立的弊病。有鉴于此,杜维明倡导一种包容科学技术的环保伦理观——深度生态学。杜氏非常欣赏深度生态学,且常自豪地视儒家天人合一观为其典范。然而,从“包容性人文主义”出发,其儒家生态伦理构想与深度生态学实际上存在着关键的差异。表面上看,两者都强调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在与宇宙自然的关系网络中达成自我实现。但是,深度生态学一方面从生态圈平等主义出发否定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要求人发挥道德主体地位以保护、发展生态自然,这一革命性思想不仅过分依赖人的道德觉悟而缺乏实践力,而且也未能从理论上充分说明人何以能够成为道德主体。与之不同,儒家生态伦理并不采取一般人难以接受的生物平等进路,而是从“天命之性”的儒学传统出发肯定“人是最高的价值”[1](537),在承认人与其他自然物存在价值差异的前提下追求成己成物。当然,“人是最高的价值”强调的不是人在主客对待关系中的价值主体地位,而是人因禀具天命善性而可以知觉、同情他物,进而可以成为大自然的参与者、保护者、共同创造者的德性能力。儒家生态伦理因避免将人物化(与物平等)而显得更切合实际,也因承继传统思想而更有理论说服力。
第三,杜维明关于儒家生态伦理的构想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落实。龚鹏程先生在评论现代新儒家的工作时指出,他们对时代课题的论议“多半只是虚地谈”[20]。所谓“虚地谈”,指的是重在评估理念的可行性与目的性而缺乏一套完整系统的建设规划与操作程序。尽管龚氏的批评对象主要是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但对于杜维明的生态伦理构想来说也同样有效。后者的论说,更多的是性质与意义的描述,对理论的整体框架与具体构成则较少措意。这种轮廓式的议论当然只能算是“虚地谈”。更深一层看,对于一种生态伦理而言,建设成体系的理论不是终点,是否具有可行性才是根本指标。这种将理论转化成实际行动的工作杜维明也做得不够,李晨阳就此指出:“为了发展一种成熟的儒家环境哲学,儒家思想家必须认真讨论这个议题(指理论落实为行动的议题——笔者按)。任何明智的、可行的、实用的儒家环境哲学都必定是儒家思想家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结果。”[18]
注释:
① 关于“inclusive humanism”一词,中文的翻译有多种,如“包容(性)的人文主义”“涵盖(性)的人文主义”等,本文将之统译为“包容性人文主义”。
②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哈特(Joseph K. Hart)在动乱的时代背景下就已提出,人类要重归和平,必须创造一种视野广阔、生命力旺盛、足以主导现代“工具”且具有建设性的文化,即“一种新的、广泛包容的人文主义”;并认为,这种新人文主义将涵括人类全部的精神生活与道德生活。参见Joseph K. Hart. The General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Crisis[J].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941,(3):612-616。哈特关于“包容性人文主义”的论说无疑极具远见,可惜除了方向的宣示外,并未提出具体的理论建设规划。
[1] 杜维明文集·第四卷[C]. 郭齐勇, 郑文龙编.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
[2] 杜维明文集·第三卷[C]. 郭齐勇, 郑文龙编.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 463.
[3] 杜维明文集·第五卷[C]. 郭齐勇, 郑文龙编.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 504.
[4] Anthony Giddens.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J]. The Modern Law Review, 1999(1): 1−10.
[5] 杜维明.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J]. 回族研究, 2003(3): 5−13.
[6] 杜维明. 儒家心性之学的当代意义[J]. 开放时代, 2011(4): 102−121.
[7] 杜维明, 衣俊卿.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J]. 求是学刊, 2009(1): 5−18.
[8] 杜维明. 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 一种儒家视角[J]. 中外法学, 2010(3): 326−341.
[9] 杜维明. 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4): 214−222.
[10] Tu Weiming. Sociality, Individuality and Anthropocosmic Vision in Confucian Humanism [C]// Marthe Chandler and Ronnie Littlejohn. Polishing the Chinese Mirror: Essays in Honor of Henry Rosemont, Jr Chicago: Open Court, 2007: 158.
[11] Tu Weiming.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C]//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H. Berthrong.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 杜维明. 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 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J]. 中国哲学史, 2002(2): 5−20.
[13] 杜维明. 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J].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2008(4): 1−8.
[14] 杜维明. 杜维明访谈录(之一)[J]. 贵州大学学报, 1998(3): 58−65.
[15] 杜维明. 儒家人文精神与生态[J]. 中国哲学史, 2003(1): 6−8.
[16] Tu Weiming. Family,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global ethic as a modern confucian quest [J]. Social Semiotics, 1998, (2/3): 283−295.
[17] Tu Weiming. Self-Cultivation as education embodying humanity [C]// David M. Steiner.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1998. Bowling Green: Philosophy Documentation Centre,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1999: 34.
[18] Chenyang Li. Fiv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for confucianism [J]. 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 2012(1): 53−68.
[19] Wan Sze-kar. The Viability of Confucian Transcendence: Grappling with TU Weimi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J]. Dao, 2008(4): 407−421.
[20] 龚鹏程. 儒学新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22.
On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inclusive humanism: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u Weiming’s ecological ethics
LIN Xiongzhou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China)
Tu Weiming’s inclusive humanism with Confucianism as its base, with nature and religion as its direction, and with guid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iving faith as its aim, is a new humanism that fit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has a clear ecological dimension. Its horizon mainly comes from the deep reflec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revealing that the root of problem is a de-spirited and de-natured value orientation caused by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Its foundation is “the harmony of heaven and man”, which attempts to embrace, through reform, both nature and religion simultaneously. Its aim is to reconstruct new outlooks of world and life, and one important aspect is the Confucian ecological ethics with religious feelings.
Tu Weiming; humanism;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harmony of heaven and man; Confucian ecological ethics
B26
A
1672-3104(2015)04−0169−06
[编辑:颜关明]
2014−10−13;
2014−12−11
林雄洲(1982−),男,广东汕头人,汕头大学社科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生态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