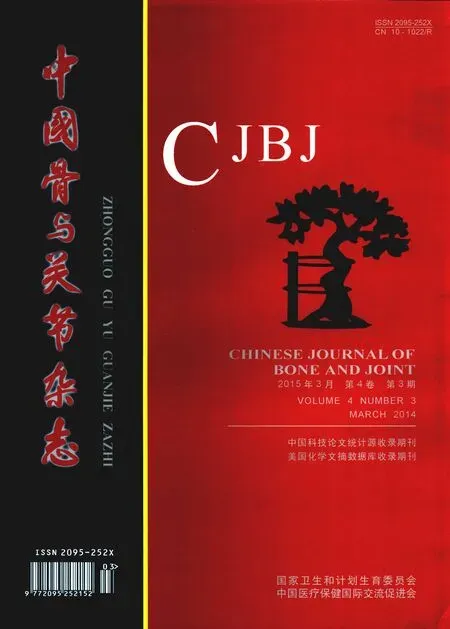重视症状与影像的综合评估 阶梯化治疗退变性脊柱侧凸
2015-01-21姜建元
姜建元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退变性脊柱侧凸 ( degenerative scoliosis,DS ) 的临床发病率逐年增多,如何进行合理的临床诊疗逐渐成为脊柱外科领域的学术热点和国内外广大脊柱外科医师关注的焦点问题。DS 患者影像学表现复杂多样、临床症状轻重不一,采取统一的干预方案显然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对于某些影像学表现为较严重的侧凸畸形,但临床仅伴有轻微症状,甚至无明显不适的 DS 患者,其侧凸角度的大小对治疗选择的影响有限。故重视临床症状与影像学表现的综合评估,以此进行临床干预方案的选择是 DS 临床阶梯化治疗的关键所在。
一、重视症状与影像的综合评估
1. DS 仅是一个影像学概念:成人脊柱侧凸是指年龄 > 20 岁,冠状面 Cobb’s 角 > 10° 的脊柱畸形。其中40 岁后新出现、多集中在腰段、伴有腰椎退变性改变 ( 或侧凸由退变引起 ) 的脊柱侧凸畸形即为 DS。其基于椎间盘和椎小关节严重的退行性改变、椎体间稳定性降低而出现,影像特点是腰段严重的退行性改变,侧凸角度一般不大,顶椎位置多存在明显的侧方滑移或旋转滑移。该概念仅从影像学角度对 DS 进行了阐述,并未包含临床症状与体征的界定。故严格意义上讲,DS 仅为一个影像学概念[1-5]。
2. 并非所有的症状都来自侧凸畸形:多项研究表明,DS 在老年人群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但多数个体可以长时间不伴有任何不适症状。出现症状的 DS 患者常伴有中度至重度的腰痛以及局限于侧凸节段的椎管狭窄症状,伴或不伴有根性症状。由于 DS 多伴有腰段严重的退行性改变,包括侧向滑移、节段不稳、椎管狭窄、关节突关节炎等,故 DS 人群的临床症状并不能全部归因于侧凸畸形,而是由多方面因素所致[6]。腰痛症状可能有复杂的伴随症状,因此,临床上应重点关注每个个体疼痛的特点,并进一步明确症状的来源部位和责任节段,这与后期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最终的临床预后密切相关。
腰痛发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腰部肌肉强度不足,关节突关节炎,椎间盘退变 (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IDD ),躯体矢状位或冠状位的显性或者隐性失稳 ( 后凸畸形或平背畸形 ),椎体的滑脱或者侧向滑移[7-8]。肌肉疲劳导致的,与直立活动密切相关的疼痛,即为轴性腰痛。其常表现为长时间直立时加重 ( 或仅在直立或坐位时发生 ),或在某种特定的位置或者活动时发生,平卧时缓解。位于髂嵴和骶骨的肌肉酸痛常成为导致整个脊柱区域疼痛不适的触发点,遍布于整个椎旁肌区域的疼痛无法继续维持脊柱的稳定,从而也触发腰痛,此现象在腰椎前凸丢失患者中尤为明显。此外,椎旁肌疲劳也是脊柱过度载荷及失代偿引发的平背畸形综合征的显著表现[9-10]。事实上,这也间接证实了侧凸患者的腰痛为机械性腰痛。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对该类患者进行减压联合融合内固定治疗,仍有部分患者腰痛无法得到明显缓解,因为小关节来源的疼痛症状可蔓延至侧凸累及范围之外[1]。腰痛在侧凸的凹侧与凸侧均可发生。侧凸凹侧的疼痛常由小关节及椎间隙退变 ( 包括 IDD、韧带的牵张撕裂、骨赘等 ) 引起,矢状位的失稳程度与此腰痛呈线性相关,疼痛部位常位于侧凸的凹侧中心区域并向四周弥散。椎体的侧滑程度,胸腰段后凸、腰椎前凸的丢失程度,终板 ( 特别是 L3、L4上终板 ) 的倾斜程度以及椎体的旋转程度均与腰痛程度直接相关,而与腰椎侧凸角度和侧凸畸形累及的椎体数量无明确相关性[8]。
除腰痛症状,DS 患者常会伴有根性疼痛,伴或不伴神经源性间歇性跛行。有研究提示此类患者的根性症状中,15% 会自发缓解,40% 在 2~3 年随访中症状不断加重以致需要外科干预,其余 45% 的患者能在长时间内维持相对稳定[6]。一般认为,退变及侧凸的进展均会导致椎管或者根管狭窄。侧凸患者凸侧神经根的牵拉以及凹侧根管 ( 特别是顶椎节段 ) 的狭窄导致的神经根受压会引起根性症状及椎管狭窄症状,股前区的根性疼痛与椎体的旋转程度联系更为密切,特别是在 L3~4及 L4~5节段[2,11-12]。而单纯退变引起的黄韧带增生钙化、椎间盘突出以及小关节退变也能引起类似症状,但无法通过躯干前屈获得缓解。因此,临床上需要分析患者的根性症状及间歇性跛行症状的来源,主要处理椎管狭窄还是矫正畸形阻止侧凸发展,该问题的明确对于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非常重要。Zeng 等[13]在 2012 年根据症状把 DS 患者分为椎管狭窄症状组 ( 如由椎管狭窄引起的下肢疼痛麻木等根性症状,主要手术方式为减压伴或不伴后路固定 ) 与侧凸组 ( 包括侧凸进展、腰痛为主要症状,腿痛症状不明显的患者,主要处理方式为矫形,前路 / 后路固定,伴或者不伴减压 ),结果显示通过症状将患者进行分类治疗的诊疗方式切实可行,两组均获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于那些具有退变和侧凸同时造成的临床症状,常常需要选择减压术合并长节段融合术。急性加剧的神经功能损害症状在DS 患者中并不常见,可能是椎间盘组织突然进入椎管直接压迫神经结构,或是侧凸进展导致突然失代偿所造成[7,9-10]。
3. 重视侧凸进展因素的评估:据报道,DS 的发生率在 50 岁以上的人群中为 6%~68% 并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步上升,且右侧凸随着年龄增长进展程度大于左侧凸。在一份无侧凸病史 60 人 ( 50~84 岁 ) 的研究中,22 例 ( 36.7% ) 出现了 DS ( 平均 13° )[1,3,5,14];Robin 等[15]对 160 例腰椎曲度较差的患者进行随访,在 7 年的时间内有 55 例 ( 34.4% ) 出现了侧凸表现。现在认为,在中老年人群中,年龄 > 65 岁、终板侧缘出现 > 5 mm的骨赘或者出现 > 3° 的非对称性椎间隙成角为侧凸发生的危险因素[16-17]。此外,由于大量患者为 > 50 岁的女性,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绝经期后的骨质疏松也是导致侧凸发生的一个潜在因素,但仍有一部分学者持不同意见[14,17]。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报道说明何种侧凸患者需要密切随访并治疗,无干预的 DS 自然转归也不清楚。有文献报道,侧凸会以每年 1°~6° ( 平均 3° ) 的速度进展,且在不同年龄及性别的患者中进展程度无异[14]。虽然侧凸也会通过椎间隙或者椎体的楔形变自发纠正,但在临床中仍需要十分重视并能够准确判断侧凸是否会进展加重[18]。综合看来,Cobb’s 角 > 30°,顶椎旋转程度在 Nash-Moe II 级 ( 也有报道认为 III 级,或者旋转 30% ) 以上,顶椎上下椎间盘存在不对称性退变,顶椎的侧向滑移超过 6 mm,L5椎体位于髂棘连线以上,存在 L3节段以下特别是 L5~S1IDD 的侧凸进展可能性较大[7-8,14,17]。对于 Cobb’s 角 < 30° 的患者,Chin等[19]认为其侧凸也会进展,并可能突然加重并呈非线性变化。这种现象在 > 69 岁并伴有 5 mm 侧向滑移的左旋型脊柱侧凸女性患者中尤为明显。对于影响 DS 长期转归资料较少,Jimbo 等[20]在 2012 年曾经对 144 例女性患者进行了长达 12 年的随访,结果显示发病年龄较小、L4椎体较小、腰椎前凸角度小、侧凸程度大以及L4终板倾斜角度大是 DS 的始动因素;而不对称的 IDD、L4椎体小为退变进展的危险因素。
二、DS 的阶梯治疗策略
众所周知,矫形和美观并非 DS 临床治疗的主要目的。首先要对临床症状以及症状与影像学表现的一致性方面进行评估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影像学评估结果选择合理的临床干预方案。
( 一 ) 正确把握 DS 的手术指征
对于无症状的 DS 患者,并不需要进行特殊处理,但是周期性随访侧凸进展程度仍十分必要。手术只在积极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方能考虑。DS 患者中,严重的腰痛是最常见的手术指征,然而腰痛的程度在每个个体中描述不同,也颇为主观,无法进行严格标准化。此外,因手术对患者腰痛的缓解效果尚不明确,因此术前 ( 特别是在行融合术前 ) ,须告知患者疼痛可能不会完全缓解。除腰痛外,伴有矢状位失稳的进展性侧凸、伴有严重根性疼痛的侧凸同时伴或不伴神经功能受损、间歇性跛行、出现进行性神经功能损伤也是常见的手术指征[1-3,8]。
手术治疗的主要目的为:通过创伤最小的术式解除神经压迫、缓解腰痛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重建脊柱在冠状位及矢状位的稳定性,同时矫正畸形,实现牢固的骨性融合,尽量避免二次手术;而对于同时有椎管狭窄症状的患者,须解除对神经组织的压迫,缓解根性症状及间歇性跛行[2,8,14]。手术须全面考虑患者的综合情况,力求做到安全、有效,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至最低。相比微创手术,传统的开放手术能更好地恢复患者的矢状面平衡[21-22]。最理想的办法即采用创伤最小的术式 ( 常为单纯后路,包括减压及固定 ) 通过一次手术解决问题。腰椎对生理前凸丢失的耐受力较低,因此手术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重建矢状位稳定,但并不要求完全矫正,仅须维持腰椎前凸与骶骨倾斜角度相对平衡即可[23]。腰椎生理前凸与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提高息息相关,单纯后路固定常难以重建腰椎前凸,且后柱的短缩与固定常常导致椎间孔的进一步狭窄,因此需要前柱的支撑 ( 如椎间融合 ) 或者椎体截骨[24]。因为 DS 患者的年龄跨度较大,临床症状各异,伴随疾病多,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术式选择指南,手术方案必须针对每个患者进行个体化制订,充分考虑患者主诉发生的原因,区分主要是由椎管狭窄还是由脊柱畸形引起的。
( 二 ) 阶梯化干预策略与融合节段的选择
1. 阶梯化干预策略:Silva 和 Lenke[17]在综合分析临床症状、疼痛来源、节段稳定性、矢状面平衡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 DS 患者的手术治疗提出了 6 级干预策略,具体为:( 1 ) 单纯减压,适用指征为:中央管狭窄引起的神经源性间歇性跛行患者,仅须进行有限的椎管减压;影像学表现为:椎体前方骨赘形成、侧向滑移 < 2 mm、具有良好的矢状面 / 冠状面平衡;患者无或仅有轻微腰痛和 ( 或 ) 畸形相关症状,侧凸 < 30°,没有明显的胸椎后凸畸形和 ( 或 ) 失平衡。需要指出的是单纯减压可能导致畸形进展和症状加重,不能用于侧隐窝及椎间孔狭窄者[1,21]。( 2 ) 减压 + 短节段后路融合内固定,适用指征为:中央管和 ( 或 ) 侧隐窝、椎间孔狭窄引起的神经根性症状,需要进行广泛减压;影像学表现为:侧凸 < 30°、侧向滑移 < 2 mm,但减压部位的椎体前方无明显骨赘形成;患者无或仅有轻微腰痛和 ( 或 ) 畸形相关症状,没有明显的胸椎后凸畸形、患者的总体平衡尚可。( 3 ) 腰弯融合内固定 + 必要的减压,适用指征为:侧凸畸形引起的腰痛症状较为明显;影像学表现为:侧凸 > 45°、侧向滑移 > 2 mm、手术节段椎体前方缺少骨赘形成;腰椎无明显的后凸畸形,脊柱的矢状面总体平衡尚可。( 4 ) 减压 + 前后路联合融合内固定,适用指征为:椎管狭窄严重、腰痛和畸形症状明显;腰椎后凸畸形明显;影像学表现为:矢状面总体平衡尚可,而且椎体前方无明显骨赘形成、无明显的胸椎后凸畸形、侧向滑移 > 2 mm。( 5 ) 融合内固定延伸至胸椎,适用指征为:椎管狭窄严重、腰痛和畸形症状明显;影像学表现为:椎体前方无明显骨赘形成、侧向滑移 > 2 mm;伴有明显的矢状位总体失平衡,如:明显的胸椎后凸畸形,但畸形的柔韧性尚可。另外,当脊柱总体失平衡或冠状面失平衡时也要考虑进行胸椎融合内固定[25]。( 6 ) 对特殊畸形进行截骨矫形,具有严重的畸形相关的腰痛等临床症状,且影像学提示伴有明显的僵硬性畸形。需要指出的是僵硬性畸形临床上较为常见,该类患者脊柱处于非平衡状态,且通过单纯内固定可能无法获得良好的矫正,常需要进行截骨矫正;截骨矫形的合理使用,需要基于临床和影像学方面对脊柱冠状面和矢状面平衡状态的准确判断。Berjano 和 Lamartina 针对成人退变性脊柱畸形而最新提出的临床分型系统与 Silva 和 Lenke 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也明显体现出 DS 阶梯化治疗的临床理念。
2. 融合节段的选择:如果患者主诉为明显的腰痛,无论是否伴下肢疼痛或其它症状,均建议进行腰椎融合术。融合节段的选择一般需要遵从以下 5 个要点:( 1 ) 融合节段不得止于顶椎;( 2 ) 交界性后凸应包含在融合节段内;( 3 ) 严重的椎体侧滑应包含在融合节段内;( 4 ) 椎体滑脱及旋转节段包含在融合节段内;( 5 )融合节段的上端椎体最好为水平椎[14]。
1 ) 短节段融合:短节段融合指不对整个侧凸进行固定及融合,仅仅处理减压节段,旨在保持减压节段的术后稳定性和 ( 或 ) 缓解因 1~2 个责任节段导致的腰痛,其术后邻近节段退变发生率较高。下列情况可选择单纯减压术:Cobb’s 角 < 25°;轻度的顶椎半脱位;脊柱总体稳定性好;下位胸椎局限性后凸角度 < 10°,不存在交界性后凸;融合节段以外、侧凸范围以内脊柱的退变程度尚可接受[25]。
2 ) 长节段融合:需要长节段融合的情况包括:责任节段无法确定并且侧凸进展;轴性腰痛为主要症状,且腰椎失稳;腰椎侧凸角度大,伴有严重的顶椎半脱位及椎体严重的旋转畸形。术前须全面评估患者的腰椎稳定情况,腰椎前凸角、骶骨后上缘与 C7铅垂线的距离、骨盆倾斜度等因素。正确的节段及融合方式的选择与术后的疗效密切相关[2,21-22]。
目前为止,尚无指南明确提出在 DS 患者中,融合近端椎体应如何选择。理想的融合应该包含冠状面失稳的所有节段,选择水平椎作为融合的近端止点,术前通过左右 Bending 位摄片来评估侧凸的可复性;在矢状面上,融合需要重建腰椎生理前凸并纠正胸腰段后凸畸形 ( 此时融合节段应上移至合适的胸椎节段 );当前,近端融合椎体选择的一个争论热点是融合至 T10还是 L1[26]。融合至 L1术后发生在胸腰段的邻近节段退变概率较高,而 T10因为有肋骨对胸腰段关节进行加固 ( 比 T11、T12相对更为稳定 ),术后稳定性好,邻近节段退变发生率低。但仍然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临近节段的退变是年龄增长、脊柱退变的必然结果,融合至 T10意义不大,且会延长手术时间、增加术中出血与术后并发症,因此 Cho 等[14]认为,在融合止点高于侧凸顶点的情况下,中立椎 ( 常常为 T11、T12) 也可作为融合的止点。Kim 等[27]曾报道将融合止点选择在稳定椎以及中立椎术后均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但稳定椎的选择应除外伴有冠状位失代偿的患者 ( 中段腰椎椎体出现侧滑导致冠状位垂线偏离了双侧髂嵴中点 2 cm 以上 )。因此,融合止点的椎体应高于侧凸顶端的椎体,水平椎、中立椎以及稳定的椎体均可以作为长节段融合的近端止点,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换取最好的手术效果。
长节段融合中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远端融合止点应选择 L5还是 S1。既往报道认为 L5为更好的选择,因为侧凸的顶点常常位于 L2~4,且 L4~5椎间盘也已有退变,而融合至 S1虽然可以重建更好的矢状面稳定,但也可能发生更多的生物力学相关并发症 ( 16.5% ),且常需要尽可能减少近端椎体的融合数量,并采用椎间融合术或者应用骶髂螺钉提供额外支持,其再次手术率也不低[6,9]。因此,笔者认为在能保证手术效果的前提下,尽量保持 L5~S1关节活动度,使更多患者得到治疗并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到最低。但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以下情况者,建议一期融合至 L5~S1,具体包括:L5~S1椎间盘已有严重退变;L5~S1滑脱;L5~S1节段椎管狭窄;L5~S1手术史;腰骶严重倾斜;伴有严重冠状位或矢状位失稳,无论 L5~S1有无退变表现( 更可能导致 L5~S1退变 )[2,14,22]。
随着中老年人群数量的增长与平均寿命的增加,DS 的发病率将会越来越高。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应对该类患者进行临床症状与影像学检查相结合的全面评估,明确每个症状的临床特点、来源部位及责任节段;根据患者全身健康状况、骨质疏松程度、侧凸类型与部位、脊柱稳定和平衡状况以及与临床表现的相关性,权衡各种手术方案的利弊,制订合理的阶梯化治疗方案,以期在尽可能小的创伤条件下,达到有效解除神经压迫、稳定脊柱和重建脊柱平衡的目的。
[1] Ploumis A, Transfl edt EE, Denis F.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 associated with spinal stenosis. Spine J, 2007, 7(4):428-436.
[2] Kleinstueck FS, Fekete TF, Jeszenszky D, et al. Adult degenerative scoliosis: comparison of patient-rated outcome after three different surgical treatments. Eur Spine J, 2014. [Epub ahead of print]
[3] Liang CZ, Li FC, Li H, et al. Surgery is an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treatment for degenerative scoli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J Int Med Res,2012, 40(2):399-405.
[4] Lee SE, Jahng TA, Kim HJ. Decompression and nonfusion dynamic stabilization for spinal stenosis with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J Neurosurg Spine, 2014, 21(4):585-594.
[5] Di Silvestre M, Lolli F, Greggi T, et al. Adult’s degenerative scoliosis: midterm results of dynamic stabilization without fusion in elderly patients-is it effective? Adv Orthop, 2013, 2013:365059.
[6] Khajavi K, Shen AY. Two-year radiographic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a minimally invasive, lateral, transpsoas approach for an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dult degenerative scoliosis. Eur Spine J, 2014, 23(6):1215-1223.
[7] Kotwal S, Pumberger M, Hughes A, et al. Degenerative scoliosis: a review. HSS J, 2011, 7(3):257-264.
[8] Palmisani M, Dema E, Cervellati S. Surgical treatment of adult degenerative scoliosis. Eur Spine J, 2013, 22(Suppl 6):S829-833.
[9] Ploumis A, Transfl edt EE, Denis F.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 associated with spinal stenosis. Spine J, 2007, 7(4):428-436.
[10] Aebi M. The adult scoliosis. Eur Spine J, 2005, 14(10):925-948.
[11] Tsutsui S, Kagotani R, Yamada H, et al. Can decompression surgery relieve low back pain in patients with lumbar spinal stenosis combined with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 Eur Spine J, 2013, 22(9):2010-2014.
[12] Ploumis A, Transfeldt EE, Gilbert TJ Jr, et al.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 radiographic correlation of lateral rotatory olisthesis with neural canal dimensions. Spine, 2006, 31(20):2353-2358.
[13] Zeng Y, White AP, Albert TJ, et al. Surgical strategy in adult lumbar scoliosis: the utility of categorization into 2 groups based on primary symptom, each with 2-year minimum follow-up. Spine, 2012, 37(9):E556-561.
[14] Cho KJ, Kim YT, Shin SH, et al. Surgical treatment of adult degenerativescoliosis. Asian Spine J, 2014, 8(3):371-381.
[15] Robin GC, Span Y, Steinberg R, et al. Scoliosis in the elderly: a follow-up study. Spine, 1982, 7(4):355-359.
[16] Ha KY, Son JM, Im JH, et al. Risk factors for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surgical correction of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Indian J Orthop, 2013, 47(4):346-351.
[17] Silva FE, Lenke LG. Adult degenerative scoliosis: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Neurosurg Focus, 2010, 28(3):E1.
[18] Murata Y, Takahashi K, Hanaoka E, et al. Changes in scoliotic curvature and lordotic angle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 Spine, 2002, 27(20):2268-2273.
[19] Chin KR, Furey C, Bohlman HH. Risk of progression in de novo low-magnitude degenerative lumbar curves: natur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view. Am J Orthop, 2009, 38(8):404-409.
[20] Jimbo S, Kobayashi T, Aono K, et al. Epidemiology of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 a communitybased cohort study. Spine, 2012,37(20):1763-1770.
[21] Deukmedjian AR, Ahmadian A, Bach K, 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lateral approach for adult degenerative scoliosis: lessons learned.Neurosurg Focus, 2013, 35(2):E4.
[22] Boachie-Adjei O, Cho W, King AB. Axi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xiaLIF) approach for adult scoliosis. Eur Spine J, 2013, 22(Suppl 2):S225-231.
[23] Tempel ZJ, Gandhoke GS, Bonfi eld CM, et al. Radiographic and clinical outcomes following combined later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nd posterior segmental stabilization in patients with adult degenerative scoliosis. Neurosurg Focus, 2014, 36(5):E11.
[24] 刘海鹰, 周殿阁, 王会民, 等. 退变性脊柱侧弯的外科治疗探讨. 中华医学杂志, 2003, 8(12):1066-1069.
[25] Cho KJ, Suk SI, Park SR, et al. Selection of proximal fusion level for adult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 Eur Spine J, 2013, 22(2):394-401.
[26] Simmons ED. Surg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lumbar spinal stenosis with associated scoliosis.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01, (384):45-53.
[27] Kim YJ, Bridwell KH, Lenke LG, et al. Is the T9, T11, or L1 the more reliable proximal level after adult lumbar or lumbosacral instrumented fusion to L5 or S1? Spine, 2007, 32(24):2653-2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