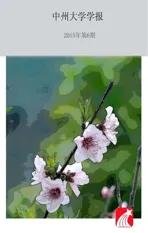简析《白鹿原》中女性的生存境遇
2015-01-21惠萍
惠 萍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简析《白鹿原》中女性的生存境遇
惠 萍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白鹿原》塑造了一大批生动活泼的女性形象,细致刻画了传统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书写出她们被忽视、被压抑的历史。她们或消极顺从命运的安排或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是结局都一样悲惨,只有少数个别女性能够善始善终。《白鹿原》既是一曲传统女性的悲歌,也是一曲传统女性的挽歌。
《白鹿原》;女性生存境遇;自我救赎;个性解放
随着2012年9月同名电影在中国大陆公映,当代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白鹿原》再次引起人们关注。这部长达50万字的作品初版于1993年6月,修订再版于1997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在电影是否把一部史诗般的民族秘史改编成了一部“田小娥的情爱史”的一片质疑声中,笔者再次捧读修订版的《白鹿原》,随着翻动的书页慢慢走近白鹿原,走近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男男女女。这部陈忠实准备死后“垫棺作枕”[1]33的书所展现出的厚重与悲壮足以引发我们方方面面的思考,本文仅就《白鹿原》中的女性生存境遇来谈谈传统女性自我救赎的可能与尴尬。
一、《白鹿原》传统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白鹿原那片绵延数千年的土地上,男权统治下的女人大都“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2]13-14,而在白稼轩父亲的眼里,女人的价值略等于“一匹骡驹”[2]4。在这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里,女人首先是繁育后代的工具和家庭事务的劳力,所以才有了白稼轩娶过七房媳妇六死一生传奇婚姻的到来。白稼轩父亲白秉德即将离开人世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白稼轩答应他去世后赶紧迎娶第五任媳妇。而母亲则在父亲去世后就催促,“不要等了,等也是白等,家里太孤清了;况且她一个人单是扫屋扫院洗衣拆被做饭都支应不下来,再甭说纺线织布等家务了”[2]11。白家得知孝义不能生育的消息后,甚至不惜偷偷让孝义媳妇和兔娃借种生孩儿。其次,女人的另一功能是充当性工具。田小娥就是年纪一大把的郭举人娶来满足自己特殊需求的养生工具,还有土匪窝里的白牡丹和黑牡丹,地位也大抵如此。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显而易见是被忽略、被轻视的。她们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儿育女的生活,很少有人关心她们的尊严和幸福。她们中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嫁人之后随夫姓加上自己的姓以及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氏”字,如白赵氏、朱白氏、鹿贺氏、鹿冷氏等。书中显示在白稼轩引以为豪壮的七房媳妇里只有第七房媳妇白吴氏仙草有名字,其余来自白鹿原附近东、西、南、北原的六房媳妇均没有名字。在开头长长的介绍这些媳妇们的叙述中,多是提到村名、家族姓氏和家庭经济状况,这些远比女性本人更能决定有无与大户人家白家联姻的可能。颇有声望的村医冷先生的两个女儿在书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一个是发了淫疯病而被父亲毒死的鹿冷氏,一个是不太机灵但还算能够顾得住场面的白冷氏,大家口中的二姐。
即便在一般家庭里看似正常的女性也未必就能被关注,更谈不不上与男子平等。比如,看似沉静幸福的仙草。当她独自在家生下女儿白灵后,碰巧回来的白稼轩赶紧给她烧水端水,以至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这是她进这个门楼以后男人第一次为她烧水端水。而鹿三媳妇鹿惠氏(在第六章却说是鹿张氏[2]80,也许是作者无心之失,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作者也不甚在意鹿三媳妇到底姓啥,我们只要知道说的是鹿三媳妇就行了),在鹿三准备杀田小娥而磨梭镖时问他干什么,鹿三没有回答,她就不敢再继续问下去,直到小娥托梦才端晓缘由,而且“鹿三说不进家门就不进家门……”
可以说,《白鹿原》中女性被忽略、被压抑的历史不是一两个人的历史,而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所有女性的不平等史。
二、遵从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孝文媳妇、冷家大女儿和孝义媳妇
书中涉及到的女性,不管详略加起来有二三十个,其中绝大多数是遵循传统礼教的普通女性,她们从生到死、生生死死,了无波澜,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但还是有那么几个,她们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却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比如孝文媳妇、冷家大女儿和孝义媳妇。
白孝文直到结婚前对两性关系都懵懂无知,是孝文媳妇启蒙了他。然而虽是初享云雨之欢的孝文不愿节制,孝文媳妇却受到全家成人的侧目,奶奶对她的口头告诫不止一次,孝文媳妇难堪却奈何不了孝文。更难堪的是,因孝文与小娥纠缠在一起,白稼轩让小两口另立门户,孝文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因少了父母约束更加肆无忌惮。分家后白孝文卖地卖房,她都不见分文。没有粮食,两个孩子被领到公婆处吃饭,而自己最后却被活活饿死,临死她走到白稼轩的面前控诉 :“爸,我到咱屋多年了,勤咧懒咧瞎咧好咧你都看见。我想过这想过那,独独儿没想过我会饿死……”[2]318这是对白孝文的控诉,也是对以白稼轩为代表的封建家长的冷酷无情的控诉,更是对杀人不眨眼的封建礼教的控诉。
冷家大女儿鹿冷氏在嫁到鹿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明白过来鹿兆鹏不喜欢自己,等她明白一些的时候却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冲破牢笼,既缺乏田小娥式的毫无顾忌,也缺乏白灵那样的机灵和学识,只有在漫长的岁月中郁郁寡欢。没有人关心她,也没有人给她指点,即便是在这块土地上以善解人们身体上的疾病痛苦而著名的父亲也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心和爱护。最后,无可排遣的孤独寂寞以及难以遏制的抑郁和情欲交织在一起促成了她的疯癫。而此时婆家和娘家真正关心的不是她受伤的心灵以及她悲惨的生活现实,他们关心的仅仅是家族的面子问题。为了不让她再发疯说胡话,亲生父亲冷先生用药结束了她的生命。临死前由于药物的作用,她说不出话来。如果能够像孝文媳妇那样说话,想必她会说:“想到过这想到过那,独独没有想到会被亲生父亲毒死。”然而彼时的死亡,告别这个冰冷的世界对她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如果说孝文媳妇和冷家大女儿的鲜活生命被封建礼教所吞噬恰好对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古训的话,那么孝义媳妇所受的“屈辱”也暗中对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教条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孝义媳妇是白稼轩迎娶到白家门里三个儿媳妇中最称心最完美的一个。孝义媳妇模样周正、落落大方。正是在娶孝义媳妇时,书中安排白稼轩这个白鹿原上的族长对女性之于家庭的重要性作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阐述:白稼轩“闲时研究过白鹿村同辈和晚辈的所有家庭,结论是所有男人成不成景戏的关键在女人。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更不要说像黑娃拾烂菜帮子一样拾掇下的那种货色了,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2]490。然而这个无可挑剔的媳妇进门后,让白家人发愁的是没有为白家添一男半女,最终弄清楚问题不在女方而在孝义,遂在家人的安排下向兔娃借种生下了孩子。孝义媳妇在这其中所受的屈辱书中没提,但“无可挑剔”的孝义媳妇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有怨言又何尝能正常表达呢?
孝文媳妇、冷家大女儿和孝义媳妇,没有一个不是“乖乖女”,遵父母之命、依媒妁之言,过着千百年来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普通生活。她们遵从封建礼教,相信救赎就在其中,因而没有任何反抗,不承想封建礼教却一次又一次让平凡善良的她们“乖乖”地成为牺牲品。是啊,“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 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 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3]49。
三、追求个性解放的先行者:田小娥、白灵和小翠
笔者不是那么在意电影版的《白鹿原》是否被改编成了“田小娥的情爱史”,因为在有限的电影表达时段里,要充分展现半个多世纪白鹿原的历史毕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但电影舍弃掉白灵这个女性形象还是有些遗憾的。《白鹿原》一书中个性比较突出、着墨最多的两个女性是白灵和田小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主动还是被动,她们是两个走在追求个性解放前列的女性典型。事因难能,所以可贵。
田小娥和白灵都是反叛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先行者。但田小娥是迫于时世、源于本能的反叛,是不自觉的反叛。父母自顾把她许给郭举人做小妾,而且也不受待见,主要的事情就是每天在郭举人大老婆的监督下负责给郭举人“泡枣”。而她的出场也是在这项不那么能见人的活儿被长工嚼舌头根儿的“卧谈会”上被带出来的。直到遇上重情义的黑娃,田小娥才开始了自己对幸福的追寻。但命运一波三折:偷情被抓,被休回娘家;黑娃带他回家,既不被祝福、也不让进祠堂;村口窑洞寄生,短暂幸福生活因黑娃革命而中断;为救黑娃被鹿子霖霸占,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被鹿三杀害,死后“报复”而被塔镇骨灰。当她摆脱小妾的屈辱和黑娃自由恋爱过上“吃糠咽菜”也愿意的生活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会成为被白鹿原上人们所不耻的“婊子”。她委身鹿子霖一方面有为救黑娃被鹿利用的原因,一方面也有黑娃一时回不来而没有经济来源的考虑。后来跟孝文在一起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感情的原因,但是也不能否认这里面的经济因素:白孝文宁肯卖掉房子和土地也要把钱给她,与此对照的是白孝文的妻子被活活饿死(尽管一开始他不知道她会饿死)。尽管田小娥死后控诉“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2]462也不能否认她在追求个性、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只能利用自己的美色,在经济不独立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对抗这个世界的唯一武器,但是她与命运抗争了,即便没有足够的能力。
白灵则带着先天的优越条件追求自己认定的幸福:出生的时候“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梧桐树上叫着,尾巴一翘一翘的”[2]76-77。她得到了全家人的钟爱,被朱先生认为“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能统领千军万马”[2]402。她是新学堂里走出来的女学生,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追求个性解放:为了上新式学堂,不惜把刀架在脖子上逼白稼轩让步;为了退婚,不惜和家庭决裂;发动学生起事儿,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反动者扔砖头;和兆海私定终身,却又因政见不同与兆海分手转而爱上同党兆鹏,全然不以兆海兆鹏的兄弟关系而掩藏自己的感情。她是“革命”的“宁馨儿”,是活泼的、生动的、福佑白鹿原的白鹿精灵。她去世时好几位亲人都梦到了白鹿,却是委屈的白鹿,流泪的白鹿。她没有被敌人投井或活埋、也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却惨死在自己人手之中。她的追求给自己开了个玩笑:命运不但让追求个性解放的她背叛自己的家庭,逃离了世俗的婚姻,也背叛了初恋情人;向往革命却最终为革命献身,成为革命的祭品。虽然她有鹿鸣这个孩子,应该说也算留下了希望,但事实却证明:虽然她有追求个性解放的能力和资本,但自我救赎之理想的实现仍然极为遥远和虚无。
书中还塑造了一个敢于追求爱情的小翠。文中对小翠着墨不多,但同样惊心动魄: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小翠是一个木匠师傅的女儿,因为被人看到和喜欢的人的暧昧情景并报告给了夫家,夫家不动声色地把她娶进门,第二天便到大街上羞辱她。夫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狠狠地“报复”了这个天真女子的“不忠”。过门第二天,听着外面的喧哗,小翠在婆家上吊死了——仅仅因为一次“暧昧”,世间种种便都与她无关了。
田小娥、白灵,包括小翠们的反抗都可视为被封建礼教重重帷幕所包围的女性试图自我突围的一种大胆尝试,是沉沉暗夜所散发出的希望之光。她们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先行者,以生命为代价向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她们悲惨的结局和遵从封建礼教的女性一样令人唏嘘。陈忠实“以她们的悲剧有力地批判了传统仁义文化阴暗、残忍的一面, 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小说以她们的反叛呼吁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新文化的追求。文化冲突让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也展示了文化进步的艰难”[4]89。
四、男权社会下的极个别善始善终者:白碧玉和高玉凤
考察《白鹿原》传统女性的命运,人们往往关注田小娥、白灵等个性鲜明的形象而忽略一些看似平常的人物,而这些看似平常的人物也是构成白鹿原女性生存图谱的一部分,因而有着独特的寓意和作用。比如白碧玉和高玉凤,她们是《白鹿原》中男权社会下少有的能够善始善终的传统女性形象。《白鹿原》中有太多无名的女性,人们也许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这两个人物到底是谁,她们分别是朱先生的妻子朱白氏和黑娃后来明媒正娶的妻子高老秀才之女玉凤。笔者之所以把这两位作为传统女性的完美代表,是源于她们两个都让自己的丈夫在其有生之年想叫她们一声“妈”,她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玉字,大概象征着她们的个性如白璧无瑕。
文中传统文化的代表朱先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当着全家的面让妻子给他洗头,洗完头后后脸贴在妻子的大腿上时说“我想叫你一声妈——”当朱白氏非常疑惑而儿子儿媳也非常不好意思之时,朱先生又扬起头诚恳地说:“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就盼有个妈!”[2]627-628说罢竟然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两行泪珠滚滚而下。而黑娃带着高玉凤回家认祖归宗、进了祠堂之后黑娃谢绝了白稼轩为他备好的炕铺,引着妻子走进自家那个残破的敞院,深情地对高玉凤说“咱们在妈妈的炕上睡一夜吧!”躺进破棉絮里。当他闻到一股烟熏和汗腥气味,一股幽幽的母乳的气味,颤着声羞怯怯地说:“我这会儿真想叫一声‘妈’……”[2]587玉凤把黑娃紧紧搂住,黑娃静静在枕着玉凤的臂弯贴着她的胸脯沉静下来。这两声看似莫名其妙的“妈”的呼唤,而且是白鹿原上两个最具自省意识的男性对着自己妻子深情的呼唤,忽然间让我对白鹿原上生活着的众多女性生存境遇有了新的认识。
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她们要么顺从,在被侮辱、被戕害时也无力反抗,如前面提到的封建礼教的几个牺牲者的代表;要么反抗,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如前面分析的田小娥和白灵,最后也不得善终,一个被压在塔下,一个被活埋地下。还有小翠,前脚进了婆家门,后脚就离开了人世。那么什么应该是女性原本的宿命?书中没提。但笔者从这两声“妈”的呼唤中似乎明白些什么,那就是还需要以儒家文化精神滋养的健康女性,既不甘于落后愚昧也不至于激烈反抗。碧玉是大儒朱先生的妻子,当初朱先生选择白碧玉做妻子时主要是因为那双眼睛,碧玉的眼睛“刚柔相济”:男子眼里难得一缕柔媚,而女子难得一丝刚强。他见到碧玉时就断然肯定,即使自已走到人生的半路上淬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而在他即将离世时妻子在他眼中愈见深沉愈见刚正,愈见慈爱了。碧玉本身品性高洁,加上在朱先生身边耳濡目染,也更臻于完美。高玉凤是秀才之女,婚后烧火做饭时还在看书,而黑娃就想找一个知书达理的媳妇管束管束自己的野性。玉凤跟黑娃结婚的条件是黑娃必须戒掉吃“土”的毛病,否则将“以死抗婚”。她不计较他从前种种,只求今后表现良好。她沉静地安排着自己和黑娃的生活,使黑娃感受到这个女性的全部美好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安全和可靠。这两个女性的丈夫在男权社会统治下的日常生活中忍不住想叫她们一声“妈”,这不正是对传统人性中母性的呼唤吗?这更是对女性知书达理、温柔敦厚的呼唤。
朱先生在深情告别碧玉后过世,完成了一个相对完美、自足的生命历程。而黑娃在跟玉凤结婚后真正成了鹿兆谦,回乡祭祖不仅标志着被家族接纳,也标志传统文化反叛者黑娃彻底回归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他是自觉向传统文化归顺,回乡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朝向压着小娥骨灰的六棱塔方向张望一眼,他是彻底地告别了过去,从而真正从心底里“学为好人”。这些细节无不彰显出传统儒家文化的教化功能。朱先生也说自己最好的学生是曾为土匪的关门弟子黑娃,也标志着高举儒家文化旗帜,代表白鹿精灵的朱先生对儒家文化再一次发挥神奇的归化作用的肯定,他告诉朱白氏自己内心“孤清”得很,何尝不是对儒家文化逐渐式微的慨叹。在他眼里鹿兆鹏和白孝文等都算不得“好人”,而革命就像鏊子,翻来覆去,没有反正。不管时局如何变幻莫测,唯有儒家文化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就像朱先生起草而被白鹿原上人们世代传颂的《乡约》,虽历经被毁、重修,始终见证和调整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生活以及每个家族的繁衍生息。因为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 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 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3]50。
母亲创造生命,母亲给自己创造的生命以无可替代的静谧与安稳,她们以柔弱之躯为孩子们构建起强大的精神家园,而传统儒家文化正是支撑这个家园的精神支柱。白赵氏在白秉德去世后显示出少有的刚毅和果断,在儿子主事以前有条不紊地安排着白家的生活,而鹿子霖的媳妇鹿贺氏在鹿子霖被抓后,也迸发出少有的主见,变卖所有的家产只为保鹿子霖回家。这些一向隐忍的女性蕴藏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和决断力,常常在一个个不可预料的家庭变故面前表现得异常坚强,因而使得家庭渡过难关。她们没有文化,但同样是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母亲和拥有母性个体特色的伟大女性。
五、余论
如果说白碧玉和高玉凤是传统女性在现世生活中相对完美的典型,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拥有儒家文化温柔敦厚、刚柔相济的“母性”特质,就是传统女性实现在男权社会中自我救赎最为稳妥的道路之一?然而即便如此,男权社会对“妈”的呼唤,对“母性”的肯定和褒扬恰恰是建立在忽略了女性本来的“女人性”的基础上,作为“女性”的个体在封建社会依然是被压抑和遮蔽的。传统女性自我救赎的可能与尴尬也在这里。
孝文媳妇、冷家大女儿、孝义媳妇何尝不是对封建礼教所提倡的三纲五常亦步亦趋,却也逃不过被封建礼教吞噬的命运;田小娥也是秀才之女,何尝没有亲近过儒家文化,受诗书礼仪的熏陶?但还是被父亲嫁到郭举人家,而在郭举人夫妇眼里,她只是个工具而已,黑娃冒险带她回家,但带不进自家的祠堂里……最终还是在父权、夫权和族权的重压下走向了毁灭——肉身被戕、灵魂也被压在塔下——成为一个生动的反抗者的典型。最终她是孤独的,因为在儒家文化的感召下鹿兆谦带着玉凤走近祠堂时,田小娥终于失去了最爱她而她也深爱着的黑娃。白灵在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愿望中游走在国共两党之间,感情也在鹿家两个兄弟之间转换。不管在身体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白灵看似都是出离于父权、夫权和族权控制的自由而独立的时代新女性。然而她却因不见容于自己的组织,被自己人出卖而被活埋。或顺从或反抗,这些女性多舛的生活际遇充分显示出命运无常的魔力。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白鹿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大多数女性依然找不到自己的救赎之路?封建礼教作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一开始并不是“吃人”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却变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有些方面反倒走到了它原本的对立面。传统儒家文化孕育了男权思想,在男权思想统治下造成了一个个贞妇烈女,留下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陈忠实在他的《白鹿原》创作手记中写道:“为她们(贞妇烈女)行一个注目礼, 或者说挽歌。”[3]49《白鹿原》中女性的命运说明无原则地遵从封建礼教或者刻意追求个性解放都不能善始善终,最终还是要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寻找抚慰,不管是像文中朱先生那样的“大儒”还是像黑娃那样学为好人的“土匪”。因此怎样理解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影响仍然是今天一个重要的课题。
“当成文形式的中国传统作为现代中国的指南而大部分受到怀疑时,实际上中国的价值体系、个人相对于政府的地位、农村父系家庭制度的支配地位和中国生活的成百个特征却表现了明显的延续性。人们用各不相同的歌词唱同一个老调子。人们自觉思维领域中的变化大于日常行为的变化。”[5]23陈忠实的《白鹿原》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看来严复,这个19世纪向国人传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著名思想家在遗嘱中写到的“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6]360是有着深刻道理的。《白鹿原》中传统女性日常生存境遇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依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容小觑,今天也是如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审慎地评价也许是今天我们对待传统文化最好的态度。
[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J].小说评论,2007(5).
[2]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人学出版社,1997.
[3]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J].小说评论,2007(4).
[4]沈远川,马筱蓉.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3).
[5]〔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 许峻)
An Analysis of Women’s Living Circumstances inWhiteDeerPlain
HUI 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The novelWhiteDeerPlaindepicts the living predicament and an ignored and depressed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and portrays a number of female characters. Some of them yield to their destiny, and others pursue self-liberation and resist the feudal restriction. However, destiny leaves them no difference in the feudal society, and unfortunately only few of the female could obtain a good ending.WhiteDeerPlainis a lamentation as well as an elegy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WhiteDeerPlain; women’s living circumstances; self-redemption; self-liberation
2015-10-20
惠萍(1974—),女,河南社旗人,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编辑出版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5.06.008
I207.42
A
1008-3715(2015)06-0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