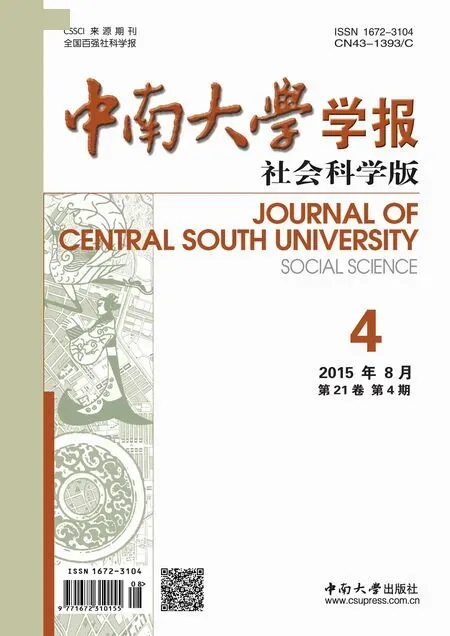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创业史》与“十七年”小说的欲望抒写问题
2015-01-21王再兴
王再兴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418008)
《创业史》与“十七年”小说的欲望抒写问题
王再兴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418008)
如何处理“欲望”,一直是当年集体主义文学令人纠结的问题。但欲望始终隐蔽地存在,却是客观的事实。《创业史》仍然反向地表现出了欲望的诸多踪迹。另一方面,由于1950年代末特殊的历史语境,个人欲望与尊严均被压抑,这意味着主体之间间性关系的萎顿。由此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个人(“新人”)的不完全的主体性。这个庞大的讲述农村集体主义改造“历史”的故事体系,看起来还是有着太多的脆弱之处。究其根源,或许在于讲述之始就被作者刻意隐藏的“欲望”,以及被鄙弃的作为欲望转换中介的“计算”。它们成为柳青和《创业史》遗留至今的未尽的话题。
农民小说;欲望;“历史”化;集体主义文学
1952年,作家柳青从《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任上离开北京,举家迁往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半山坡一座破旧的中宫寺里安身,在这里扎根落户,生儿育女,一住就是十四年。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已经“完全农民化了”。期间他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一个互助组“王家斌互助组”的巩固工作,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一个初级社“胜利社”的建社工作,亲身参与了长安县合作化运动充满了斗争和曲折的整个历程,直到1966年夏被打成“黑作家”后揪往西安批斗时为止。正是在皇甫村的十四年里,柳青完成了《创业史》的第一部(包括第二部的部分章节,后手稿在西安揪斗期间丢失),并于1959年4月在《延河》上开始连载。《创业史》发表伊始,就被喻指为“丰富地深刻地反映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真实面貌的作品”“全面地历史地描写出合作化运动在广大农村中所产生的深远剧烈的影响和变化的作品”[1],此后也一直被认为是反映中国当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最为突出的小说。毫不奇怪,它也被认为具有“史诗”性,即呈现出一种历史化的格调。如冯牧先生《初读〈创业史〉》(1960)一文即称,作者在作品里为我们描绘的,不只是一幅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简略而单纯的图画,而是一幅展示了广大农民历史命运与前进道路的深刻而鲜明的生活画卷,并认为作者将作品题名为《创业史》,绝非偶然。冯牧的说法,在后来柳青针对严家炎先生的反批评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也得到了作者的自我确认。[2]但我们仍然应该注意的是,《创业史》第一部诞生之时,已距第一部主要内容的互助组时代有6年之久,期间已历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制度变迁或社会运动的不同阶段,包括当中的各种论争。显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其实已经只能算是“追述”,而在这个追述里,一般而言很难避免柯文所说的“神话化”特征。诚然,历史并非自然时间,它意味着现在与过去两者关系的连续不断的重建,这其中必然隐喻着从现在的立场来评判“过去”的这一严肃问题。也正因为这种特征,“历史”一词不仅指向了政治,也指向了阐释,而这正是詹姆逊之谓“历史化”的涵义。[3](1)
一种文学讲述,虽然自称为是一部“生活故事”,但无论是在作者或者批评者那里,都被指明其包含了“史”的品格。那么,这个话题如何承续了各种合作化的问题,比如欲望、个人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等等话题?或许,一切问题的真正的讨论,都必须首先始于对于历史的原生“意义”的凝视吧。
一、《创业史》:“欲望”的踪迹
作为一部歌颂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完成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后,并进行了多次修改。它虽然讲述的是蛤蟆滩1953年约一年时间里发生的互助组及初级社的故事,但这个追述显然添加了1953年以后才变得普及的历史“阐释”的内容。最明显的是,1946年以后的互助组比较获得公认的特征是承认土地、农具、牲畜等私有,实行等价交换,以及自愿、互利、民主管理等原则。但这些特征在1950年代中后期实际上遭遇了极大的改变。譬如在“公”与“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等对立的思潮中,“私”或者“资”(资产阶级)迅速成为需要被打上“×”号的时代秽词。与互助组时代确认私有制合法,土地可以买卖,并曾经提出“党员也可以雇工剥削”(刘少奇语)很不一样,1959年的《创业史》则对“私有财产”表现了极大的焦虑。然而有意思的是,尽管作家柳青在小说中反复表达了对于“私有财产”的厌憎,但无论是在那篇精彩的《题叙》所讲述的“创立家业”、屡仆屡起的历史里(后续章节亦不例外),还是在同时期评论者的分析文章里,都指明了这部小说与“欲望”之间的明显关联。比如,1929年的梁三仍在说,当成我梁三这辈子就算完了吗?我还要创家立业哩。而当梁三老汉在解放战争后期——据文中推测,应为1948年,终于看到创业无望,并认为和命运对抗终是徒然的时候,小说称,他们已没有了什么指望,只是像土拨鼠一样静俏悄地活着。这里的“指望”,正是梁三毕生都在追求的创家立业的“欲望”。在几乎随后出现的冯牧先生的前述批评文章中,借分析新中农郭振山的形象,就将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直接指称为了“欲望”[1]。而“发家致富”正是“创立家业”的另一种说法,这比柳青在小说中的说法要明朗得多。
但让人惊讶的是,小说却在这个欲望或者创业之史的讲述里,表现出了最明显的分裂。首先,小说中梁三老汉有两次关于幸福生活的图示化想象,即第一部“题叙”部分关于三合头瓦房院和厚实棉衣的梦,第二部第十八章关于一个聪明、能干、孝敬的儿媳和又胖又精的小孙孙的欢乐景象。但是,不仅原先梦境里的“瓦房院”到了第二个想象里依然变回了“草棚院”,而且直到第二部结束,梁三老汉的实际幸福仅是穿上了“一套崭新的棉衣”而已。这套棉衣在第一部的结局时,甚至曾被生宝升格成为老人“圆梦”的象征。乡人民代表高增福同样如此。直到1954年,大伙看见已是灯塔社副主任的他穿着一套新棉衣,这与长期穿着开花烂棉袄的那个高增福形成鲜明的反差,小说于是夸张地说道,要是在路上碰见,你会误以为他是哪个走亲戚的富裕中农吧。其次,农民私自不舍得交售更多的“余粮”,但第一部的结局称:“……他们都谨小慎微地拿出来了。”在中国农村长久的历史中,粮食一直是如金本位一般的硬通货,“粮食”由此成为差不多与“财富”同义的符号,也成为“欲望”非常直接的一个象征物。小说中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虽然互助组有过良好愿望,引进新稻种,“今年秋后不种青稞!那算什么粮食?”但是事实上,可怜的贫雇农种了稻子,却吃不上大米,青稞饼子、玉米糁糁(糊糊)、窝窝头、小米稀饭等等仍然是小说中梁三老汉、梁生宝、高增福们的日常主食。甚至春荒时节,揭不开锅的穷困农民只买饲料——玉米和青稞,以延续一家大小的性命。另一方面,在1953年冬,蛤蟆滩的粮食统购工作中,下堡乡人民代表会按耕作面积、当年产量和人口调查,计算出第五村应该收购三十五万斤余粮的任务。其中梁生宝互助组八户人家,全组自报向国家交售余粮五十石,合一万二千斤。而依据卢支书的说法,“咱们把任务超额完成了”,上级给下堡乡分下二百二十万斤的任务,“咱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万斤”。关于粮食的欲望是如此,关于房屋的欲望也大致差不多。不仅梁三老汉的“三合头瓦房院”的梦并没有实现,到第二部的想象里居然回归了“草棚院”; 高增福父子拆了自家的草棚屋盖饲养室,后来住在生茂家从前喂牛的草棚里,没能住进新的草棚屋。小说中郭世富盖四合头的新房及关于富农姚士杰的四合院场景的描写,其实只是以嘲讽和负面的格调来展开的。郭振山“一根椽一根檩地备料”准备盖瓦房的计划,不仅受到严厉批判,并且最终也没有能够成功,而遗忘在故事的其他枝节中。所以我们说,小说显然对于蛤蟆滩的农户们的“欲望”,如粮食、居住等,衣服则是一个同义的反证——形成了实际的压抑与批判: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是有路线错误的;在意个人利益的计算则是思想“落后”的。它们在小说的第二部里被追认为“自发道路”,从而与“社会道路”,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之谓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对立。
同样因为“欲望”的问题,小说还出现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关于“身体”的略有诡异的现象:身体成为《创业史》中不在场的在场者,可能正是因为它是强有力的“意义”源出的核心地带之一。小说中非常常见的身体反应是“脸红”——这涉及了郭振山、梁生宝、改霞、秀兰、高增福、任欢喜、赵素芳等等许多人,并且贯穿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始终。当然,它是一种比较典雅并且克制的处理方式,也是那个年代常见的风格。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回首检视整篇小说,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脸红”大多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年轻儿女情窦初开的自然反应,以第一部为多见,如生宝、改霞、秀兰,例如,“她看出来的:生宝最近一见她就脸红,是对她怀着念头哩”;一是“政治”场景中受到一时的窘迫,则以第二部为更多,如郭振山、赵素芳、高增福,例如建社工作组的王亚梅同志叫赵素芳发言的时候后者的脸红了,浑身急得冒汗,等等。由此说明在《创业史》中,作为身体表征的“脸红”,其实是一个被架空了的能指符号——即身体在此通常并不指向真实的欲望,无论是性本能、自我或者利益。身体的真正的政治性意味被强有力地削弱了(性亦“政治”),或许正是因为作为建构主义方式之一的“身体”,具有太多不可监测的冲动力,随时都有“逸出”意识形态规训的可能的缘故吧。但是,作家柳青其实并没有忘记欲望的身体。它们在很多地方都在隐隐闪现。特别是第一部第十一章富农姚士杰全家“宴请高增福”一段。在这里,姚的年轻漂亮的三妹子主动与高增福“身子贴身子紧挨”着走路以外,“有弹性的胖奶头”更是两度出现,证明欲望的身体确实是在场的;不过随后的见到美食之后高增福的“呕吐”同样也出现了两次(下文有“他鄙视地看也不看桌上摆好的酒菜,他看见就发呕”),却再度证明欲望的身体轻易就被意识形态,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派头”和“堂堂正正的雇农”所改写。作为过程,这个欲望的身体也曾在第一部第二十一章“素芳被辱”事件里,无意中被作者复活过,最终的处理方式却与上述的“呕吐”相同。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同样的关于粮食以及安居才能乐业的欲望等,换了一个视角后却是完全正面和“正直”的。比如,杨副书记说“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梁生宝并多次想起此语以自勉。另如,梁生宝对高增福说,到了秋后,灯塔社如若真的丰产了,户户社员都真正增加了收入,那时候,人家还说咱俩不行,才是对咱俩有意见;杨国华负责的大王村联社章程也通过了,总目标就是“做到户户社员都能增加收入”,等等。这里的“多打粮食”“丰产”及“户户社员增加收入”,是否是欲望?小说称党可以限期把祖国建设成为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按需分配”,其中的“需”,即个人需要,是否是欲望?当欲望指向个人利益的时候,“计算”就成为其表层的隐喻,社会主义时期作为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就是一种计算方式。例如,小说第二部在三级干部会和互助合作代表会期间,杨国华召集的全县农业社主任的小会上,讨论了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各农业社主任所汇集的“经营管理经验”体现出了两个原则,一是差异原则,一是“计算”原则:合理安排,克服窝工浪费和盲乱现象;克服平均主义,社员们以工票记分结算;甚至男女同工(同酬)等。无独有偶,作者在1956年的《灯塔,照耀着我们吧!》中也说道:“我也常参加区上和县上讨论互助合作问题的会议。计工自由的方法、解决做活先后问题的方法、民主管理的方法——应有尽有,方法很重要,有些方法也的确是好……”[4](116)而实际上,这两个原则又是内在统一的,即此处的“差异”可以因“计算”而在不同主体间合理地转换。这里可以重新回到个人与社会的通融问题。当然,客观来说,“计算”并不否认“激情”。如赵树理1959年9月的小说《老定额》所写的,“民主革命时候还能跟社会主义建设时候一样吗?”“谁说完全一样?从前没有定额如今不是有了定额了吗?可是有了定额也不是就不要革命精神了!”——但事实上,“激情”可能仍然有着事后的信赖或认同等感情的模糊计算。作为证明,如果这种激情遭遇冷漠或者甚至挫折,它将可能被主体压抑下去,不再容易被重新唤醒。在这个特殊的1950—1960年代,赵树理曾经严肃地思索过这个问题,今天有少数研究赵树理的论者也曾经注意到过这一问题。缺失这种“计算”的方式,而过度强调对个人自我和利益的压抑,即“欲望”的抑止,将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缺乏可靠和持久的中介转换通道,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导致“社会”的崩溃。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来看,我们似乎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年同样是力争多打粮食,在个人是错误的,在集体则是正确的这一矛盾现象;自然也就可能想不通为什么牲口统一到社里合槽喂养,就瘦了(此事在小说中延续了多个章节,成为情节的推动力之一)①;以及到了1956年高级社以后,为什么粮食会持续大幅减产②。
然而,关于小说中的“欲望”讲述,恐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可能是一种选择性的压抑。以郭振山为例,土改时代这位因为斗争地主时敢于出头被人们称作“轰炸机”的农会主席,由于给他评下“全部一等一级稻地”并且“他接受了”,就由一个最初的租不到足够的地种只好兼着挑担儿卖瓦盆营生的佃户,转而发展成了土改后最早出现的新中农之一。郭振山不仅买了地(郭振山是1951年冬天,从下堡村钉鞋匠王跛子手里,买了这二亩桃林地的),而且还有余粮投资私商的砖瓦窑,并且暗中准备盖四合院。他的家业俨然已经与大庄稼院的气象相近。然而,一方面,郭振山“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951年,正是土改运动他得到优质稻地的时间,这意味着他的财富“起源”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郭振山第一个五年计划未能实现,买地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整党时已经把共产党员买地的问题,提到犯纪律的水平上来了,但是不仅土地仍然在他手上,而且他们兄弟三人仍然醉心于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让人瞩目的是,不仅郭振
山在土改中分得好地是在“斗争地主”的组织路线内,以隐蔽而无名的形式获得实现的;在合作化运动中,因投机砖瓦窑受到卢明昌的警告批评以后,他更注意以“在党”这一组织路线内的形式,来维护他的个人利益和威望,也即他的财富及权力“欲望”。在《创业史》第一部第十二章“共产党员郭振山痛斥庄稼人兼卖瓦盆的郭振山”的那段文字中,与其说是郭振山在赞美“在党”,倒不如说真切地透露出了他所看重的,不过是“党”在那个时期的无上威权。而对于这种政治性威权的赞美,作者在通篇小说中都在表现着,不嫌其繁复。这些“欲望”由于处于实际的匿名状态,反而得到作者一再的表达与赞扬。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据作于1979年2月阎纲的《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一文,文革后1977年新版的《创业史》第一部,柳青仍然做了较大修改,删去了两万多字。而这些被删去的文字,多直接与欲望或者诱惑的身体有关。该文作者阎纲先生含蓄地说,以上引文,全部删去;为什么删去?读者可以进一步研究。[5]不过,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个欲望的身体即使被删去这么多字,也仍然还是隐蔽在场的,因为刻意的删去,正是在场的反证。作为删除的痕迹,如小说中有万与生宝间互相打趣的那些话,仍然活跃着“性”乃至“性生活”的影子(第一部第八章、第二部第十五章),等等。
二、欲望矛盾导向主体性问题
当年对于普通个人的“欲望”,确实都是极力抑止的。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全国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比较集中地讲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即今天所谓资产阶级式的个人权利的问题。他说:“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8月21日上午的讲话中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6](171−173)《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以后,引起了理论和学术界的争论。然而,在当时所谓“吃饭不要钱”,而且主张穿、用以及其他各种需要都应当由人民公社包下来等美好愿景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不仅“私”或者“资产阶级法权”受到严厉的批判,更重要的可能还有一个貌似非常渺小的问题:“计算”的方式正在被全面鄙弃。这终于导致了小说《创业史》中某些明显的粗鄙与错乱。如“活跃借贷”那一段,为什么高增福、任老四、任欢喜(任志光)可以向郭世富借粮,不仅欠而不还(他们去终南山割竹子、运扫帚后各自分得了一笔钱款),反倒还放肆唾骂,显得非常有理,而且作者也显然赞同他们。虽然倒卖粮食和进城收破烂在当时不一定正确,但高增福们应不应该无故只盯着别人(郭世富、姚士杰)的私家粮食和追究别人(姚士杰、白占魁)的私人行为?包括郭振山希望不要宣布土改结束,强制命令征用姚士杰家的大秤等工具,以及郭振山、高增福带着大群贫雇农到姚士杰家逼收余粮甚至陈粮的情节等,是否这其中仍然也有着“公平”的问题需要讨论?——因为我们注意到,以1950年代初的土改为界,郭世富乃至姚士杰在《创业史》第一部中主要还是作为勤劳、节俭、有谋划的农民形象而出现的。如郭世富本为佃户出身,土改后被评为富裕中农,亦证明其地亩、牲畜、财产等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可能并无多大突出之处;即便说土改前他也并未剥削,因郭振山说过,要不是他阻挡郭世富,后者这时的成分就是转租剥削的二地主了。在后来的普选中,郭世富甚至被选为官渠岸东头的乡人民代表。姚士杰虽然是富农出身,但是“一九五○年按土地改革法,征收了他多余的土地,又清算了他的高利贷剥削;那些过去给他的利息已经和本金相等的,就一笔勾销了”。这意味着土改后的姚士杰和其他人一样,仅剩下了基本数量的土地作为生活资料。土改的那两年,姚士杰每年春天还拿出十石粮食交给村干部去周借给困难户。姚的“敦实的身体”也是典型的勤奋劳动者的体貌,第一部第十章里他吸着水烟在院子里一刻不歇地一面谋划一面劳动的情景,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但是,在活跃借贷、征购余粮等过程当中,郭振山们不仅未曾以“计算”的公平对待过他们,而且使得他们的身心受到极度的恐惧与压抑。这里仅仅想说明,“计算”被鄙弃,欲望由此遇挫,积极性就成了一个严重问题;这样一来,“创国家大业”又如何可成呢(“创业”本为欲望)?小说第一部也延伸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词语:尊严。但是,当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两相混同,“计算”作为劳动成果转移中介被完全抛弃,也就是说,当“公平”成为一个隐蔽而强硬在场的因素时,何为个人“尊严”的边界?
个人的“欲望”被抑止,个人“尊严”的边界模糊,虽然高增福们的“尊严”貎似被作者强有力地表现着,实际上,这一切仍然意味着主体之间间性关系的溃败。至少,从《创业史》来看,它或许引起了我们的满腹狐疑: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个人主体的不信赖和压抑?因此,主体之间间性关系的溃败可能同时也意味着,真正完全的个人“主体”很难在这一讲述中被确立,因为“主体”通常会凭借混含着个人欲望与尊严的自我来获得确认/认同。有意思的是,自《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暴风骤雨》(1949)等斗争小说起,“县委干部”尤其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如上述小说中的县农会主席老杨、牺盟会的县特派员小常、县宣传部长章品、县委书记萧祥等,常常被委派下来纠正基层政策工作的失误而成为“党”的直接代言人。应该说,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土改小说以后,或者由于政策的复杂性,这种代言人的身份更多地趋向于“县委书记”的职务。如《山乡巨变》(1957)中的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创业史》(1959)中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里为时代所需要的高昂“主体性”,其实是一种“上溯”的主体性:一方面是文本主人公的实质的不完全“主体性”,另一方面是时代所需要而在文本里强烈表现的高昂“主体性”,它们在文本里往往统一在相同人物的身上;而这两种主体性之间的弥合,常常是以纵向的清官之链来呈现的,它使原本是个人“主体性”的抽象内涵层层上溯,以时间、空间均不可见的隐喻方式,朝向那个“超级主体”。具体来说,无论是《暴风骤雨》,还是《创业史》《艳阳天》,甚至《李双双小传》这样的短篇,都有“村(大队)支书——乡(区)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宣传部长”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独有偶,基本都是“书记”或“宣传部长”,而很少其他的职别。并且,这个链条最后朝向“国家”和“毛主席”。《暴风骤雨》里的那个在有无萧祥的支持下,能力表现得殊为不同的郭全海,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在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有党在,咱怕啥。”这不仅表现为个人主体对独立思考和个人利益面向上溯“主体”的主动让渡,更表现为个人主体的休眠而被一个更有力的上溯主体所取代。因此,《创业史》里梁生宝动辄跑到镇上王书记家里,甚至会碰到县上副书记,演绎出大段大段的议论文字就不奇怪了。在这些景象的后面,那个“超级主体”的身影影影绰绰可见。[7](201, 213)在小说第一部的第十六章中,不仅梁生宝一见到王书记,就有一个“把庄稼人粗硬的大手,交到党书记手里”的交出自我的隐喻,而且在预备党员梁生宝、区委书记王佐民、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之间,他们并非是作为个人主体在进行平等的对话,而是作为不同等级的上溯主体,即“党”的代言人在交流。其间,下一层级的主体面对上一层级的主体时,他们的对话心态是并不一致的。比如王佐民向杨国华说话时,其五次明显的个人态度在小说中都被表述为谦恭有加;而梁生宝的表现也大致差不多,像“杨书记吸烟的时候,生宝用那么尊敬和佩服的眼光,看他那聪明、理智和有力的面部表情”,等等。小说在后来的行文中甚至假韩培生的沉思而有了更为直接的表达:“渭原县委陶书记、杨副书记、黄堡区委王书记和下堡乡卢支书——这三级党委书记不约而同的那股为人民操心的劲头,渐渐地注入了韩培生的精神。”[7](379)同样在这个第十六章里,既出现了“毛选”,也出现了“马列主义”,还出现了“毛主席的话”。事实上,这种恭敬一类的对话词汇在小说中是非常多的。并且,小说中把下至郭振山的代表主任/互助组长、梁生宝的互助组长/农业社主任、高增福的互助组副组长/农业社副主任、杨加喜的互助组副组长,中至卢明昌的乡党委书记、王佐民的区委书记,上至陶宽的县委书记、杨国华的县委副书记等,一概称为“领导人”或“首长”,并在农业社章程中和讨论对农业社应有的态度时特别说明,“不能兵不认将”,即应该服从干部。要是不服管,就是犯了社章。排除政治属性的讨论在外,这一切至少表明了不同主体在交接时,其间性关系是处于萎缩与不发达状态的。
让我们深思的是,随着个人欲望、尊严及主体间性关系的抑制,个人“幸福”也变得非常难以被指认。虽然在第一部的结局中,写到了“在宣传总路线的时候,人们说的那些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前景,使得他们没有办法不欢笑啊”这样的话,但小说提及真正幸福生活的地方极为罕见。仅第二部第十二章略有提到:“年轻人们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是幸福生活;老年人说,牲口合槽,就是幸福生活了。”当然,这仍然是非常简朴的“幸福生活”。正如前述文字提过的一样,梁三老汉的“三合头瓦房院”的梦并没能实现,郭振山的四合头的新房后文也并无提到,高增福的草棚屋其实也没见建起来。倒是第二部作为故事推动力来进行夸张处理的白占魁的“坐车唱戏”事件,被村民们纷纷称为是“农业社有优越性儿”和“过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这样的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件,居然惊动了区委和县委的领导,确实让人觉得颇有些不可思议。与此相关的,小说中有一段梁生宝的自白或者不太引人注意,但如今读上去,不能不说隐隐有肃杀之气,正体现了唐小兵所谓“日常生活的焦虑”:
我说: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也活得没一点意思了。不是我好胜,也不是我好面子。自决定办灯塔社,除过互助合作,我啥话也听不进耳朵里去了嘛!我走在路上,听人家一边走路一边谈叙:某某人给他儿订下媳妇了;某某人的婆娘养下小子了;某某人的有奖储蓄中奖了;南瓜和小米煮在一块好吃……我心里头想:啊呀!这伙人怎么活得这么乏味!这么俗气!我紧走几步,把他们丢在后边。我不愿和他们一块走路。要是我在路上听见人们谈叙怎样把互助组办好,怎样领导互助联组,怎样准备办社……我看见这些不认识的人可亲爱哩。我由不得走慢点,听听他们谈叙;要是他们有不得法的,我还由不得插嘴,给他们建个议。我就是这号货嘛。拿起来就放不下,一条路跑到黑!我给老魏说:县上要是决定停办灯塔社,我不服从
平心说来,梁生宝如此坚决地反对日常生活,这只能直接意味着他反对寻常百姓的任何“幸福”可能。
三、“生活故事”与讲述“历史”
上述所有这些关于1950—1960年代中国农民们的欲望、尊严、主体性、幸福等内容的讲述,在柳青的《创业史》中虽然自谦为不过是一部“生活故事”,但作者显然意不在此,而是以更大的雄心将其转化为“历史”本身,甚至不只是“嵌入”到历史中去。无论是冯牧的《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何文轩的《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史诗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2月号),还是徐民和的《一生心血即此书——柳青写作〈创业史〉漫忆》(《延河》1978年10月号),阎纲的《史诗——〈创业史〉》(《延河》1979年第3期),抑或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座谈会纪要》(《陕西日报》1978年1月31日),以及长期以来通行的各种当代文学史中关于这部小说的概述文字等,都指证了这一判断。③尤其是阎纲先生的上述文章,对于这一判断的阐释铺陈了许多文字,如“《创业史》在认识历史、反映历史上所达到的深刻程度,大大超过了同类题材的作品”;“《创业史》的‘史’的性质就显得很突出了”,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段,如下:
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柳青同志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相融合而达到的客观效果,即这部长篇巨著达到的“史”的效果。当然,它不是抽象的历史,不是创业过程的刻板记述;而是形象的历史、诗化了的历史。“史”和“诗”在《创业史》里融合得非常和谐。把《创业史》称为“诗化了的历史”和“历史性的诗”,是由于柳青同志在描绘历史画面和历史进程时,运用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的方法,严格的典型化的法则。[9]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历史”都是一个与“真实”相纠结的概念,虽然它并不等同于实证主义的真实。这也正是我们应该谨慎地对待“历史”与“讲述”两者关系的原因。不能不说,作家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这在阎文的结尾有一大段诠释,以证明小说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都得于实际的经验,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着笔,或者都是“非身历者不能描写”的。前述徐民和《一生心血即此书——柳青写作〈创业史〉漫忆》一文,曾指出小说中“进山割竹子”一段,在正式出版前经历了前后三次的修改,作者不惜为此“亲自进了一趟终南山”[10]。甚至《创业史》中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着相似度相当高的原型的:梁生宝——土改后王家斌互助组组长,后来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4](118−119);卢明昌——解放初期皇甫乡党支部书记董廷芝[10];县委副书记杨国华——柳青本人[11];区委书记王佐民——当年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改霞——柳青夫人马葳,等等[12]。但小说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的“意味深长的沉默”(马舍雷语),今天依然是我们考察《创业史》时无法与真实的历史记述形成有效互文对话的困扰。它涉及到许多方面。当然,首先是关于1953年冬以后的“统购统销”。这一事件是关于十七年农民命运的一个严重症结:从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由于建设事业的规模急遽扩大,非农就业人口迅速增加,粮食需要量大增,给农村带来极大压力。1953年10月全国粮食会议召开以后,确定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方案(即“统购统销”)。陈云对此有过一段著名的话,将其比拟为“是挑着一担‘炸药’”[13](187)。从历史事实来看,“统购统销”对农民造成了极大伤害。一方面是当年集体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的低效率,1955年后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另一方面是随着城市和工业建设的扩大,粮食征购量逐年大幅攀升、甚至翻倍,以至于造成农民的最低口粮水准数十年处于极为匮乏的状态。客观地说,仅以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所述,陈云当年担心的“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曾经在不同地区演变成事实。例如,以高王凌书中《湘中县人均口粮数字》一表来看,自1955年至1978年,除1978年为641斤以外,仅有1956年达到569斤,其他则都低于1956年水平,大部分年份在410斤至480斤左右(均指稻谷)[14](100−105)。这一严峻问题同样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1959年的郑州会议上说: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地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他们的做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利。毛泽东认为,从1958年秋收以后的全国性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正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15](62, 70)但小说显然回避了这一事实,对统购统销进行了轻描淡写,并将这一盛大的粮食入仓工作称之为“历史壮举”。当然,这是1953年,当时的农民相对来说对于国家的农业政策仍然是特别信赖的。但问题在于,《创业史》并不是写于1953年,而是最早发表于1959年,第二部甚至发表于1970年代末。遗憾的是,我们却在小说中看不到丝毫的历史性笔调。而让人惊讶的是,早在1960年初冯牧先生的《初读〈创业史〉》一文,就对此提出了批评:“作品以实行统购统销、准备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而告终;但是,对于这个曾经震动了广大农村的重大事件,在这里解决得似乎是过于轻易和匆促了。读者原是希望能够看到关于这一事件的更为丰满和深刻的描写的。”[1]1961年的李士文《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谈〈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形象创造》一文,也据作者1956年出版的《皇甫村的三年》的内容指出,王家斌曾经打算过买地,并曾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一度感到过迷惑。[16]但作者似乎相当迷恋于扮演全知全能的“上帝般的”讲述者,从而排定一切矛盾、冲突以及解决方案。当年引来许多争议的严家炎先生《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正是在历史与现实两者之间,针对《创业史》提出了非常纠结的疑难:
是紧紧扣住作为先进农民的王家斌那种农民的气质,即使在加高时也不离开这个基础呢,还是可以忽视这个基础?是让人物的先进思想和行为紧紧跟本身的个性特征相结合呢,还是可以忽视其个性特征?是按照生活和艺术本身的要求,让人物的思想光辉通过活生生的行动和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展现呢,还是离开(哪怕只是某种程度上的离开)这个规律,让人物思想面貌在比较静止的状态中来显示呢?……
经过煞费苦心的安排之后,主人公原则性强、公而忘私的品质当然是突出了,但同时,生活和性格的逻辑却模糊了,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个性“消溶到原则里”的情形也就多少出现了。[17]
《创业史》对于“历史”的改写,当然不尽在“统购统销”事件一端。此外,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籍制度,也被改写成了改霞以共青团员的理想积极参加国家工业建设的高昂的政治热情。这里甚至出现了“蛤蟆滩的社会主义”与“城里的社会主义”的区隔。1953年春改霞到县城投考国棉三厂时,被王亚梅严肃地告知:党中央和国务院有个教育农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昨天才到县上。王亚梅称,中央指示,首先要照顾城市居民里考不上中学的,没有职业的闺女,至于农村,以后仍恢复有计划、有组织的输送;有几个大城市的经验已经证明,原有派人到各县进行大招考的方式,“影响不大好”④。当年的“三大差别”,即农工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亦被作者明显改写。例如,仅以其综合表现之一的“干群差别”为例,就可以看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醒目悬隔:县委书记陶宽堪称奢华舒适的办公室陈设以及咖啡糖等美食,与梁生宝简陋的单身草棚屋与青稞饼子;作为“首长”威仪被作者反复宣示的杨国华副书记的狐皮领大氅,与高增福身上长期穿着的开花烂棉袄;王亚梅握住赵素芳粗糙双手的“白净的手”——第一部里“这是县上哪个负责同志的爱人呢?改霞想不起来了”的王亚梅,终于在第二部里被作者安排为县委书记陶宽的爱人。以《创业史》中的农民而论,赵素芳已经算得上是可爱并且有些贪图安逸的妇女了,但工作组亚梅同志“手指纤细白净的两手,捉住素芳粗糙结实的两手”的图景,依然让人读后感到有些刺目;县委会议期间(互助合作代表会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穿着四个口袋制服的农村干部”和“穿着两个口袋衣服的庄稼人”,“穿棉制服”的乡以上干部和“穿庄稼人衣裳”的互助组长、合作社主任们;以及小说中“戴制帽”的脱产干部与“包头巾”的庄稼人脑袋,等等。让人吃惊的还在于,小说不仅提到了梁三老汉脖颈上的“一大块死肉疙瘩”,而且提到了郭世富以及到下堡村乡政府参加会议的二十几个庄稼人,都有着长期超负荷劳作而造成的“重劳动过的体形”。事实上,这些正是某种程度的畸残的身体。而郭二老汉和任老四因为长年勤苦劳动,以至于小农具的“木把被手磨细了”的描述,堪称让人惊心动魄!当然,另一方面,作者将那些白净、庄严、优雅的身姿派给了县委的那些干部们。甚至于在进步、光荣、完全醉心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蛤蟆滩,因为其水质的原因,村民们老年以后往往会得“粗脖子”病,却没能引起任何干部的注意(第二部第七章、第二十三章;即碘缺乏症)。小说也提到了对于“富农”的措施,但却只是简单地将其融入到对于富农的嘲讽之中,“‘看这样事,共产党学不学苏联吧。’姚士杰说,‘要是也学老大哥,可就苦了咱们了……’”等等。
引人注目的改写,还在于柳青对于“时间”暴力的巧妙借用。开篇神奇的《题叙》,正是以典型的“时间”的方式,隐蔽地安排了一些事件,使它们在时间之维中看似互为原因与结果——纵向的时间,恰恰成为“历史”的隐喻,这也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齐泽克意义上的“闭合叙述”。它的“主题”企图应该说是过于明显的,让我们感到满腹狐疑的是:如果梁三和生宝的故事是必然如此的,我们将如何解释郭世富、郭庆喜、梁生禄和冯有义们的故事?因为梁三家总体来说非劳动能力人口比例很小,又无长期卧病者,也没有出现大牲畜死亡等偶然变故;全家“破命”劳动,按理说正是中国乡村中应该较早脱离赤贫境遇的农户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必然的原因⑤,则如何确认以梁三、生宝为代表的农民们的未解放状态?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第一部中作者还没来得及慎加安排的梁大老汉以及姚士杰的财富“起源”的故事,在第二部中被作者追叙为典型的时间及偶然模式了。其中最为奇特的,是姚家的发迹故事。富成老汉的财富“起源”竟然是溃兵的意外丰厚的馈赠,即“一百二十两银子”,它看起来多么勉强,好似天外飞来般的“起源”神话。与此类似的,还有离奇地被追述的梁大老汉最初发迹的故事:两次舍命替下堡村地主杨大剥皮到汉中府走私烟土,换得了共十八亩地和一头牛。这一切过于刻意的讲述,是否意味着作者对于第一部中郭世富、姚士杰们到底为什么会比其他人先富裕起来的问题,感觉到了阐释的焦虑?把姚士杰、郭世富乃至梁大老汉的发家故事,追述为如此偶然和神奇的际遇,作者的努力是否正在于:如果上述姚、郭、梁三家是如此“邪恶”发家的,所以就无怪乎破命劳动、老实巴交的梁三父子必然无法脱离赤贫生活了。看起来,“时间”真是个好东西,一切叙述上的矛盾之处,作家柳青都可以从容不迫地在历史的回叙里铺展成纵向的因果关系,而予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那篇神奇的《题叙》里最让人觉得突兀跳跃的一处文字恰好在于:“……但是,又过了一年(据小说,应指1952年),梁三老汉失望地得出了新的结论:生宝创立家业的劲头,没有他忙着办工作的劲头大。”“他比解放的时候更积极,只要一听说乡政府叫他,掼下手里正干的活儿,就跑过汤河去了。”—那个原文中就有的省略号的后面,被略去了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和过程?
四、结语
柳青当年的《创业史》可算是一部真正峻急于“教育农民”,或者说解放农民的宣讲式作品。今天重读这部被称为描写了19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史诗性的“伟大作品”,不禁使人感慨良多。不得不说,柳青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他的《转弯路上》(1949年6月)[18](414−418)、《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人民日报》1951年9月10日)、《永远听党的话》(《人民日报》1960年1月7日)等篇,非常细致地记述了他严肃地进行思想改造以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心路历程。“长安十四年”,至今仍然是我们应该深思的“柳青的遗产”的厚重内容。但是,我们同样也很难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同是一个柳青,作于1942年的《喜事》以及1956年的《皇甫村的三年》中的诸篇,读起来要让人觉得平和、厚实得多?我们读那些篇章的时候,不仅可以与那个“不在场的在场者”的“历史”形成从容而丰富的对话,而且也可以享受到作者充实而多姿的“讲述”之美。然而,阅读《创业史》却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同:一方面,我们不由得时时会从作者的讲述中分神游移出来,面对当年厚重的历史,因对话关系的断裂而使自己满腹狐疑;另一方面,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柳青却给人一种雄心与犹疑、坦荡与欲望、忠诚与偏狭、厚重与单调等等驳杂混同的印象。而这一切,又是为什么?所有这些,或许正是因为柳青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过于强烈的“历史”化努力。通过一系列特别的策略,柳青的故事似乎很圆满地讲述完了,“历史”似乎也已经非常完美地被给予了再现与诠释。然而,这个庞大的讲述体系看起来仍然有着太多的脆弱之处。而其根源,可能正在于柳青先生在讲述之始就被刻意隐藏的“欲望”,及其作为欲望转换中介的“计算”。本文依然相信,与弱者的“解放”密切相关的社会正义,其前景正在于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正像汪晖先生的《死火重温》和美国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等所说的,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行将作为理论的社会主义与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做出区别对待。[19](47, 29)毋宁说,毛泽东当年所赞扬的“鸡毛上天”,正是弱者解放的一种隐喻,也正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种期许。但是无论多么绚烂多彩的理想,仍然需要一星一点地将其落实为切实稳妥的现实。这也正是本文主张“历史”应该得到我们全神贯注的凝视,并且应该先于“讲述”的考虑[20],虽然这样说可能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注释:
① 柳青曾因为发现农业社牲口由于管理不善、出现死亡,专门编写过一篇《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该文最早发表于1962年12月22日《陕西日报》,后被《延河》1963年2月号、《中国农报》1963年第6期转载。
② 杜润生称:合作化以后,农村并没有发生原先预期的变化,1956年粮食反而减产了,而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减产。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7页。高王凌也称: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曾说过,集体经济是一个不增产的经济,这是从全国角度所做的一个观察。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③ 冯牧引述见前。何文认为,从“思想高度”与“艺术高度”两个方面,“柳青以雄伟的结构与规模完成了《创业史》的史诗般的构图”。徐文则回顾了作者的自述,“他说:‘我这个小说只有一个主题——农民是如何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并且称,“无怪乎一位和柳青过从甚密的作家这样感叹道:‘《创业史》他是作为历史的画卷来写的,他要把这本书写成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发生、发展的史诗。为了这个事业,他什么样的苦都可以吃。他给自己挑的这付担子,是十分沉重的。’”另外,《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座谈会纪要》也称:“柳青同志的《创业史》,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等等。
④ 据小说中的内容与史实相印证,此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应指《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七日)。参见于建嵘:《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 第二卷(1949—2007)》(下册),北京:中国农业发展出版社,2007年,第2012-2013页。
⑤ 梁三年轻时死过两次大牛,仅是《题叙》的“前史”。而梁三出卖大黄牛是在生宝被拉了壮丁以后;但“拉壮丁”仍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偶然遭遇,因为与生宝一样的年轻人都会被拉壮丁,所以“卖黄牛”也就较难被解释成一定会贫于其他人家的必然性原因。
[1] 冯牧. 初读《创业史》[J]. 文艺报, 1960(1): 20−23.
[2] 柳青. 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J]. 延河, 1963(8): 57−61.
[3] 王逢振. 政治无意识和文化阐释(前言)[C]// 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 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 柳青. 灯塔, 照耀着我们吧![C]// 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 阎纲. 新版《创业史》的修改情况[J]. 新文学史料, 1980(2): 258−265.
[6] 毛泽东. 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 北戴河)[C]// 毛泽东思想万岁(内部出版物). 编辑出版者不详, 1967.
[7] 柳青. 创业史(第一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8] 柳青. 创业史(第二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9] 阎纲. 史诗——《创业史》[J]. 延河, 1979(3): 56−67.
[10] 徐民和. 一生心血即此书——柳青写作《创业史》漫忆[J]. 延河, 1978(10): 16−21.
[11] 阎纲. 四访柳青[J]. 当代, 1979(2): 164−173.
[12] 韩毓海. 春风到处说柳青——再读《创业史》[J]. 天涯, 2007(3): 12−22.
[1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14] 高王凌.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M].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15] 毛泽东.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二月),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C]//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16] 李士文. 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谈《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形象创造[N], 人民日报, 1961-8-9.
[17] 严家炎. 关于梁生宝形象[J]. 文学评论, 1963(3): 13−23.
[18]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C]. 新华书店, 1950.
[19] 汪晖. 死火重温[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20] 王再兴. “人民性”与“人民性”文学的二律背反[J].中国文学研究, 2012(1): 111−115.
The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and desire expression of the novels in“17 years”
WANG Zaix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418008, China)
How to handle “desires” was always a serious problem for the collectivist literature of those years. But the fact was that desires were always there though concealed by the reality.The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indicated many traces of desires reversely. On the other hand, oppression of personal desires and dignity meant that the intersubjectivity withered because of special historical context in the late 1950s. Those resulted in incomple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individuals (“New People”). This grand story system still looked having too many weak points. The deep reasons probably lay in “desires” concealed by the author intentionally from beginning, and “calculation” as the desire conversion agent disdained. Since then, desires and calculation have become never-ending topics left behind by Liu Qing andThe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farmer novels; desires; “historicize”; collectivist literature
I206.7
A
1672-3104(2015)04−0183−09
[编辑: 胡兴华]
2014−12−15;
2015−06−15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A263);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4A115)
王再兴(1968−),男,湖北鄂州人,文学博士,湖南怀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农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