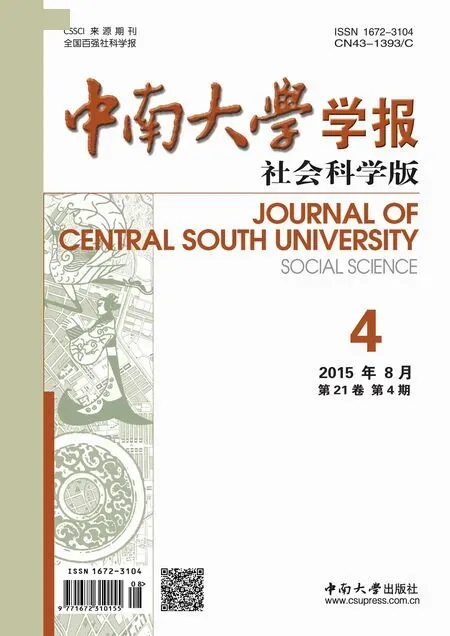洛克关于自然权利“天赋性”的三种论证
2015-01-21储昭华汤波兰
储昭华,汤波兰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洛克关于自然权利“天赋性”的三种论证
储昭华,汤波兰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洛克对自然权利的“天赋性”提出了三种论证:一是自然法论证,认为自然权利是自然法之规定;二是神学论证,认为自然权利是上帝意志之体现;三是理性主义论证,认为自然权利是人类理性自身之内在要求。这三种论证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不同缘于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三种论证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神学论证中,没有解决好上帝的普遍存在问题;自然法论证中,自然法观念非常含糊不清,既包含不证自明的超验成分,也包含有待证明的经验成分;理性主义论证中,其理性是“超历史的”,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
洛克;自然权利;自然法论证;神学论证;理性主义论证
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在国内学术界又被译为“天赋人权”),是近代西方人权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弥尔顿、霍布斯等人都提出过“自然权利”,但是,第一个将“自然权利”观念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系统阐发,进而奠定西方人权学说基础的是洛克,如论者所言,“在洛克那里,自然权利不再是零散的、并列的,而是形成一个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1](16−17)斯特劳斯也正确地指出:“所有现代自然权利理论的导师中,最为著名和影响最大的就是洛克。”[2](168)洛克在《政府论》《自然法论文集》等著作中有关于“自然权利”思想的完整论述,通过这些论述,洛克不仅向我们详细展示了自然权利的内容、特征和原则,还对其“天赋性”进行了论证。洛克论证自然权利“天赋性”的路径主要有三条:其一为自然法论证,证明自然权利乃自然法之规定;其二为神学论证,证明自然权利乃上帝意志之体现;其三为理性主义论证,证明自然权利乃人类理性自身之内在要求。这三种论证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且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以下就此作些探讨。
一、自然权利:作为自然法之规定
近代西方人权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理论。众所周知,自然法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在洛克之前,自然法理论已经产生了两千多年。从古希腊到近现代,这一传统之所以被不断传承和弘扬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代代思想家们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对其展开新的阐释,赋予其新的含义。不仅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自然法的解释迥然不同,而且同一历史阶段如近代西方的思想家们——从洛克之前的格老秀斯、霍布斯到其后的卢梭、孟德斯鸠等,对自然法具体内涵的阐释也既有前后传承和彼此相通之处,又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差异。
古希腊智者学派、斯多葛学派、教父哲学家等最早提出和发展了有关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他们大多将自然法看作关于正义、判断是非善恶的终极性的道德规范或原则。自然法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过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并且,自然法是一种普遍性的标准,亦即,自然法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的任何人。作为近代西方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洛克复兴了自然法传统,正如论者所说,自然法乃是“洛克思考的核心,尤其是其论人和政府的所有思想的核心”[3](71)。洛克的自然法思想既是对前人的继承,更有着重大的发展,他不仅赋予了自然法一系列新的、丰富的含义,更将其与人的自由与社会进步密切地联系起来。
洛克对自然权利的论证首先是从自然法开始的。如上所述,传统自然法理论强调道德规范和原则的自然性、普遍性,以及它们所表征的道德义务,洛克关注的则是道德规范和原则中引申出来的每一个人所享有的一种(道德)权利。洛克认为,自然法和“各国的明文法一样可以理解和浅显,甚至可能还要浅显一些”[4](8)。与此同时,洛克坚持认为,社会状态中的明文法是人造的,但是其根源又是自然的。
为了追溯自然权利的起源,与霍布斯等的自然权利观念的先驱者一样,洛克也预设人类在进入国家(社会)状态之前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在此前提下,洛克对人类在自然状态这种前国家状态中的权利状况进行了考察。不同于霍布斯,洛克认为,自然状态并不是一种霍布斯所描述的混乱无序、无法无天、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相反,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状态,是一种自由、平等和无限美好的状态。“自然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规则以约束人的行动,自然状态中存在着自然法。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受到自然法的约束,人与人的关系,由自然法调整。为了保护人们彼此之间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受侵害,自然法为个人的自由行为划定了界限,设置了约束条件。自然法教导人类,首先,“虽然人具有处理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4](36),换句话说,他有义务自我保存;其次,每个人除了自我保存外,还必须保存他人。
表面上,洛克的自然法表达了“应然”的规范性特征,规定人们应当怎么做,进而使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展现出区别于动物的文明性。实质上,洛克的自然法并不是一种只体现义务或规范的道德原则,相反,它更多的是一种权利的道德原则,“意指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为人在自然界中的生存提供了起码的条件,在这种意义上,自然法和天赋权利是一回事。”[5](148)洛克的基本论点是:人类在国家出现以前处于自然状态之下,并享有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惩罚违反自然法犯罪等在内的自然权利,从自然法角度看,所谓自然权利,就是“人们生来就享有完全自由的权利,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或许多人相等”[4](5)。
这一界定表明:一方面,自然权利是由自然法这个终极的、超验的权威来赋予、规定和支持的,其逻辑是:在自然状态中,人具有自然法所规定的自然本性,人的自然本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自然本性规定人应该享有什么,人之作为人就享有什么,而个人权利既然出自自然本性或自然法,因此就是与生俱来且不可剥夺的;另一方面,自然法具有普遍性,自然本性是人所共有的,因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的任何人都可以凭藉自然本性或自然法——也就是人之作为人的资格而享有权利,有权按照符合自然法要求的方式获得相应对待。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人既不能放弃、让渡自己的权利,也不能损害、剥夺任何其他人的权利。
洛克将自然法确立为自然权利的源头,近现代占主导地位的权利话语即滥觞于此,洛克关于自然权利“天赋性”的自然法论证,“通过将重心由自然义务或责任转移到自然权利,个人、自我成为了道德世界的中心和源泉。”[4](253)
二、自然权利:作为上帝意志之体现
在征引自然法论证自然权利时,洛克又转到了对自然权利的神学证明。从历史来看,将自然权利的最终依据归结到上帝那里,这并不是由洛克首创的。受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在近代西方各种“自然权利论”中,总能发现“上帝”的“身影”。究其原因,自然权利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不可避免地具有形而上学性,而诉诸超验权威——上帝,无疑是论证自然权利的一条便捷途径。洛克也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甚至,在洛克看来,“上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上帝的信仰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这个信仰,人就与动物别无二样,就不能形成社会。
那么,洛克是如何从上帝的意志推论出人的自然权利呢?在《自然法论文集》开篇处,洛克指出,上帝创造了世间万物,并且为万物设定了秩序,亦即一定的生存法则,而我们并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只有人类可以不受任何生存法则的控制和支配,因为人类也是上帝的造物。然后,洛克从上帝存在、从人与上帝这种造与被造的关系中一步步演绎出人的自然权利。
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看,由上帝造人,产生出上帝对人类拥有的单方面的、无条件的权利,也就是说,人类对于上帝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因此,人类对上帝的第一条义务就是敬拜上帝和服从上帝的意志。但是,只告诉人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向人们指出上帝的意志是什么。洛克认为,首先,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创造人类这个作品自然是希望人类能够繁衍生息,而不是走向毁灭,因此,上帝印刻在人心中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要保存自己(在个体与种族两个层面上):“上帝既创造人类,便在他身上,如同在其他一切动物身上一样,扎下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保存的欲望。”[6](74)其次,敬拜上帝,服从上帝的意志,不仅可以引申出自我保存的义务,还可以引申出保存他人的义务:“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他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4](5)所有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人们之所以不能彼此伤害,是因为没有人有权毁灭上帝的、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不过,关键的问题是,人们所肩负的对上帝的义务何以会成为一种自然权利?对此,洛克的解释是,从对上帝的义务中可以推论出人的自然权利:我既有保存自我的义务,同时也有保存他人的义务,这两项义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对于“我”而言保存自我的义务,对于他人而言,即是保存他人的义务,这意味着自我保存的义务就是我的权利。同时,我保存他人的义务对他人而言也是一种权利。在此,我们会发现,保存自我和保存他人的义务,在洛克的推论中被悄然转换成一种保存自我和保存他人的自然权利了。从保存自我与保存他人的义务中也不难推导出一些具体的基本权利:比如财产权——为了完成保存自我和他人的义务,获得基本食物、住所和衣物的权利必须被满足;比如自由权——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生活,彼此之间应该是自由的,个体的自由活动是他人不应随意侵犯的;比如平等权——上帝之光融化了人与人之间种类、等级之别,赋予作为其造物的人以平等的人格,因此,在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绝对服从关系,从而使平等的权利诉求成为可能。
可见,是上帝赋予了人类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洛克认为,虽然人的权利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但权利却是与生俱来的。假如没有上帝,自然权利也就不可能出现,上帝意志是自然权利的终极根源。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洛克为何格外重视对《圣经》文本的解读,原因在于上帝的意志是通过《圣经》来展现的,《圣经》就是上帝意志的宣告。在《政府论》上篇中,洛克严格以《圣经》文本为依据,辅以逻辑的推理分析,对保皇党人罗伯特·菲尔麦的君权神授说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洛克还注意到,为了吸引和鼓励人们去追求自然权利(对上帝的义务),《圣经》还附有“来世的永恒而无限的赏罚”[6](35),上帝通过永恒的赏罚——末日审判,为自然权利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三、自然权利:作为理性之内在要求
洛克对自然权利的第三种论证是理性主义论证,这一论证的核心主张是将自然权利的最终源头确立为人类自身的理性。西方近代人权思想总体上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精神催生了近代人权观念,并且构成了西方近代人权思想的一个支撑点。
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专门讨论了人的理性,提出并论证了理性是人自身的产物。概括来说,“理性”这一概念,在洛克那里,主要有四种主要涵义:第一,某些正确的原则;第二,有关这些原则的清楚明白的推导演绎;第三,某个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第四,人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人性的特殊本质,是人区别于畜类并超过畜类之所在。[7](717)洛克认为,人是一种兼有感性和理性的生物。一方面,人有感情,所以人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人有理性,人可以借理性来权衡利弊得失,从而判断出哪些行为有助于人追求快乐和美好的事物。因此,洛克对理性赞誉有加,认为理性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星辰和罗盘”“固定的、明确的行为原则”和“最终的评判和向导”。[8](82)
在洛克那里,人类固定的、明确的行为原则之一就是趋乐避苦。在趋乐避苦的过程中,理性宣示人们,不仅应当考虑眼下的苦乐,还要看到行为的后果,既不能因为一时的快乐而无视将来更大的痛苦,也不能因为一时的痛苦而放弃将来更大的快乐。此时,理性意味着一种计算,一种关于如何满足人的欲望(即趋乐避苦)并使多种欲望相互调和的精明计算。在满足人的欲望时,快乐和痛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洛克认为,与快乐相比,痛苦在决定人们的意志方面起到的作用更大。而在诸多痛苦之中,最大、最强有力的痛苦无疑是死亡,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实现自我保存。自我存续决定了趋乐避苦的意义。因此,理性计算有一个人性前提,即人有自我保存的本能倾向。洛克认为,虽然“在人心中注入了‘保全他的生命和存在的强烈欲望’的是自然(上帝),而教导他何者‘对他的存在是必需的和有用的’只能是理性”[2](232−233)。理性是上帝创世设计的一个必要因素。“上帝既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亦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而加以利用。”[4](17)
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对自然权利的讨论,很少用自然法和上帝的意志等话语,而更多地是以理性的力量来独立说明自然权利的起源。
洛克以理性为桥梁从假设的自然状态中(洛克预设了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是按照理性生活在一起的)推出自然权利似乎很顺利。
一方面,遵循理性指导在自然状态下生活的人,并不服从什么外在的行为规则,他们只根据自己的欲望行事,即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自我保存。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理性需要计算人类生存欲望过程中的一切相关因素。由理性计算必然产生权利需求。也就是说,假如按理性计算来指导生活的话,人们必然会尊重、信奉并追求自然权利。理性教导我们“凡是主宰自己和自己的生命的人也享有设法保护生命的权利”[4](110)。自我保存的需求——理性计算而来的需求,内在地倾向于自然权利的生长。人类将“按照他所具有的自我保存的自然趋向行
事”[6](74),“权利和生活需要是并行不悖的”[4](32)。另一方面,理性维持着人们的整体秩序,防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侵害。理性计算的结果表明,一种相互享有平等权利的和平环境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内在要求,在肯定自己的自然权利时,肯定他人的自然权利将是有益的。自然法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保存自己”[4](4)。甚至,如果一个人觉得另一个人背弃了理性,进而威胁到自己的自我保存,那么,他有权利把他“当作人类不能与之共处和不能有安全保障的一只野兽加以毁灭”[4](7)。
在此,洛克总的观点是,自然权利必须通过理性得到明示,并借助理性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生活。自然权利的确立,假如没有人类理性的参与,就只能外在于人类的生存境遇。
四、三种论证之间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看到,为了论证任何人都享有一系列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洛克提供了三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洛克出现了矛盾:在将自然权利视为自然法之规定的同时,又将自然权利确立为上帝意志的体现与人类理性之内在要求。然而,事实上,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缘于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在洛克的视野中,“自然法”有三方面的内涵:其一,就它可以为人类的行为提供指导而言,自然法是一种道德法;其二,就自然法是上帝的意志而言,自然法是一种神意法;其三,就它可以为理性之光所辨识而言,自然法又是理性,或理性法。假如我们认定自然法是神意法,第一种论证就转化为第二种论证;假如我们认定自然法是理性法,第一种论证就转化为第三种论证。
一方面,自然法是神意法。与格劳秀斯、霍布斯等先驱一样,洛克在很多时候都将自然法归结到上帝那里。正如扎科特所指出:“洛克坚持认为对于自然法来说上帝完全不可或缺。”[9](253)自然法被洛克定义为“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宣告”[4](85),“这一自然法可被看作是神圣意志的命令”[10](82)。因此,“所谓‘自然的’也就是遵从上帝的意志。”[11](9)而如上所述,上帝意志的宣告就是《圣经》,所以洛克声称,《圣经》就是全部、充分的自然法。自然法与上帝的启示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有着同样的内涵和指向,其根本原因不是别的,乃是由于二者最终都是根据理性原则来判断、选择和阐释的。因此,另一方面,自然法又是理性法。自然法与理性向来关系密切,有自然法学家甚至将理性与自然法等同起来。他们认为,自然法即是理性的法则,是理性的箴言和命令。洛克也有类似的表达:“理性,也就是自然法。”[4](6)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性行事。在洛克看来,所谓自然法,就是人凭借理性能力确立的处理自身事务的一些正确而明白的原则。
洛克所谓的自然法到底是一种神意法还是一种理性法?正是在这一点上,引来了后世不同研究者的争议。剑桥学派思想家们认为,洛克的自然法如果没有神意法的支持,就不可能存在,理性只是发现神意法的一种能力或手段。而在施特劳斯看来,洛克的自然法类似于霍布斯的“无神的自然法”[2](208−214),表面上强调神意法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理性法。笔者认为,洛克并无意搞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满足于一种模糊的界定和描述,自然法被赋予神意法与理性法两种性质,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揭示出自然权利的诸项内容。
一方面,洛克敏锐地意识到,无论自然法是一种神意法还是一种理性法,自然法之存在都要以它的可认识性为前提。因此,洛克强调,“自然法可以被理性之光所认识”[10](88),似乎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够理解自然法。但是,另一方面,洛克又认为:“单凭理性自身,它实在难以担当起让道德全面地、真正牢固地建立起来并散发出清明显赫的光明的重任。”[12](133)由于无法对自然法对象的终极性质形成观念,导致人们“对自然法缺乏研究而茫然无知”[4](78)。因此,需要借助于一种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向人们晓谕自然法,这就是“上帝的启示”——信仰:“大多数人无法了解,因此他们必须信仰。”[13](157−158)
不过,信仰也是需要根基的,否则难以赢得信众的选择和信任。信仰的根基就是理性。洛克认为,信仰必须得到共同观念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信仰必须经理性的判定才能得到明确。洛克坚持认为,对于理性的人来说,对任何事物,“我们只有运用自己的理性,才能同意它,而凡与理性相反的东西,理性又是不能允许我们相信的;理性所视为非理性的东西,它是从不会加以同意的。”[7](746)对待上帝的启示也不例外,“凡上帝所启示的都是确乎真实的,我们并不能怀疑它,这正是信仰的固有对象。不过它究竟是否是神圣的启示,则只有理性能来判断。”[7](749)当二者相互冲突时,应该最终服从理性,“任何被假设为启示的事情,如果同理性的明白原则相反,如果同人心对自己明白而清晰的观念所有的明显的知识相反,则我们必须听从自己的理性,因为这事情正是属于理性的范围的。”[7](748)在洛克看来,理性不是要对信仰宣战,相反,理性是一种可以使人达成信仰、感受信仰的方式:“我们必须依靠理性,必须借理性来考察那个命题是否是由上帝而来的启示。”[6](49)任何命题,只要和理性相冲突,就不能把它作为神圣的启示。
在洛克这里,理性与信仰乃是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理性乃是上帝所赐予的;另一方面,上帝的启示又必须经受理性的判断(实质上是选择)。借此,洛克重新解析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确立了二者各自的地位。洛克的这一主张,可视为康德“理性为信仰留地盘”思想的先声。
五、简评:洛克论证中的问题
洛克对自然权利“天赋性”的三种论证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最显而易见的,是在对自然权利的神学论证中,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帝的普遍存在——并没有解决好。将自然法等同于神意法,这就意味着:“自然法之所以能够被证明,那是因为上帝的存在和秉性能够被证明。”[2](207)但是,洛克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公开承认,在基督教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并不信奉基督教的“伟大而文明”的民族,这些民族不读《圣经》,也没有上帝、天堂和地狱的概念。[6](116)因此,在“所有人都认为上帝的启示是明白无误的”这一点上,即使洛克本人也不十分确定。然而,洛克在对自然权利的论证中却依旧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上帝意志。既然这些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也能过上有德性的生活,那么,自然权利就不可能建立在启示、神意的基础之上,要为自然权利提供稳固的的基石,《圣经》并不够格。
其次,在无法解决上帝—神意的普遍性前提之下,洛克必然也“不能够承认任何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法”[2](225)。洛克有意忽略了这一问题,即,在“自然法作为神意法”与“自然法作为理性法”这两种解释之间潜存着巨大冲突。假如自然法是一种神意法,那么理性将只作为上帝意志的发现者而存在,“自然法是理性法”自然就不成立,因为理性只具有工具价值,理性法根本就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而假如自然法是理性法,是一种由人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所建立的生存法则,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身的理性,那么,“上帝的意志”也就没有其地位和存在的必要。此外,洛克的自然法观念非常含糊不清,既包含不证自明的超验成分,也包含有待证明的经验成分。但是,哪些是不证自明的,哪些是需要证明的,洛克并没有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
而当洛克将理性确立为自然权利的真实基础时,我们能够意识到,洛克所指的不可能是某一个体在某一时间段内的理性,计算利益的理性在某一个体身上往往不够强大。因而,自然权利的认知和确认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然是无数人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但是,洛克的论证恰恰脱离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是直接诉诸超历史的理性来完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人权作为一种价值,毫无疑问乃是有理性的人所创设的,也必须通过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才能得到贯彻和落实,作为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论证方法,洛克的自然权利说本来就不是一种人类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事实描述,而是一种有着明确价值指向的理论设定。总的来说,洛克对于自然权利的理性主义论证,很少涉及具体的社会历史,其对自然权利“天赋性”的证成方法是抽象的、超验的,不符合历史的、经验的真实,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这一“反向”的特征,使洛克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被许多人指责为反历史的和唯心的,例如,实证主义者称他的“自然权利”为一种“先验权利”,并非毫无道理。
[1] 谷春德, 郑杭生. 人权: 从世界到中国[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1999.
[2] 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3] 卡尔·J·弗里德里希. 超验正义: 宪法的宗教之维[M]. 周勇,王丽芝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4] 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5] 邹铁军. 自由的历史建构[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6] 洛克. 政府论·上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7] 洛克. 人类理解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8] John Locke. Essays on the Law of Na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迈克尔·扎科特. 自然权利和新共和主义[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8.
[10] Locke. Locke Political Essays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11] 黄伟合. 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从洛克、边沁到密尔[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2] 洛克. 基督教的合理性[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3] Locke. The Reasonable of Christian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Locke’s three arguments about the naturality of natural rights
CHU Zhaohua, TANG Bol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John Locke presents three arguments on the naturality of rights: one is the natural law argument, which claims that right is the provision of the natural law; another is theological argument, which claims that righ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will of God; the last is the rationalist argument, which claims that the right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human rationality itself. These three arguments are both independent from and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but in essence they are the same. The difference on the surface should be due to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law.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about all the three arguments: in theological argument, there is no final solution to God’s omnipresnece; in natural law argument, the concept of natural law itself is ambiguous in that ist includes both some self-evident and transcendential ingredients and experiential ingredients which need to be proven; in rationalist argument, its rationality is “super-historical”, which is far away from the certain context of social development.
Locke; natural right; natural law argument; theological argument; rationalist argument
B504
A
1672-3104(2015)04−0032−06
[编辑: 颜关明]
2014−09−11;
2015−06−18
储昭华(1963−),男,安徽潜山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西方伦理思想比较;汤波兰(1987),女,湖南益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