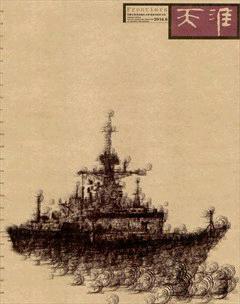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浪潮》:世界离独裁为什么只有五天?
2014-12-17谢宗玉
谢宗玉
一
学者熊培云看完德国电影《浪潮》,以《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为题,写了一篇影评。在《浪潮》海量影评中,那篇文章并不算特拔尖,但这个标题却被广泛引用。
《浪潮》改编于一个真实事件。1967年,美国加州某高中的一位年轻老师罗恩·琼斯为了让学生更深刻领会独裁政治的含义,他在课堂上搞了一个独裁主义运动试验。没想到假戏成真,几天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其中,大家逐渐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之中。直到最后琼斯给学生播放纳粹暴行的图片,惊醒过来的学生才解散了他们的群体。2008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这个事件搬上银幕,不过,地点却由美国换成了独裁政治曾经的大本营——德国,并把温和的结尾改得面目狰狞——让“浪潮”骨干成员死的死,伤的伤,抓的抓。因为这场运动从开始到蔓延,到几乎无法控制,只有短短五天时间,所以熊培云才精辟而俏皮地概括: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很显然,他准确地把握了导演的意图。甘赛尔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世人,像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随时可能酿成风暴一样,只要给点时机,独裁政治也会“兴风作浪”。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随时都要警惕它死灰复燃。
仅只豆瓣网,对这部电影的评论就有近千篇。基本上都是借电影的情节,对独裁主义、极权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等系列概念,进行解读和批判。其中以影评界大腕图宾根木匠的那篇《〈浪潮〉:极权主义起源》最为精彩。在那篇评论中,他详尽地把《浪潮》中的学生运动,与纳粹极权主义做了一个全面的对较,结果发现斗榫合缝,不差毫厘。就像我认为电影《十二怒汉》中的审判是建立民主国家的桌面推演一样,图宾根木匠认为,《浪潮》中的学生闹剧是极权主义运动的试验场。豆瓣网赞同他观点的人高达一千五百多人,而反对者,只有区区二十几个。
相对《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的推论,我更感兴趣的是“世界离独裁为什么只有五天?”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始终只与独裁隔着一层一捅就破的窗纸?
二
三年来,我把这部电影看了三遍。但我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去网上查阅独裁主义、极权主义、纳粹主义、集权主义、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区别。结果发现,这些概念就像一个同心圆,只是各自的外延和内涵不尽相同。而要把它们之间的详细区别说清楚,一本书是不能够的。如果单从那些影评看,包括熊培云和图宾根木匠在内的几乎所有影评人都应该没弄清楚这些概念的真正内涵。或许这些概念的真正定义,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人完全弄明白,也包括写《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汉娜·阿伦特,写《通往劳役之路》的哈耶克,写《现代性与大屠杀》的齐格蒙·鲍曼。
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人文学科内的词条在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几乎就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件的,它的外延并不具有普遍适应性。加上作者和读者的“三观”各有各的局限性,以至对这些人文概念的种种诠释,总带着很强的片面性。
正因为这样,一些中性的人文词条,在读者眼中居然带有很强的褒贬色彩。比如说,直至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平心静气地把“独裁”和“极权”当作中性词来解剖。只要一提起它们,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希特勒”、“纳粹”和“种族大屠杀”,然后几乎不用讨论,就直接宣判了这两个词的“死刑”,跟着连罪的还有集体主义、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等等。反映在电影《浪潮》中,甚至连正常的行动口号,比如“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行动铸造力量”,通过导演强烈暗示,也带上了邪恶色彩。
很奇怪,对不对?这是因为“独裁”和“极权”这两个名词的诞生本来就是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量身定做的。出于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厌恶,我们才把“独裁”和“极权”这样的中性词本身也一并厌恶了。
三年前,我给电影《浪潮》打满分,三年后,我只给它及格分。原因是我惊诧地发现,导演甘赛尔拍摄这部电影时,抱持的不是平常心。出于对独裁政治的恐惧,他似乎长期处在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态下,以至把一场平常的学生运动主观地冠以“独裁主义”的大帽,并把同样对“独裁”谈虎色变的观众们,吓得直冒冷汗。
我这么一定性,估计很多人要愤怒了。
且慢!我这才刚刚开始呢。
三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让我们深恶痛绝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的含义。
“法西斯”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的Fasces,原意是“束棒”,亦古罗马权力和威信的标志。法西斯主义最原始的口号是:“团结就是力量。”法西斯主义最典型的概括就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
“极权主义”则指的是权力主义,通常的意旨:某一人或政党、特定群体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政策皆由独裁者所掌控,没有第二人或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
我要声明的是,这两个定义都不是我原创的,是我摘抄的。出于对人文概念准确性的一贯怀疑,我当然不会认为以上定义就百分之百准确,但马马虎虎也算一个比较中庸的概括吧?
你肯定发现了,如果单从词条解释来看,这两个词似乎并没有那么恐怖。至少,对我们国度的人们而言,这些概念的内涵一点都不陌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认为它是真理。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它与邪恶“法西斯”和“极权”联系起来。
事实上,出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或其他需要,西方政府也没有把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观念与那些惊悚名词纽结在一起,把它们纽结在一起的,主要是西方一些学者。其中以汉娜·阿伦特为最。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就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我们读那本书时,免不了就会产生一种“瓜田李下”和“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的心态。但奇怪的是,放下书,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会觉得自己的社会生活有多荒谬。
如果《浪潮》给我国导演拍摄,会怎么样?只要把里面有关“独裁”、“法西斯”和“极权”等观念性的东西去掉,电影马上就变成了一部青春励志片。主题就是集体主义的胜利。内容还是那些内容,改掉个别台词,然后换上一个光明的结尾,就会看得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同样的道理,很多有关团结起来走向辉煌的励志片,若加上“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帽子,也会变成甘赛尔镜头下的声名狼藉的“浪潮”运动。endprint
四
独裁离世界为什么这么近?学者熊培云给出的答案是“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影评家九尾黑猫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人性中无法摆脱的事实。人们想要寻找强大的力量,并躲避其下”。影评家图宾根木匠给出的答案则是“极权主义与普通人的生活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他们说得都对,但都过于含糊。他们没有往纵深处去审视人类的文明,以及文明的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辉煌灿烂的文明就是集体的产物、团结的产物、纪律的产物,以及行动力的产物。人类最意味深长的文明就是制度——限制个体种种自由的制度。如果把人类文明比喻成一幢大厦,那么制度文明便是支撑整个大厦的钢筋结构。离开了制度,整个人类文明便会轰然坍塌。
单兵作战的能力,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如很多哺乳动物。我们是依靠了集体,依靠了指挥集体统一行动的权力,才成了这个星球的王者,才会把其他生物远远抛在后面。权力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但权力的精心铸造和精妙运用无疑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硕果之一。
文明要向前发展,人类就只能越来越集体化。社会分工的细化、科技的大繁荣,使得整个星球像极了一座巨大的工厂,我们只有捆绑在一起,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集大家的智慧才能将文明日益沉重的巨轮推向未来。文明越发展,集体的巨大潜力就会越彰显,个体的综合能力就会越萎缩。文明让整个人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个体与个体相比较,一个现代人的生存能力却远远不如一个原始人。原因是文明让一个现代人变成了集体的一分子,必须依靠集体才能存活。一个现代人如果不依靠他人,不借助任何文明,他在原始丛林中,生活不了一周。而一个原始人,可以在莽莽丛林中独来独往一辈子。原因是他不是集体的一分子,他是一个完整的独立体、“单干户”。
甚至在某些生物社会学家眼里,人类正日趋生物群落化。就是说,整个人类才是一个独立实体。就像生物界里的蚂蚁群落,单只蚁后、工蚁、雄蚁、兵蚁的存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单个的它们,既不能繁衍,又不能生存。只有组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实体。而这种组合带来的能量是相当可怕的。几乎大部分适宜生存的土地,都被这种社会性昆虫群落占据了,其他独居性昆虫只能生活在剩下的间隙中。它们就像一个堡垒,其他独居性昆虫根本无法与之对抗。一个蚂蚁群落搬迁至一段腐木里,就像是沃尔玛超市搬进了你的社区,其他小型商店都得关门。
蚂蚁的这种组合能力依靠的是基因里的遗传密码,而人类的这种组合能力依靠的是越来越强大的文明。文明俨然成了人类这个庞大生物群落的神经系统。人类的强大正是依靠了集体的合力。如果有一天,繁衍只需要克隆就行,不再需要依靠个体的男女,在生物社会学家眼中,人类个体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显然,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集体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历史。当个体的人越来越不能依靠自身的能力去生存时,我们就只能服从各种各样的号令了。以服从换取生存,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无可奈何的趋势。
团结、组织、纪律、统一、集权等等这些概念,其实已渗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文明制度下,我们要反思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会不会让上帝发笑?
五
其实我们真正反对的、并为之惊恐不已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就是政体。这种政体由于能够迅速聚集一种摧枯拉朽的能量而让人心惊胆寒,这种能量又因为它的不可把握和不可琢磨,让人觉得无比邪恶,并且被“种族大屠杀”的事例给证实了。所以,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将希特勒的极权政府摧毁掉。
在幼稚的人看来,摧毁了希特勒的极权政府,人类就迎来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导演甘赛尔之所以要拍摄《浪潮》,就是想给这种人醒醒脑。可惜的是,他选择这个题材存在很多破绽,并不能作为“世界离独裁很近”最贴切的证据。
而实际上,都不需要他证明什么,所有的文明都在告诉我们,世界离极权主义永远只有一步之遥。因为只要那些约束人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骨架,那么集权便是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也就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保障,而“极权”则是“集权”向前多迈了一大步,从而坠入万丈深渊。
人类要提防的纳粹式社会组织形式其实只是小疥而已,而将人类越来越集体化的整个文明,才是人类的心头大患。我们现在陶醉在它无所不能的“丰富”和“便利”之中,可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把我们带入灭顶之灾中呢?
阿伦特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的苏维埃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大抵没错,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怜的民主政府想要扳倒希特勒,还不得不与斯大林携手呢。按阿伦特的逻辑,斯大林更应该与希特勒合作,对付罗斯福和丘吉尔才是。斯大林之所以不与希特勒合作,是因为地缘政治利益的严重冲突。而斯大林之所以选择与罗斯福合作,无非是外交上“远交近攻”而已。
可见,在历史重要的关口,把生存摆在首位的人类,选择的不是道义上的对错是非,而是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既然这样,我们在摧毁纳粹法西斯主义之后,再以邪恶的罪名,将它批了又批,究竟有多大现实意义?纳粹法西斯主义最大的罪恶其实还不是组织制度,而是这种已不受控制的组织制度为了小部分人——雅利安民族的利益,大有将整个人类进行绝灭式清扫之势。这与人类集体利益是相违背的,因而就是反人类的。
平心而论,在组织制度上,纳粹法西斯主义犯下了“过犹不及”的错误,因为说到底,他们的组织制度和历史以及现代很多国家的组织制度是同质、同母、同源的。只是这种组织制度被一种错误的观念操纵了,就像身体里被感染了病毒的癌细胞,从而背离了人类文明的初衷。
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公权力对私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但我们的神经似乎只对其政治组织形式敏感,仿佛摧毁了人家的政府就万事大吉了。那么军事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去反击人家武装到牙齿的装甲部队?无他,只有比他们更团结,更集权,更残酷,甚至更野蛮。如果把极权主义的外延扩大化,那么,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的军事管理系统无疑都是极权主义的最佳注脚。著名导演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就军队的极权化、野蛮化,有过非常精彩的诠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