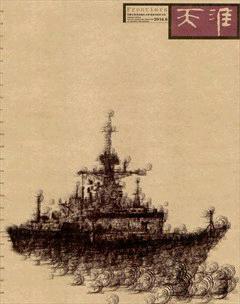我是80后,我怎么办?
2014-12-17黄江苏
黄江苏
存在统一的80后群体吗?
当我看到杨庆祥《80后,怎么办?》(编者注:本刊2014年6期发表时改为《希望我到那条路》)这篇文章,第一时间里曾产生很多错愕,在脑海里久久盘旋:这是谁在说话?以什么语气说话?存在统一的80后群体吗?这个群体陷入危机了吗?因为我知道作者杨庆祥也是80后,所以这让我更加糊涂。一个80后说“80后,怎么办?”这究竟是自问,还是将自己拎出来问别人?是以先觉者自居而唤醒后觉者指点迷津吗?他怎么知道别人还在沉睡,而不是如他一样已经醒过来各自寻路呢?
我想这是杨庆祥此文面临的最大难题。他既在80后之中,又想置身在80后之外;既有可能是问题的当事人,又想成为问题的审判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有几分尴尬。问题的症结就出在80后这个称谓上。这是一个既实又虚的称谓。我们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人,我们确实面临着相似甚或相同的社会形势与时代困境,可是我们又是独立的个体,既不是绑在一起的连体兄弟,也不是程序相同的流水线上的产品,所以我们的认识与反应都可能迥异。也缘于此,当我看到杨庆祥在文中发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的时候,竟然哑口无言,一个都回答不出来。倒是最后一问:“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自我历史的叙述来完成自觉的、真实的抵抗?”因为有“自我历史的叙述”几个字,让我觉得有几分作答的可能。实际上,我这篇回应文章也可以算是一份“自我历史的叙述”吧。
我常常想,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他们,作为1880年代出生的人,当其出场时,为什么没有被称为80后?莫言、贾平凹、张炜、池莉他们,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为什么也没有被称为50后?所以我去查考80后这个词的来源及含义,结果颇让我意外。据说它最早是于2001年出现在网络论坛上,指一批活跃的出生于1980年代的诗人,后来扩大到指称1980年代出生的写手、作家,后来又扩大到指称整个这个年代出生的青年人。意外在于这是少有的由文学界贡献到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概念;其次在于它竟然被认为是一个实体,包含了某种文化含义。也许这就是50后不名于世,而80后到处通行的原因吧。可是简单一想,80后青年人已经数以亿万计,商人、政客、学者、文人、工人、农民行行皆有,这样一来,除了共同的年龄标记之外,在他们中还能真的概括出多少共同的文化内涵呢?
所以我还是坚持前面说的,80后面对的大世界可能是相似甚或相同的,可是他们内在的小世界却各个不同。以是之故,谈论“80后,怎么办?”是困难的,有多少个80后就可能有多少种回答。我相信,这个问题需要80后们众声喧哗,每个人都来回答“我是80后,我怎么办?”而不是由一个人领衔独唱,高屋建瓴,指点迷津。
80后有问题,但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
在我看来,杨庆祥的文章很了不起,他提出了值得一代人思考的问题,没有他的文章就不会有我这篇文章。可是在行文逻辑上,我觉得他却有些飘忽跳跃。第一部分,他讲到“我们被时代淘汰了”,“社会的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鼓励正常的生活和发展”,我们注定是失败者。按照一般的思路,接下来他应该分析社会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至于把我们这部分人甩到了外面,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写,而是转到了批评80后自身的问题,认为80后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历史漠不经心,缺乏历史的存在感。正当我想反驳不是每个80后都这样,“韩寒”(假如他是真实存在的写作者)就是一个明显的反例,他如同鲁迅一样,用自己的杂文,同自己时代中的各种事件,诸如毒奶粉、强拆迁等等,作着坚韧的战斗,转而却看到杨庆祥紧接着就对“韩寒”展开了批评,认为他的抵抗缺乏高度和深度,仍然是消极的。最后,杨庆祥的文章跳到了认识80后自身的阶级属性上去,认为80后是小资产阶级,而在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之下,小资之梦注定破碎,80后急需重新寻路。
先说“历史虚无主义”吧。从杨庆祥的文章来看,它的意思是指对历史没有记性,诸如包产到户、1980年代末的大事件、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等事件,都没有对80后的生命构成冲击。事实上,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80后们确实还小,这些事情基本上只留在父辈和兄长的记忆中,这没有什么好沮丧的。如果历史事件的影响强烈到连幼儿都不由自主卷入其中,那倒很有可能是不正常的了。我们只参与我们长大成人以后的历史事件,例如杨自己也提到的汶川大地震等等,我们只需对成人以后的历史事件负责,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评判我们的历史意识如何。退一步说,即使80后真的都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个责任就完全在于80后自身吗?回望一下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打量一下我们对当下重大事件的了解,我们到底知道多少真相呢?或者说,我们到底有多少自由地探究真相的权力呢?
在这一点上,我认同陶东风先生的观点。在谈到青年人对父辈话语的隔膜时,陶东风曾说,这“其实是制度化的记忆剥夺的结果”,“因为经历的不同造成的个人记忆差异,只是一种生理——心理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由于没有共同经历而缺乏共同个人记忆的两代人,不见得一定不能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集体记忆如果通过文化符号(包括文学艺术和各种建筑物、纪念碑、博物馆等)得到记录、铭刻、物化,通过制度化的仪式(比如每年一度的反法西斯主义活动),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比如在教科书中认真如实地记录在历史上的各种灾难),是完全可以得到传承的(德国没有经历过二战的青年同样具有与父辈分享的二战记忆就是证明),我们和子辈缺乏共同的集体记忆因此不是自然现象或生理现象,而是人为的文化现象”。我认为杨庆祥提出来的80后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这并非80后自己不争气,冷漠,无知,而是社会塑造的结果。
扩大开去,我还想指出,还有很多对80后的批评指责,实际上是轻率而不公平的。正如80后作家笛安所说,我们跟父辈之间成长背景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年轻人跟父辈的差距。因着这样的巨变,年轻人的某些生活方式、审美趣味、话语特征的不同,父辈应该尽最大可能去包容,在不能理解之前,且保持沉默观察,而不应急于棒喝。要知道时代更迭之际,这些现象是自然出现的,“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又何尝不被视为奇装异服、无君无父呢?除此之外,如果80后真的犯了什么原则性错误,那当然应该批评教育。可是,要记得长远地看待问题。我还是要再提到陶东风先生,在前引的同一篇文章中,他批评了青年人的自私、颓废、犬儒主义、分裂人格等许多严重的问题,可是接下去却意识到:“这样简单的指责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公平的。即使今天的青年文化是畸形的、变态的,那也一定联系着父辈文化的畸形和变态,联系着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畸形和变态”,“扪心自问,我们做父母的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说假话、空话?做到心口合一?言行一致?……我甚至认为,很难说青年们的这一套不是从父母那里学的”。我因着这些话而对陶先生充满了敬意。这样设身处地的同情之理解实在太少了,这样诚恳的反躬自省也实在太少了。“子不教,父之过”,“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朴素的常识道理,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很多人在对年轻人的轻率指责中,快意地抹去了自己身上的污点。
80后有问题,但并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80后身上的病毒并不是突然凭空长出来的。80后并没有降生和成长在无菌室里,相反,80后是被父辈带到了一个混乱污糟的世界里。以切身经验而论,我没有想到十年寒窗,等我具备了写论文的能力时,面对的却是一个发表论文要交版面费的局面。就在最近,我还获得了一个很震撼的经验。新近认识的一个正在打点着成为畅销童书作家的女孩子告诉我,为了将名人的商业效应利用到极致,出版商、书商雇用枪手写书署上名人的名字出版,这是业内很常见的做法。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好歹也学了这么多年文学,但我却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内幕。这对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以至于现在看到80后名作家过于密集出版的作品,我就忍不住想它是不是枪手代笔的。当韩寒之真假的争论出现的时候,我是很坚定地在情感上支持韩寒的,现在却不得不多几分保留。我钟爱的文学居然也不纯洁了,世界上还有哪一个角落没曾被弄脏过呢?这些坏点子,都是80后想出来的么?出版商、书商,都是80后么?我们生活的年代,确实不曾如前辈人那样遭遇战争和饥荒,可是,我们遭受的精神上的混乱与荼毒,就真的比他们轻吗?
灵魂得救之路
我并不是推脱责任,更不是说,因着世界整体的败坏,80后就可以心安理得,狂欢作恶。相反,我想说的是,面对这样的世界,80后,准确地说,是身为80后的我,该如何在世,如何得救。
我对世界的基本体认是,在好的一面,它当然还有让人热爱、敬畏、欣赏、沉醉的地方;但在坏的一面,它也已经坏到了极点。不幸的是,在我的观察里,前者是处于弱势的;更不幸的是,我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和势头。许多人已经没有了独立不移的良心标尺,永远只是在趋附利益和权势而摆动。与鲁迅当年的绝望一样,我看不到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我不相信凭个人的力量可以扭转这种局面,但是,闷死吗?沉沦吗?在死去之前狂欢作恶吗?
我的答案是,不可以,一定要做个好人。像易卜生说的,世界像一艘船要沉了,要紧的是救出你自己。在黑暗的世道里,首先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正确的人。当掀翻铁屋子无望,我只有转向内心,在肉身死去之前,让内里的灵魂得救。当我不敢与恶势力抗争的时候,我至少不与它合作;当我不敢公然斥责它的时候,我至少不违心地赞美。在任何时候都要求自己谦卑爱人,反躬自省,对天上的神明和内心的良知负责,心甘情愿承受代价。我曾将自己出版的小书自序题为“萤光自照,汇涓成海”,当时我也说过,“汇涓成海”是太遥远的理想,现在我要补充的是,在自己成为一个正确的人的前提下,能感染三两个知己好友,互相扶持走完一生,在不完美的现世享一点瞬时和局部的喜乐,也已经很不错了。
杨庆祥的文章中说,80后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之梦的以下内容是明确的:“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障之中。”这话是对的,我的梦想之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内容。可是他后面说:“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我就不太明白了。他还说:“小资产阶级在当下日益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它唯一的现实出路也许是赤贫化,成为新的城市无产阶级”,这话我也看不明白。我的确也如杨庆祥文中说的,在农村里没有了我的田地,在工厂里没有了我的车间,可是在大学里暂时还有我的教席,不管写下的文章能不能发表,手中也还有一支相当于锄头与矿锤的笔,在我工作的金华这个小城市,生活总不至于没有着落。对于我这样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来说,生活在逐渐改善,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物质生存不是最大的苦难,精神生存才是。所以我对杨庆祥这些话感到不解。也许在话语生产的自身逻辑中,它们是顺畅的,可是揆诸个体生活的实感,我又觉得它们是虚假的。这也是我在个人学术取向上疏离这一套话语的原因。但我能理解它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譬如杨庆祥在文中谈到工农阶级地位的变化,谈到“现实迫使我们重返十九世纪的一些重要命题:公平、正义、反抗和革命”,我都深有同感。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借用两个我并不是很熟悉因而可能不很恰当的词汇来描述我们学术取向的不同,也许姑且可以说,他走的是“外王”之道,而我走的是“内圣”之路。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小爱写些散文、诗歌,心思比较敏感细腻。我常常头疼于学术界爱舞弄理论术语,追求“范式”、“架构”,并以为这就是有学术价值,气象阔大,因此而懒于做微观研究。但我觉得那些东西一方面常常空疏而多有漏洞,另一方面与现实生命的触动和干连并不大。其恶果之一是现在有了各种课题基金申报以后,有的差到连句子都写不通顺的人,因着搬弄几个宏大的术语,加上投合某种需要,居然也名利双收,开始睥睨自得起来。我为此感到痛心,所以希望自己能走相反的路。尽量做一些微观研究,聚焦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做到下笔有底,有理有据,而且有所言说都指向“人”。关心作家寄寓在作品中的核心思想,关心作品的语言和技巧背后的审美趣味、逻辑能力,以及对人生的启示裨益。这是我认定的一条路。我敬重文化研究、制度批评,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的批评。我想,无论何种形式的变革,都需要人来承担,也将要作用于人。假如人不愿意反思自己,净化自己,任何形式的变革都可能是一场徒劳。相反,假如人人都能见贤思齐,修身成圣,可能无需激烈的变革,罪恶和苦难都已经自行瓦解,人间的天国自然实现。纵然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愿意以与绝望捣乱的心态,以文学为武器,终毕生之精力,拷问人心善恶、人情真伪。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拷问我自己,涤荡我自己,纵然因此而在世界上受苦受累,但至少内心知道灵魂在得救。假如能触动感染两三同道,看到80后中多出几个逆天抗俗、在潮流中如一块寂寞的石头、对一切表演加以冷眼、对真理与灵魂得救却充满热忱的人,那就更是齐天之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