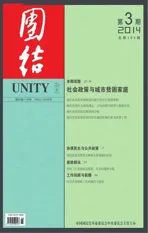社区工作改革的问题与进路
2014-12-12吴晓静
◎吴晓静 舒 蔚
(吴晓静,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民革重庆南岸区委会副主委;舒蔚,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阳光社区居委会主任/责编 张栋)
2013年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由此,社区治理进一步受到有关方面重视,但是各地的相关努力尚未从整体上带来社区局面改观,一些举措甚至未必起到正面效用。
概括起来,社区治理方面目前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1.“婆婆”太多,压力向下集中于社区组织。一直以来,政府各部委办局乃至工青妇等群团都习惯于向社区组织 (村居两委)下任务、作指导、搞考核,这一方面为社区工作提供了有力引导与支撑,但另一方面,也让社区组织穷于应付,感觉 “压力山大”,此即所谓 “上头千条线,下头一根针”。有些地方近来出台了 “社区工作准入名单”之类的限制向社区交任务加担子的举措,但往往限于 “合并同类项”,项目数减少了,事情差不多还是那些,截至目前 “减负”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2.越受重视压力越大。习总书记前述讲话传达下来后, “婆婆”们贯彻力度大多体现在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工作的指导上,往往各自有新的指导意见要求贯彻落实,社区的感觉就是压力不降反增,因为即使只是 “指导”,也需要认真接受、积极反馈,也要占用时间和精力。
3.一些指导、要求的正确性存疑。一些 “婆婆”对社区具体工作提出硬性要求,认其为社区相关工作所必需,社区则认为其脱离实际,不愿意执行,或者只能勉强敷衍。有些 “婆婆”给社区组织所下的指标任务属于 “自创”项目,社区往往认为无端增加了社区工作量,例如本属自愿范畴的孕优检查,一些地方也给社区下指标并纳入考核。
4.隐形负担沉重。政府职能部门、银行等社会单位常以 “社区是基层,应该掌握情况,而且可以调查”为由,让当事人 “有事找社区”,从而把自己的负担推给社区,而这些事情往往是社区无法做到或者做好的。例如让当事人找社区出具居民的夫妻关系证明、居民家庭成员构成情况的证明、在本辖区居住的证明、伤害发生情况的证明,甚至子女在某个学校读书的证明等等。由于是有关部门告知当事人找社区的,所以社区很难让当事人相信这些事本不是社区正常工作事项,导致矛盾在基层积累。 “大事”往往是 “小事”拖延累积而成的,并且往往可以分解为 “小事”处理,因此,在 “小事不出村居”理念之下, “婆婆”感觉比较麻烦的事情通常都会成为社区需要化解或者帮忙的任务。
5.待遇长期不到位。社区工作者待遇偏低的问题长期存在。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解决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报酬问题,“其标准原则上不低于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但是这一目标在许多地方还远远没有实现。
6.社区工作群众关注度、参与度双低。社区群众普遍不愿意主动参与社区事务,普遍认为社区工作与自己关系不大,仅在有事需要帮助时才会与社区联系。
以上问题,我们认为根源有两个方面。
一是社区组织从诞生背景到现实环境都有很强的行政依附性。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一直就明确规定了社区居委会有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相关管理工作的职能,实践中,社区组织的工作经费也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因此,社区组织可以说生来就是政府的帮手,只要政府还需要社区帮忙,社区就有责任提供帮助,而这种需求背景短时间内还难以根本扭转。 “对上负责”与 “对下服务”这两个我国社区组织基本职能之间存在 “跷跷板”关系,在 “为政府帮忙”成为压倒性任务的情况下, “为社区服务”的职能自然会被挤压。
二是我国近年来的社区改革目标设定有些脱离实际。近年来的社区工作改革探索有个大的方向,就是追求事情解决在基层,最好解决在社区,为此,不少工作 “重心下沉”到社区,各地实践中一般都依赖社区组织去完成, “希望寄托在社区”,社区减负难免成为空谈。实际上,无论 “下沉”与否,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主渠道毕竟还是在于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社会单位,我国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至今为止几乎全部是围绕这些主体职能发挥来制定的,在建设法治社会大背景下,这些主体的工作大多需要由各事权主体依法依规在自己的权责范围内去处理,社区组织并无相应事权,也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不适合处理相关事务,也很难处理好相关事务,相关工作的改善有赖于各事权单位自己,而不应指望社区。
综上,我们认为,对习总书记所讲的“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这个话,应当有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解:一方面,社会治理的重心,包括政府相关工作的重心,确实需要而且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把社区群众身边的事情处理好,把社区群众日常遭遇的问题解决好。在这方面,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一个时期以来普遍有一些高高在上、脱离社区群众,需要注意纠正;另一方面,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到社区,绝不是说把担子都交给社区组织去挑,也不是让政府部门以下任务、作指导、搞考核等方式 “通过社区组织”来完成任务,而是说社会各方面,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有关单位,当然也包括社区组织,都要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好社区治理、社区服务工作。
社区工作改革下一步往何处去?我们建议:
1.正确认识 “重心下沉”。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社会单位应当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尽量减少对社区支持的依赖。近年来,新兴技术迅速改变着社会生活各方面,也给政府部门提高服务能力 (包括直接面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发挥作用的能力)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可能性,使得主要因迅速城市化而导致的政府职能与群众之间 “联系虚脱化”的现象有望以技术手段加以克服,政府部门应该利用好这一条件,重新建立起与广大社区群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当然,新一届中央政府一直力倡的政府自身的缩权 “减负”,对于社区 “减负”也有积极意义。
2.逐步减少社区居委会协助管理职能。相关 “社区职能准入名单”应当科学制定,严格落实,并进一步缩减社区协助管理项目。
3.减少 “婆婆”。合并、归口社区工作考核职能,切实防止借考核之名给社区加担子。逐步转换政府部门与社区组织基本关系,一般政府部门不再将社区及其居委会作为管理对象来对待,和以下任务、作指示、搞考核作为基本工作内容,而应将其作为服务对象,以按需指导、应要求提供政策咨询意见及其他帮助作为对社区及其居委会的基本工作方式。
4.社区组织转变工作重心。社区居委会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服务社区上面来,努力了解、引导和满足社区内居民及社区内有关单位的需求,使社区组织真正成为社区 “自己的组织”,以社区群众的满意度为基本指向改进其工作。
5.社区组织自身的社区服务工作要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服务内容分类处理。能够通过互助方式解决的事情,积极引导互助;适合由社区组织直接提供的服务,尽力提供;需要医疗、卫生、教育、康乐等社会服务专门机构提供服务的事情,社区要做好沟通联系、协调关系、帮助解决问题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