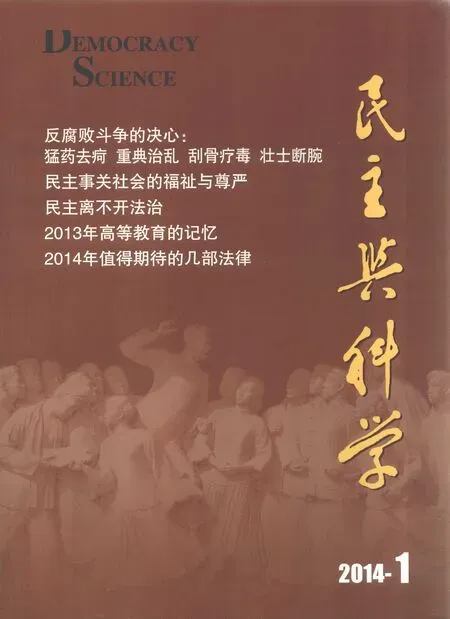诗苑玫瑰——莪默的诗魂
2014-12-12孙慕天
孙慕天
又一个春天来了,虽然年齿日增,看着灿烂的春阳,心中仍然充满了希望。除夕清晨,突然想起儿时读过莪默歌咏春天的名诗:
来呀,请来浮此一觞
在春阳之中脱去忏悔的衣裳
“鸿鸟”是飞不多时的——
鸟已在振翮飞翔
这是《鲁拜集》中的诗。念初中时,学校后面就是市图书馆,我当时可能是该馆持有外借图书证的最小读者,一次可以借出三本书。13岁那年,我读初二,借到郭沫若译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郭沫若以写作《女神》的浪漫情怀,有意模仿李白诗的神韵,把莪默的清词丽句演绎得荡气回肠,像声声春雷冲激着我少年的心,令我爱不释手,一口气抄录了印象最深刻的若干诗句。上面的一首就是当时抄录的郭译《鲁拜集》第七首。一个甲子以后翻出儿时笔记重读,兴之所至,又找到菲兹杰拉德的英文译本,上面这首诗的英文原文是:
Come,fill the cup,and in the fire of spring,
Your winter-garment of repentance fling:
The bird of time has but a little way,
To flutter——and the bird is on the wing
中英对照,郭译确是大师手笔,达雅兼具,令人心折。反复吟哦,心中所感自与童稚时迥乎不同,似有所悟。春节甫至,忽然兴起,自忖何妨迳操拙笔重译,藉以辞岁,不想竟得四韵:
来呀,请浮此一觞
春阳似火,焚去悔恨的冬裳
韶华如鸿,而前路日蹙
这只鸟儿已振翅飞翔
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翻译中损失的那部分。”至少对莪默的诗来说,这是不易之论。拙译虽不免滥竽之讥,但直抒胸臆,倒也有几分个性,想想干脆当作今年春节贺词,用短信发给同好此道的文友,倒也别致,心下颇为自得。
时下中国的年轻读者中,知道这位中古波斯诗人的恐怕不多了。我年幼时通过郭译《鲁拜集》,初识这位诗国怪杰,但也只不过略知其名而已。在京念书时,得母校图书馆开架之便,徜徉在书海之中,想起稚龄读莪默之乐,随手翻看了许多关于这位诗人的文献,也浏览了不少《鲁拜集》的其他中文译本,这才对相关掌故有了较多了解。
《鲁拜集》 作者的波斯文全名按拉丁拼法是Ghiyasuddin Albual-FalhOmar Khayyam,“五四”时代的先贤译为莪默·伽亚谟,今日多译欧玛尔·海亚姆,但由于早期郭译《鲁拜集》的广泛影响,时下国内文化人有的仍喜欢用莪默·伽亚谟的译名。
莪默其实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早期著作《算术问题》只留下封面和几篇残页,但幸运的是,其代表作《还原与对消问题的论证》流传下来,这就是他的经典数学名著《代数学》。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一般三次方程解法的研究,他通过圆锥曲线寻求方程的解,给出了x3+Bx=C,x3+ax2=c3,x3±ax2+b2x=b2c等类型的方程的根。在几何学上,他留下了《辩明欧几里德几何公理中的难点》一文,试图证明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论者认为,他关于平行公设的证明已经隐含了后世非欧几何的思想。莪默曾经出任天文台台长18年之久,编制了《马利克沙天文表》,记录了黄道坐标和最亮的数百颗恒星。他还制定了堪与格利高里历相比的新历法,其法每3770年(一说5000年)误差一天,格利高里历则每3330年误差一天。
据说莪默是在科学研究之余从事诗歌写作的。他的诗集《鲁拜集》,波斯名Robaiyat是Robai的复数形式,因此亦译《柔巴依集》。Robai是波斯一种四行诗体,类似中国的绝句,也是一、二、四句押韵。也许正因为莪默是科学家,对自然本体的客观本性有深刻的理性认知,所以他的诗与中古世界的宗教神秘主义大相径庭:浩瀚广漠的宇宙,无限绵延的时间,飘忽落寞的人生,都以个体的自我体验出之,超越了那个时代,充满了现代意味。希腊哲人德谟克里特说过:“不失常态者成不了诗人。”莪默正是个高标出世的奇人。有个关于他流传甚广的轶事:莪默与两个朋友尼扎姆·穆尔克和哈桑·沙巴一道,师从伊玛目莫瓦法克;穆尔克后来发迹,成了塞尔柱帝国的宰相,并决定厚遇两位同窗。哈桑要求官位,遂得掌重权,后却野心膨胀,谋反叛乱而被流放;莪默却只求一块住地,一笔年金,于是获居纳霞堡,得到一笔1200密(mithkals)的黄金,过着隐居的生活。莪默终身未娶,以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为人生的归宿。他用灵魂的眼睛去透视宇宙和人生,他的诗是以有限的生命去体验无限,生动地印证了法国作家克洛黛尔的诗论:诗的目的是“沉到有限之底去发现无穷尽”。
莪默的自我放逐是对自由的选择,他强烈地自觉到,只有挣脱尘俗的囚笼傲然孑立,才能完美地实现生命的价值。天堂在哪里?就在自己的世界中。《鲁拜集》中最脍炙人口的是第12首诗,郭本译作:
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
有你在这荒原中伴我歌唱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台湾黄克孙先生用七言绝句体译的更妙:
一箪疏食一壶浆
一卷诗书树下凉
卿为阿侬歌瀚海
茫茫瀚海即天堂
人生的美好,人格的独立,人性的自由——这些近代主题竟然在文艺复兴前的五百多年出现在中古波斯诗人的笔下。在第66首中,莪默放歌长啸:
我遣灵魂到那不可知世界
去读来世的文字
即刻我的灵魂返回
答曰:“我即是天堂和地狱”
“我就是天堂和地狱”,这是莪默的解放宣言。当神学教条、禁欲主义和宗教裁判的阴沉雾霾笼罩着欧洲大地的时候,《鲁拜集》却如春阳在东方冉冉升起。那明媚清绮的自然风光,奇幻瑰丽的异国情调,汪洋恣肆的豪迈诗情,超脱隽永的人生思考,在中亚的荒原上高奏出旷代的绝响。记得中国宋代词人秦观(少游)曾给所谓“论理之文”定出标准:“采道德之理,述生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生死之变”,可以说莪默的诗正是达到了这样的美学高度,难怪至今弦歌不绝。
莪默为欧人所知,是因为《鲁拜集》有了一位不世出的英文译者——爱德华·菲兹杰拉德。菲兹杰拉德和莪默一样,也是个特立独行的异人。他青年时代就读剑桥三一学院。作为莘莘学子中的翘楚,他跻身剑桥的精英学生团体,这个俱乐部仅接纳12个人,因而被称作“使徒”,当时的成员包括后来的著名文学家丁尼生、萨克雷,他们都是菲兹杰拉德的终生挚友。顺便说,同时期的“使徒”成员中还有科学巨匠麦克斯韦。但是,菲兹杰拉德离开剑桥后,却回到了乡间,靠着丰厚的遗产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直到四十四岁才结婚,婚后不久即离异,以后一直孑然一身,读书,泛舟,吸烟,听乐,优哉游哉。有件轶事颇能显示他的个性。有一次他驾船去荷兰欣赏一幅名画,海上颠簸,备尝风浪之苦;谁知到达港口后,伸手试风向觉得适合返航,于是立即命令水手掉头驶向归途。这像极了我国晋人王徽之(子猷)的故事。王徽之是王羲之的三公子,一日推窗见大雪纷飞,突然兴起,立即乘舟从山阴到剡溪访好友戴逵(安道),舟行竟夜,始抵剡溪,不料王徽之竟令船夫即刻返回,船夫大惑不解,这位子猷先生答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耶?”菲兹杰拉德死后,墓碑上镌刻的铭文是I am all for short and merry life,“我一生短暂而快乐”——这实在是盖棺定论。
1852年菲兹杰拉德从师科威尔学习波斯语。科威尔在牛津波德莱图书馆发现了一份1460年的波斯文手抄本,正是包含158首诗的《鲁拜集》,随即誊写了一份交给了菲兹杰拉德。后来科威尔又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图书馆发现了另一部《鲁拜集》抄稿,也誊写了一份送给菲兹杰拉德。菲兹杰拉德读后受到了强烈震撼,于是在1857年用了半年时间翻译《鲁拜集》,1859年4月9日该书英译本初版正式出版。英文第一版《鲁拜集》是菲兹杰拉德自费出版的,仅仅发行了250本,自己还留了50本,而售价虽从5先令一路直落到1便士,仍然无人问津,可谓备受冷落。后来,由于著名诗人罗塞蒂和斯温伯恩的推介,才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从1868年起,1872年,1879年,直到1889年一连出到第五版。第一版收入75首诗,第四版增至101首,成为最流行的版本。到1925年,这个译本已重印了139次,逐渐传布到世界各地。受菲兹杰拉德译本的影响,世界文坛兴起了经久不衰的“鲁拜热”,译者纷起效尤。据统计全球共有700多种版本的《鲁拜集》,其中包括32种英译本,16种法译本,12种德译本,5种意译本,4种俄译本。到1929年,关于莪默的论文已经发表了1500多篇。而早期菲译《鲁拜集》的版本也洛阳纸贵,成了文物,如今一本1929年版的菲兹杰拉德译《鲁拜集》,在纽约已卖到8000美元。时至今日,《鲁拜集》发行量之巨在世界各种出版物中仅仅次于《圣经》,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闻一多称菲兹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是“西洋第一流的古今名著”。其实,惠因菲尔德,多尔和佩恩等人的《鲁拜集》英译本比菲兹杰拉德(以下简称菲本)更忠实于原文,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历史影响却与菲本判若云泥。菲译《鲁拜集》出版于1859年,适逢达尔文《物种起源》于同年问世。人们认为,菲兹杰拉德和达尔文一样,在英国文化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风暴。按照17世纪英国著名翻译大师约翰·德纳姆的观点,“译诗必须保留火焰,即原诗活的灵魂;而不是保留‘灰烬’,即原诗死的形式”。不仅如此,还要“加进新的力量,弥补由于时代、语言、地点的变异而引起的走失”。菲兹杰拉德译《鲁拜集》,完美地实现了译诗的这些最高要求。菲兹杰拉德坚持“译者的特权”,主张有权在保留原作精神的同时,“注入一些艺术的东西使其更加完美”,不能刻板地泥守原文的字句,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比较灵活、比较自由的处理方式,进行文学重构。菲本的译文忠实地传达了莪默的两个基本精神:张扬人的主体意识和回归自然的怀抱,而这两点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读者的审美理想和心理需要恰恰若合符节。但是,菲氏在弘扬《鲁拜集》基本精神的同时,又根据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时尚,刻意重新剪裁和增删,不是死译,而是活译。菲氏自己说:“无论如何译本一定要有生命,译作也要以转化过来的较差的生命而存在。宁为活麻雀,不做死老鹰。”为此,他不仅在内容上进行再创作,大胆地“在12世纪的诗中加入19世纪的音符”,而且形式上也勇敢地突破英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在遣词用句上敷上波斯语的色彩,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宁要东方式的隐晦,不要欧洲式的明晰”。20世纪初年的美国艺术评论家查尔斯·诺顿深刻揭示了菲兹杰拉德翻译《鲁拜集》的美学特质:“应当说明诗魂在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时那种诗性的注入,并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表达原作的观念和形象,但其复现却十分适合新的时代背景,处境,风俗和心性。译本具有杰出原本的一切优点,而它的精彩则成为这位波斯诗人使人铭记和珍视的无与伦比的表征。这个译作是一个诗人被另一位诗人的作品激发起来的,它不是一个抄本,而是一次再创作;不是一个译作,而是诗人灵感的再现。”钱钟书在《七缀集》中借评论林纾阐发翻译理论,曾举出若干事例,证明有的译本甚至高出原作,从而为原著大大增色,甚至连原作者本人都为之倾倒。惠特曼认为弗莱利格拉特的德译《草叶集》也许胜过自己的英文原作;博尔赫斯称赞伊巴拉把他的诗译成法语,远胜西班牙语原文。的确有人说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要比波斯文原本更富诗意,虽然这一说法需要精通英波双语的专家裁定,但菲本百年流传,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激起的热情经久不衰,这正是其不朽艺术魅力的最好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诗人丁尼生专门赋诗,热情赞颂自己这位挚友翻译《鲁拜集》的卓越成就:
你置身金色的东方
我不知道哪个英文译本更具灵光
它照耀你那位伟大的异教徒莪默
像太阳把星星照亮
有人查阅文献,发现莪默·伽亚谟的诗作进入中国可以上溯到元大德十年,即公元1306年。一位波斯侨民客死闽地,埋骨福州郊外,墓碑刻石居然是莪默的诗:
从地底的深处直到土星之巅
我已解决了宇宙间一切疑难
如今没有什么问题使我困惑
但是面对死亡我仍感到茫然
这位波斯朋友无疑是莪默的粉丝,终老异乡仍然不忘吟诵他这位伟大同胞的诗句。他第一个把《鲁拜集》传到了神州大地,可算是中波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可惜那时的历史语境早已注定,这粒诗坛上的星火只能默默地消逝在历史的夜空之中。
《鲁拜集》真正引起中国知识界的热烈共鸣是在“五四”时代,这当然不是偶然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王朝的腐败,列强的侵凌,激发了变革图强的强烈愿望。严译《天演论》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胡适的名字就是“适者生存”,连军阀陈炯明的字也叫“竞存”。强国必强种,强种需强人。新民树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而为此就必须冲破两千年来儒教思想对人性自由的压抑。五四运动的纲领是民主与科学,但是从价值论说,核心却是弘扬人的主体性。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锋的一翼,而文学革命的宗旨则是人的发现。1918年5月,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对老大中华的“吃人”体制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同年12月乃弟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被胡适誉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文章高喊的口号正是“人的意识”,“人的生命”,“人的光芒”。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下面,莪默·伽亚谟以讴歌人的生命和自由为主题的诗篇,像域外温煦的春风,吹开了中国精英们的心扉。
经查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翻译莪默诗的是胡适。1919年2月28日,就在“五四”前夕,胡适翻译了《鲁拜集》第73首:
要是天空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打破
再团再炼再调和
把世界重新改造过
诗的英文原文是
Ah love!Could thou and with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and then
Re 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显然这是一首爱情诗,开始就是爱的呼唤:Ah,love,——啊,爱!但是胡译却略去了这个开宗明义的题头,大大淡化了爱情的主题,其译文触目而来的是“把这糊涂世界一起打破”,“把世界重新改造过”。这简直成了五四运动的政治口号。胡适十分喜爱这首诗,一生曾三次译过,认为是自己“最得意的一首译诗”。但只有这第一次的译文充满了火药味,像是一首“造反”歌;尔后时过境迁,锋芒消退,原诗的爱情意蕴凸显出来。第二次翻译是1924年11月7日,徐志摩当时在场,说胡适一面用寸楷写了出来,一面用徽州腔调高声朗诵:
爱啊,假如天公肯跟着你我谋反
一把抓住这整个儿寒伧的世界
你我还不趁机把它完全捣碎
再来称你我心愿,改造它一个痛快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情侣的心意和对象世界之间的矛盾,把“你我的心愿”放在了突出位置。第三次是1942年2月17日,在致赵元任的信中提到该诗的新译:
爱啊,(要是)咱们俩能和老天爷打成了一气
好教咱抓住了整个儿天和地
咱(岂)不先砸碎了这不成样的东西
再从头改造翻新,好教它真个称了心子如意
世界已不再是“糊涂”或“寒伧”,仅仅是“不成样”而已,也不再要求“天公”一起“谋反”,而是和老天爷“打成一气”。这里我们不讨论诗人胡适的心路历程,只是想说,现代中国精英确实曾把莪默的诗当作号筒,吹奏出时代的强音。胡适说过,他是借莪默·伽亚谟的杯中残酒,浇自己的胸中块垒。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郭译始于1922年9月,最初发表在《创造》第1卷第3号。1923年,闻一多曾就郭沫若的译文做过评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也就一些具体诗句的译法提出商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24年由泰东书局作为单行本出版了郭沫若的全部译文101首,这是中国最早的《鲁拜集》完整译本。解放前的郭译本附有郭氏撰写的《读了“鲁拜集”之后的感想》和《莪默·伽亚谟传略》,可惜后来的新版删掉了前一篇文章。郭沫若在这篇“感想”中含蓄地透露了自己翻译《鲁拜集》的动机。他认为,莪默·伽亚谟是看透了宇宙和人生的“大悟”之人。但看透了又如何呢?结果就是走向彻底的享乐主义。不过享乐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郭氏认为积极的享乐主义是彻底的享乐主义,那就是做个英雄主义的精神胜利者,“把自身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做一个无私发展的“有作为者”。看来,郭沫若同样是想通过翻译《鲁拜集》呼应五四精神,只是和胡适的视角不同,其切入点是张扬主体积极的创造和奉献精神,号召年轻一代冲破庸俗卑陋的生活天地,成为时代的先锋。
比郭译稍晚,闻一多1922年10月12日发表了《鲁拜集》中的5首译诗;徐志摩也于1924年11月发表了译自《鲁拜集》的诗。一时之间,翻译和评论莪默·伽亚谟蔚然成风。自此以后,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在民族苦难的艰辛岁月里,在战场硝烟的生命搏击中,人们对《鲁拜集》的热爱之情并没有冷却下来。李霁野就曾在抗日的烽火中,怀揣着菲兹杰拉德的译本,在流亡途中一首首地用七言绝句体裁译出整部诗集。诗人们各自选择独特方式和风格争先恐后地推出一个又一个新译本,在胡适和郭沫若之后,除上面提到的闻一多、徐志摩、李霁野以外,刘半农,成仿吾,林语堂,吴宓,郑振铎,朱湘,钱钟书,梁实秋,绿原等名家都曾全部或部分地译过此书,大师云集,群星闪耀,成为我国自有新文学以来空前未有的盛况。这种特异的“鲁拜现象”,可以作为文本解释学的专题深入进行研究。张承志在《波斯人的礼物》中针对《鲁拜集》的翻译指出:“放肆的剖白,明快的哲理,鲜活的句子,这些胡姬当垆的妙歌,挑逗了中国人的渴望与趣味,教导了他们个性解放的极致,文人们也出于惊喜,争相一译,寄托自由的悲愿。它不仅是一股清风,对翻译家们来说,它若是世界末日的洪水才好,他们盼它帮忙,冲毁压抑人性的旧中国于一个早晨——于是译笔缤纷,华章比美。”这段话透露出中国知识界热衷于《鲁拜集》译事的深沉历史动机。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又迎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长久郁积的自由渴想一朝释放出来,莪默·伽亚谟又成了一颗颗跃动的心灵借力的风帆,而争相翻译《鲁拜集》的新一轮热潮再次出现了。据我的不完全统计,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不同译者分别翻译的整部《鲁拜集》新版本竟达12种之多,其中张晖、邢来顺、张鸿年分别推出三种从波斯文直接翻译的《柔巴依集》。这里还不算在各个杂志上发表的选译,也没有计入港台译者的译本和解放前旧译的重印本。一些文化耆宿也重新登场,或评介,或迻译。1990年,柏丽以《怒湃诗草》为题推出《鲁拜集》的新译本,书名是钱钟书题写的,而李霁野则欣然为之作序。研究中国翻译《鲁拜集》的历史和经验也成了专门的学问。老文化人施蛰存就专门写了《鲁拜,柔巴依,怒湃》的专题著作,而黄渝的《鲁拜集翻译一甲子》,慈恩的《三十五年鲁拜翻译沧桑录》,更是考证入微,力争纤毫必录。莪默甚至进入了时尚文化。众多不知何为“鲁拜”的时尚青年,只要是金庸的拥趸,读过《倚天屠龙记》,都会被他笔下的那位波斯圣女小昭所倾倒,同时也顺便知道了有个波斯诗人“峨默”(金庸的译法)。金庸在该书后记中有段自白:“我自己心中,最爱小昭,只可惜不能让她跟张无忌在一起,想起来常常有些惆怅。”小昭之迷人,不仅是因为美丽纯情,而且因为她有渊博深厚的文化教养,悲天悯人的善良心地。作者对小昭的性格描写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恰恰借重于莪默的事迹和诗篇。他让小昭对张无忌讲述莪默的高尚人格:“不愿居官,只求一笔年金,以便静居研习天文历数,饮酒吟诗,”并与那位同窗野心家“山中老人”霍山(即上文提到的哈桑·沙巴)做了对比。小昭在危难时刻给张无忌吟唱的诗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正是用楚辞文体译出的《鲁拜集》第29首:
来到此世,却不知从何而来
如水一样身不由己地流淌
出了此世,就像荒野上空的风
不知向何处,身不由己地飘荡
金庸以生花妙笔演绎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不知感动了多少少男少女,披览之余,口角留香,无意中成为中国《鲁拜集》翻译史上的一朵奇花。
为什么在中国热气腾腾的伟大变革时代,莪默·伽亚谟始终受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青睐?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说过:“诗人是那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们的代言人。”莪默通过《鲁拜集》充当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追求进步,向往高尚人生境界的知识精英们的代言者,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萨特说:“诗人位于语言之外。”通过诗悟解宇宙和人生,与哲学和科学的语言阐释迥然不同,诗意使人直接洞悉了世界和人心的本质,所以精品诗篇会超越时空,拥有永恒的魅力。象征派大师瓦莱里说过:“一句好诗能无数次再生。”诚哉是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位一千多年前伟大波斯诗人的瑰丽诗句却一直在世世代代的人心头回响。
2009年11月14日,作家王蒙在一次给大学生作的讲座中说:“我给你们背诵一首诗,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棒的诗,古老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鲁拜集》里的一首诗。”王蒙背诵的这首“世界上最棒的诗”是:
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
我们是智慧的眼珠的黑眸子
如果把偌大的宇宙比喻成一个指环
我们无疑是镶在上面的颗颗宝石
读《鲁拜集》吧,你一定会洗净自己的心灵,一步步攀上生命的光辉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