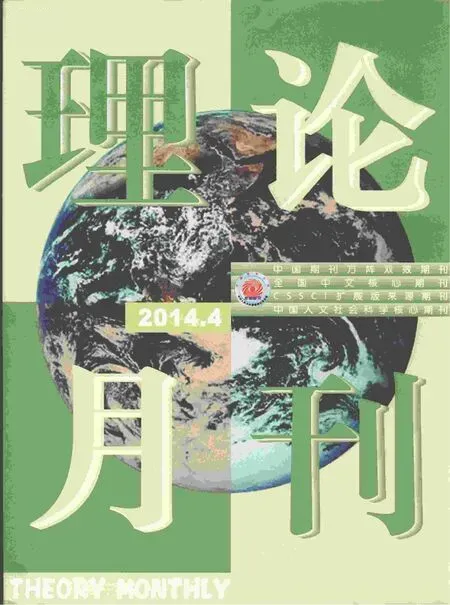朱熹理学思想述论
2014-12-04柏家文
柏家文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2)
南宋朱熹继承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邵雍的儒学思想,尤其是二程理气学说思想,将儒学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儒学亦成为极具思辨性的学说思想体系,回答了宇宙、自然、人及社会等一系列思想命题。
一、理的宇宙本体论
理本体论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对于宇宙本体,朱熹提出太极即理、阴阳是气、理气动静、理一分殊等范畴。朱熹认为理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他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 ”[1]“理者,天之体。 ”[2]“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3]宇宙间天地万物莫不是由理而形成的,万物也莫不从宇宙太极中禀受了这个“理”,不论是有生命的生物,或是无生命的舟车,皆有“理”寓于其中。“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车只可行之於陆。 ’”[4]
朱熹认为没有“理”,便没有天地,没有人物,没有一切。从逻辑上说,有了“理”便有了阴阳“气”的流动,遂化育为万物。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 ”[5]“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6]“理”是促使事物生成的法则,“气”是构成万物的质料。万物皆由“气”依“理”而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7]
朱熹认为理气的运行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有是理后生是气”,是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逻辑推来的。[8]因而他认为理气只是有逻辑上的先后,“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9]太极之理是形而上者,无形无迹,阴阳之气是形而下者,有形有迹。有迹之气是无形之理的载体,无形之理是有迹之气运行的法则。两者相伴而生,相伴而行,合为一体,非为二物。“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10]“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 ”[11]“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12]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阳交感,理与气合,万物生化。朱熹认为作为本然的太极是不动的,动静的是阴阳之气,太极只是乘阴阳二气的动静之机而动,“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 ”[13]太极之理作为本体存在于阴阳二气的动静之中,不是动的主体,气才是动静的主体,动则为阳,静则为阴,而作为这动静根据的“理”亦在“气”中,“理”随“气”动。 “盖太极是理,形而上者;阴阳是气,形而下者。然理无形,而气却有迹。气既有动静,则所载之理亦安得谓之无动静!”[14]朱熹以人骑马作比,动的是马,而人随马动。“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 ”[15]
太极阴阳的动静也是没有先后的,朱子并以人的呼吸作比。他说,“在阴阳言,则用在阳而体在阴,然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不可分先后。今只就起处言之,毕竟动前又是静,用前又是体,感前又是寂,阳前又是阴,而寂前又是感,静前又是动,将何者为先后?不可只道今日动便为始,而昨日静更不说也。如鼻息,言呼吸则辞顺,不可道吸呼。毕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16]动静前后相继,无始无终。朱熹引述程子的话说,“‘动静无端’,盖此亦是且自那动处说起。若论著动以前又有静,静以前又有动,如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这‘继’字便是动之端。若只一开一阖而无继,便是阖杀了。 ”[17]“‘继是动静之间否? ’曰:‘是静之终,动之始也。 ’”[18]
朱熹认为太极之理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理与气合,化育万物,万物皆禀受此理,而万物又各具有为此物而不为彼物的特定之理。他引述程子的话说,“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19]“理固是一贯。谓之一理,则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为万事,则灿然有条而不可乱,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当。”[20]他以草木桃李人物之不同为例说,“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21]万物禀受太极之理,而物各有不同,朱熹认为这是因气有精粗偏正的结果。二气五行,絪缊交感,千变万化。他还进一步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然而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22]
二、性即理的心性论
心性论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及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朱熹提出“性即理”的心性论命题,将人性论与理气的宇宙本体论很好地贯通起来。认为“心”统“性”与“情”,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心”有“道心”与“人心”之分,“性”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
理本体论告诉我们,宇宙间万物皆由“理”而形成,“理”附着于“气”而万物化育。朱熹认为“天命之谓性”,“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23]所有人之“心”即由“性”这个太极天命之“理”与“阴阳二气”交缊而成,“性”附于了“心”上。“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 ”[24]
人自其诞生,心的作用是从不停息的,但其作用过程可以分为思虑未萌的“未发”状态和思虑已萌的“已发”状态。思虑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说,“性是未发”。[25]“性情一物也,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 ”[26]“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 ”[27]也就是说,“情”还没有发出来时,此时的“心”表现为浑然状态,就是“中”,就是“性”,但各种“情”也还是附于“心”的,只是没表现出来而已,一旦发出就表现为“情”。“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只是浑然,所谓气质之性亦皆在其中。至于喜怒哀乐,却只是情。 ”[28]
朱熹认为“性”与“情”是一体的,都附着于可见可把握的物“心”,“心”就是“性”“情”物化的主体。 他说,“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 ”[29]“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30]他还举邵雍的话说,“邵尧夫说:‘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此说甚好。盖道无形体,只性便是道之形体。然若无个心,却将性在甚处!须是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来。”[31]朱熹并高度评价张载“心统性情”说,他说“后来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有大功,始寻得个‘情’字著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又曰‘仁义礼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见得心。盖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32]
“心”是“性”“情”的物化载体,两者统一于“心”,“性”是形而上之理,通过“情”来表现出来,因而已发之“性”已不是“性”之本体,而是“性”之用。所以说“盖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亦即心有体用,思虑未萌未发是性是体,一旦萌发之际即变为情,变为心之用。“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 ”[33]“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34]他举孟子的话说,“且如仁义自是性,孟子则曰‘仁义之心’;恻隐、羞恶自是情,孟子则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盖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35]
朱熹认为“性”是“心”的未发状态,是太极之“理”,天命之“性”,没有不善的;“情”是已发,受精粗偏正“气”的影响,有善与不善。“性有已发之性,有未发之性。曰性才发,便是情。情有善恶,性则全善。”[36]“性未发时,无有不善,虽气禀至恶者亦然。但方发之时,气一乘之,则有善有不善耳。 ”[37]
朱熹认为人之“心”有“道心”“人心”两种,他说,“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气质。若以天命之性为根于心,则气质之性又安顿在何处!谓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38]朱熹认为人的知觉活动出于“理”的便是“道心”,出于“欲”的便是“人心”。 “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 ”[39]“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40]这就是说,道心是出于天理的道德意识,人心是出于个体情欲的感性欲念。朱熹认为造成道心人心之别的原因在于人是“理气”合一,禀“理”成性,禀“气”成形,性则一,气则有所不同。“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41]
宇宙万物皆禀“理”成性,禀“气”成形。 “心”是“气”的物化,在物化过程中,禀受了天地之理的“本性”,这就是来自太极纯然的“天命之性”。然而“气”有精粗偏正,万物也就有了“气质之性”。因此,朱熹认为人之“性”有“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之分,发展了程颢程颐关于人性论的思想。“天命之性”万物皆同得于天,而之所以有人与物,善与恶,贤与愚之别,皆由于所禀“气质之性”的不同。“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皆受天地之气以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气有昏明厚薄之异。”[42]“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天命之性,本未尝偏。但气质所禀,却有偏处,气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义礼智,亦无阙一之理,……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43]“人物之性,有所谓同者,又有所谓异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异,然后可以论性矣。夫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则是其所谓同者;而二气五行,絪缊交感,万变不齐,则是其所谓异者。同者,其理也;异者,其气也。必得是理,而后有以为人物之性,则其所谓同然者,固不得而异也;必得是气,而后有以为人物之形,则所谓异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于《大学或问》因谓,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有所不能齐者,盖以此也。 ”[44]
三、穷理致知的认识论
理本体论认为,万物皆由“理”与“气”合而成,“理”在物中,太极有太极之“理”,万物又各有其“理”。太极之“理”是宇宙的普遍原则,物物之“理”是其各自为物的法则。人类认识的活动就在于穷索宇宙万物之“理”。朱熹认为其手段就是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穷理致知的主体条件就是体认者要主敬涵养。
“格物致知”语出《礼记·大学》篇,朱熹解释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5]“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到也。”[46]就是说在认识的实践活动中,要努力穷索事物之理,在通晓事物之理后,才能使我们的知识完备,达到“致知”。
那怎样才能“致知”呢?朱熹主张“格物穷理”,他在《补大学格物传》中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47]
穷理又是怎样的功夫呢?朱熹说,“穷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穷理者,只是足于已知已达,而不能穷其未知未达,故见得一截,不曾又见得一截,此其所以于理未精也。然仍须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进得一步,右脚又进一步;右脚进得一步,左脚又进,接续不已,自然贯通。”[48]心有知,物有理;理有未穷,所以知有未尽。以现有的知不断穷索未知之理,一物一物地格,持之以恒,自然就贯通了。这是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人的认识就会有豁然贯通达到理的质的飞跃。
在穷理过程中,亦并非须格尽天下所有之物,他说“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49]这是由特殊到普遍,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
朱熹认为要达到穷理致知须用主敬涵养的态度,何为主敬呢?他说,“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 ”[50]还说,“敬只是惺惺法,所谓静中有个觉处。”[51]这是穷理致知的主体条件,没有主敬,则心思散乱而不清明,是不可能体认事物之理的。“身心散慢,无缘见得义理分明,故欲先且习为端庄严肃,不至放肆怠惰,庶几心定理明耳。”[52]“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53]
四、知而行理的实践论
知行即致知力行,致知属于认识论范畴,力行属于实践论。朱熹认为只有求得反映“理”即事物规律或道德准则的“知”,才能作出合乎“理”的“行”。 “知”和“行”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偏废。他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54]认识了宇宙万物之“理”,即事物的普遍法则和规律,具备了处事所需的丰富完备的知识,就要用这些知识来指导我们人类现实的社会和生活实践。在人性论上说只有认知了道德,确立起完善的道德意识,才能达到主体的道德自觉,才能在社会活动中践行道德。朱熹理学思想所体认的“知”即太极之“理”,人性论上也就是人所禀受的先天固有的“天命之性”仁义礼智,因而人类所有的“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以“仁义礼智”为道德标准,至于“中”“和”,方能成就或“圣”或“贤”。
如上文所说人类在禀受了天理“仁义礼智”之“性”的同时,是由精粗偏正之“气”成形的。体现“仁义礼智”的先天之“性”都是善的,而这气则有致贤愚、善与不善。朱子理学告诉人们,可以通过为学的途径和克治之功来变化“粗偏”之气禀。“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且如天地之运,万端而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为学,却是要变化气禀。……须知气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胜而归于中乃可。 ”[55]
朱熹认为,用功克治首要的要在“心”上下功夫。“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乐未发则谓之中,发而皆中节则谓之和’,心是做工夫处。”[56]心是统一性情的,心有道心人心之分,性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别。道心是符合天理的道德意识,人心则是个人的感性欲念。符合天理的道德意识是天命之性的反映,个人欲念则是气质之性的体现。符合天理的道德意识即仁义礼智,出于“理”,皆善;个人欲念出于“气”,有善与不善,若不加以“省察克治”,则会流于不善。“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57]所以要时刻省察克治,以致存“仁义礼智”之“天理”,灭“恶和不善”之“人欲”。
主敬涵养是在“心”上做功夫的重要方法,它不仅是穷理致知认识论的方法,也是躬行实践的方法。他说,“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58]也就是说在生活实践中要收敛身心,使内心常处于一种敬畏、警省状态,专一而不放纵散逸,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同为学穷理一样,不用主敬的功夫和态度,是不可能践行真正意义上的“理”的,“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 ”[59]
践行道德,朱熹认为还要努力为学,变化气禀。他引述《大学》中的话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认识论,“亲民”“止于至善”是实践论,为学致知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也就是说为学之目的,在于明白上天赋予我们的“理”、“性”,即先天的道德法则“仁义礼智”。在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各项实践中,要贯彻“仁义礼智”,亲而爱人,摒却由于“气”之不同所致的恶和不善的私欲杂念,唤回“道心”,向纯净的天命之性“理”仁义礼智迈进,最终达到善之极,是为圣贤。
在实践中,要践行“仁义礼智”重要的是要做到“信”,“信”是成就并体现“仁义礼智”的。“‘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谓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60]“诚是个自然之实,信是个人所为之实。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便是诚。若‘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61]
[1][3][5][6][8][9][10][11][16][17][18][1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M].
[2][14][23][24][25][29][30][32][33][34][35][36][56]〔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5[M].
[4][12][22][28][31][37][38][42][43][44][55][5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4[M].
[7]答黄道夫[A].朱文公文集:卷 58[C].
[13]太极图说解[M].
[15]朱子语类:卷 94[M].
[20][21][60][6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6[M].
[26]答何叔京十八[A].朱文公文集:卷 40[C].
[27]太极说[A].朱文公文集:卷 67[C].
[39]答郑子上八[A].朱文公文集:卷 56[C].
[4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78[M].
[41]中庸章句序[A].四书章句集注[C].第14页.
[45]大学章句·经一[M].
[46]大学章句·公圣一[M].
[47]大学章句[M].
[48]〔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7[M].
[4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8[M].
[50][58]〔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2[M].
[5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63[M].
[52]朱文公文集:别集三[M].
[53][59]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勉齐集:卷 36[M].
[54]〔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