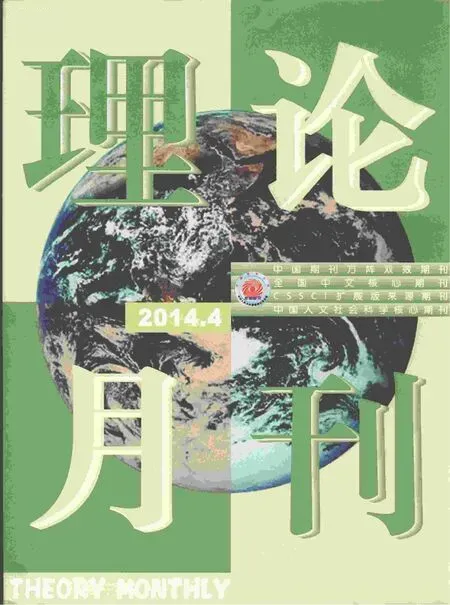农民工思想观念矛盾性透析*
2014-12-04刘建涛冯菲菲
刘建涛,冯菲菲
(1.辽宁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2.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6)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充满着矛盾,而且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也都存在着矛盾,没有无矛盾的事物,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农民工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同样是包含着多种相互排斥的冲突和矛盾,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
一、迫切的“入城”意愿与融入心理游离的矛盾
进城后的农民工,亲眼看到了城市的色彩斑斓和富裕,更看到了城里人过的现代时尚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等的工钱,住在低矮狭小的租住屋里,在清苦、微薄、单调枯燥的生活中挣扎。人类之痛苦在于有比较之心,如此鲜明的对比冲击着农民工们固有的观念,痛到他们的灵魂深处,他们太渴望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了,他们急切地想融入现代城市文明,也让下一代能够拥有更加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享有优质的社会“资源”。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出生成长,实现本地化的诉求更加强烈。但是,由于城市社会还没有从制度上准备好接纳他们,还有很多因素的制约使得他们想“融入”城市也难以融进去,这里不论是所谓农民工中的“不融入者”、“半融入者”包括“融入者”都是如此。就是假定他们已经被制度化为城市人口的情况下,然而无论从主观条件看,还是从客观经济条件看,他们在短期内还不可能真正处在市民的地位上、很难真正过上市民的生活。这就使得农民工在融入心理上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并且这种融入心理的游离状态与制度、土地、市民歧视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正是这些现实的制约因素导致了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上想融入城市而又“怕”或对融入城市持担忧、疑虑态度。
(一)“制度不准入”导致农民工融入心理游离
与户籍相关联的多方面的社会差异,使得农民工在城里多方面不能融入,与农民工利益直接相关的有三大主要方面:一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不融入。尽管不少城市在国家三令五申的情况下,承诺城市的公办教育体系要接纳农民工子女进入,但实际上市民子女与农民工子女仍然处于城市教育中两个天地。且不说网上抨击的某些地方出现的市民子女与农民工子女处于一所学校的两个不同校区的“隔离”现象,仅就高考制度来说,所有外来人口的子女都很难与所在地子女平等参加当地的高考,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城里接受了6年义务教育,后面的“中考”、“高考”也完全无法衔接。所以,农民工子女在城里的非全程式教育被学者李强称为“中断式”教育。更何况,一些地方违背国家政策,对农民工子女歧视性收费。二是多种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公共医疗的不融入。据调查统计,“到2009年末,在城镇就业的1.5亿农民工中,参加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占28.90%,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7.65%,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占10.95%,参加了工伤保险的比例最高,但也仅为37.25%”。[1]农民工不参加城镇的各种保险虽然短视但有它的道理,户籍制度的福利安排,根本没有将他们纳入,所以,除了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略高一些,因为他们担心在劳动中受伤,像养老、失业的参保率都十分低下,因为农民工认为自己不属于城里人,将来要回农村老家。三是住房体系的不融入。据调查,绝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简陋的房屋中,其条件之差令人震惊。学者李强认为,“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农民工住房的不融入是断裂式的不融入,即完全没有可能进入城市住房体系,城市的商品房体系不要说农民工买房,就连城市居民也难以承受如此高的房价。户籍的制度障碍又阻止了农民工享受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的可能性”。[2]当然,农民工在外打工租房住是太平常的事,问题在于农民工有能力承租的房屋基本上是城乡接合部私搭乱建的违章小平房,且本身就有隐患,房租高的租不起,所以,农民工连正常的租房市场也很难进入,再加上严格化的城市管理,他们常常处于被驱赶的状态。
(二)怕失去土地断了生存后路使农民工融入心理游离
一方面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情愿以失去土地为代价换取城市户口。据学者李强研究发现,近年来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人口,即“农转非”。在探讨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人口的原因时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工怕失去土地,断了后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份报告也证明,农民工不愿意以“双放弃”,即放弃承包地、放弃宅基地来换取城镇户口。农民工的这种融入矛盾心理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今天的农转非和过去传统的农转非含义大不相同。过去农民渴望农转非,是因为一旦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就如进入“保险箱”,意味着一辈子享受“铁饭碗”的待遇。而今天,过去那种传统的安置政策已不复存在。很多农民工不接受农转非的最大理由就是,怕失去“宅基地”,怕失去“责任田”,怕失去与土地相联系的各种利益。实际上,如今的户籍制度接纳,仅仅是农民身份转变的一部,即是说仅仅解决了户籍并不能改变诸多其它方面的生存境况,比如,在已经“农转非”的许多人中,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诸多方面,既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也不能享受单位提供的,处于“真空”状态,他们在城里与原来的市民在很长的时间内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在许多地方竟出现了农民工主动放弃变为城镇户口的现象。在很多农民工看来,由于他们的职业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的城市往往是不确定的,一旦转战到其他城市务工,就是落了户,弄上了永久居住权也意义不大,为此放弃家乡的土地资源收益,“断了”后路不划算,即使在城市生存不下去,只要土地在,还可以再回家务农。
(三)城市歧视的负面印象体验使农民工融入心理游离
社会学的研究证明,心理上的差异感,特别是被排斥、被歧视感的负面印象体验,对一个人的心理影响虽然不太好用物质的客观指标来界定,但是,它作为一种明确的“社会事实”,即便是农民工在客观上已经被称为城市市民的情景下,由于他们在心理上还是持有被城市、被原有市民排斥的观念和印象,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他们仍是怀疑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如,问农转非之后你愿意参与社区的管理吗?回答‘不确定’的为40.4%。又比如,问农转非之后愿意和原市民做邻居吗?回答‘不确定’的为35.4%。又如,问,农转非之后你愿意和原市民一起工作吗?回答‘不确定’的为35.4%。再如,问农转非之后你愿意和原市民做朋友吗?回答‘不确定’的为39.2%。总之,在总评价中,农转非还不认同自己的城市居民地位”。[3]另一方面,促使农民工个体产生疏远情绪,进而排斥融入城市生活。这种负面印象对农民工个体造成的影响越深,情绪也越浓,如果这种负面印象是农民工个体自身在现实的打工经历中受到伤害而产生的,那么,这种伤害将成为其生命中的烙印,很难遗忘。
二、渴望摆脱精神孤寂与人文关怀缺失的矛盾
农民工参与创造了精神财富理应享用精神成果及精神生活所带来的快乐和意义,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物质背景不同决定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不同。两代农民工几乎处于同一样的社会物质空间、同一样的劳动环境空间和同一样的生活空间,因此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生活遭遇—孤寂,主要表现为精神生活的单调和乏味,空虚和孤独,一些农民工甚至由此走上赌博、偷盗、吸毒的犯罪道路。
(一)农民工渴望摆脱精神孤寂与政府人文关怀缺失的矛盾
传统政府公共文化职能缺失和精神生活享用供给渠道不畅,是农民工陷入精神孤寂的重要原因。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享用和消费虽是农民工个人行为,但更多的却要依赖社会的公共供给。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均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农民工没有能力去通过自己的支付来实现精神生活享用和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群体应当享受的精神生活方面的场所或设施,更多的应是一种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场所,诸如公共图书馆、城市阅报栏以及必要的农民工休闲娱乐活动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本应当由政府提供的精神娱乐场所和设施,都存在严重不足。为农民工提供的精神文化活动公共场所或设施的短缺和供求渠道不畅,是形成目前农民工精神文化活动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调查情况看,政府为农民工在享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所提供的设施和服务微乎其微。当地政府也很少专门为农民工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文化活动的基础设施,即便是像阅报栏等这些农民工借以了解方针政策等必要信息的文化设施,也都集中设在市区的一些工地上,只有在这些区域务工的农民工才可能附带地享受到政府所提供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服务,而即便是可以享受,也时常可能受到多方面的种种歧视。而农民工对政府部门提供精神文化设施有太多的期待。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必须的精神文化服务。有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要求政府出面督促企业为他们提供 “电视”、“书报阅览室”和 “休闲娱乐活动室”,“27.0%的农民工要求为他们订购‘图书报纸’,另有27.0%的人要求为他们安装‘电脑’,还有19.1%的农民工要求为他们组织精神文化活动等”。[4]这些要求和期待属于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但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他们是很难得到与城市居民完全相同的精神文化享用权利的,闲暇时间大多只能睡觉、看电视、打扑克或侃大山来消磨时间,年复一年就出现了精神空虚、失落和寂寞,出现了精神世界的孤岛化。
(二)农民工渴望摆脱精神孤寂与企业人文关怀缺失的矛盾
如今,企业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严重缺失。由于整个社会仍处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阶段,而“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争取最大的利益。经营者作为“经济人”为了使经济利益最大化,把人视为挣钱的机器,忽略了人文需求的重要性。譬如在我国许多加工制造业吸纳了众多新生代农民工,而目前这些企业大多仍采用以计件制或流水线操作为特征的管理方式。再比如,“农民工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现象,人均周工时竟达52.44小时,超过法定标准一个半工作日以上;周工时超过40小时的农民工占76.3%。农民工在制度工时内的工资仅相当于城镇职工的67.5%。”[5]事实上农民工已经逐渐由经济人发展到社会人,但是城市、企业管理者对他们的认知、管理还仍沿用着“泰罗制”即“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这种缺少人文关怀的企业管理模式,不但不能激发农民工的劳动积极性,反而会使他们心理悲观、消极进而精神孤独。据调查:“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自身的比例为16.9%。有32.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 ‘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6]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精神上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和经营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特别是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企业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更是缺少。有些企业为农民工除了提供简易的宿舍外,基本没有提供其它文化设施。一半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所在企业没有图书室、多功能厅、阅览室、体育设施、艺术场所、健身房等。像图书、报纸,企业都很少提供,在北京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60.9%的人说在工地和宿舍里从来没有看到过报纸,80%的人说在工地和宿舍从来没有看到过体育设施,90%的人说工地上没有提供阅览室”。[7]各个城市的工地情况大体类似。对于类似组织农民工看看电影或是参与一些其他娱乐活动就更少。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业余生活内容太枯燥、乏味。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业余生活满意度很低,仅占12.8%,32.1%的人认为一般,超过半数(55.1%)的人对业余生活表示不满意”。[8]而他们中多数人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单位或企业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借以分散一下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精神压力。然而,现实中企业人文关怀的严重缺失,更加重了农民工精神上的孤寂。因此,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把企业的人文关怀做为找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三)农民工渴望摆脱精神孤寂与城市居民人文关怀缺失的矛盾
中国长期的二元体制结构,在造就城乡差别的同时,也衍生出城里人的诸多优越感,久而久之市民也将这些身份优势内化为一种市民性格,加上受中国传统观念蔑视体力劳动这种认知惯性的影响,市民有意或无意地对农民工以偏见甚至带有歧视。而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由于难以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圈,他们自成为一种文化圈,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亚文化圈”,与城市市民的主流文化圈基本不接触。据浙江大学调查组调查表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普遍存在社群隔离现象,市民对农民工关心的积极性不高”。“杭州市真正与农民工打交道的人不到1/3,其他一些则是很少或从未和农民工打过交道。超过一半(51.86%)的城市居民与身边的人对谈农民工问题是不感兴趣的,6.45%的城市居民有反感,也有四成(41.94%)的城市居民是较为感兴趣。但一半以上的市民与别人谈论农民工是态度较为冷漠”。[9]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不仅疏离,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着戒心和歧视。仅从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看,农民工在城市中经常遭遇偏见和歧视,如不少市民认为农民工抢了他们的饭碗;觉得农民工是城市治安恶化的罪魁祸首,就连丢了东西都认定是农民工所为;一些城市管理者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带上有色眼镜来看待农民工,对在大街上摆摊卖货的农民工动辄罚款、毁坏东西甚至任意打骂;有些市场、酒店、浴池等公共场所以农民工衣冠不整、有碍店容以及影响其他人消费等种种借口拒绝他们进入,凡此种种。这些来自城里人的偏见和歧视,直接伤害了农民工的人格尊严。所以,农民工普遍认为,虽然在城市生活工作,却未感受到城里人的尊重,更谈不上“关怀”。“零点”课题组调查发现,2004年,认为在城市受到非常尊重和比较尊重的比例为69.6%,而2011年则下降至59.2%,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中建筑行业农民工自认为被尊重度下降的程度最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正处于培养自尊自信的关键阶段,处于一个爱体面的人生阶段,渴望得到市民的接纳、认可与尊重,渴望取得市民的待见、理解和信任,但现实却是在城市里很少得到尊重,还遭到无数的白眼与蔑视。他们为城市的工作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是希望城里人不再对他们的身份对他们的身心以歧视。在城里,农民工尊严上的失落是最不能接受的。许多农民工伤感地说:“我们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望着自己劳动的成果,心里却没有幸福感、成就感和尊严感。”[10]这些因素致使农民工对城市形成极为复杂的心理情绪,他们喜欢羡慕城市的繁荣,向往文明的城市生活,而他们又认为城市的繁华与自己无缘,城市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自己只不过是陌生城市的过客,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的自卑、孤独与无奈。
三、超值的发展预期与自身资本薄弱的矛盾
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他们现有的教育程度和专业经验积累等人力资本和所依托的社会资本,都远远不能满足其超值发展预期的需要。从而出现了超值的发展预期与自身资本薄弱相悖的矛盾状况。
(一)自身人力资本不足与发展预期相悖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个人所具有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和工作经验等资源总和。人力资本是个人在社会领域中获取各种机会并取得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比如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上,衡量教育程度的学历文凭已经成为敲开就业大门的主要筹码,拥有高学历虽然不是找到一份理想工作的充分条件,但却往往是必要条件。更有甚者,学历文凭的高低还可能成为是否获取某些“名城”户籍的首要条件。显然农民工的教育资源竞争力是不及的。事实上,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数据显示,在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4.8%,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13.3%,而同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职业教育程度也是获得较好就业机会的一个因素,但是,在这一方面农民工的专业技能储备也不占优势,很多农民工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经济实力有限,他们很少有能力再去接受技能培训,一项对北京与宁波两地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在两地中非常希望接受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分别为23.8%和37.2%,但是真正接受培训的农民工只有12.7%和17.6%。而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的更新换代,如今企业对劳动者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当今的农民工已不再像早期那样仅靠出卖体力就能生存下去了,城市就业市场对劳动力有了更高的需求。从企业招聘人才的工种结构看,目前紧缺的是技术工种,对熟练操作工与技能人才需求量大。而且这些技术工种与岗位,如喷漆工、电子装配工、电子缝纫工、印刷工、焊接工等还要求具有一定的技术实践经验,并不是只要有体力就能适应的,不经过专门培训这些工作很难做得了。然而,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缺乏的恰恰就是相应的技术能力,他们现有的技术水平、教育程度滞后于当前市场的需求。自身人力资本的不足,决定了要实现他们在城市找到理想工作的期望是难以实现的。此外,农民工储备的所谓的工作经验对其就业和从业更是弱势,一方面,他们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低、准入门槛低、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农民工职业更换频繁、职业种类繁杂,有的人前一份工作是保洁员,后一份工作是服务员,这样就很难有工作经验上的积累和提升。总之,知识储备不足,缺乏技能,少于工作经验直接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也就更难以求发展。也正由于农民工受到自身教育程度的制约,他们在竞争中不具备职业地位上升的条件;同样,农民工由于受到自身技能水平的限制,也很难在竞争中获得职业地位的上升。这样就产生了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不足与其超值发展预期不符的矛盾。
(二)自身社会资本的微薄与发展预期相悖
所谓社会资本,概括讲“是指个体从社会网络和社会制度中可以获得的资源”。[11]具体说,社会资本就是通过人际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所带来的潜在社会资源,它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其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其基础,实质上就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存在于人们的交往里。日常生活中它只是一种静态的网络关系,只有当被行为者利用和调动时,它才成为一种资源和能量,并发挥社会资本在实践中的作用,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源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个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资源,即关系型社会资本;另一个层面是个体从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中可以获得的资源,即契约型社会资本”。[12]在城里,农民工所获取的社会资源主要来自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网络之中。因为他们进城后,虽然在生活方式和职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的边界,还是主要与自己相同群体的人交往,“社会交往圈基本上限定于老乡(占47.7%)、同事(占 40.7%)、朋友(占 31.9%)、亲戚(占31.8%)和同学(占192%)等这些熟人关系网之内。在其他的交往关系中,包工头是比较多的交往对象(占9.8%),但基本上是一种工作上的交往。而与代表农民工权益组织的交往,比如与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的交往仅占2.4%,与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只占3%”。[13]由此农民工在城里找工作也主要依赖亲戚朋友介绍,老乡、亲戚及朋友介绍找工作的比例超过了80%,而由政府组织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的只有3%。这就足以说明,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社会工作和生活中却仍然没有摆脱乡土社会的特性——无论是从他们进城打工的途径还是从其居住情况包括寻求援助的对象看,他们主要依赖的仍然是建立在亲缘或地缘基础之上的乡土社会支持网络。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几乎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唯一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本。因此,农民工从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等契约型社会资本中可以获得的资源十分有限。所以就出现了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微薄与其超值发展预期不相符的矛盾。
当然,农民工对未来发展有更高的期待和需求,这既合乎时代的发展需要也是他们的权利所在,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甚至主体意识觉醒水平等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弱势,高期待、低技能的矛盾格外凸显。从整体上评价,当今绝大多数农民工他们在就业市场上一直处于“被选择”的角色,而不是“选择岗位”的主体位置。因此农民工的自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和专业经验等个人资源的劣势,加之所依托的社会资本资源的缺失,使农民工所预期的未来发展值实现的可能性就更加茫然,从而导致农民工更加的焦虑和矛盾。
[1]李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半融入”与“不融入”[J].河北学刊,2011,(05):109-111.
[2][3]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5,60.
[4][9]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2,27-28.
[5]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160.
[6]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44.
[7][11]张天乐.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56,233.
[8]刘志强.谁为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和情感买单[EB/0L].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02/16/22164659_0.shtm l.2013-2-16.
[10]董碧水.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孤独化[N].中国青年报,2012-01-18.
[12]刘传江.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63.
[13]黄进.价值冲突与精神皈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