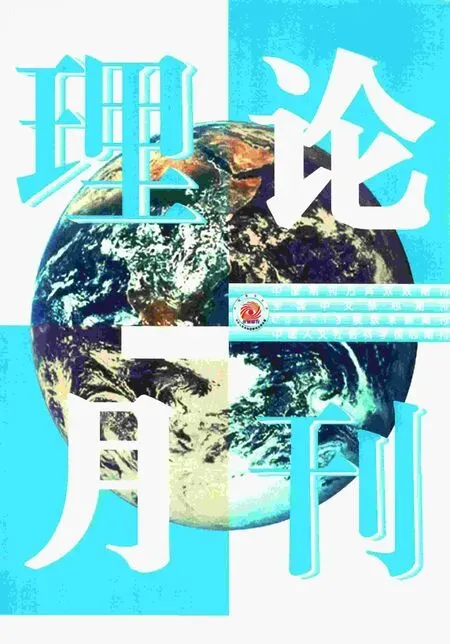“死亡”:作为被规训的禁忌*——儿童文学中的死亡书写尺度
2014-12-04徐杰
徐 杰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儿童文学之中暗含的死亡主题越来越多,于是死亡应不应该成为儿童文学的一部分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侯颖在《激活死亡母题的中国当代儿童小说》一文中描述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之中 “坦然面对死亡”、“内部和外部”原因的平衡点以及“叙述手法、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上”与成人文学区别的三大特征。[1]赵霞在《死亡:断层与永恒——以安徒生三则童话故事为例》中分析了梦作为安徒生童话之中生存与死亡之间的模糊地带所形成的张力的问题。[2]桑俊在《来自天堂的关爱——安徒生童话中的死亡意象研究》中谈到了童话中主人公死亡的类型、原因,死亡的意义和作者安徒生的悲剧情节。[3]以上学者们的研究将儿童文学中的死亡话题明确提出来,并且进行了现象描述和原因分析。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已有研究主要是在对儿童文学中的死亡书写的总结和描述,并且对其深层原因也只是归结为作家自身的悲剧意识。
让儿童直接或者间接面对死亡,在成人看来是残酷的,于是死亡主题在成人书写的儿童文学中逐渐被抹去。但是,在此我们必须得面对两个问题:第一,是否成人眼中对儿童应有的禁忌在儿童看来并不存在或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可触摸呢?第二,有些不能避开的禁忌,在儿童文学中又应该怎样处理才能达到既让儿童得到审美享受,又不至于伤害他们的心灵?
一、从语言禁忌到儿童文学禁忌
禁忌语言指日常生活中,在言语活上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不敢或者不愿说的令人忌讳的语言。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塔布(Taboo),就我们看来,它代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4](p19)这些禁忌言语指代的对象或言语本身在某个时间之内、某个空间地域抑或是某个群体社会中被拒斥为极为神圣的或者极为不祥的,以至于令人窘迫的,甚至是不能让人接受或使人感到愤怒的。禁忌言语体现于个人和社会价值体系之中,具象化为情态性倾向。禁忌是主体内在心理的一种否定性意识。这种否定性并非纯粹世界导致的,而是一种社会性文化规约形成的。因此,对于违反禁忌的惩罚并非来自自然规律对人的惩罚,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文化体对违禁者或自我被文化群体抛弃产生的受罚的内在心理。文学本身就作为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建构着文化,也为文化所约束着。文学禁忌一方面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不能碰触的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伦理,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底线。文学创作者在进行作品创作的过程之中,需要时时关注作品的内容、材料是否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发生矛盾与冲突,从而时时保持一种禁忌的意识。另一方面,文学禁忌也包括在表现形式层面不能完全违背接受者和整个社会的审美观。
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组成部分,具有文学的普遍属性,即总体性文学的共性。但是,普遍性体现在个别性之中,以个别性的存在而存在着。因此,儿童文学在遵循着文学创作、阅读、发展规律的同时,更加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而在儿童文学的禁忌上也必然有着与成人文学不同的品性。成人文学可以将暴力纳入自己的文字之中,形成一种阅读刺激感,甚至形成一种暴力美学,但儿童文学只能宣扬一种温柔而优雅的行为;成人文学可以堂而皇之将“性”置入作品之中,形成最基本的生命体验,像身体写作,但儿童文学只能将具有性爱暗示的章节或话语切除,比如《小红帽》的不同版本;[5](p78-79)成人文学可以凸显鬼怪的恐怖性和灵异的神秘性,探求心理底线的恐惧享受;而儿童文学则必须将制造恐怖的对象和事件驱除,剩下的只有暖色调的温馨。因此,总的来说儿童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要求,即对死亡,暴力,性,乱伦,鬼怪,神秘,惊险等的禁忌。这种禁忌主要来自两方面:(1)客观方面,社会教育对孩子的要求,特别是在成人世界作为他者视界中,儿童应该是怎么样;(2)主观方面,孩子本身的心理年龄特征的要求,比如儿童心智的脆弱性。
而儿童文学为儿童创作的,这一创作必须以适应儿童生活体验的广狭程度和精神发展阶段为前提。一些极端的创作者或编者就完全将含有死亡内容和场景作品排除在儿童文学之外,使之远离儿童读者,如《柳林风声》的作者格雷厄姆。但是,将死亡从儿童生活中和儿童文学之中清除掉是不可能、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
第一,死亡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是永远无法排除在儿童文学之外的,比如小主人公父母死了,或者爷爷奶奶死了,抑或是喂养的小宠物,养的花花草草死了,乃至无生命的洋娃娃死了,这些在童话中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并且不可避免的。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一生,无论在哪个阶段都存在着对死亡的恐惧。即使儿童文学将死亡阉割了,他们也依然存在着恐惧的感受,因为周遭的世界真切地包围、裹挟着他们逐渐成长的心灵。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之中,自然中的小动物、小植物的死亡,亲人的离世,听闻的死亡事件等不可能不对儿童心理产生冲击。因此,死亡不可能从儿童的世界里完全排除出去。
第二,儿童文学的体裁本身决定了死亡叙事存在的必然性。首先,社会关系的正邪角色的对立之中。儿童文学叙事必须遵从一般叙事的规则,即冲突的设置,于是在儿童文学就经常见到主人公总是要面对邪恶的女巫、食人怪兽等,或者恶势力欲吃掉主人公的情形。其次,叙事空间维度的天上与人间或者人间和地狱的差异之中。之所以,善良的人最终都会去到天上,成为神仙,就是因为神仙可以永久不死。但是在人间,总是会面临各种死亡的威胁。再次、叙事时间维度的“变形”、“轮回”和“复活”之中。 “变形”由于受到诅咒或者魔法,主人公就从人形变化成动物,变形是一种对死亡的意识,因为人失去了自己生命得以存在的肉身。“复活”的对立面就是死亡,“复活”是对死亡的一种超越形式。
所以,死亡主题、场景、对象都可以进入儿童文学。但是,进入的方式不能像成人文学那样粗粝和直接,而应该用文学手法慎重处理死亡在儿童文学中呈现的样态,这样才可以引领儿童逐渐认识死亡,珍惜生命和生活。正如威特·布莱希特所认为的:“儿童文学不仅仅是要让孩子学到知识,了解社会,更主要的是让孩子读完一本书后能够得到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会对孩子的个性发展及人生道路发生重要影响。 ”[6]
二、从文学中的“死亡”叙事到儿童文学书写中的“死亡”表征
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和过程,死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件。但是作为人类来说,死亡却有着不同的涵义,因为人类是唯一能意识到自己必死的生物。人的所有行为都在追寻和追问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于是在文学艺术中,死亡就成为永恒的母题;哲学中,死亡成为人类智慧所能思考的最终极话题。作家自然不能摆脱对死亡的思考,同时他还将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和领悟到的生命的意义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中国古代文学中像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的期望和屈原开启的“美人迟暮”,道家的“齐生死”和归隐自然乃至李白诗歌中呈现的享乐主义,游仙、求仙诗歌传统,晏殊的忧思愁绪之词等,作家都是以领悟生命短暂作为审美前提的。近代文学中的革命文学表现的崇高“死亡”美学,先锋小说和新历史题材小说中的无意义“死亡叙事”以及毕淑敏、陆幼青正视死亡的坚强叙事。西方文学中,从《圣经》中文学叙事的死亡书写到中世纪宗教文学对天堂和地狱的描写,从文艺复兴时世俗文学传播者死亡模式到启蒙运动文学中的自杀叙事,最后到二十世纪存在主义、荒诞意识和“垮掉的一代”等等无一不对死亡进行着文学式的思考。
死亡叙事在文学中被分为文学中死亡书写呈现出虚无消极的荒诞感和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第一种是对死亡残酷的大肆渲染。作家以血淋淋的死亡描写探问人类天性中潜意识里隐含的残忍动物性和报复欲,渲染人性恶的层面,人类心灵的扭曲和阴暗,如戈尔丁的《蝇王》、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死亡叙述》等等。这是一种死亡恐惧书写,面对死亡文学塑造的是一种对死亡的惧怕和逃避。第二种是直面和超越死亡。人不同于一般动物,既然能意识到自己是 “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7](p296)的存在,也就会在精神上千方百计超越死亡和死亡威胁带来的痛苦心理。(1)诗意的死亡——将死亡与爱和快乐结合,同时渲染死亡中蕴含的神秘朦胧的美感和,如徐志摩的《哀曼殊菲儿》(2)宗教层面的超脱——禅境中的皈依,万物皆空的涅槃之境,“微笑生死”(3)寻求自由和生命尊严的“英雄壮歌”,如古有夸父、荆轲,今有江姐、许云峰,西有阿喀琉斯、赫克托尔,中国现代的“普罗诗派”。
如果将死亡在成人文学中的第一种描写方式直接搬入儿童文学之中,其现实呈现方式就是对凶杀和死亡渲染的校园死亡文学的盛行,扭曲儿童心灵,如《末日祭奠》、《诛仙》、《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等这种对死亡的无限度敞开。而将第二种成人式的超越死亡的叙事方式直接植入儿童文学,也并不恰当。因为成人文学中的死亡叙事完成了的是对意义的追寻、情感的分享以及审美享受,而儿童心智并不能完成对文学的此种高层次接受。儿童过早在文学之中接触到死亡会对儿童带来迷惑、焦虑或者恐惧,影响心理健康和将来对正面事物与观念的接受。Nagy在研究中得出结论:3-5岁的儿童倾向于将死亡视为睡眠或一种暂时的状态;5-8岁的儿童能意识到死亡是人类的最终状态,但是否认自己会死亡;9岁以上的孩子能理性地认识到死亡对人意味着什么,接受自己将来也会死的观念。[8](P228~229)儿童对于死亡的认识分为几个阶段就意味着儿童文学必须分级提供给儿童阅读吗?这倒不必。Nagy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儿童心智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儿童文学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度。我们可以从超越死亡的模式中吸取有益元素,作为儿童文学的写作的考量。将爱、希望和勇气,对人性的信任,对生命的热爱等正向、积极的处理死亡的叙事手段植入儿童文学之中。
可以说死亡主题在儿童文学诞生时就一直伴随着它。比如《睡美人》中的王子被蛇蝎活活吃下去,《蓝胡子》中的变态杀人狂,《白雪公主》中精心策划的谋杀,《三只小猪》中狼吃掉小猪,后面的小猪又吃掉狼的血腥。随着儿童文学的发展,死亡叙事在儿童文学中越来越多。比如安徒生 《冰姑娘》、《幸运的贝儿》、《海的女儿》、《柳树下的梦》、《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主人公都是以死亡作为归宿。王尔德的《星孩》、《渔夫和他的灵魂》等作品,也都是让故事的主人公死亡作为对生命领悟的最终归宿。怀特的《夏洛的网》以一只蜘蛛在他乡的死亡将奉献的精神渲染到极致。圣·德克旭贝《小王子》以死亡作为结尾从而成为了无可超越的童话经典。还有日本小川未明的《爬上树的孩子》,宫泽贤治的《夜鹰之星》、《布多力传记》等等。
一方面,成人文学中的死亡叙事并不适合直接植入儿童文学;另一方面,死亡是儿童文学不能避开的叙事主题。因此,怎么样处理好死亡书写的尺度就成为儿童文学作家面对挑战。死亡作为题材需要也好,还是作为情节需要也好,都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儿童文学家的任务是编织人生中的真善美,揭示生命的意义。死亡在儿童文学中处理得好与不好体现着作家对题材的驾驭技术,也体现出作家直面人生时的悲悯情怀和审美诉求。将死亡规训于儿童文学中,而不是清除出去。
三、儿童文学作家对死亡主题的处理
作家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对死亡意象的处理的:一方面是在内容上,赋予死亡各种不同的积极正向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从语言上将对死亡的恐怖模糊在语言能指的优美书写之中。
儿童文学家主要通过几种方式打磨掉死亡的粗粝,驱除掉死亡的阴冷,从而实现审美层面或者伦理层面的超越。第一,作家会在叙事最后以一种美好的死亡归属作为结尾,将死亡看作爱和信仰的归宿。比如安徒生的童话《红鞋》和《安妮·莉斯贝》作为赎罪模式,主人公的死亡并不会给小读者带来一种可怕的或者悲伤的回忆,相反是一种爱的升华和超越;《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圣诞夜与亲爱的祖母一道走进了没有痛苦的天国,这难道不是对死亡的一种审美转化吗?第二,将死亡塑造成一种伟大的奉献,英雄般的壮举。《海的女儿》小人鱼用自己的声音换得了人类的外表,虽然并没有得到王子的爱情,为了成全王子的幸福,于是跳入海中化为水上的泡沫。《夏洛的网》中夏洛吐尽自己的蛛丝也是为了救得朋友威尔伯,到最后悲惨的死在他乡。第三,将死亡更换为一种轮回永生,比如《最后一战》、《银河铁道之夜》、《狮心兄弟》、《北风的背后》主人公的死亡被作者暗示为一种回归,他并没有消失,而是回到曾经的或者应该去的地方了。还有像法国作家巴达的《圣诞树》中死亡是生命对大自然的回归;《湖孩子》中,男孩儿的死亡是回归水下世界。第四,主人公的死亡被赋予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是为死去人创建了一个新的世界,儿童在阅读中就将对死亡的恐惧立马转向为一种安全感,比如林格伦在《米欧、我的米欧》为死去的孩子建立另外的国度来;琼·艾肯的《小埃丝的摇木马》则让木马带着孤独的小女孩在月光中飞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五,直面死亡,但死亡描述为大自然最自然不过的生命过程。比如安徒生的《小意达的花儿》中,作者告诉孩子们人的生命与万物的生命一样,都会逐渐衰老死亡,不论大小强弱。同时,死亡是沉寂的、自然的、不可逆转的。
语言层面上的文学处理,会大大降低儿童阅读时产生的恐惧,相反一种审美的愉悦性会将儿童导向正面的、积极面对的态度中去。第一,作家用纯澈的语言将死亡笼罩上一层恬静之美,并通过象征的手法将死亡的文字威胁降到最低程度,让读者有隔岸观火和雾里看花之感。比如安徒生作品《海的女儿》小人鱼因看到心爱的王子结婚,而跳下海,化为了小泡沫;《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将小女孩的死亡描述得那么优美,“她幸福地和她慈祥的奶奶一起微笑着步入了那个遥远又美丽的天堂”;《祖母》中去世的祖母“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安宁,宛若被阳光照耀得容光焕发”,同时墓地是玫瑰、花丛中的夜莺,管风琴优美的旋律和轻柔的月光。第二,作家将死亡能指化,在语言中模糊直至消失。比如马克斯·维尔修思的《鸟儿在唱歌》中青蛙、小猪、小鸭和野兔一起埋葬他们的朋友鸟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对话都充满了悲伤,眼里噙着眼泪,但“突然青蛙跑到前面兴奋地大叫:‘我们;来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小猪,你来抓我。’”[9](p49)一下就将整个故事的氛围换成快乐的了。生命真美好,这就是马克斯用文字的转换,置换掉了死亡的恐惧和悲伤,带来了“一只黑鸟如往常一样在树上唱着美妙的歌”。[9](p49)对于作家而言,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就会传达不同的情感、思想和审美感受,对于死亡的描述和判断,直接通过文字传达给儿童,是恐怖、悲惨、痛苦还是高兴、淡定、崇高等都取决于作家对作品的把握和文字的处理。
反过来,我们同会考虑,赋予死亡以积极的意义或者进行优美书写,是否对于儿童的成长适当?答案是肯定的。对死亡的因素的合理把握,可以将死亡意识对儿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并不失去给儿童带来面对死亡时的那份勇敢。死亡的内涵包括普遍性(universality)(包括总括一切、必然性和不可预测)、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原因性(causality)、无机能性(nonfunctionality)、非肉体的持续(noncorporeal continuation)、拟人化等[10]儿童文学中也包含着这几层死亡内涵:就普遍死亡概念而言,主人公的祖父母、野生动物宠物非常普遍;就原因性死亡概念而言,主要是外力、疾病、自然死亡等;就不可逆性概念而言,永远的消失;无机能性死亡概念而言,以无呼吸、不动、丧失知觉等为主;拟人化死亡概念而言,以死神、上帝、神鬼、天使等为形象出现;非肉体的持续概念而言,转化为天使、灵魂,或者去到了天上、地狱等。
这些死亡因素被作家作为意象或材料进行正向情节加工和审美化语言处理,就会使得儿童文学散发出一种阳光的味道。就普遍性而言,作家可以将人的死亡与万事万物的死亡同体悟,让死亡成为一种自然之事;在死亡的原因上,可以将原因浪漫化,审美化,或者崇高化,比如安徒生童话中的主人公很多都在水或者冰雪中死去,给人一种纯洁、柔情之美;作家也可以将死亡不可逆性转化为可逆性,像“复活”母题,穿梭于天堂、人间和地狱;让死去的人或物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甚至比正常人更漂亮、更具有爱心等等。因而,死亡是儿童文学中可以出现而且应该出现的。同时更应该通过作家手中之笔的运转,让儿童感受到死亡不是冰冷、让人战栗的悲剧,而是温暖的、感动的、美丽的和悄然的“离去”。
四、结语
死亡作为一种文化的禁忌是可以进入儿童文学之中的。纵观儿童文学发展的历程,其实在发展的初步阶段是死亡在儿童作品中的残酷性较之成人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儿童文学范畴是成人按照自己的理想世界建构起来的,作为儿童文学阅读对象的儿童的概念也是在17世纪末才建立起来的。儿童文学作为成人创作的作品和建构的观念,是否完全被儿童所接受,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因为儿童在我们的眼中就应该是温室的花朵,就不能接触成人所认为的文化禁忌,在成人与儿童之间我们看不到对话的声音,儿童只是成人内心理想的一种投射物。我们会用儿童的不成熟作为搪塞,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儿童的世界是由成人区隔化建构起来的,被成人眼中的文化所归驯了的。因而,儿童文学的纯净化过程与成人对儿童理想化设想直接相关,于是,儿童文学中的性、死亡、暴力等等都被全面性剔除。如果我们不想儿童永远静止于我们脑子中希望如是的儿童的状态,不妨让真实的世界更合理、更艺术地进入儿童的世界。
[1]侯颖.激活死亡母题的中国当代儿童小说[J].中国儿童文学,2005,(04).
[2]赵霞.死亡:断层与永恒——以安徒生三则童话故事为例[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2).
[3]桑俊.来自天堂的关爱——安徒生童话中的死亡意象研究[J].名作欣赏,2010,(5).
[4]〔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文良文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5]凯瑟琳·奥兰丝坦.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的性、道德和演变[M].杨淑智译.台北:张老师文化,2003.
[6]〔德〕 赫尔姆特·萨克夫斯基.“双把儿铁锅” 卡琦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
[7]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M].Oxford:Blackw ell Publishing Ltd,2005.
[8]Edvin S.Shneidman.Death:Current Perspectives[M].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1984.
[9]马克斯·维尔修思.鸟儿在唱歌[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10]Speece,M.W.,& Brent,s.B.,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death:Are view ofthree componentsofdeath concept.Child Development,55,1671-1686,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