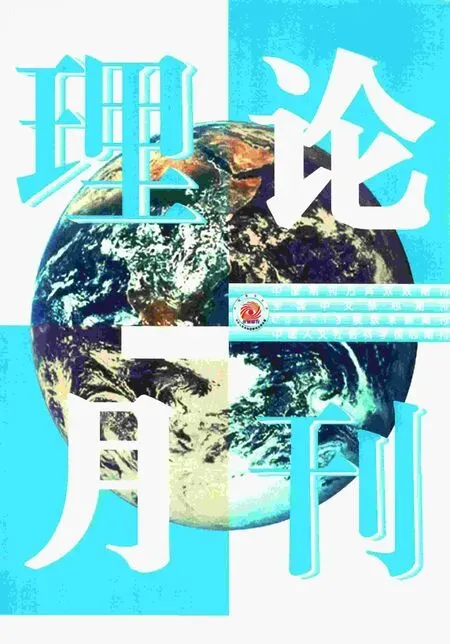辽代的图书出版与书籍传播诸问题论析*
2014-12-04施国新
施国新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自上世纪20、3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出版史的研究代有所陈,成果日渐丰富。无论是对于传世出版物版本的考订、真伪的辨析、内容的解读、类目的归纳,还是出版思想的总结,更或是相关史事的分析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美国汉学家卡德所著《中国印刷术源流史》[1]一书,最早利用西方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结合当时流传印刷品,对中国印刷技术及图书出版情况作了详尽的叙述。该书于1938年经国内翻译家刘麟生编译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研究的观点、方法等在当时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52年《文物参考资料》第四期发表的杨万里《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2]一文,则是利用传统考据学的方法对传统文献中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了补正与汇考,其方法与结论被认为极具学术眼光,受到当时学界广泛赞誉。此外,诸如周一良、来新夏、李瑞良、肖东发、黄宽重及美国学者周绍明等人也均从宏观或微观视角对古代图书出版情况做过相应研究。[3]然而囿于史料原因,目前研究成果仍只集中于传统所谓的中原王朝及文献材料保存较好的民族政权或地方政权,而对于那些文献散佚非常严重或文献记载相对薄弱的政权的图书出版情况则少有专门论述。如与宋代前后并存的五代十国诸割据政权及辽国、西夏等的研究就大体如此。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材料,专对契丹族所建辽朝的图书出版情况加以讨论,望有助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讨论。
一、辽代图书编修及藏书机构
众所周知,辽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建国,后来随着统治区域的日渐扩大,遂于境内施行南北面官制度。所谓南北面官制度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4]从文献记载来看,辽代修书一如宋人,有官修、私修之别。辽代官方的修书机构主要是南面官系统之下的国史院,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据《辽史·百官志》“国史院”条载:“国史院。监修国史,圣宗统和九年见监修国史室昉。史馆学士,景宗保宁八年见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刘辉大安末为史馆修撰。修国史耶律玦重熙初修国史。”[5]据此可认定,辽代国史院设有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官职。与北宋一样,监修国史一职大多由宰相兼领,无专官。如《辽史》云:统和二十八年(1010)十二月甲子,圣宗就曾“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为北院枢密使封岐王,以宰臣刘晟监修国史。”[6]至于其它官职是否一如宋人,为兼官之设,则不能详考。
辽代另外几个重要的官方修书机构首先是起居舍人院、中书舍人院。起居舍人院设立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等官职。《辽史·百官志》载:“起居舍人,圣宗开泰五年见起居舍人程翥。知起居注,耶律敌烈重熙末知起居注。起居郎,杜防开泰中为起居郎。”[7]起居舍人院,主要负责编修历代皇帝起居注。对于中书舍人院的修史职能,辽代文献不做记录。但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记载来看,它应该承担有史职。该书言,“契丹史官,契丹称中书舍人。或中书舍人即兼史职也。”[8]其次是日历编修机构,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三月,朝廷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 ”《辽史·圣宗本纪》又载:统和二十九年(1011)五月甲戌朔诏,诸臣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从中可以看出,辽代也有一套完整的日历编修机构。一般来说,日历逐日记录朝政之事情,按日月编次,修撰成书。据史料记载,宋人修撰日历,有专门的日历编修机构日历所,归秘书省执掌。辽亦仿唐宋之制,设有秘书省,然是否下设专门日历所编修日历则不得而知。辽代还设有日月四时堂,用以修史,这一点与北宋以及之前的中原王朝都有不同,应该属于契丹人新创。《辽史》记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六月癸巳,“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9]除南面官系统修书机构外,北面官系统也有一套修书机构。但此类史料极度缺乏,仅知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10]文班司下设有文班吏。这些机构或许也会参与书籍编修,但具体如何操作,均已不详。
受宋人影响,辽代汉族及一些契丹族文人也多有私人著述行世。据《辽史》、《契丹国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人厉鄂《辽史拾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杨复吉《辽史拾遗补》、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等书所作搜录,辽代但凡诗文、史学、经学、农学、佛经等书籍不一而足,且多有刊布。朱子方先生《新补〈辽史·艺文志〉》一文曾作统计,目前辽代文献存世者约有341种,其中经部著作有6种,史部22种,子部129种,集部184种。明确为私人著述的有319种,几乎占到了文献总数的94%。[11]宋人就有谓:“北虏中多有图籍,亦有文雅相尚。”[12]同北宋一样,辽代官方也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辽代官方藏书机构主要集中于上京临潢府。如据《辽史》记载,太宗时期,契丹占燕云地,太宗即下令“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13]上京是国都所在,为契丹文化中心,很多机构都有藏书,如与杂礼有关书籍就多藏于太常寺下的法务库,史载“法物库。辽朝杂礼有法物库所掌图籍。”[14]法务库设有法务库使、法务库副使等官职。而内省、内侍省下面的诸库也是书籍收藏的重要场所。北宋诸书库按照收藏品种不同有着严格的划分,比如印版书收藏有专门的印板书库;收藏印版有印版库,此外,还有国史库、经史子集四库、秘阁上下库等等。对于辽人是否也有如此严格的划分,史无明文,但是从法务库专收礼乐典籍的记载来推断,辽代书库也应该是有完整功能划分的。
至于书籍的抄录、刻印辽代也有专人负责,如秘书省内就设有很多吏职,专行抄录、摹写以及刻印之事。而北面官系统的承应小底局,下面也设有笔砚小底、裁造小底。笔砚局有笔砚祗候、郎君、笔砚吏等负责文墨之事。辽代还设有印经院,专人负责佛经雕印。除了官刻书籍之外,辽代私人刻印书籍也非常兴盛。从文献记载来看,早在辽代初期南京刻印业就非常发达。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有一批辽代典籍,其中有些文献上就有 “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印造”、“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造”等题记,从这些文字判断,这些文献就应为民间刻印而成。另据史载,大安十年(1094)十月,道宗下令“禁民私刊印文字。”皇帝下令民间不许私自刊印文字,足见当时民间私刻的普遍。
二、辽代图书的装帧与版式
据考证,中国的图书编篡与制作起源较早,有学者认为,最早的“书籍编撰源于夏代。”[15]然而就版刻书籍而言,则大约出现在“唐太宗贞观年间。”[16]唐末、五代以后,公私刻书日渐盛行。及至辽宋时期,刻书活动更进入了黄金时期,辽宋境内各府路军州都有刻书活动进行。
建国以后,山西应县木塔、河北省丰润县天宫寺塔以及新疆吐鲁番地区等也曾陆续有辽代纸质文献出土。虽然数量有限,但从以上出土文物中,我们仍能归结出辽代版刻书籍的一些共性和特点。
一般认为,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和河北奉润县天宫寺塔所发现的辽代佛教典籍装帧方式不尽相同。应县所出辽代典籍绝大多数为卷轴装,总共有四十二件。另有小部分为蝴蝶装,共有四件。此外还有梵夹装文献一件。辽代卷轴装印纸版式较为横长,由数张纸至数十张纸粘接拼合为一卷,四边设有边框,每卷内各纸的行数以及每行内所刻字数基本上能够做到一致。这一点与宋代卷轴装典籍基本一致。而辽代蝴蝶装的版式为长方形,在中间留有书口,这样经过对折之后,就形成了两个版面,且各版面又各有边框。装订时,刻工将印有文字的一面加以对折,再把折后所形成中缝的脊背面依次进行粘连,从而形成一册完整书籍。对于这种装订方式实际上也与宋本大同小异。现存辽代梵夹装典籍最少,但是从应县木塔所出土梵夹装刻经来看,其刻印亦称精良,该经页页相连,且各有边框,如展开其自成一长卷,合之则又为一册。可以说鲜明体现了当时梵夹装典籍的一般特色。宋人云:“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五代国初犹然。”而从这些已发现辽代书籍来看,辽籍也基本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装帧方式。
从出土文献推断,辽刻书籍版式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下单线边框,每纸自右开始分别雕印书名、各卷次、版码以及帙号。另一种则是上下双线边框,在每纸第一二行的中间分别雕印书名、各卷次、版码、帙号。另外,每套书籍亦有帙套、缥带、封面题签等与北宋古籍样式基本无异。而就刻印文字来看,山西应县佛宫寺塔出土的卷轴装辽藏,均以汉子刻印而成,字体均为楷书大字,行文疏朗,且排列整齐有序。而河北天宫寺塔出土的蝴蝶装《辽藏》,字体虽然相对较小,行款也较山西出土紧密。二者相比,看似风格不尽相同,实际上二者行文字体均有明显的颜体风格。明人总结宋刻古籍特点时提出,但凡宋刻本“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欵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不薄,不蛀。”[17]从中可以看出,辽刻颜体的书写风格,或许是受过宋刻书籍的影响。史料就记载说,辽代书肆中多有自北宋贩运而来的书籍出售,因此,辽人模仿宋刻进行书籍刊印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辽刻文献好用颜体字这与颜体字在唐代以后就在北方地区盛行不无关系。
三、辽代书籍的传播与交流
终辽之世,契丹人与周边各族文化交流一直较为密切,这其中书籍、文献的传播与交流就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辽廷对书籍的传播政策并不是一视同仁的。
对于与其长期对峙、实力相当的赵宋政权,辽廷一度严禁本国书籍流入宋境。《梦溪笔谈》就记载说,“契丹重熙二年,禁契丹书集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18]对于辽廷因何禁止书籍入宋,史料中少有直接的记载。但从当时历史局势来看,重熙二年(1033)也就是宋仁宗赵祯明道二年。这一时期契丹人虽然形容两国关系“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19]实则双方剑拔弩张,此时距澶渊之盟签订时间并不久,数年来两国在交往礼仪、增减岁币等问题上一直就是龌龊不断。同时,辽为了牵制北宋暗中扶持西夏、吐蕃等赵宋周边政权,这也让宋廷一直大为不满,宋人张方平即云,辽人“今其与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与戎人之亲盛也在内。外虽我睦,阴为戎助,此又不可不过虑也。”[20]因此,基于防范辽国的需要,宋人就在双方贸易中,严禁本国书籍外流。《续资治通鉴长编》即载,仁宗天圣五年(1027),宋廷诏“民间摹印文字并上有司,候委官看详,方定镂板,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缘边榷塲商人往来多以本朝臣僚文集传鬻境外,其间载朝廷得失或经制边事,深为未便,故禁止之。”[21]需知,辽人颁布禁书诏令距宋令施行间隔不足六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辽代书禁的目的与宋人应该是一致的。到了辽道宗清宁十年(1064)十月戊午,辽廷还曾颁布诏令“禁民私刊印文字。”[22]对于这次禁书,文献记述同样很简单,但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存在。
实际上,宋辽间关于禁止书籍流通的制度,执行力度并不如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么严格。宋人即云:“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23]宋辽之间大量书籍不但通过“榷场贸易、走私贸易、官方的馈赠以及战争中的掠夺”[24]等方式流通,双方“归明人”的献纳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归明人亦称归正人,是宋辽时期对沦于外邦而返回本朝者的代称。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十一月,就有辽国归明人赵至忠“上契丹地图及杂记十卷。”赵至忠在辽时为史官,因此所存辽代文献甚多,嘉祐三年(1058)二月,“又上国俗、官称、仪物録。”嘉祐六年(1061)五月“又献契丹蕃汉兵马机事十册,并契丹出猎图。”[25]至于其它一些书籍传播方式,以及书籍传播事例刘浦江先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一文已有所详述,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相比北宋,辽对于其它周边民族政权的图书交流活动则相对宽松一些,姑不论边界榷场贸易中的图籍播迁,辽朝官方也时而会将一些书籍赐予诸族。例如辽道宗咸雍三年(1067)十一月,以回鹘遣使进贡为由,遣使赠“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26]大安八年(1082)十一月,辽又以坤宁节大赦天下,“赐高丽佛经一藏。”[27]此外,辽廷还为周边诸族颁赐历书,宋人即谓“辽及高丽、日本国历与奉元历同。”相对这些民族,宋人则无法获睹辽历全貌,于是只好借“高丽所进《大辽事迹》,载诸王册文颇见月朔”来推演辽历。[28]
就史论事,辽廷之所以在图书管制过程中,实施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主要有以下考虑。一方面,宋辽国力相当,以兄弟之国互称,澶渊之盟后虽貌似和平,但是又均视对方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因此,对彼此的防范就自然大于双方正面的交流。正如前文所言,外传书籍由于可能会涉及本国机密,于是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另一方面,就汉文化承接而言,辽人虽于五代末,尽掠中原旧藏,正所谓“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29]但宋人在以汉人治汉事,则更显优势。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也很容易导致辽国对宋文化输出政策的日趋内敛。而与此同时,辽对于其它民族政权而言,文化上又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因此,很容易将自身视为文化的宗主,自然乐于输出本国文化,以此来强化对周边国家或地区政权的控制与渗透能力,这样辽廷对以上地区文物典籍的管制也就相对较为温和了。
结语
总之,辽籍无论是编修还是刻印更或是流通等环节都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程序。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均有大量汉文或契丹文文献刊。另从河北、山西、新疆等地辽刻可以看出,辽代刻书固然有本民族文化的影子,但更多是对唐五代及宋人刻书的借鉴与模仿。它与宋刻一起共同勾勒了中国10到12世纪前期中国图书出版史的完整面貌。
[1]〔美〕卡德.中国印刷术源流史[M].刘麟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2]杨万里.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J].文物参考资料,1952,(4).
[3]周一良.纸与印刷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A].李光壁,钱君晔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C].北京:三联书局,1955;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黄宽重.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关问题[A].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辑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5][6][7][9][10][13][14][22][26][27][28][29](元)脱脱等.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685,781,174,776,44,695,59,786,264,1527,274,567,919.
[8][21][25]〔宋〕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2004.4475,2436,4475.
[11]朱子方.新补 <辽史·艺文志 >[A].辽金史论集:七[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2]〔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17.
[15]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7.
[16]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历代刻书概况[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188.
[17]〔明〕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26.
[18]〔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32.
[19]〔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1.
[20]〔宋〕张方平.乐全集[C].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04,173.
[23]〔宋〕岳珂.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16.
[24]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A].张希清等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