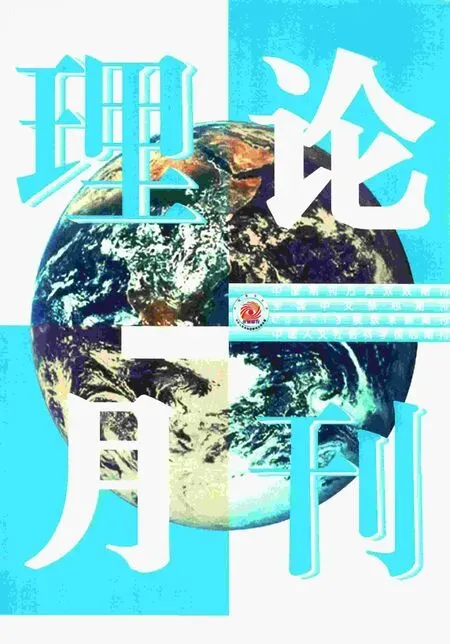论国际行政法概念的理论根基*
2014-12-04林泰
林 泰
(重庆工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67)
一、国际行政法产生的全球背景
晚近,911事件、SARS、禽流感及其它跨疆域自然或人为灾难的爆发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世界中所体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最近几年已越来越明显,这种明显特征的一个最为突出表现就是各国政府无法单独处理这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恐怖主义、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传染病,以及全球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等,于是国家间的协作以及对统一国际决策应对国际公共问题的需要也随之显现,并且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重视。[1]
分散的国内规制和管理措施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这些后果,因此,全球治理的提出成为必然。在全球治理中,各种跨国规制体系或规制合作通过国际条约和较为非正式的政府间合作网络建立起来,使得许多规制决策从国内层面转移到全球层面。而且,此类规制的具体内容多是由那些实施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受国内政府或国内法律体系控制的跨国行政机构所实施。与此同时,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很多学者对所谓全球治理的提法仍然持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这在实践中体现为对超越国家范围决策的保守态度及怀疑态度,反全球化活动者的身影活跃在各个国际组织的会场之外,很多人认为全球化以及超越国家边界的行为损害了主权国家的民主、主权和管理的自主权。而跨国行政机构的权力行使中同样存在种种问题,如民主缺失、参与性、可问责性等,于是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国内行政法的视角审视上述种种难题。随着国内的决策者和行政法学者开始倡导制定规则和程序以加强行政机构的合法性,一种行政法的国际化趋势开始显现:即寻求行政法的首要原则以纠正跨国层面上民主缺失、合法性以及可问责性等问题。这种国际化的趋势不但体现为为更多的超国家治理制定规范标准,还包括确保跨国规制机构必须采取基本的行政法程序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并加强公众对他们所做的选择和提出的政策的信心。在这个框架下,建立在通过条约或者习惯所表达的国家授权基础上的传统机制对于所有的全球活动不再具有普遍价值。新的管理空间正在浮现,它与国家间关系相区别,超越了国际法和国内行政法的影响范围,这可以被定义为“国际行政空间”,首当其冲的是一部分特殊国际组织,在特定的层面上已经作为真正的超越国界的国际行政管理主体而出现。
但是,这种全球化中出现的新的行政法发展趋势与传统的行政法概念有所背离,从世界上各国行政法的发展脉络来看,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基本上限于国家范畴之内,即行政法是关于国内行政的公法。学界对行政法的判断,大多立足于行政法为国内法,实践中则基于行政法是作为国内管制与国内治理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活动来理解的,因此,国家主权是行政法难以逾越的界限,尽管学术史上也曾经有关于“国际行政法”的提法,但在当时环境中大多仅限于极其狭义的指 “国际组织在处理劳动争议和其他内部事项中形成的规则”,[2]所以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显然是对行政法只能是属于国内公法的这一传统学术论断的挑战。与国内意义上的行政活动相区别,在定义这些全球性管理体系的组织和活动的行政性质时,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传统国际法的概念结构之内,缺乏类似国内语境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一样的成熟制衡体系,并且这单独的导致了在它们的正当性和有责性方面的特殊问题。换句话说,为适用于全球体系之管理决策的结构、程序和规范准则,和为执行这些准则的规则治理机制正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一个特殊的领域:那就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型“国际行政法”。这个浮现的领域主要的焦点既包括由全球管理体系所产生的有关实体规则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还有潜在的对原则、程序规则、审查和其他在全球治理中关于问责性、透明度、参与和法律规则方面的机制的应用。当然,这些多种多样的监管制度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一些仅仅提供了国家行为的框架,其他的却为国内行政机构制定了指导方针,而一些仍然对国内市民社会主体直接产生作用。一些监管制度创设了它们自己的执行机制,而一些却依赖国内或区域当局来处理事务。为了解决争端,一些监管制度已经创建了司法(或准司法)机构,而其他则诉诸于较为“温和”的方式,如协商谈判。另外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全球化趋势下私人①本文所称“私人”与“私人主体”等概念同义,泛指自然人人、公司法人、私人机制的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开始结构性有序参与国际监管秩序,既可能成为国际规制机构直接行使权力的对象和受体,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国际规制者,这对制度层面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事实上,尽管如上述,但观察学术史发展轨迹,我们也不难发现曾经在某个时期个别学者曾前瞻性的提出有关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相类似的国际行政法概念,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30年代已经有对国际行政和国际行政法比较宽泛解释的学说提出,例如,“将跨国治理视为一类受制于不同行政法原则的行政的理念出现在19世纪晚期社会改革者和机构缔造者的著述中”,[3]如后面将要述及的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经济学家、社会哲学家拉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但在1945年之后,除了少部分的国际法学者,如 Wilfred Jenks、Soji Yamamoto等的著述里能看到类似的界定,这些对国际行政与国际行政法理解的宽泛视角在大多数的国际法著述中已经基本消逝。[4]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国际行政的概念重构就是试图复兴这些早期的学术观点背后的广阔视角。
如果说,行政法体现的是对国内政府监管行为的一种法律规则,那么,监管的国际化相应带来的是法律制度的行政法的国际化,所以说,监管国际化与国际行政法的产生存在逻辑上的关联。在全球化、全球治理语境下,作为对全球化中种种全球性问题与监管制度国际化的历史回应,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与形成已经在现实上成为可能,更是一种持续发展的法律发展趋势和过程。
二、国际行政法概念证成的理论根基
新兴的“国际行政法”这一术语以及其中的“法”究竟包含哪些涵义?笔者回顾了学术史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由其中众多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国际行政法概念并非近期才提出,而是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整理之后,笔者发现大致可以归纳为七种观点:(1)国际组织在处理劳动争议和其他内部事项中形成的规则、程序和机制。持该观点的有弗莱德曼(Friedman)、斯蒂夫·查诺维兹,国内的余敏友教授、曾令良教授等,这可以看做是对国际行政法的最为狭义的理解。(2)国际行政法是国际组织法的一部分。持该观点的如英国学者J·G·斯塔克、国内的学者何顺善先生、饶戈平教授等。(3)国际组织法是国际行政法的一部分。持该观点的如梁西教授。(4)国际行政法就是国际组织法。持该观点如李双元教授和于喜富教授。(5)国际行政法是一种冲突规范。持该观点如李浩培教授、台湾学者吴庚等。(6)国际行政法是和国际经济法、国际刑法等相对应的学科。持该观点的有章尚锦教授、姜世波教授等。(7)国际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持该观点的保尔·内古莱斯科(Paul Négulesco)、拉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以及国内的张泽想(杨解君)教授等。②有关详细的相关学者观点综述可参见林泰、赵学清:“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载 《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99-101页。
以上学者的观点表明了一点结论,“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学术用语国内外早已有之,但是由于种种局限,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去看国际行政法问题,其根源是对自身的立场和学识对“行政”与“国际”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关于“国际”,一直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秉承国际、国内二元对立的观点,“国际”是和“国内”泾渭分明的一个空间概念,所以,所谓“国际行政法”即就是在国际层面(再狭义之就是国际组织了)的行政法问题。这样的理解对“国际行政法”而言当然是一个极其狭义的理解。
另一方面,对于“国际行政法”这一新兴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中使用“法”这个术语具有怎样的合理性,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有人对此作出富有创见性的探讨,即上述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经济学家、社会哲学家拉伦茨·冯·施泰因,他在1866年提出国际行政法(Internationales Verwaltungsrecht)概念,并将其视为调整国际领域行政活动的国际法律规则和国内法律规则的总和。[5]拉伦茨·冯·施泰因所要强调的,是界定并描述公共行政的现实而非其内在法律基础。[6]所以,在讨论国际行政法问题时,首先要推究的是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具有实际意义,超越国家的权力行使与国家及其内部机构在国内法律和政治秩序下对权力的行使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国内适用的行政法概念工具中,我们只能得到有限的能适用于国际行政空间的直接类似的东西。不能将国际行政法理解为一个简单的向国际行政空间进行的功能的移植,更不能说是特定规则和制度性的相互复制。同理,在基于国家法基础的法概念,实际上不能解释和涵盖“国际行政法”这一论题下所出现和需要探讨的各种现象。所以,对国际行政法概念的理论根基不能局限于国家的法概念之上。
命令理论认为法律由一个单独的决策主体所做出的命令组成,并以有效的制裁措施做支撑,因此这种理论在讨论国际行政法时不大可能产生有意义的或全面的结果。例如,霍姆斯的命令理论就体现了他对国家法律和政治理论的浓厚兴趣,认为它们是促使国内和平不受可怕的内战所威胁的最合适的保护者。[7]无疑,这意味着霍姆斯的法律理论不会给国际法起多大作用——尽管他对自然法和民法的关系的观点曾被Noel Malcolm认为是为国际关系的法律理论提供了某种基础,[8]而其他学者曾试图从霍姆斯对法律颁布和其它程序性要求以及合法性的观点中推导出一个普遍的法治理论。[9]霍姆斯特别关注权力的标志,它们将法律与拥有足够权力的私人“不遵循或违背立法权限公布那些他们喜好的法律”[10]的情形区别开来,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决定法律的权威性渊源的标准对法律的概念非常重要,另外,由权威渊源而来的法律不应考虑其道德内涵或其他实体性特点。这种观点至今对实证主义法律观念还有影响。哈特则提出由主要行为规范,和承认、改变主要行为规范并以其为裁决依据的二级规范组成的社会习惯,可以成为一个法律体系,前提是“相关不论任何人均要接受同样的承认规则,并有一种内在责任感去遵守这些跟他们与遵循相联系的威胁和回报毫不相关的规则”。[11]因此,哈特的观点与霍姆斯将法概念建立在主权的基础上的观点有着决定性的区别,但保留了实证主义者将渊源和承认作为法律概念的核心的观点。[12]所以说,哈特的理论提供了一个供现代实证主义者研究国际法和国际行政法中的法律的更具扩展性和前景的理论起点。
对法律概念分歧进一步阐释有助于解释和论证实证主义者的法律概念在国际法的相关著述和实践中的普遍适用。实证主义观点认为规范的权威渊源对其作为法律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在不存在决定什么是法律的统一的基于内容或事实的标准的情况下,以及在缺乏能够支持任何其他法律研究方法的统一政治理论的情况下,作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承认。在国际法背景下,可能确实存在道德的或政治的原因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实证主义者的法律概念;这也许是为促进基本秩序、互不干涉、和平、为民主目的的肯定性自由、或其他形式的集体自治和个人自由的最好方式。[13]
在涉及到国际行政法时,可以在一个经过扩展的实证主义法律概念中找到理论根据,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以及其他著述中所体现的法理学方法的某些特点,对于描述国际行政法中的法律概念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特点包括哈特对社会习惯、法律渊源和承认行为的强调。[14]在这个经过扩展的实证主义法律概念中,首先强调的是基于“社会事实”的法的概念。法律存在的一个条件应该是主要参与者所实际持有的态度,以及与他们相关并对他们及其行为进行评价的人所持有的态度。国家、法院、以及行使国际公共权力的机构的相关官员的态度有助于确立:分散的承认规则;就某个惩罚性主要规范的内容和适用,以及就其是否在此种二级承认规则范围内所做的具体决定;以及解决或裁决此种问题的体制和以规范性方式确立新的规范或改变规范的体制。评定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标准包括,对其具有的一种内部责任感,以及在重要官员之间就有关其渊源应具备制定法律规范的能力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哈特为法律的经验性确证提供了一个研究方法。其次是强调法律的渊源。国际行政法由条约、基本国际法惯例所组成,并援引强行法、一般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理念。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能从国内法演化而来。但是仅具有上述几个渊源的法的概念并不充分,需要更进一步的考虑,其中也包含对渊源的关注。再次,在国际行政法的承认以及承认规则上,哈特认为国际法的统一要求理解和论证的统一,在超越了公认的国际法之外的程度上,不存在一个拥有普遍的承认规则的国际行政法或全球治理配套的法律体系。一个具有说服力且不只是国家间体系性质的法律体系还未形成,“裁决”机构通常是非司法性质的,且某些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涉及到规范时,变化的过程并非那么容易阐明。与“国际法”一样,“国际行政法”不是一个已经确立的规范和义务领域,它不具有统一的宪章,层次性的法院,没有如赋予国内法律地位的国内宪法似的成文的法例,也没有意义深远的漫长历史。很可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这种统一体将有所发展。但是现在,任何国际行政法对其是法律的主张都不是建立在一个由相关参与者所公认的承认规则基础之上,这种承认规则确认并界定一个统一的国际行政法律体系。但是,在国际行政法的特定实践领域中的不同社会制度群体中,还是存在不同的承认规则。在这些领域当然存在一些有关承认的习惯做法,因此,即使很难提炼出一个统一的承认规则,承认对于法律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最后,对哈特实证主义的拓展必须强调公法具有的内在特质。
对于国际行政法的概念而言,哈特有关法的概念的几个要素是必需的,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创造和规范国际公共权力的法律还需要更多的内容,因此对这种实证主义方法的拓展或者修正就有必要。正如金斯伯里教授所认为的,在选择主张其为法律时,或在追求基于法律式的推理习惯中,或在被其它确定应对特定全球治理实体的规范和决定赋予怎样的重要性的参与者评定为具有法律属性的规范秩序时,“一个特定的全球治理实体或制度应包含或应在对其评估时援引公法所具有的内在特质、强制服从力以及规范性承诺”。[15]这些规范有多种具体渊源,但是可以辨别出它们区别于不同国家体系以及跨国性和国际公法领域内的公法惯例。它们不只是本应可以或不可以在各个领域所做出的选择,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以此种方式开始得到一定的普遍性和被予以接纳。相反,作为普遍的规范惯例的一部分,它们基于比较性研究和认为其具有强制性的观念得到支持和适用。当他们没有被相关国际组织等的条约或裁决所直接适用时,通常的情况是他们由普遍认为的公法的内在属性所要求。这个观点与通常理解的哈特的观点有所冲突。当然,认为国际行政空间内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遵循公法规范的观点,与哈特的观点并不完全吻合,但是如果承认规则被理解为包含这样一个条件,即只有规则和法令符合公开性要求这一公法的内在属性才被视为法律,则与上述哈特法的概念的各要素具有更加紧密的潜在一致性。
三、国际行政法概念之确立
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蓬勃兴起的 “国际行政法”事实上可以做出和拉伦茨·冯·施泰因相似的界定。近来的国内外一些文献对国际行政法的范围做出了宽泛的界定,这显示出这样一种归纳研究方法,即“首先研究全球治理实践中现实存在的种类繁多的手段和规范”,[16]以及它们之间的能动作用及其变化发展,而非研究其法律基础,更非煞费心机地研究其具体的法律特性。对相关现象进行如此宽泛的探讨,以及对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可以为以下事项打下基础:对国际行政法现象的原因及结果的积极性社会学评定,对哪些利益得到满足而哪些没有得到满足的哲学和政治标准评定,以及各种正义理念所具有的涵义或可能的涵义的确定。[17]笔者对国际行政法定义的探讨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试图在理论主张和实践问题之间建立共同的解释和说明。
在全球化的视域中,全球治理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超国家行政行为。由各种不同层次的主体共同组成一个“国际行政空间”,其中包括国际机构、跨国网络,以及在国际事务中行使职能或做出有跨国规制效果的行为的国内行政机构。[18]“国际行政空间”的理念与业已公认的国际法理念区分开来,当前公认的国际法理念认为国际的涵义主要是指政府间,在国内与国际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在全球治理实践中,跨国网络的规则制定者、解释者以及适用者打破了这种严格的界限。在这国际行政空间中,正日益充满着“跨国私人规制者、诸如国家、国家间组织或其行为具有终局效力但可能并不受控于中央行政当局的国内公共规制者参与的公私合作组织这样的混合机构、无条约基础的非正式国家间机构,以及通过行政性行为影响第三方的国家间组织”。[19]多数全球治理的管理行为具有很强的分散性,不成体系。一些机构在全球规制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出自其本意,或者说这些机构不是特别为这些职能而设置或准备的。例如国内法院可能会发现它们在审查国际行为或跨国行为,特别是那些实际上管理着分散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国内机构的行为。某些情况下,国内法院本身不仅参与审查,还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实际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国际行政法正是随着各种不断发展的规制组织为提升可信度而面临着透明度、磋商、参与、合理裁决以及审查机制的要求而产生。这些要求以及对此采取的行动逐渐形成了具有普遍规范性质特别是行政法性质的各种条文。这些行政法类型的原则和惯例不断提升的普遍性,使得那些本来完全不同的管理领域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承认这些领域间存在一个恰当的原则和惯例的统一体,关系到这些不同的管理领域内合法性及有效性是增强还是削弱。尽力考虑这些现象,以将国际行政法理解为促进或影响国际行政机构的法律机制、原则和习惯做法,以及支持性社会理解,特别是通过保证这些机构能够达到透明度、磋商性、参与性、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适当标准,以及通过对这些机构制定的规则和决定进行有效审查的方式实现上述目的。[21]
由于国际行政法在多个领域适用,这种分析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国际行政法规则也与其它法律渊源相互交错,这些渊源可能包括:一国当地的国内法、规则适用机构的组织法和规范、设立私人权利的合同和涉及其它事项的国际法规则等。如果在上述某些情况下适用国际行政法这个名称时提出它是“法律”的主张,这种主张将偏离传统的公认的国家间的国际法模式和大多数国内法律模式,甚至与其产生尖锐的冲突。[22]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对国际行政法理解中所蕴含的法律内涵进行认真地分析。首先,需要对本文将使用的对法律的概念进行分析的方法的三个要素进行讨论:首先,不能认为这里的法的概念与规范评价无关:“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措辞。为了解释和描述所要评价的现象而对法的概念进行的阐释是法律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23]其次,法的概念可能包含政治意义。法官、法律学者、相关官员,或更广泛的公众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在不同的国内体系中有所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在全球治理这一充满多样性的领域非常显著。有些人言论上赞同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但在他们的实践中却并非如此,比如,一个法官可能在解释法的概念时将其与道德相分离,但在所宣布的判决中则会考虑到道德因素。[24]其他学者则可能赞同非实证主义者的法律概念,如由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所发展而来的观点。有些学者从政治理论中推理出法的概念,还有一些从其他的理念中演化出法的概念。这些态度所做出的选择是一个拥有政治意义的政治性选择。试图在可行的法的概念上达成一致,或至少在某些竞存的法的概念中寻找到重叠之处,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没有一个唯一的代理者能够决定性地为实际目的而解决这个问题时,即使这只是临时性的。[25]再次,将国际行政法理解为“法”不仅涉及到效力问题,还涉及到规范的重要性问题。鉴于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在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关注的是有效和无效,或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的问题,则全球治理领域内规范和机构高度等级化的缺乏,以及在多数情况下决定上述问题的权力机构的缺乏,意味着国际行政法中的实际问题通常涉及到规范和决定的重要性问题。法律是一种社会习惯,在国际行政法中涉及到的这一特定的社会习惯中,效力和重要性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一个有意义的国际行政法的法概念必须对两个问题都进行阐释。
在前述对国际行政法理解中所蕴含的法律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对新兴的国际行政法做一个界定。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法律体系现在要做出精确的界定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笔者尝试在宽泛意义上对其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国际行政法是指有关全球治理实践中实际存在的跨国或者国际性行政权力行使的法律规制,是全球治理法治化的表现。此概念和全球治理概念相连结,强调全球治理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的性质,并且强调其规制对象是任何和跨越国家的或者在全球层面上行使的规制权力,但也并不排斥早期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国际行政是国际组织内部对其雇员进行管理的活动这种观点,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语境下来讨论国际行政与国际行政法问题,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前者:把全球治理作为国际行政行为来理解,并试图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进行某种层面上的有效的问责与监督。国际行政法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特色的法律体系。相对于国内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脉络相对清楚,①国内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基本上脉络是比较清楚的,大体分为:行政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行政主体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诉讼关系等。国际行政法所调整的国际行政关系异常复杂,呈现主体、形态的多样化特征,这种规制型行政既可以是一个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或机构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比如WTO争端解决机构(DSB)针对主权国家之裁决,也可以是由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或机构直接对私人实施——比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对难民身份之认定以及对难民营的管理,甚至可以是一个私人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来实施——比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大量的世界范围的产品和方法体系的标准直接影响了全世界大量公司法人的权益等。
关于国际行政法的定义与内容在国际上存在着争论,在术语表达上也有分歧,在英文中就有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与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两种表达方式,金斯伯里教授采用的就是后者,中文译为“全球行政法”。笔者则倾向于前者,采用国际行政法的传统表达方式,因为在中国语境下,全球通常是在最高、统一的层面上运用的,使用全球行政法、世界行政法在中文语境下容易引起歧义,使用国际行政法的提法一来体现了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二来更精确的阐明一些分散性行政,比如国内当局的涉外行政等。后面在论述国际行政法的规范构成时,从空间层次来划分,笔者认为国际行政法由世界行政法(全球行政法)、区域行政法(比如欧盟行政法)以及一个国家的涉外行政法三个层次构成,由此,笔者认为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国际行政法)是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全球行政法)或World Administrative Law(世界行政法)的上位概念。
四、结语
“国际行政法”并非所公认的现行法或拟议法的一部分,相反它涉及非正式的制度设计,很多涉及到非国家主体的突出地位以及其他规范性实践的渊源,这些都不包含在传统的“国际法”理念中。所以,在全球治理语境中讨论的规范性实践已经超出了“国际法”的渊源。国际行政法这个术语可以用来形容一系列具有共同点的规范和由规范指引的实践做法,它们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具有强制性,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地位,即使他们显然不是国家法或常规的国家间法律的一部分。和晚近备受争议的“国际经济法”概念相类似,“国际行政法”所体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分类,在实践中摒弃国内、国际的二元对立,所以“国际行政法”不仅仅是国际法。国家与个人不能是同一个法律系统的主体,这是法律二元性的概念基础。根据此二元性,“国家内部有国内法,国家之间有国际法。国内法的主体是个人,国际法的主体是且只能是国家。”[26]笔者所定义的“国际行政法”或者“国际行政空间”试图打破传统的国际、国内二元对立的结构,全球治理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的内涵,因为私人主体一方的参与(尽管可能是被动的),并且权益受到了跨国或国际规制机构直接的影响。应该承认,这种界定和尝试在学理上肯定存在较大的争议,但笔者相信将能经得住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及学术史发展的验证。
[1]See Daniel C. Esty,Good Governance at the Supranational Scale:Globalizing Administrative Law,Yale Law Journal,2006.
[2]林泰.论国际行政法概念之重构[J].兰州学刊,2010,(6):126-129.
[3]〔美〕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等.全球行政法的产生[J].范云鹏译.环球法律评论,2008,(5):119.
[4]See C.Wilfred Jenks,The Proper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1963);Soji Yamamoto, Kokusai gyoseiho(InternationalAdministrative Law), in SHINPAN,GENDAI KOKUSAIHO (NEW EDITION,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LAW)251-66(Shigeru Oda et al., eds., 1986).
[5]Vogel,‘Administrative Law:International Aspects,’ in R. Bernhardt (ed.),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1992)22, at 23.
[6]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 ‘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ILJWorking Paper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7]See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ILJ Working Paper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8]See Malcolm, Hobbes’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Malcolm, Aspects of Hobbes (2002),at 432-456.
[9]See Gauthier, Hobbes:The Law s of Nature, 82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2)258.
[10]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 ‘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IILJ Working Paper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11]SeeH.L.A.Hart, TheConceptofLaw (second edition),edited by Penelope A.Bulloch and Joseph Raz, Oxford:Carendon Press,1994.
[12]SeeH.L.A.Hart, TheConceptofLaw (second edition),edited by Penelope A.Bulloch and Joseph Raz, Oxford:Carendon Press,1994.
[13]Kingsbury, Legal Positivism as Normative Politics, 13 EJIL (2002)401.
[14]See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 ‘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IILJ Working Paper 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15]Kingsbury, International Law as Inter-Public Law, in H.Richardson and M.Williams (eds), Moral Universalism and Pluralism (2009),167.
[16]Cassese, ‘Administrative Law w ithout the State:The Challenge of Global Regulation’, 37 NYUJILP (2005)663.
[17]See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IILJ Working Paper 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18]Kingsburyetal.,Forew ord:GlobalGovernanceas Administration,68:3-4Law&Contemp Probs (2005)1.
[19]See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IILJ Working Paper 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20]Kingsbury, Weighing Global Regulatory Decisions in National Courts, Acta Juridica (2009).
[21]Kingsbury, Krisch and Stew ar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68:3-4 Law&Contemp Probs (2005)15.
[22]See Krisch and Kingsbury, ‘Introduction: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17 EJIL (2006)1, at 10.
[23]See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 ‘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IILJ Working Paper 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24]See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Law’in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IILJ Working Paper 2009/1 available at http://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9-1.GAL.Kingsbury.pdf.
[25]See Murphy, ‘Concepts of Law’, 30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 (2005)1 and Murphy,‘Better to See Law this Way’, 83 NYU Law Review(2008)1088;and Harlow,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The Quest for Principles and Values’, 17 EJIL (2006)187.
[26]Stefano Battin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Subjects:A Move Tow ard A GlobalAdministrative Law?, IILJ Working Paper 2005/3, available at http://w w w.iilj.org/publications/documents/2005.3Battini.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