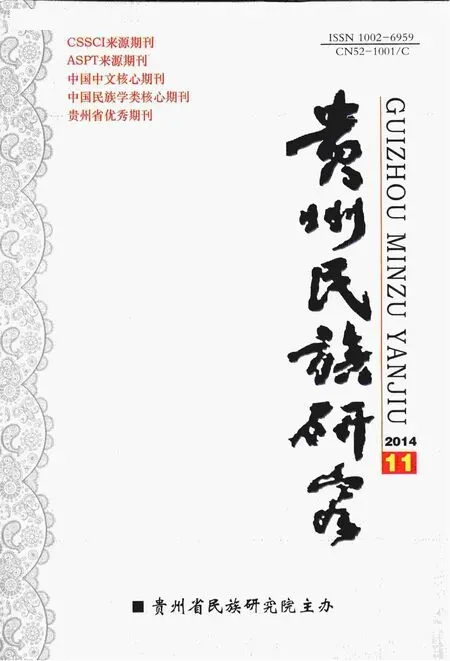群体交往与社会网络的建构——以打同年为例
2014-12-03徐赣丽
徐赣丽 彭 晔
(1.华东师范大学 民俗学研究所,上海 200241;2.广西环江中学,广西·环江 547100)
风俗的力量历来为国家所重视,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指出,“相对于广土众民的国家规模,中央为控制地方所投入的资源,特别是强力机构的配置,非常有限”[1]。对于地方上的管理,“控制的方式大半是靠意识形态、风俗、道德素养之类”[2],而不是诉诸武力。如果说,汉族地区的地方管理主要依赖风俗习惯,更为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则更是如此。如广泛流传在苗、侗、壮、瑶、汉等民族中的一种集体交往习俗——打同年,具娱乐、婚姻、结盟等多种功能,可视为地方民众为自我生存而创造出的民间智慧。
对乡村社会交往的研究,大多数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分析人际交往中的社会结构,多为宏观和理性化的分析,注重族际交往或个体之间的交往,而对于群体之间的交往不太关注,对边远地区的村寨广泛存在着的村际交往活动更少研究。笔者十余年的田野调查经验发现,集体交往习俗的产生是为了联合地方力量,扩大自我实力,形成资源网络,在国家层面管理不足或不到的地方,建立自我保护、自我管理的机制。少数民族在有限的环境中获得生存资源构造地方社会,形成了自己本民族内部独特的文化体系。打同年作为缔结村寨的姻亲关系和村寨之间地缘关系的媒介,显示了地方社会民众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策略,展示了地方所拥有的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文对此加以讨论。
一、打同年习俗的分布、由来与内涵
中国人很早就有结拜的传统,多以歃血盟誓,建立拟亲属关系。《广西通志·民俗志》提到广西壮、汉、瑶、苗、侗等民族都存在形式基本相似的结老同习俗,谓打老同对增进团结、解决纠纷有重要的作用[3]。各民族对“打同年”的称谓虽有所区别,但其活动内容和目的都大同小异。这种民间交际礼仪,分个人与集体两种形式。个人打同年似结拜兄弟姐妹,集体打同年类似现在的结对友好村寨。集体仪式多于每年正月或农闲时举行,是以团队形式进行的村寨间的歌舞展演或比赛,既神圣又具有娱乐性[4]。而其中,以普遍流传于黔桂等省(区)的融水、龙胜、三江、榕江、从江、桂林、柳州等县市的苗族、侗族中的村际打同年,最为隆重而意义重大,最具代表性。苗侗村寨打同年是在春节期间一个村寨向邻近的另一个村寨赠送礼物、两个村寨杀牛祭祀并进行同年宣誓,然后一起娱乐(芦笙踩堂、聚餐、坐妹、对歌等)的习俗,是一种集娱乐、婚姻、结盟为一体的民俗活动,会引发两寨之间的各种礼物、金钱、人力、人员等的相互交换,使双方结为类似于亲属关系的同伴关系(当然,通常打同年的村寨不限于一村与另一村之间,而可能是一村与多村之间,本文为了方便,仅以两村之间打同年为示例)。打同年活动之后,日常生活中两寨之间的互惠交换、互助交往,使基于地缘和姻亲关系的跨村联盟得以产生。
关于打同年的由来,苗族传说古时“映央”和“作耶”为促使双方男女青年婚配而发起打同年[5],这说明其最初缘起更多是为了给青年男女制造交往机会,并最终缔结姻亲关系;但其实在许多地方不止于青年,全村老少都可以参加,除了两村结为友好兄弟村,参加活动的每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结交个体的同年朋友。又有人认为,打同年是“集体联谊”或古代“村寨结盟”的残存[6]。特别是在1949年前,为了防御匪患和反抗官府的压迫,各地均打破民族或村寨的界限,共同组成联盟,由民间社会逢难互助的“古教遗风”,逐渐发展到娱乐习俗。[7]这都说明,打同年主要目的是结交。
苗侗村寨打同年在各民族中最负盛名,其活动分邀请、转牛、会餐、送礼四个阶段[8],每个阶段都具仪式性,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传统。邀请环节,注重的是双方的资源和能力的相当,即婚配对象之间的“门当户对”,这也为结交提供合适的条件。杀牛告祖,以牛肉待客,显示其隆重而郑重。踩堂和吹芦笙,是借助舞蹈和音乐形式进行表达和交流,同时,也制造欢乐的气氛。送礼和礼物交换,是以物为载体传达情谊,也为仪式提供了必要的意义和物质。通过打同年,双方在节日仪式场娱乐共庆,在日常生活领域互助合作、互惠交换。这也是此俗在许多地方长盛不衰的原因。
二、打同年:寻婚恋对象建构姻亲社会网络
通婚对强化社会关系有突出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指出,不同群体之间的通婚是社会交往的最高形式,它成为衡量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敏感指标[9]。
法国人类学非常重视对通婚的考察,研究不同群体的社会纽带如何形成、社会构成原理等问题。他们认为两性之间的交往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机制,不同群体的结合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而群体结合的最初纽带正在于两性之间的通婚行为和关系[10]。列维-斯特劳斯提出,居于不同地域的两个集团通过相互提供新娘而形成一种联盟关系”[11]。这在我国也是如此。
在我国西南地区以打同年为媒介的村际交往中,通婚率的高低是衡量两寨关系是否亲密的重要指标。不同村寨打同年,既可能是同一民族,也可以是不同民族,但打同年的对象往往决定通婚范围。在本民族之外,苗侗通婚最为普遍[12]。因为,苗族侗族之间文化认同度高,打同年多,结亲多。
1.个体婚姻缔结的媒介
受交通、语言、婚育观的制约,很多民族村寨的通婚圈局限在本村,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环境中,村内婚是保证人口繁殖和族群延续最常用的手段;但村内婚的长期延续需要人口众多的大规模村落的支撑,这样才不至于造成近亲结婚而影响人口质量和素质,因此,村内婚这种婚姻制度无法长期实行。简美玲发现:“村寨内婚倾向双边、平等互惠形式的女人交换,村寨外婚倾向单边女人交换,……村寨内婚的双边形式,有可能是为了巩固小范围、封闭、互惠、平行往来的婚姻市场,而跨村通婚可能开放一个出口,扩大婚姻市场。以女人去的方向,不同于来的方向,有限度扩大婚姻的交换圈。……跨村通婚……有积极促成广泛人群互动的特征。”[13]由此看来,村内婚普遍将女人作为交换砝码来看待,而村外婚则扩大了婚姻视野。具有长期村内婚历史的少数民族村寨急需拓展可信任的村外婚空间,来弥补村内婚造成的缺失或预防村内婚潜在的危险。
村寨之间的集体交往活动有缔结姻亲的目的。打同年在相对封闭的传统少数民族社会为未婚男女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提供自然的、适合的交往机会。打同年创造了不依靠媒人的、自由愉快的男女交往;除了充当“媒人”角色,打同年还作为一种“掩护”手段存在。同年寨的年轻人的结合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参加活动的男女青年一般会先在同年寨找一个同年,然后平时会借“走同年”的幌子经常到同年寨了解和接触自己心仪的对象。男孩考察女孩的持家能力、歌才和绣染水平等,女孩考察男孩对农事的熟练程度、人品好坏、勤劳与否等等,相互了解之后才会结婚。仅就打同年促使男女青年结合来看,打同年“制造”了多次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对方的可靠的“相亲”。对此,有人说“其实打同年说白了就是为了解决年轻人的婚姻问题”。
许多苗侗民族地区的人们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就是姑娘应该嫁在本村或邻村,嫁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汉族聚居村就太远了,是大逆不道,既不能照顾老人也不能协助家人干活,而且那些地方的人也让人难以信任。在当地人“姑娘不远嫁,不嫁不可信者”观念影响下,打同年被视为开辟更广阔通婚空间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前,由于交通落后,缺乏对外面村寨的了解,适龄女子不是嫁在本村就是嫁在邻村,而对于她们来说相对熟悉的、不近不远的同年寨的适婚男子,既有新鲜感也有安全感,他们自然成为适龄女子结婚的首选目标。打同年促成婚姻的缔结是无可否认的,一位被访者反映“打同年结婚的有蛮多的啊,我三嫂和四嫂、我姐都是通过打同年结婚的啊”,婚配结对数目一度成为衡量一年一度打同年成功与否的量化标准。
2.姻亲联盟形成的基础
苗族或侗族的社会交往是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基础的,在相同半径的地域范围内,文化认同一致的血缘关系在其社会交往中处于优先地位;血缘的先赋性以及村寨聚族而居的状况,使血缘关系在当地起着重要的情感维系作用。人们在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占据社会资源,会给自己编织一个模拟家族关系网并且把关系较为密切的人都纳入其中,并不断扩大这个关系网,以成为自己的支柱或靠山。打同年既可以弥补历史上两寨内部长期实行的村内婚的不足,解决长期村内婚可能产生的人口质量问题,又可以开辟可供选择的结婚对象的广阔空间,与同年寨建立起亲密的亲属关系网。
打同年作为一种村际交往活动,可以提供可信赖的村外婚对象,为村外婚的形成创造条件,促进了同年寨的联合,从而打破了村内婚的历史。婚姻缔结是村际得以联合的最主要手段,它使两村内部由于村内婚形成的婚姻圈连通,在姻缘关系的支撑下,血缘关系得以诞生。依靠姻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形成的跨村亲属关系网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可依赖、可信任的跨村亲缘联盟,形成跨村亲属关系网。相比起村落内亲属关系网来说,跨村亲属关系网是更加广泛、抵御能力更加强大的关系堡垒。这种以姻缘为连接点、以血缘的扩大为表现形式的通婚中,也是一种跨越村际的宗族互助形态,这种宗族互助是协调资源均衡的有效机制。正如王铭铭所说,“中国的乡村传统里面,地方性的协调机制是存在的,且居主导地位。家族之间的通婚也可以造成大量的社会互助资源。……由于通婚形成一种超家族的联网,这一联网制度化以后可以转变为超村落的地域。”[14]打同年是当地普遍存在的强化人际关系的社交习俗。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得社会资源,打同年扩大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超越村寨边界约束的社会资本,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强化社会人际关系的保障。这种“化邻为亲”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侗族、苗族的结群策略。
有人调查贵州东部苗族的婚姻习俗时,发现当地人择偶倾向于外村靠近集镇附近的,认为“这样的话,到处有亲戚,亲戚越多,门路就越大,人家就觉得你家亲戚多,家族大,也能让我的弟妹以后做事方便”[15]。这显示了当地人以婚姻缔结来扩大社会网络,获得社会资源的目的。朱炳祥在研究血缘、姻缘与地域性社会构成时提出,“女性的交换”提供了地域内各集团之间的机械整合,因它仍然维持着各宗族之间的边界;“男性的交换”则使地域内各集团间得以实现有机整合,因为宗族边界发生模糊,宗族意识逐渐淡薄,随之形成的则是各宗族关于地域共同体的“集体意识”。[16]打同年这种方式,既有女性交换,同时也因为有拟亲属(“同年”即结拜的兄弟姐妹)关系的建立,形成了不同村寨不同宗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盟,使各集团之间实现有机整合。
不同于现代城市通过法律和契约来保障信任,农村的信任机制主要依靠血缘关系支撑,跨村联姻是保障彼此信任的重要手段。地方社会的有效运行得益于亲密而频繁的人际交往,团结统一、稳定发展的地方社会的创建,离不开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虽然苗乡侗寨在农忙时节,会较多的求助于地缘关系形成的群体,地缘关系网能够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会有“远亲不如近邻”一说,但毕竟农村依然是并将会长期是一个重视宗法制的社会,地缘关系在少数民族村寨很难独立地成为强有力的凝聚手段。中国人自古以来所信任的人群一向以血缘姻亲为主,信任在农村社会是一种重要资源,亲属关系造就了这种资源。亲属关系是被血缘消解了信任危机的、基于亲缘关系建立起可靠的联盟,是获得生存资源的重要途径。“信任”是一种依赖亲属间互动交流的机制,交流越频繁,越可能对对方产生稳定的预期,信任度也越大,由亲属、同年、普通朋友组成的人际关系圈中,从内向外,随着互动频率的降低,信任度也依次降低。偏远山区的苗侗民族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打同年来创造人际间更多互动的机会,血缘亲属之间的互动为村民建立了最基础的归属感,也给他们的生存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人们很注重建立血缘关系,村民间的亲密关系往往靠血缘来维系,基于婚姻家庭建立起来的血缘亲属关系,是传统乡村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它决定乡村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也决定着该地的生活方式。
从两村打同年的历史来看,由于前期以婚姻为主要目的,哪怕现在两寨之间婚姻配对数不多,但只要曾经存在过村内婚和两村通婚,在村内婚形成的亲属网的协助下,就必定会形成两个村落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具有血缘关系的两村联合体。在两村形成的跨村联盟之中,亲属关系已经从村内延伸到同年村,扩大了亲属关系网的同时也形成了两村稳定的信任机制,保证了地方社会的情感基础,从而生成了一个以亲情为基础的可信赖的地方社会。正如齐美尔所说,婚姻本身也在丰富和扩大利益关系[17]。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接触外界的机会越来越多,同年寨之间婚姻的缔结已经不是打同年的重点目标,他们更加注重以此形成亲密的人际关系从而寻求更多的社会资源。
三、打同年:行村际交往构建地缘社会网络
通婚是打同年潜在的动机,村际交往才是其最本质的特征。村寨之间的打同年将周边村落纳入发展计划中,跨越村界实现人际交往圈向周边村寨延伸,通过与同年寨创造亲密安全的同盟关系来规范整合一方社会。
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不流动性促使邻近村落之间进行跨地域的交往,注重与相邻地域的联合,以扩大自我发展的空间,并形成地缘共同体社会。苗族或侗族的打同年,是在环境和资源双重压力下生发的改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活动,是在集体主义指导下的民间文化交流。打同年在空间上和心理上都拉近了两村的距离,有助于亲密的社会关系的生成;通过村际间的社会交往形成的同年关系,是一种频繁互动的社会关系,基于此产生的拟亲属关系网络,也是一种可信赖的地方社会关系网。
从农村社会的农业生产模式来看,打同年是实现人际关系亲密和谐的有效措施,农村比城市更加依赖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助合作生产。农村的农业(包括林业和建造房屋)生产活动是很难在一个家庭内部独立完成的,需要通过换工互助来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农业生产,这就使农村社会形成了不同于城市的、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地缘关系。此外,缔结村寨同盟也是人们面对兵、匪、官、自然或人为灾害等未知变故时可以获得的外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社会越来越开放,他们要应对以前茫然不知的外部世界和新的生计方式,也需要借助更多更广的社会关系资源。
打同年是当地人在应对环境压力时对民俗文化的成功运用,是对集体主义观念的有效践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侗寨苗乡偏远的地理位置使他们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压力越大,就越依赖于集体。为了避免同一生态区内部的各群体相互竞争,他们就组织联合成较大的群体对内进行合作创造资源,向外与其他群体争夺资源,这种集体化行动是当地侗族苗族的生存策略之一。因此,他们一直都很重视与周边社会群体的交往和结交,形成了互助合作的传统,升华出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村落合作”理念,各个群体结群的有效策略,是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互动的基本方式,它构建了超越户际、跨越村界的生产合作共同体。以打同年为桥梁形成的侗族、苗族地方社会,组成了以村寨间互助关系凝结起来的生产共同体,跟个体结拜不同的是,它是一种融合了个体和群体的混合型交往。打同年是一些少数民族特有的社会文化,这种地域共享的民俗文化被当地人作为一种调适策略来应对环境的挑战,在化解环境恶劣、资源不足等生存困境时得到充分突显。
除了环境这一客观因素的推动,打同年本身体现的人人平等的观念也让两寨之间的地理界限模糊化,加强了跨村交流与合作,全面地协调人际关系、户际关系、村际关系,实现了人与人、户与户、村与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合作生产、交换资源、交流经验等等,产生了除亲属关系网之外的、可供信赖的社会关系网,创造出和谐统一的村寨统一体。
社会网络学派代表齐美尔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认为社会是相互之间有多重关系的单个的人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网络,这些单个的人处于经常的相互作用之中[18]。帕特南认为,人们的社会交往网络对于构建社会资本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在人们相互之间形成密集的交往网络的基础上,他们相互之间才可以形成普遍的互惠规范和建立起广泛的信任[19]。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关系发展的基础,有关系网络才能形成互惠的社会规范,才能建立广泛的信任合作。打同年这种社会交往过程事实上就是两个少数民族村寨之间社会关系网络不断确认和强化的过程,是社会规范信任合作逐步建立和稳固的过程。在“节日打同年”活动开展之后,人们还有日常的同年交往实践,关系网络和社会规范呈现为一种递进的状态,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民间社会交往不断深入,实现关系良好的村寨联盟的建构。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姻亲和地缘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但以地缘关系建立的地方社会网络和以血缘关系生成的地方社会网络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甚至是相互转化的。第一,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都是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组合而成的社区,血缘关系固然是传统农村社区稳固而安全的关系,但当血缘关系不足以满足村寨建设对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需求时,人们就会冲破村界内血缘的束缚,开辟村界之外的亲属关系和拟亲属关系,建构新的社会网络,谋得新的社会资源。打同年促成了同伴关系(包括村际、家户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同年关系)的缔结,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进一步促成婚姻的结合,实现非血缘关系的群体向血缘关系群体的转换;两者的转化使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结合,使亲缘关系扩张伸展,使互助责任化和义务化;同年关系建构模式,也是当地苗(侗)族地方社会的一种综合地缘性和血缘性的传统规范。第二,苗(侗)人通过打同年实现跨村交往,既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农业生产为目的的跨村户际联盟、跨村跨户团体,也形成了以婚姻缔结为目的而衍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跨村联盟,跨越村界的个体结拜、户际结盟、血亲联盟,都是地方社会运行的基本单位,三者之间重叠交叉,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最大的“机构”和“组织”——村际联盟。在基于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建立的村际联盟内部展开的农业生产互助协作、人力物力互惠交往,这些长期的频繁互动不仅反过来维持和再生产了村与村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同时也是对同伴之间相互权利与义务的确认,维系和加强了地方社会的秩序。
村际打同年的存在使同年村之间存在多种关系网。哈贝马斯在研究社会交往的功能时提出:“从协调行动的角度来看,交往行为起着社会整体化和创造团结互助的功能”。[20]因此可以说,这样一种社会交往习俗,其实是缔造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机制。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和维系的纽带,利用本民族文化对族群成员所面临的困境和矛盾进行调解,从而达到生存的安定与和谐,是少数民族化解生存危机常用的方式。打同年充分体现了苗侗等民族人民的生存智慧。苗族和侗族都是迁徙民族,生存资源缺乏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们衍生出了“自尊、自立、自适”的生存哲学,让他们掌握了“联合与己相似的共同体,互换互惠,共同抗压”和“选择共同性的、根基性的文化,建构双方认同”的民间智慧。打同年反映了苗侗人民的结群策略、结群理想和文化策略,这不是应时性的策略,这是长期以来苗侗人民应对自然和社会压力所作出的选择,是一种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表达了苗侗人民对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的塑造的积极而主动的实践。
[1]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A].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66.
[2]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0.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M].南宁市: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192-194.
[4]叶春生,施爱东.广东民俗大典[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高占祥.中国民族节日大全[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453.
[6]杨开春等.侗族风情与习俗[A].从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从江县志资料汇编[C].1985.
[7]从江县志编委会办公室.从江县志[M].1999:732一745.
[8]高占祥.中国民族节日大全[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453.
[9](美)彼得·布劳.不平等性和异质性[M].王春光,谢圣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唐利平.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J].开放时代,2005,(2).
[11](日)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M].周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23-125.
[12]吴承德,贾 晔.南方山居少数民族现代化探索——融水苗族发展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13]简美玲.贵州东部高地民族的情感与婚姻[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223.
[14]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5-26.
[15]曹端波等.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婚姻、市场与文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2.
[16]朱炳祥.继嗣与交换:地域社会的构成-对摩哈苴彝村的历史人类学分析[J].民族研究,2004,(6):39.
[17](德)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96.
[18]科 塞.社会学思想名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
[19]胡 荣,胡 康.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20]艾四林.哈贝马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