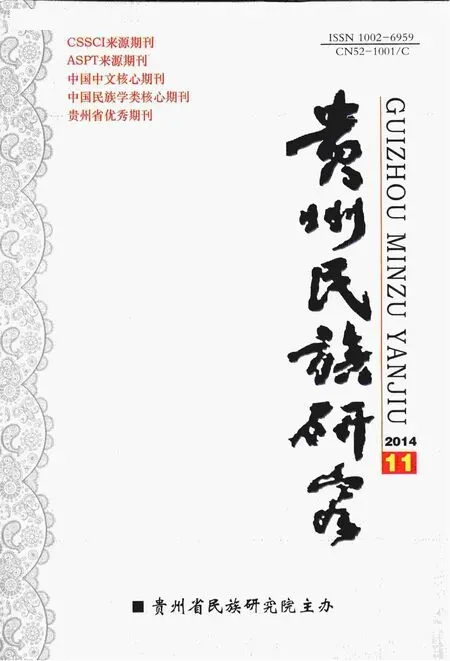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研究
2014-12-03曾静
曾 静
(四川农业大学 林学院,四川·雅安 625014)
一、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现象
少数民族元素设计是以可视的艺术形式为基础,透过对少数民族符号的造型活动来传递特定信息的视觉设计行为,由于包含着少数民族历史沿传下来的具体形象与无实型的精神内涵,因此需要通过民族文化迁移来施加对传递对象的心理影响。文化参与在民族元素设计中尤为常见,一般从审美感知的角度来审视文化信息的视觉识别效果,针对文化参与的受众交互性考察甚少,即少数民族元素设计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局限于感官吸引范畴,容易造成视觉传递的文化模糊性。例如哈尼族的手工纸包装设计融入哈尼族的梯田波浪元素,就设计的可行性上来说似乎无可厚非,从中亚到中东以及近东地区,“世界范围内的手工纸包装设计均采用梯田元素来区分产品与动力机械造纸的不同”[1],但这仅仅是对产品概念的反映,并没有起到民族文化输出的传播效应,相反壮族手工纸包装的“龙脊梯田”设计将梯田符号与壮族独一无二的“龙脊纹”相结合,以“龙脊纸”的噱头脱颖而出,击败了拥有世界著名梯田景观的哈尼族造纸工艺,成功占领市场。“梯田纹”与“龙脊梯田纹”虽然感官体验不一,但均具备审美设计的功能表现,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民族文化输出是模糊的,后者在对壮族“越城岭”山脉的摹状之中还暗含着中华民族龙崇拜的文化神韵,可见人们对民族元素设计具有一种稳定的心理期待,即要求元素应用不仅要满足图案、线条、肌理形象等直接的、群体表象性的感官愉悦,“还应折射整体关联的、非逻辑性、用于意象体验的情志心理”[2],推动视觉传递过程中文化迁移现象的发生。
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迁移现象是发生在本体与受体之间的文化转移,即通过元素造型将特定民族的思想观念、经验技巧、审美情趣、礼仪习俗等文化特质移植到设计对象之中,促成不同文化受众间的相互沟通,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迁移都是有效的,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现象亦有“正迁移”与“负迁移”之分。国内学术研究领域对文化迁移的判断并不明确,通常用“文化关联性不足”来一言蔽之,实际上我国少数民族元素设计最常见的问题不是文化关联性不足,而是“对文化关系的处理存在信息转换故障”[3],例如现代室内装潢喜好运用民族元素来做装饰图案,诸如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傣族雨伞图案等民族元素的设计应用不可谓不多,但具体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使用效果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例如灯罩设计,采用纳西族服饰的袖口图案来做灯罩口的环形装饰,以“霓裳”寄寓“霓虹”传达出的文化美感远远超过当前设计领域对纳西族象形字符的跟风。因此少数民族元素设计并不存在文化关联性不足的问题,而应考察文化信息的迁移衔接是否得当,对于某些设计来说,不当的文化关联性所引发的破坏效应能使产品形象一败涂地。以现代商品标志设计对少数民族图符的仿拟应用为例,中国联通公司为了突显通信与通心的相关性,其商品标志设计专门对我国藏族佛教文化中的佛心造型进行改造,总共采用了三组藏族“佛心”图符,将它们拼接成相互交错、首尾呼应的“佛莲心”形象,“‘佛’又与‘户’谐音,寓意通心服务,为用户着想”[4],此乃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文化正迁移的代表。同样都是对藏族佛教文化图案的摄取,国内某家烟草公司将藏族佛教文化中象征婉柔敦厚、静谧开放的“卷草图案”用在香烟包装设计中则是文化负迁移的表现,藏族佛教文化中“卷草”是“宝相”,将“卷草”与“烟草”硬性联系,是以“普护众生”的宝物去指示对身体有损的烟草,不仅有失敬畏,其语义表达的矛盾还会造成两相冲突的混乱体验。因此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必然是发生在介质交互的和谐融洽状态,这样才能产生如实的沟通引导效能。
二、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方式
少数民族元素设计要尽可能触发文化正迁移、规避文化负迁移,其基本途径是文化定位,然而至今为止,我国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定位研究始终没能与主流元素设计的文化定位区别开来,相关文献在把握人、设计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通常以地域文化为标准,实质上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现当代少数民族元素设计多出现在商品行为之中,地域文化与地域消费紧密联系,使用地域符号代替民族符号的设计行为容易造成本体文化定位与受众文化定位的歧义,导致文化负迁移现象的发生。例如苗族服饰领口的“井”字纹是对苗族地域范围内生态布局的模拟,如果“井”字纹出现在瑶族服饰领口,则被认为寄托着瑶族水崇拜的民俗文化内涵,当“井”字纹出现在藏族服饰领口,则会指向藏族袈裟文化,可见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地域文化定位会随着受众身份的变化而迁移,引发与设计主体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理解,而采用民族文化定位方式则可有效地回避该问题的发生,例如苗族服饰的蜡染图案与针点刺绣元素代表着苗族特有的工艺水平,即使应用于其他地域也不会失去专属的文化传播功能。
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定位是为了建立文化主体与文化受众之间的联系,因此少数民族元素的提取过程具备了对设计主体的文化感知,那么受众方的文化感知程度要不要考虑呢,又该如何进行考虑呢?现行研究领域较多认为受众方的文化感知是被动发生的,主体文化的设计中已经包涵着受众方的感知期待,笔者则认为即便如此,“人类对有机世界的认知边界仍然在不断扩大中”[1],民族元素拥有稳定的历史延续性,促使民族元素焕发生机的除了元素本身的文化生命,还有赖于对民族元素所承载的知识话语的开发、更新,不断推动文化受众方的认知边界拓展,因此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迁移应具备对时代特征的反映、对交叉学科的融合,以及对平面、空间、语意表达的多元嫁接,促使人们能够通过古老的民族元素“打开一扇了解与接触现当代艺术的窗口”[5]。例如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陶瓷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正赶上90年代人本主义设计思潮的兴起,以往商品标签设计中的微缩陶器元素被全部拿掉,取而代之的是陶瓷未完成状态下的“泥料”、“釉胎”、“火花”等线条勾勒,突出制瓷过程的人工力量,从“瓷巧”到“人巧”的视角转化,带出了对艺术从业者、无名创作者的生命关怀,由此响应与满足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崭新艺术观。
除此之外,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正迁移还与艺术的表现力度有关,具体指向如何提升民族元素应用的情绪感染力与精神号召力,情绪感染力是艺术表现所容纳的认知兴奋点,精神号召力则旨在达成文化主体与文化受众之间的价值契合,促使后者从设计中获得社会认同。例如白族女性饰品设计的拟形取材,“以衣衫垂下的穗子象征下关风,以白色的流苏帽沿象征苍山雪、以月牙耳环象征洱海月”[6]等等,寄寓云南人文景观的“风花雪月”之意,其浪漫的民族情怀、对美好容颜的暗示顺利打开了女性审美的兴奋阀门,而“纳西族披肩的‘七星’元素设计通过隐喻纳西族妇女披星戴月、勤力劳作的意志品性与道德情操”[7],有效衔接民族价值观,促成文化受众方的社会认同体验。可见,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正迁移不仅表达了设计思维的契合,还反映了人们对优秀艺术品格的主体选择性,因此在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迁移现象暗含着文化竞争的成分,文化信息的可辨识性、表现形式的合理化、视觉美感的赏心悦目、作品立意的高远格调都会左右受众方文化选择的结果。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论指出,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源于文化、超越文化,因为人类实践的艺术表现力不断地在挑战自我、发明新形式、释放想象力,正是由于民族元素设计的艺术发展表征,才使得传统文化的说教、僵化、实验性成分降低,具备圆融的生存能力,“从而脱离了历史政教范畴的严肃形态,焕发归真、觉醒与新生的鲜活生机”[8],辅助设计对象“尽物之性”。
三、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价值
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迁移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一般人们都会从经济的层面来思考文化参与的获益,但就视觉传达而言,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最直接的作用是“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大众文化品位”[9]。对此相关文献研究曾出现过重大分歧,即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与主流元素设计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度哪一个更显著?一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元素的价值系统与公共价值系统的差异较大,对于社会公共事件中的民心聚集更益于采用主流元素设计来进行文化自省,但从文化迁移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元素的最大特色是强调民族文化,而“任何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都能够丰富个体对‘小我’的认知”[10],民族文化中的身份代入感有助于人们看到文化与小我的关系。例如城市生活对“雅”的追求,采用城市主流设计元素通常会涉猎黄金海岸线、沙沙作响的棕榈树、午后咖啡馆等等突显生活品质的标杆式元素,但如果考虑应用少数民族元素则会呈现奇妙的化学反应,以云南少数民族的城市宣传为例,品位雅致生活中的“雅”转变为了云南成年普洱画青花的“雅”,并立足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善缘”来寄托人们对生活至善的追求,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11],少数民族文化中的隽永精神与心灵依存意味往往能促使社会公众从内心开始肯定人生。
设计行业没有文化类型的高低之分,安德烈·纪德曾说:“重要的不是目光,而是你看见的东西,它们是设计者对民族话语权的发声”[12],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迁移本质是民族话语系统的扩散,而文化迁移的结果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公众对历史的分享,并基于分享与交流的文化映衬共同成长、进步、升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迁移推动着视觉传达设计的理性发展,越是理性的设计氛围越能够吸纳与包容少数民族元素的异质性,其对公共文化的倡导也就越有力,原因并不是民族文化在倡导社会美德方面更有优势,而是因为少数民族元素的生源性知识结构本身便具有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西方知识管理学将人类知识结构分为基础系统与价值系统两部分,由于主流社会的知识系统变迁较为剧烈,基础系统(物质文化)常常与价值系统(精神文化)不在同一个层面,那些存在于相同层面的稳定性知识构成被称之为“生源性知识”,生源性知识越丰富的民族,其社会结构越稳定,民族文化积淀越深厚,文化迁移也就越顺畅,如果少数民族元素设计中的文化迁移不顺畅或发生文化负迁移现象,往往可以发现该设计体例一定存在着与民族生源性知识相悖或不相称的地方。例如汉族人在茶文化盛行的藏区推广茶饮料通常会遭遇拒绝,原因在于藏族茶文化的认知体系中没有“茶饮料”这一概念,藏族人喝茶就是吃饭,其营养学知识的归类也与汉族社会存在着明显差异。
可见,生源性知识结构是少数民族元素设计无法忽视的“场域逻辑”,它们渗透在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少数民族元素设计的文化迁移建立在对此类生源性知识的挖掘、改造与利用之上。在文化迁移的发生过程中,少数民族生源性知识按照设计者的知识提炼方式来创造价值,其社会服务职能表现为信息服务方式,文化迁移即是知识信息的迁移,“设计者对设计对象的知识捕捉、分析、重组、应用过程缔造了民族文化持续服务的动态过程”[13],生源性知识所代表的价值系统不仅能维系少数民族个体与族群之间的社群关系,还能以此为起点,形成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与传播体例,少数民族的乡村与原野是“散”的,但主流社会城市却是社群共融的“集合”,至今为止民族元素设计如何维持不同层次的社群关系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议题,但艺术的无限可能即在于此,而少数民族元素设计所创造的额外收获是,通过优秀的民族文化体验让人在万物面前保持恭敬之心。
[1]殷之明.民族元素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J].美术与设计,2012,(9).
[2]谭有进.平面设计的民族化表现[D].中央民族大学,2013,(5).
[3]欧新菊.论民族设计审美内涵的文化特征及表达[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9).
[4]姜在新.蒙古传统文化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贵州民族研究,2013,(6).
[5]刘 震.设计艺术批评客体的类型体系研究[J].艺术设计研究,2014,(2).
[6]张鲁凝.设计中的受众感知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12,(3).
[7]陈汗青.民族认同——设计文化民族性再阐释[J].艺术生活,2010,(10).
[8]孔凡康.民族元素设计的市场化应用探究[J].装饰,2014,(2).
[9]廖 曦.设计文化的现实意义[D].复旦大学,2010,(2).
[10]李龙生.设计文化的价值及其文化传播[J].理论与改革,2012,(1).
[11]常跃中.少数民族设计的价值和社会效应[J],民族研究,2011,(5).
[12]张 力.中国少数民族元素在视觉设计中的思考[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13]孙福民.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化进程与文化产业扩张[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