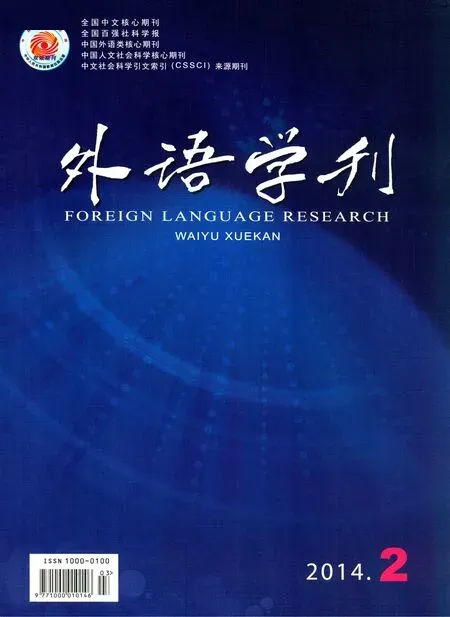我国文化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上)*
2014-12-03季红琴
季红琴
(长沙理工大学,长沙 410114)
我国文化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上)*
季红琴
(长沙理工大学,长沙 410114)
我国文化典籍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文化典籍外译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却有其基本规律。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主体在时代性中体现多样性,外译对象在选择性中体现丰富性,外译传播在世界性中体现区域性。
文化典籍;外译主体;外译对象;外译传播
1 概念厘定
《古代汉语大词典》(2007:325)将“典籍”定义为“国家重要文献”、“统称各种典册、书籍”,据此可知,典籍包含两方面的义项:一是法典、制度;二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汪榕培等(2009:1)将典籍界定为“中国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文献和书籍”,由此,典籍不仅包含文学作品,也包含医学、经济、军事、天文、地理、法律等诸多方面的作品。李致忠等(2004:3-11)认为,典籍是一种文化载体,是“人们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扬思想、宣传主张,经过创造编撰,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具备物质形态,同时又具备意识形态”,“典籍的本质是双重的,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又有精神属性的一面”,典籍构成包含3个要素:文字、完整而系统的信息记录、编连成册。
我国典籍数量繁多,据《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5日文章《我国典籍正在逐步整理出版》统计,我国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古籍约有8-10万种(汪榕培等2009: 1)。从我国典籍翻译与研究的成果来看,文化典籍所占比例最大。根据何其莘等对文化典籍的界定,文化典籍主要包含3个基本理念:(1)覆盖文史哲3科,兼顾儒释道3教,坚持开放与全球视野,尝试打通与贯穿的思路;(2)尝试以汉族文献为主,兼顾其他民族文献的多元文化格局;(3)以统一的文明史理念,确定典籍选材的上下限、重点以及思路贯穿的途径(何其莘 仲伟合 许钧 2009:2-4)。
2 我国文化典籍外译现象与规律
我国文化典籍外译现象和规律与整个汉籍外译现象和规律基本相吻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外译对象覆盖面广,几乎包含所有类型的文化典籍作品,如哲学著作、宗教文献、历史文献、社会学著作、语言学和艺术学著作、文学著作和其他社科类作品等;(2)转译现象较为普遍,尤其在外译初期,在未建立汉学或汉学不发达、或缺少汉语翻译工作者的国家和地区,转译现象较为常见;(3)外译形式多样,既有独译,也有合译:合译既包括本国人员的小规模或大规模合译,也包括跨国的合作与翻译;(4)外译方法和策略多样,既有节译,也有全译,整体而言,翻译方法与策略由节译走向全译,由零星散译走向集合型翻译,由偶然随意性翻译走向计划系统性翻译(马祖毅 任荣珍 2003: 21-23);(5)外译主体既有本国译者,也有外国译者,译者群体呈现多样性,外国译者以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为主,本国译者以海内外学者、翻译家为主;(6)我国文化典籍外译发展高峰与中西文化交流紧密相连,外译繁荣之时多为中西文化交流活跃时期。
3 我国文化典籍的外译
3.1 外译主体
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主体随着历史的发展具有动态变更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翻译主体。整体而言,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主体主要来源于4个方面:僧侣、来华传教士、国外汉学家、海内外华人学者等。
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之初,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时,外译主体多为来华外国僧人或本国僧人,如菩提流支、彦琮、玄奘等。
13世纪马可波罗远航来到中国后,不断有西方探险者和追随者来到中国,这其中就包括大批西方传教士。他们怀揣政治或宗教目的来华,在华期间认识到了汉语、汉学和汉典的重要性,遂学习汉语、研究汉学、翻译汉典,产生了一批较具影响的译者,如西班牙的高母羡,意大利的罗明坚、利玛窦、殷铎泽、卫匡国,葡萄牙的郭纳爵,奥地利的白乃心,比利时的柏应理、卫方济,法国的金尼阁、马若瑟、顾塞芬、蒋友仁,英国的理雅阁,德国的花之安、卫礼贤等(费赖之 1995)。
除了传教士译者,随着汉学在国外的兴起,还有一批汉学家和东方学家加入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活动中,如法国的宋君荣、雷慕沙、儒莲、 鲍吉耶、戴密微,英国的马克斯·缪勒、亚瑟·韦利、翟理思与翟林奈父子、戴维·霍克斯与闵福德父子,德国的福克、弗朗茨·库恩,瑞典的高本汉,匈牙利的杜克义,美国的赛珍珠、庞德、宇文所安等。
在我国文化典籍外译早期,华人译者不多,但却不乏优秀者,如晚清民初的辜鸿铭、苏曼殊等。此外,还有一部分协助国外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学者,辅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王涛便是典型代表。进入20世纪上半叶,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主体中华人译者依旧十分有限,但也出现了一批十分优秀的译者,如林语堂、贺敬瞻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华人译者异军突起,逐渐成为我国文化典籍外译的主力军,产生了一批在翻译界享有盛誉,对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译者,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刘殿爵、许渊冲、汪榕培、萧乾、叶君健、林戊荪、梁良兴、刘德友、李士俊等,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新生代的翻译家,如王刚毅、王复、江宛棣等。
3.2 外译对象
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主要围绕以下几类作品展开: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哲学经典;以佛教经书为主的宗教文献;以《史记》、《汉书》为重点的历史文献;以经典小说和诗歌为主的文学著作。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对文化典籍外译对象的综述将主要围绕前两类著作,后两类著作的外译综述将在“下篇”中集中探讨。
3.21 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
《四书》最早的外译本为拉丁文译本,关于此书最早的译者有两种说法,一说由利玛窦于1594年翻译但未出版,另一说由罗明坚翻译①,目前尚无定论。《四书》最早的出版译本来自殷铎泽和郭纳爵合译的《四书》拉丁文本,取名《中国的智慧》。1687年,白乃心翻译的意大利文版《中庸》以附录的形式在白氏的《中国札记》中出版。1687年,柏应理与欧洲耶稣会②士合作编译的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中文名《西文四书直解》③,该书是17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作最完备的书籍,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11年,布拉格大学出版了卫方济翻译的《四书》拉丁文全译本(缺《孟子》)《中华帝国经典》和《中国哲学》,之后被转译为法文。理雅阁的《四书》译本规范、全面,具有权威性,对《四书》的翻译与外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汉学家儒莲参考满文版本翻译过《孟子》。德国人卫礼贤翻译了《论语》、《孟子》(1916)、《大学》(1920)等。
1626年,由金尼阁翻译的第一个《五经》拉丁文译本在杭州刊印,成为中国经典最早《五经》西文译本。康熙年间,由于康熙推崇外传中国文化,鼓励传教士了解和翻译中国经典,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呈现繁荣景象。在此期间,《五经》被广泛地翻译与传播。《书经选》、《诗经》(第八章)被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翻译成法文,并入选《中华帝国全志》。《诗经》、《书经》、《礼记》和《易经》均被法国人宋君荣翻译成法文。《书经》也由蒋友仁翻译成了拉丁文。1838年,《诗经》第一本全译本在法国出现,该译本为拉丁文,由神父沙尔穆翻译。1872年,法国出现了第二部《诗经》全译本,全名《诗经,作为正统经典的中国古代诗集》,由汉学家鲍吉耶翻译,法国第三部《诗经》全译本出自顾塞芬, 顾氏精通汉学,翻译了包含《诗经》在内的多部中国文化典籍。此外,法国的孙璋将《诗经》译为拉丁文,取名《孔夫子的诗经》,成为欧洲的第一个《诗经》全译本,他还成功翻译了《礼记》。《五经》最早的德文译本出自弗·律刻特和维克多·斯特劳斯。前者根据孙璋的拉丁译本将《诗经》译为德文,取名《诗经·出自孔夫子的中国诗集》,后者的德文《诗经》译本为《诗经:中国经典式的诗集》,该译本被誉为欧洲最好的《诗经》译本。此外,克拉默和噶伯冷兹也分别于1844和1864年将《诗经》译为德文。1855年,《诗经》的第一部俄文译本由俄修道士西维洛夫完成,此后,王西里也将《诗经》翻译成俄文。
《五经》的英文译本出现较晚,18世纪晚期,语言学家威廉·琼斯曾将部分《诗经》译为英文,1846年,英国学者梅赫斯特翻译了《书经》,此后,直到传教士理雅阁的《五经》英译本出版,才有了全面、系统的《五经》英译本。1891年,英国传教士詹宁斯翻译了《诗经》并在香港发表,同年,阿连壁的《诗经》译本——《诗经:中国的诗集》也得以出版。20世纪,韦利首次根据《诗经》的内容翻译并编排了整部《诗经》,于1937年出版。高本汉的《五经》翻译不只停留在“译”的层面,更是拓展到了研究层面。1946年和1950年,他的《诗经注释》和《诗经》英译本分别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影响强烈。1950年他又完成了《书经译注》,并完整翻译了《书经》。英国翟理思与其子翟林奈也都翻译过《五经》。20世纪下半叶,《诗经》的翻译与传播从欧洲移到了美洲,美国汉学兴起。1955年,由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翻译的《诗经》在美国出版,该译本取名《孔子歌颂集》。1957年,匈牙利首次出版了《诗经》,同年,苏联也出版了两部《诗经》俄文译本。1986年,米拉和康斯坦丁·鲁贝亚努夫妇合译的《诗经》在罗马尼亚出版。《易经》的外译本也较多,从清康熙年到20世纪60年代,至少有14本《易经》译本传入西方。在众多译本中,当属1924年出版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易经》译本最为完整。如今《易经》已成为拥有译本最多的《五经》之一,仅企鹅出版社就出版了十几种译本。
《四书》、《五经》在东方尤其是在东南亚的翻译却不甚相同。历史上日本、朝鲜、越南等一度是中国的属国,曾在较长时间内使用汉语,因此无需翻译。这些国家发展了自己的文字之后,才逐渐需要翻译。1448年,《四书》曾被翻译为朝鲜语,日文版的《四书》、《五经》则为数不少。
3.22 以佛教经书为主的宗教文献
我国宗教主要包括本土的道教以及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景教等五大教。从我国宗教的发展历史、相互融合和社会影响来看,我国的宗教并不只是唯心的世界观或盲目的封建迷信,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产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宗教文化典籍。据马祖毅等的分类,我国宗教文化典籍的外译对象主要来源于汉文佛教典籍和道教经典(马祖毅 任荣珍 2003)。
汉文佛教典籍的外译主要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19世纪,日本净土宗南条文雄将《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介绍汉文佛典的概貌。1852年,法国语言学家尤金·伯努夫将《妙法莲花经》译成法文。1863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将《法显传》翻译成法文并出版,书名《法显佛国游记》。法国的戴密微将《临济语录》翻译成法语,并于1972年出版。
英国学者马克斯·缪勒分别于1884和1894 年将《法集经》和《般若心经》译成英文。1869年,英国学者萨缪·比尔将《法显传》译成英文。1877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思也翻译了此书,采用该书的另一名字《佛国记》。
俄国的巴拉第·卡法罗夫分别于1844年翻译了《大藏经》中的《金七十论》,1852年翻译了《佛陀传》,1853年翻译了《古代佛教史略》等。19世纪,沙俄的瓦西里耶夫将《大唐西域记》翻译成俄语。苏联时期的古列维奇将《百喻经》翻译成俄文,并于1985年出版。
1885年,哥本哈根学者维戈·福斯贝尔将《法句经》译成拉丁语。比利时的普山曾耗时8年完成了《俱舍论》的法文翻译,并将《成唯识论》译成法文。华人陈荣捷和捷克奥克拉尔都曾翻译过《六祖坛经》。
3.3 外译传播
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传播最早始于何时,并无确切记载。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开启了中国文化典籍西译的历史。自16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文化典籍的外译传播主要以欧洲为中心,并逐步扩展到北美,在20世纪下半叶转向以美国为中心。
17至20世纪上半叶,法国是中国文化典籍在欧洲翻译与传播的中心,也是欧洲“中国热”的中心。法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传播主要集中在中国古典诗歌(包含唐诗、宋诗和清诗)以及古典戏剧和古典小说等著作上。18世纪法国的《诗经》翻译“以了解中国总体文化为出发点,以探究中国文学灿烂的源头《诗经》的基本内容”(王宁等 1999:5)。到19世纪,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化典籍译介的重点仍然在《诗经》上,但对《诗经》的翻译更注重品质,出现了多部法文和拉丁文《诗经》译本。中国戏剧在法国的译介以《赵氏孤儿》为起点,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多部中国戏剧被译介到法国。中国古典小说在法国的译介在18、19世纪以传奇类作品为主,篇幅一般不长,自20世纪开始,出现了大量长篇小说,研究角度多是纯文学的。
英国对中国的认识很长时间都停留在游记和幻想中,18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汉学家。进入18世纪,中国文化典籍在英国的译介也是寥寥无几,但得益于威廉·琼斯和翟理斯的翻译,中国《诗经》等文化典籍开始在英国传播。进入19世纪后,英国的汉学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汉学家,大批中国文化典籍被翻译和出版。据统计,近400年来,有300多部中国文学典籍被译介到了英国。
德国早期虽然有汤若望这样在中国地位显赫的传教士,但却未能出现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和传播的繁荣景象。直到20世纪初,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福克、弗朗茨·库恩等将中国《四书》、《五经》及其他中国典籍翻译成德文,中国文化典籍在德国的翻译与传播才逐渐多起来。
当然,中国文化典籍在欧洲的外译与传播并不限于以上3国,在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等都有翻译与传播。
美国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传播起步较晚,但却是美洲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与传播的中心。据统计,仅20世纪,就有多达1000多种文化典籍被译介到美国。美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成功的创新。
在亚洲,无论是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说英语国家,还是日本、韩国,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都较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在数量上领先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
此外,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非洲的南非等英语国家,均有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与传播,其中澳大利亚的中国文化典籍译本,从数量来看在大洋洲处于领先地位。
4 结束语
我国文化典籍外译历史悠久,翻译主体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翻译对象也各有取舍,传播区域所涉面广,但中心区域与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化交流紧密相连。我国文化典籍外译既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经济因素的制约,但归根到底,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中国文化传播的推进,我国典籍外译必将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注释
①参见《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39页④和⑤。
②他们是殷铎泽、恩理格和鲁日满等
③此书实际只有“三书”,缺少《孟子》。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何其莘 仲伟合 许 钧.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李致忠 周少川 张木早. 中国典籍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梁建民等. 古代汉语大词典(辞海版)[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马祖毅 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修订本)[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王 宁 钱林森 马树德.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汪榕培 王 宏. 中国典籍英译[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李玉良 罗公利. 儒家思想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张西平. 欧洲早期汉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 2009.
【责任编辑王松鹤】
AHistoricalReviewofChineseCulturalClassicsTranslation(Ⅰ)
Ji Hong-qin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are rich in meaning, and have a wide coverage. Their translation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but has its own rules. The translators who did th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are diverse in different times; there are many classics for them to choos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ir translations are regional worldwide.
cultural classics; translation subject; translation object; dissemination
H315.9
A
1000-0100(2014)02-0096-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典籍翻译与中华文化传播中的战略研究”(12CGJ020)、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典籍翻译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XJK011BGD015)和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汉语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典籍翻译——以《孟子》英译为例”(11B007)的阶段性成果。
2013-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