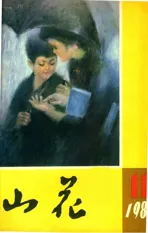与谁分付
2014-12-02
好几次爸爸欲主动介绍她的情况,林夏婴本能地回避,她一点也不想了解这个暧昧的女人,看到她心里就堵得慌。但林夏婴凭直感知道这个女人与自己是同辈人,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她穿着军装,却没有女兵通常所有的飒爽英姿,反而有点娇柔无力的做作,那军装完全就是一张皮,画皮,聊斋人物。林夏婴永远不会忘记,去年初春她第一次来造访的情景,一架变到一半的骷髅戳在门口,在门框的衬托下,像一幅拙劣的恐怖画。
是的,那一刻确实像画,阳光照着她的后背,将她镶出一圈亮边,她的正面就有些昏暗,她还伸出昏暗的右手,很有姿态地扶着门框,她的肩膀一高一低,左脚微踮,显出腰身的曲线。
林夏婴莫名的惊心,不由后退了几步。当来人蚊子叫似的询问林教授在不在时,林本生从书房快步走过来,伸着手迎过去。这时,对方的脸容竟然亮堂了,好像林本生是一道阳光,照亮了她。林夏婴由此也看清了她的脸容,半睡半醒的神态,一对圆圆的大眼,却茫然地做着白日梦。她是谁?好像在哪见过?
爸爸也有些怪异,他也有些与往常不同,驮着背部的暗影,振奋着走向门口的光亮之处,确切的说,很威风地投进了那个女人的暗影之中。他和她握手,两个合在一起的暗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规则的物形,有点像熊,阳光重新将这团新生物镀上了一道亮边。
阳光并不温暖,相反,像冰之光。一种锐利感被成千倍地放大,好像它要沿着边沿切下去。可是镂空后会怎么样呢?门框还像画框,像爸爸的那些简易画框一样围着一块洁白?不,门框外是有风景的,一棵略微歪斜的老桃树,树身到处鼓着疙疙瘩瘩的硬包,却在枝端上挤出了几朵小小的花蕾。林夏婴有些恍惚,好像身陷黑暗囹圄,她的视线很快地适应了门框处的那团暗色,看清了他们几乎一致的亢奋,他们好像有着共同的憧憬,他们憧憬什么呢?林夏婴不由愤慨起来。爸爸!她叫得那样重,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林本生仿佛才意识到女儿站在身后,他呵呵笑着转过身,夏婴,去倒茶,来客人了。
这个客人朝林夏婴一笑,那朵笑摇摇摆摆地从苍白的脸上脱落下来,磷火似的飘过来,很轻,也很诡异,更让林夏婴不快的是,她竟是跳着碎步舞进来的。这样说,是抬举她了,准确地说,是全身发抖点头哈腰跌进来的,还差点被门坎绊倒,那剧烈的震颤本能地引起了林夏婴的警觉,让她想起一个词,心怀叵测。
爸爸把书房门关上了,却关不住片刻后传出的嘤嘤哭声,轻而惊心动魄。他们不知在里面干什么?一会哭一会笑的,出来时,这个女人的眼成了鱼泡眼,林本生亲自为她开门,凝神地看着她远去,关门时还自言自语的说,瘦怯凝寒,若不胜衣啊。
咦?好熟悉的评价。想起来了,小时候爸爸就给自己讲过聊斋,这不是那些书生对女鬼们的怜爱吗?爸爸倒有一点像聊斋里的书生,那就是懦弱无能。难道他真的被女鬼魅住了吗?还是个现代女鬼,套着虎皮!
从此,林夏婴就在心里给她起了个名,聊鬼。她不是喜欢来这里和爸爸聊天吗?!
聊鬼经常来,时间没有规律,甚至是深夜零点。林夏婴故意问爸爸,飘然而至、鸡鸣欲去是什么呀?林本生想都不想地说,那是《莲香》中的李氏。又似乎明白了什么,你想到哪里去了?傻丫头。
这还用得着想吗?爸爸是故意忽略这对微陷的金鱼眼了!它们发出的白惨惨的光直直地罩在他脸上,谁都能看出里面的强烈信息,不安而又固执。作为旁人,这种眼光看到一次就足够了,爸爸一次次迎着这样的眼光,非但不难受好像还很享受,真是着了魔了!
只要聊鬼在,林夏婴就会干许多家务活,她从来没有这样勤快过,所有的家务活都需要走过书房,或者走进书房。她的眼睛都不用对准目标,余光也如雷达般的灵敏,稍大点的动静都在她的捕捉范围,只要他们不关门,关门了也可以敲门,她的听觉也空前的敏锐。有时候林本生如厕离开一会,林夏婴就发现聊鬼会走到书橱前,一动不动的站着,书橱玻璃映出她残缺而又斑斓的影像——她借了那些书色的光。她似乎特别爱面对书橱,好像要把什么见不得人的思想藏进这些书里。一开始林夏婴还认为她是爱屋及乌,后来她觉察到对方的心神根本不在那些书上,她只是假装在浏览罢了,透过那个有点僵硬的背影,以及微微往前伸的细脖,林夏婴仿佛看见了她顾影自怜的表情。
林夏婴忍不住告诉林本生,爸爸,她喜欢把你的书橱当镜子照,好像很自恋嗳。
林本生竟然这样回答女儿,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啊。
林夏婴沉默了,爸爸真是喝了迷魂汤了,连聊鬼的自我欣赏都能上升到什么故乡情结。
爸爸老护着她,林夏婴终于烦了,你真是聊斋中的狐精女鬼美妖也就罢了,一个丑八怪值得我老人家花这么多心血吗?!从此,只要她来,林夏婴就不再出来。我没看见,没听见,心里没有你聊鬼还不行吗?!
可是,林夏婴无法假装没看见父亲的微妙变化,他好像变厚变硬了,过去,爸爸和家人谈笑风生,像个透明的人一样,喜怒哀乐都看得清楚,可现在,他好像有些怕冷,穿衣比以前增多,一层又一层像套上的盔甲,把自己藏在衣服的深处……
林夏婴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将父亲书橱里的《聊斋志异》抽出来,找到《莲香》篇,并从父亲裁的纸条堆里抽出一张夹了进去,又把《聊斋志异》放在父亲正在读的一叠书上面。哼哼,爸爸总不会忘记这样的话吧:后李氏与桑生夜夜承欢,遂致桑生病入膏肓……
当这个家庭充满了激烈的暗流时,最里面的小间仍充满着过去的岁月氛围,在病床上躺了半年的王如菊还是香喷喷的,洗面奶、护肤霜、眼霜、香水照用不误,首饰虽然不戴了,但还挂在床头柜的首饰架上,红玛瑙、白珊瑚、青金石、黄发丝、黑曜石、绿松石,高高低低的流苏,猛一看有些纷乱,细看只是密集。王如菊不喜欢金银,就喜欢这些水晶石头,躺在床上没事干时,还会取下来把玩。她说林夏婴一点不像自己的女儿,太本色了,其实脖子上挂串石头增色呢,哪怕戴串手链呀。她的病容上还遗留着过去的生活痕迹,和林本生讲话,还是一个娇骄之妻的做派,和林夏婴讲话,也是一个母亲的随意。但最近一段时间她有些莫名的烦忧,好几次对女儿说,我感到家里要出什么事了。

刘 猛-《渗》 200×180cm 布面油画 2013
林夏婴就安慰她,家里好好的,不要乱想,照爸爸的话说起来,老想坏事,就等于招惹坏事,要往好里想。王如菊柳眉竖起,我是恨自己哪,跑到国外多年,也没发达起来,害得你爸爸日子过得马虎,现在拖着个重身体回来,却不能为他做些什么了,你爸爸都五十五了……
林夏婴过去也怨恨过妈妈,认为她很自私,可这一阵只是觉得妈妈可怜,她说妈妈你不要想这么多,爸爸从来没抱怨过你,要不他会叫你回来?他感觉出你身体要垮了,幸亏你回来了,否则你在国外病倒,谁照顾你呢?安心养病,爸爸不是肯定地说,你会好起来的?
林本生确实有一套办法,王如菊竟然没得褥疮,喝着他配的中药汤,她的恢复如同乱麻抽丝,缓慢周折。而聊鬼也在渐渐缓解,向人的方向化度,她和林本生正相反,好像要从衣服深处走出来,渐渐显现了一些肉感,现在她进门也不跳哆嗦舞了,改走醉步,微醺,准杨贵妃的做派。有时她还会主动地对林夏婴微笑,甚至有一次试图交谈,她说,你也喂流浪猫啊?那语调明显在套近乎。林夏婴嗯了一声就托故走开。你也爱猫?我林夏婴是和一群可爱的猫在一起,你是和猫魔们在一起吧?一身的戾气!
虽然聊鬼来这里,眼睛总是直接望向林本生的书屋,而且屏气凝神,脚步轻微,一看就是控制了响动,可躺在病榻上的人还是能够分辨出来,哦,那个女学生又来了?像我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对知识的渴望也是急吼吼的。更奇怪的是她竟没有发现林本生的变化,反而很欣慰的样子,你没发现吗?你那个木笃笃的爸爸好像精神多了。
林夏婴差点要掉泪了,妈妈内心好刚强啊!林夏婴很想找什么人吐吐苦水,她曾经都拨出一个电话了,最后还是改了话题。这个人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恩娃,过去她经常来看爸爸,她和恩娃也很亲近,两人见了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这半年来,她只来过一次,林夏婴知道,是因为自己妈妈从国外回来的关系。林夏婴知道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妈妈。其实恩娃也有点狭窄了,我妈妈是在爸爸和你妈妈离婚以后才出现的,她又没得罪你,虽然两个姑姑有点刻薄,说话不太注意,惹得你不高兴,这点我早看出来了,可我妈妈并没得罪你呀,何况她是个躺在病床上的人了。虽然林夏婴最终没有向恩娃吐露心事,恩娃还是感觉到了什么,追问她遇到什么事了,林夏婴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闲话,她无法打开心门,她怎么说呢?说爸爸又花心了?她也不忍心再在恩娃的伤口上撒盐了。
如果妈妈有感觉,两人还能结成同盟,虽然她也想到这样对妈妈可能是弊大于利。可事实却相反,王如菊对那个聊鬼也起了怜悯之情:我耳朵尖,能听出她声气弱,我敢肯定她有病,你说她是不是脸色苍白?对吧?别看我躺在床上,什么事情不知道?下回她来,你也给她端一碗红枣汤。林夏婴心不在焉地哦哦着,拿着刚给妈妈换下来的内衣朝卫生间走,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健康可人的姑娘,只是两边嘴角愤慨地向下拽拉着,她愣了一下,马上明白过来,原来镜中的形象正是自己。林夏婴将妈妈的衣服泡进盆里,暗忖道,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了?
林夏婴走回到母亲床前,王如菊看着她,眼神里有一些轻微的指责,林夏婴躲开她的眼光,看向窗外,低空中停着几摊黄白色的云,像烊化的白巧克力,国产的,死甜。
人不生病不知道生病的苦。夏婴,妈妈过去的样子你不会忘吧?想想这个姑娘,能参军,说明身体好,现在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免疫系统太低下就容易生病,要不是你爸爸帮助她,她都绝望了……
嘿嘿,原来妈妈知道她不是来拜师求学的呀,我差点以为妈妈躺傻了呢。
王如菊拍拍床榻,过来!你不信你爸爸呀?
林夏婴坐到床前,握着王如菊的手,妈妈,爸爸六十岁不到就被某些人吹成国学大师,我参加嘲笑了吗?我还骄傲呢,爸爸学识就是渊博,国画也那么灵,还懂阴阳八卦,中医理论也一套又一套,但是!坐堂门诊是需要执照的,无照行医要取缔的。妈妈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
王如菊抽出手,在空中对着林夏婴点了几下,别人不理解你爸爸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一分钱不收取的。讲心里话,我也巴不得他赚大钱呢,但是,你忍心去赚那个姑娘的钱?
妈妈!你小时候没读过农夫救蛇、东郭先生一类的寓言吗?我对故事新编不感兴趣……
王如菊笑了,大小姐!臭脾气!好了,我们以后不说她,说点开心的事,你好像胖点了?蛮好的。林夏婴扭了下腰,谁胖了?我还想减肥呢。
王如菊指指床头柜,一袋嫩黄的上海蜜梨非常触目。我看你最近有些上火,吃点水果吧,还是那个姑娘送来的呢,我一个人哪吃得完?

刘 猛-《绿色响应》 200×180cm 布面油画 2013
林夏婴有些意外,她进这个房间啦?
没有,是你爸爸不让她过来看我,说她身体不好,不想让她看了心里难受。她已经送过好几回水果了。
林夏婴很蔑视地沉默了几秒钟,反正我不喜欢她,送金子来也没用。其实她本来想说,谁知道呀,没准是爸爸买的呢,给她做面子。
窗外的天光照到床前一米处就止了,但王如菊脸上仍有着光彩,是精神上的光彩。妈妈没病倒前,是多么光彩照人,她跑到国外,奋斗了好几年,近年身体不好,爸爸硬把她叫回国,果然回来没多久,就病倒爬不起了。爸爸妈妈的血脉是相通的吧?心肠也拴在一起的吧?可是!爸爸毕竟不是圣人嗳。和妈妈分居这么多年,尝不到一个男人应有的夫妻生活,现在碰到一个主动粘上来的聊鬼,也难怪他乱了心性。聊鬼没出现之前,爸爸对妈妈是多么细心啊,除了和她一起细心地照料妈妈,还拥有着一项护理专利,这就是为王如菊导尿。
林夏婴一直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不让自己来做?她又不是儿子,没什么不方便的,可是林本生就是不许。在那个昏黄的傍晚,王如菊闭着眼睛对林夏婴说,你爸爸对女人的生殖器比女人还了解得仔细……
林夏婴微微打了个抖。这句话太有震撼力了,她的心好像被揉成一团,又狠狠砸了一下,说不上疼痛,也说不上感动,甚至不是酸楚,是心里堵了墙,闷得慌。
王如菊又觉察不出地吁出一口气,女人没结婚,那就是一朵没打开的花,我的花早开败了,现在那里是一片沼泽地,乱七八糟。你爸爸不让你上手,是为你好,他想法多多呀。
林夏婴胸部凹进凸出,身子禁不住地颤,心里的那堵墙终于垮了,乱砖废瓦的砸下来,心地还是承受了疼痛。她没想到爸爸不仅照料着妈妈,也照顾着她的心,爸爸太好了,好到让她不知怎样报答。可是,这种愧疚与感动随着聊鬼的一次次造访减轻了。有时她看着父亲坐在藤椅上的背影,后脑勺新窜出一些花白的头发,在头顶像茂草一样耸立着,像寒风中的枯草,她心疼得转过头去,怕自己忍不住口出怨言。
夏婴?有几次林本生敏感地回过头来,这时候他的白发隐退了,他的大脑门冲着她,眼神中有光点在跳,生气勃勃的,像一个刚开眼的小孩,对世界还有着新鲜感。
林夏婴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爸爸也是中壮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有两性欲求也是正常,现在八九十岁的糟老头讨二三十岁的女人也不是什么新闻,何况是这个女人自己送上门来。她不想苛求爸爸,也愿意理解爸爸,只是感情上不能完全接受,毕竟妈妈还躺在病床上呢!可爸爸也没必要继续装出坦荡的样子,说聊鬼是来讨教活下去的方子的,你如果说是找你来讨教文学的还说得过去,你毕竟是大学国文老师,中药、国画、阴阳之说只是你的业余爱好,她凭什么频频来我们家看病?!
林夏婴默默地冷冷地观察林本生,她发现爸爸变化真的很大,越来越大,他身上藏着神秘的不可解的东西。就是出门散步这样的凡俗小事,也好像有些不一样了,他总要换上旅游鞋,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随意地穿上皮鞋或者布鞋,还不时提提精神,捏着拳头出门,仿佛肩负了什么使命感?他出门,无论是先跨左脚还是右脚,那一脚就像一个奠基,有什么要在上面建立起来?若不是他是自己的爸爸,林夏婴真想悄悄地跟踪其后,看他是不是去忘年恋了。
妈妈房间的墙壁上,那幅木版画《蒲公英》好像变暗了,林夏婴用湿抹布将它擦了擦,王如菊说,现在市面上好看的油画多得很,可这张老画还是看不厌。
林夏婴还记得小时候,父母为这幅画起的一次甜蜜争执,爸爸说这是他买下的,他一眼看中了,妈妈说明明是她先看中的,是她让他买下的,两人像小孩子一样争个不停,林夏婴很稚气地插了嘴,是我看中了,才让你们买的!爸爸妈妈一愣之后都笑了起来,那时候哪有你啊?
幼儿园大班生林夏婴想不明白了,那我在哪里?总有一个地方待着,总不能在天上飞?
做母亲的小姑娘一样笑起来,你就是蒲公英生出来的,飞啊飞。
林本生对着画指指划划,这鼓起的小嘴,这飞起来的绒絮絮。我们小时候也像小姑娘一样吹过呢。
王如菊嘿嘿一笑,别人说我不信,你说我信,你从小就是个胆小鬼,玩女生的把戏是可能的。
他们两个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真正的知夫莫如妻,知妻莫如夫,王如菊刚病倒的头一个月,突生急躁情绪要把那些首饰送人,林本生还不慌不忙地说她呢,你怎么知道自己会挂掉?送掉了还能买到你这些心爱的老货?真没想到你会吓成这样。王如菊吼似的说,我才不怕死呢,我是担心这日子怎么过呢?老躺在床上,急死人了!

刘 猛-《牧》 180×200cm 布面油画 2013
急什么呢?以史为鉴,上下五千年,以时光为浮云,长城还在,秦始皇到哪里去了?你只管安心度日,一切都会过去。我看你就像吹蒲公英的小姑娘,一直没变呢。倒是你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我有什么变化,比如说要走了,抛下你们母女俩了……
像一盆旺火被泼了一瓢冷水,王如菊打了个抖,什么比方不好打,拿自己乱说什么?!
林本生轻轻地捏着她的肩,那就拿蒲公英说话,脚在泥里,心在飞。人不就是活一颗心?
林本生和王如菊结婚以来,从来没有红过脸。当然,林本生也从来不对别人红脸。在林夏婴看来,眼前的一幕才是真实的父亲。看到爸爸平静地安慰妈妈,她的心里生起一丝感动。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时间最好在这一刻停止。从她记事以来,父亲就是个老气横秋的人,三四十岁走路就背着手,像农村老大爷,同时他又是个胆小如鼠的人,碰到任何发狠的角色都会往后缩,退后一步天地宽的陈词滥调朗朗上口,结果第一次福利分房,他不敢据理力争,分了朝北的一套。妈妈没出国之前,拉他一起去旅游,他没兴趣,有过一次难得的全家游,她和妈妈爬山登高看风景,他充耳不闻地坐在山脚下喝茶,妈妈评论爸爸,他心中没山水;买当地人的茶,少了斤两,母女俩和小贩争执,他拽着王如菊就走,还说少喝几杯又何妨。王如菊说自己嫁了个木头人,需要尖刀才能刻出他的感情。他们单位的同事称他“老夫子”,也有叫“老好人”的,林本生一律接受,从不见他邀请同事来家做客,也不愿和左邻右舍闲话,见好人好事点点头,见坏人坏事叹叹气。点头也罢,叹气也罢,并不久久放在心上,亲朋好友都知道他是个缺乏激情深情的人,不具有嫉恶如仇的品性,是个典型的寡淡的好好先生。至于男女之情风流逸事他更是不闻不问,亲友们笑话他,他有女儿都像是个奇迹,没想到老了老了却被色风刮倒……
可是,只要林本生一走进王如菊的房间,就像逸出河床的水重新落回到过去的水流中。他握着王如菊的手,说你这个小老太婆呀,就是性太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懂吗?王如菊就反击他,你这个小老头,慢慢慢,慢到落在整个时代的后头。
这次两人的斗嘴又进了一步,王如菊说林本生什么都慢,慢得蜗牛都要嘲笑他。林本生就说有时缓慢也是福报啊,上次看到小区几只流浪猫,我随手扔出去一只刚买的肉包,结果那只跷脚猫逃得最慢,反而吃到了美餐。王如菊反问,照你这么说,我干脆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要做,比迟缓更加极端,是不是天上就可以降什么福报啦?林本生拍拍她的肩,你这个小老太婆嗳,天会降雨,不会降福报,谁叫你一直躺在床上了?叫夏婴扶着你慢慢走几步啊,你的机能恢复得差不多了。王如菊白他一眼,你以为我喜欢赖在床上啊,我试过,一起来就瘫在地上,脚还不是自己的……林夏婴听得有些着迷,这时候屋子里的光线会柔和下来,只是不太稳定,一会暗一会亮,但墙上的版画却似乎一直在光亮中,虽然这光亮并不强烈。
这幅画是伴着林夏婴长大的。等到她成了初中生,就不明白这幅画好在哪里了,这么简单的画我能画一百幅!到了高中阶段,林夏婴再看这幅版画简直是老掉牙的乡下情调了。其实她并不懂画,爸爸画了那么多画,也没激起她什么兴趣。
聊鬼倒对爸爸的画感兴趣,专心地坐在一边看他画画。嘴里还说个不停,有一次竟让林夏婴听到莫明其妙的闲话:就是那次,首长的笔写光了,顺手抓起红笔写了我的名字……爸爸呢,像对待小时候的她,放下笔,疼爱地拍拍聊鬼的手,她苍白的手上好像有几根青色的细筋,堵塞不通了,经林本生一拍,温暖地流动起来。林本生的声调也很耐心:呵呵,我知道你什么意思,过去判死刑或者绝交就用红笔写名字。你看你,还是军人呐,你又不是古人……他的手又摸了摸她的头。
林本生突然提高声音,夏婴!林夏婴只好从门后闪出来,她握着拳,瞪着那个侧过脸看着自己的聊鬼,好像一个孩子的玩具被小伙伴抢了,正准备拼命夺回来。
林本生说,夏婴,如果有人用红笔写你名字你怎么想?
林夏婴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突然间她发现这一切都愚蠢透了,妈妈都不在乎,她起劲个什么?!
林夏婴无所谓地耸耸肩,爸爸,红枣汤烧好了,我给你端过来。又对聊鬼点点头,妈妈说,也给你端一碗,你要吃吗?
聊鬼好像有些受宠若惊,谢谢谢谢!不吃了,我一会走。
林夏婴发现她的声音依然是小动物类,只是从蚊子变成了苍蝇。
这天,林夏婴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聊鬼走时,竟然依依不舍。而爸爸,笑得也很悲壮。林夏婴装没察觉,走进卫生间,耳朵习惯性地拉长,她听见了爸爸语重心长的叮嘱:记住我对你说过的一切。我说到做到,你不要害怕。后天下午三点你准时来。
门关上后,爸爸去了妈妈房间,林夏婴心砰砰跳,有些透不过气来。一会儿,她听见了轻微的哭声,是妈妈在哭。林夏婴再也忍不住了,她冲进自己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扑在床上咬着枕巾哭泣起来。自她记事以来,她就没有流过眼泪,连得知男朋友欺骗了自己也没有这样伤心难受。
林本生推开了门,走到林夏婴身旁,摸摸她的头,你听到什么了?不要难受,要发生的事情总要发生。今后好好照顾妈妈。爸爸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女儿,有什么事你也可以和恩娃商量,她也是个聪明的女孩,大家互相帮助,爸爸就放心了。
林夏婴松开嘴里的枕巾,咬着牙说,不要来烦我,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第二天,林本生一直在书房里忙碌着,过去,林夏婴常去帮父亲整理书桌,也会把地拖得干净。可这一次,她任凭他去自得其乐。林本生有条不紊地擦拭着书桌,把一叠叠书排在一起,像砌着一堵墙,每叠书还压着一张纸条。然后,她听到他长长的一声叹息:时间过得真快呀!
林夏婴心一动,她从未听到过爸爸叹息,就连妈妈病成这样,他都没有过悲色。林夏婴有些透不过气来,好像缺氧,一切都显示,爸爸第二天要摊牌了。
清晨林夏婴早早地醒了,趁着爸爸还未起床,她蹑手蹑脚地来到他的书房,打开门的一刹那,她不由愣住了,在石灰剥落的屋顶上出现了一把倒吊着的大红伞,这把撑开的大红伞像一朵盛开的花,把斑驳破落的屋顶也衬映出一层浅色的红光。难怪昨天爸爸站在桌子上往屋顶上拧螺丝呢,还问她讨这把按钮坏掉的伞呢,原来他要做这个勾当?
今天王如菊的精神好多了,林夏婴把她扶起来靠在床头,王如菊问你爸爸起床了吗?林夏婴欲言又止,然后兴高采烈地说,妈妈,爸爸不是说你可以起床试试了吗?今天天气好,我扶你到院子里走几步吧?
王如菊有些生气,不生病的人不知道生病人的苦,他以为走路是这么容易的事啊?这个病摊到他身上试试!
林夏婴耐心,不走也行,我用轮椅车推你出去?今天天气太好了。小区广场的桂花都开了,金桂、银桂、丹桂,各种香哦。
王如菊有些动心,想了想又说,那就明天吧,今天你爸爸要演出,他叫我等着看戏法呢。林夏婴睁大了眼睛,难怪问我讨那把收不拢的红伞呢,原来他在布置舞台啊,我的伞变成爸爸的道具了。
王如菊问了详情,一下明白了,前几天你爸爸发现书屋顶上出现了一条裂缝,他是怕泥灰剥落吧?
用伞来接坍塌?其实爸爸也挺天真的,并不像大家认为的老夫子、小老头之类。而且他还会制造悬念,今天他要给妈妈表演一个戏法,给聊鬼支付一个承诺,那么给我什么?哦,一个交代!林夏婴突然有个冲动,她想把恩娃叫来,她想叫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也来做一个见证。
三点不到,聊鬼提着一个红布包来了,她身着一套春装,竟然是黄绿色带小花的格子装,虽然艳过军装,但在林夏婴眼里,还是像牢笼的格子,囚禁着她那颗不安份的心。
聊鬼脸色紧绷绷地向林夏婴点了点头,说林老师今天有大事要做,请我照看一下他。
林夏婴说不出话来,喉头像梗阻了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她进了爸爸的书房。书房内很安静,能听到林本生轻轻的几句话,还有聊鬼简短的回答,只是几声嗯字。但这一字却带点颤抖,千回百转余味无穷。

李 瑞-《绿意吟山坳》 直径200cm 布面油画 2013
林夏婴走到妈妈屋里,王如菊靠坐在床头,闭着眼好像进入凝思。林夏婴没有打扰这份安静,她走到版画前,第一次对熟视无睹的画面有了陌生感,过去她第一眼总是看那个小姑娘,可现在,她从画的大面积空白里看出了一种虚淡,一种忘情,女孩子在吹蒲公英的那一刻是忘情的,完全专注在那轻絮的飘飞之上,它要飞走了,它要飞到哪里去呢?
版画里突然充满了不安静的追究,林夏婴觉得小姑娘不是在吹蒲公英,而是在吹一串问号,过去爸爸说的什么水墨情韵、渺远意境、单纯意象之类的并不能使她产生兴趣,可爸爸说的那句话突然跳了出来,强烈地占据着她的头脑:你喜欢整个世界只有一棵蒲公英的感觉吗?
王如菊睁开了眼睛,喃喃自语地说,她已经第三次打开书屋门了。
林夏婴的左眼皮剧烈地跳动起来,她觉得今天的事情有点不同寻常。她过去拥抱了一下王如菊,妈妈你息一会,我过去看看。
她看到书屋的门依然关着,而聊鬼却破例地站在门外,一副困惑的表情。林夏婴忍不住了,你进去三次了?
聊鬼一愣,这是林夏婴第一次主动和她说话。她想了想,好像下定了决心,是的,林老师在里面打坐……
林夏婴迟疑了一下,他在闭门修定吗?
聊鬼表情复杂,脸红一阵白一阵,他不允许我进去,让我在门口守着,他要实行自己的诺言……
林夏婴脑子轰的一响,什么意思?!她一下推开门,看到父亲端坐在那把藤椅上。她屏住呼吸,爸爸还盘着腿呢,这种姿势她可是第一次看见。聊鬼轻轻跟进来,附在林夏婴耳边,用声气说,已经两个小时了,我们再出去等一会吧,林老师关照过,等他走了才能进来。
如同一条被暴风雨吹垮的帆船,破碎的木块被海浪掀上了半空,又狠狠摔落下来。林夏婴的心也碎了,她大叫一声爸爸,冲了上去,聊鬼一把没拉住,趔趄了几步差点摔倒。
林本生一动不动,眼角含着微笑。林夏婴一声呜咽,随即头顶啪啦啦一阵乱响,仿佛降落了一场冰雹,大大小小的泥灰块砸进了倒挂的红伞之中。林夏婴头晕起来,海浪呼啸,破碎的船板变成了一些单词,栩栩如生、涅槃、归去……
一声异响,林夏婴回头,看到王如菊正爬到门口,她扶着门框努力地想站立起来。妈妈,林夏婴呜咽着扑过去,用力扶起母亲。王如菊眼睛盯着林本生,小老头,这就是你表演的预知时日啊?
聊鬼从包里拿出一把红玫瑰,郑重其事的放在书桌上,又深深地向林本生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向王如菊和林夏婴说了声对不起,就白着脸走了。林夏婴发现她的脚步似乎又恢复成了醉步。
王如菊在林夏婴的护持下,拖着脚步走到林本生面前,她的脸上带着看雕像的表情。几秒钟后,她令林夏婴搬一只凳子过来,默默地和林本生并肩坐在一起,终于她侧过脸来,对着林本生点了点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眼泪却像决堤的水。
恩娃闻讯赶来,进门就哭喊起来。爸爸,我就叫你爸爸,我就认你爸爸,你为什么扔下我走了呢?
林夏婴伤心而又诧异,恩娃的话有些奇怪呀。
恩娃双手合十,夏婴,我才知道,他其实不是我的亲爸爸,他怕伤害我,一直在冒充我爸爸,爸爸呀……
林夏婴瞪着双眼,好像听了天方夜谭,爸爸真会藏故事啊!
两个姑娘抱在了一起,林本生的父爱使特殊的姐妹情又深入了一层。
林本生事先将书都分门别类地放在了书桌上,送给谁都写得清清楚楚,书里夹着纸条,纸条上是临别之言,所有的纸条都有一句对不起,对不起,他不能照顾王如菊了;对不起,他不能陪伴林夏婴了;对不起,他不能帮助恩娃了;还有其他的亲朋好友,他都对不起,不是没帮上什么忙,就是无意中惹别人生气了,林本生似乎欠了一屁股的人情债。
林本生走后的几天,林夏婴整理爸爸画的一叠山水画,感觉自己和妈妈一起走了进去,而爸爸依然在画外喝茶,慢慢吞吞的,可是,跨进死亡的步子却这么迅猛。林夏婴迅速消瘦下来,当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也变得苍白时,她不由地心悸了,会不会被那个聊鬼传染了什么毛病?家里很安静,王如菊不和女儿说话,只是捧着林本生的医疗本,厚厚的几本,她疯狂的沉浸在其中,仔细地研究那些陌生的化验单、药名,好像要寻觅出一条生死秘道。
门铃又响了,一个满眼痛楚的男人站在了门口,他说他是小区邻居,他的女儿受到了林本生的帮助,特来致谢,同时告诉她们一个消息,女儿病得很重,已经住院了。
王如菊对林夏婴说,爸爸不在了,你应该去看看她。林夏婴觉得很别扭,为什么是应该呢?她在爸爸的书房里坐了很久,眼光落到了爸爸最后翻到的那本书页上,“唐朝的香严禅师一天铲草,碰到一块瓦块,随手一抛,瓦块打到了竹子,啪的一声响,他就忽然开悟了……”林夏婴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又站起来踢了一下桌腿,窗外各种杂声,她没开悟!终于她站起了身,去看就去看吧,没什么了不起的。

李 瑞-《田·木》 45×45cm 布面油画 2014
林夏婴来到了医院,鼻子里全是医院特有的气味,有点像爸爸书房顶上坍下来的泥灰味,当时并不能准确的闻出这股弥漫的尘味,现在她竟发现它们有某一种相似之处,那是难以描述却是独知的。她找到了那个房间那个床号,没想到那张床空着,洁白的床单很整齐地铺着。房间里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护士坐在窗前说着什么。
林夏婴有些莫名的惆怅,问护士,她呢?死了?
护士一愣,指着老太太,不是在么。
林夏婴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头发脱落,满脸病气的老太太正是聊鬼。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样大的变化?!
聊鬼平静地朝林夏婴点点头,没表现出多少惊喜,但也不算冷漠,她像天天和林夏婴见面一样,来了?坐一会吧。
你是什么病?
白血病。
你来我家时就有了?
是啊,听到医生宣布时我魂都出窍了,我不知道怎么度过最后的日子,我怕死,每晚都做恶梦,差不多要发疯了。后来听说了林老师,他有许多秘方,我就想来讨活命的药。
他究竟给了你什么?
你不是都看见了吗?我们也就是聊天,他从头到尾说的就是叫我放下心来,该干啥就干啥。
我爸爸到底向你承诺了什么?
他说他肯定会死在我之前,他会让我看到,死亡并不可怕,让我有面对死亡的勇气。
林夏婴脚踝一软,好不容易稳住,她摸着一只空椅子坐下,眼睛盯着这个聊——这个和爸爸聊了无数次的人。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听妈妈说,你叫猫人?为什么起这样奇怪的名字,是因为喜欢猫吗?
这个年轻的变成老太太的人用食指在空中书写着,毛宁啊,上海话读起来是像猫人呵呵。
林夏婴想起什么,从包里掏出一包红枣,这是免洗的即食红枣,补血的,妈妈让我带给你的。
毛宁说谢谢你妈妈,她现在能出门了吧?秋天的天气真爽啊,小区的桂花都开了吧?
林夏婴点点头,你安心养病,早点出院去闻桂花香。
毛宁苍老的脸上浮上一丝微笑,好的,我尽力。夏婴姐姐。
比我大半岁呢,叫我姐姐?!林夏婴这样想着,嘴里却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毛宁淡淡一笑,姐姐,我想求你一件事,我们家门口有四只猫,才才、果果、丑丑、小咪子,我走了,你有空喂一喂吧,我怕爸爸妈妈太伤心了顾不上它们,才才清高,气性大,猫多了它就不肯吃了,得单独给它留一份猫粮,小咪子胆小,你要慢慢接近它。哦,还有一只黄虎斑,大概只有三四个月吧,有时来有时不来,你也留意一下吧。
林夏婴抑制着心头涌上来的伤感,用力点了点头。
毛宁轻轻叹了口气,在我生病的日子里,它们始终没离开我,一直隔着玻璃窗朝屋里看,我没法回报它们了。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她低下头去,片刻又抬起头,林老师说过,就是去另一个世界,还是可以给别人祝福,我会祝福所有的人。如果看到我爸爸妈妈伤心,你就告诉他们一下,说这是真的,他们一定会收到我的祝福。
林夏婴坐不下去了,她起身告别,毛宁站起身送到门口,林夏婴发现她的脚步很软弱,比第一次到她家还不如,但她的背挺得很直,眼神里有一股她熟悉的神情,她一下认出来了,这是和爸爸一样的从容淡定。
她出来时,那个护士赶上来,轻轻对林夏婴说,有空多来看看她,她活不了多久了。
林夏婴快步走出医院,在穿过街心花园时,手机响了,王如菊的声音震荡着,你爸爸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林夏婴呆呆的反应不过来,王如菊吼起来,还不明白,就是渐冻症啊!才开始他就把自己勾走了,唔唔唔,他就是个木头人啊,看见死亡也不害怕……
一声雷响,天上下起雨来,雨点很稀,但巨大,每一滴都砸得林夏婴生疼。雨开始密集,越下越大,她跑了起来,路上已经有人撑起了伞,黄色的,紫色的,青色的,红色的,前后左右地涌动着……她的那把没法收拢的伞被爸爸吊在半空中了。林夏婴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像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一样嚎啕大哭起来,爸爸,对不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