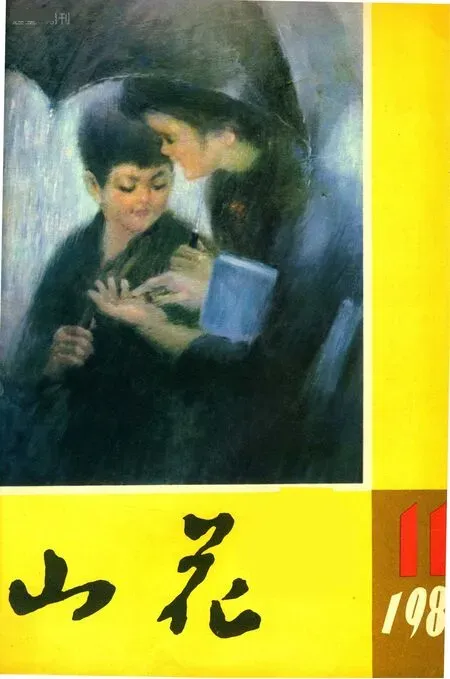灵魂在空中飘来荡去
2014-12-02
1
七年前,当庄青第一次向我走来时,他就像一株随微风摆动过来的枯草。那时,我正倚着伊铁监狱的操场围栏,在做一道英语阅读理解,正做得头疼,庄青就出现在我眼皮子底下,让我吃了一惊。我之前看过他的卷宗,二十一岁的年纪就强奸杀了人,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准是青春叛逆期就开始在街上当小混混了,满脸荷尔蒙分泌过剩,不消说也是杀气十足,这种孩子(倘若我还能称他为孩子的话)通常出身不好,要么从小父母离异,要么是在棍棒的夹击中长大的。可庄青的突然出现,彻底颠覆了我的想法。那天,他呆呆地低着头,脸圆圆的,皮肤干净柔软,劳改犯统一的发型一般会让人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可庄青却正好相反,他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一个稚气未脱的伪混混。他适合穿这种灰白格子的囚服,显得朴实,我这么说好像很不道德,可你若见过他就会发现事实的确如此。他就像个农村少年,一脸的无辜,一脸的不谙世事。我差点同情起他来。
我喝住他,没叫名字,叫他们这些罪犯名字简直是种耻辱,况且伊铁监狱那时的状况是一个狱警要管上百号人,叫名字多费劲,能省则省,反正他知道我叫他就行。
嗳?你?说你呢。放风时间,谁叫你四处走动的?我明明知道他不是四处走动,样子是来专门来找我的,可还是忍不住想杀杀他的锐气。这里全都是一些要死的人,该死的人,每天面对着这些行尸走肉,心里难免憋着一口气。
于警官,我有点事——
什么事?嗯?
大概是我的横眉冷对吓坏了他,确实,我的下意识告诉他,你不能有事。你能有什么事?你有事我还真不一定解决得了。你可别千万给我找麻烦哈!果然,他心领神会,把话憋了回去。这时,陈一河在他背后出现了,别给人家于警官找麻烦哈!陈一河身材魁梧,胡子拉碴,胸毛一直长到肚脐眼,要不是他一向客客气气,我多少会怵他。陈一河陪着笑脸,像提着一袋垃圾样的,把庄青拽了回去。
还是上点年纪的人懂事,我总算松了一口气,继续靠着围墙念着英语,眼睛还得时不时注意着操场上的一切。
我简直厌烦透了。
2
伊铁监狱位于胶东半岛北部,若让我写出它的具体地址,我想即便今天我也写不出来,我写满半个信封也只能写到某个村,可伊铁监狱,就他妈位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旮旯。

刘亚伟-《日记——不爱红妆爱武装》38×46cm 布面油画2014
七年前,大学时光在盛夏戛然而止时,我大病了一场。眼看同学们考公务员的考公务员,当老师的当老师,进企业的进企业,我好歹在离校前的半个月,搭上了“狱警”这一职业,还是个没编制的聘用工。
寝友K说,这职业好,光荣的人民警察啊!
我说光荣个屁!一个小小狱警,又不用上战场,也不用我学雷锋的,怎么光荣?我一旦“光荣”,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无耻的犯人给搞了,那真叫生得不伟大、死得很窝囊,连鸿毛的万分之一轻都算不上!丢死人!
事实上,现实比预想而言,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报到那天,车子辗转了许多高度起伏的山路,当我被扔在胶东半岛的某座石头山山坳里时,我恍若隔世,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分不清今夕何夕,辨不出东南西北。我想即便我是一条狗,都找不到来时的路了。
刚来,瑞哥说,等过几天习惯了就好了。
瑞哥是蒙古族,全名至少五个字,他说过一次,什么吉什么音什么格的我也记不清,总之最后一个字是“瑞”字,我就叫他瑞哥了。他比我早来两年,是一个不知名的学院哲学系毕业的。他嬉皮笑脸的样,完全对不上哲学的茬,可时不时说起话来,又让你觉得这就是个学哲学的人。比如第一天他就问我,小于,你觉得人生的终极信仰是什么?
我愣在那里。
于是乎他又补充了一句,那你就说说你的人生终极——他又看看我,把“终极”二字去掉了,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想到海边去。
他有点吃惊,有点无语,又有点失望,我猜我是所答非所问了罢。结果他一拍大腿,我靠!我也想看海!不光我,师傅也想看海!他俩想看海都有据可依,瑞哥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看到的都是静态的草原戈壁,想看大海的波澜壮阔再正常不过;而师傅,听瑞哥说他从小是在青岛海边渔村长大的,中年过后,反倒被命运扔到了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而我,我没对他说,我女朋友在青岛。
看海容易,别忘了我们这可是胶东半岛啊,我带你去。瑞哥说。
那个黄昏,瑞哥就扬言要带我去看海。本以为我们会真的长途跋涉到海边,哪怕是来次越野训练也行啊,只要能抵达海边,只要能走出这个山坳。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提前和岗哨打好招呼,带我到岗哨上看海。
岗哨上面能看到海?
废话,岗哨可是监狱里最高的地儿了。瑞哥说。
小武警看了看我,一脸无奈。没事儿的,就五分钟。显然,瑞哥和岗哨已经很熟识了。小武警把我俩让了进去,自己退出来站在台阶上。逼仄的空间让人不敢大声喘息,初来乍到的我跟任何人都算不上熟识,为避免尴尬,我顺理成章选择与瑞哥背对背站着,脚跟挨着脚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张望了很久,发现眼前的并非大海,在距离眼前开阔地千余米外是黑压压的石头山,依稀可见全是高矮胖瘦、形色各异的花岗岩。
海在哪?我问瑞哥。
不对,你小子站反了。海在我这边呢。瑞哥说。
于是,我们像两个木偶一样小心挪着步,交换了位置。
眼前仍旧是一片黑,这一次,视线离那些石头似乎更近了。我发现它们堆得老高,在监狱的制高点,我们就像是井底之蛙,绝望让我忍不住颤抖起来。我质问瑞哥,你耍我啊?
没有。你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海了。
我悄悄闭上了眼睛。
嘘!瑞哥故作深沉,听到了没?大海的声音。
这时,我已然意识到瑞哥所谓的看海与我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还是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唔—唔—唔,我听见了呼啸的声音,像海浪,更像山风,我分不清。
哪里有什么海!小武警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这小子在耍你呐,老子在这里呆三年了,也没见过一次大海。快出来快出来,等下让领导知道,我就死定了。
瑞哥苦笑起来,苦笑过后,他像一只狼一样冲着裹挟着我们的大山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嗓子。
小武警递给我们一人一支烟,然后把我们轰了下来。我和瑞哥坐在最下面——挨着地面的台阶上各自抽着烟。瑞哥说,别作梦了,这地方离海上百公里,山路不是一般的绕。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问题是你得走到B村去坐车,走过去也要走两个小时。
我说不出话来。
瑞哥熄灭了烟说,小于,你有什么爱好没有?
见我犹豫,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赶紧找个爱好!他捏着烟蒂,在空中抡着,像拿着粉笔的老师,我看得出他的狠劲儿。找个目标,去奋斗。他说,如果在这呆上几年,你就废了。

刘亚伟-《日记——身份证照》46×38cm 布面油画2011
那你呢?我问他。
他不紧不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本本,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又神秘地揣了回去。
那是什么?我问他。
我是虔诚的教徒。他说。
什么教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这个不可能吧,这边也没伊斯兰。
以后你就知道了。瑞哥说,有机会带你去县城参加我们神圣的聚会。不过,瑞哥有些难过的样子,我也只聚过一次,这鬼地方——
你知道每天面对死亡是什么感觉吗?
我摇摇头。
这里面有个过程,你慢慢体会。瑞哥说着突然停下来,吼出一段蒙古长调,长调尾音刚落,又接上了《鸿雁》: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
瑞哥眼里含着一汪温暖的水,看得出他把这里的荒芜想象成了草原。他说这是他家乡巴彦淖尔的市歌。
唱毕,他闭着眼回味了一会,继续先前的话题说,咱们伊铁监狱,百分之八十都是死刑犯,阴气太重。所以,不骗你小于,你一定得找点事做,你像我师傅,当然也是你师傅——徐警官。他喜欢书法,毛笔字,之前还获过省里的书法比赛大奖嘞!再比如,这小子——说着他大拇指向后指了指岗哨,这小子喜欢研究围棋。
可我什么也不会。我有点沮丧。
那你就去考试,考公务员,考研。师傅很支持咱们考公务员和考研的,在你之前也分来两个,都考走了。要不然你就得像刘刚一样。
刘刚是谁?我疑惑。
瑞哥似乎说错了话,脸上微微泛着红光。
刘刚究竟是谁呢?我疑惑着。
最后一丝晚霞在我们身后隐去。
我问瑞哥,你怎么不考公务员?
瑞哥摇了摇头,我对那个没有兴趣,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大山,哈哈哈……但是你要去考。
我勉强点了点头,我还是考研吧。
3
这一晚,我走进师傅的宿舍,到处弥漫着墨汁的香,他握着毛笔的右手停在半空,刚好做完个漂亮的收笔动作,然后挽下袖子,示意我坐过去。
毛笔尖躺在砚台上,尚存温热。桌子上放着一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书是扣下去的,书旁边的宣纸上是师傅写好的小篆,规矩、隽秀的字让人没法跟眼前这个披着警服的魁梧男人联系在一起,再看宣纸上的字,更让我对师傅的为人产生好奇,他抄写的是王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想必正出自旁边的那本古代文学作品选。趁师傅去洗手的空当,我把书翻了过来,果然猜的没错,但我随即就注意到书皮上那个赫然的名字:刘刚。
来了几个月,我并未发现这里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刚要问师傅,他却先开口打断了我,
小于,你看我这字写得如何?
我起身走到写字桌前,假意端详着,对于书法,我实在是门外汉。我说,随即看了眼师傅,又觉得说得不妥,便补充了一句,但肯定是很好的。
是嘛,好在哪里?
师傅这一问,倒把我问懵了。好在他给铺了个台阶,你说哪几句写得好?
我看着宣纸上的字,瞪大眼睛看,看了一会就觉得每个字仿佛都成了一个个舒展筋骨的人,这些人里,属这两排舒展的最为大气: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这倒也是我最喜欢的两句。师傅说。
最近复习得怎么样了?师傅问。
复习得挺烦。我实话实说,感觉压力很大。
师傅说,有压力才有动力嘛!是要认真复习,你毕竟是重点大学的本科生,可别像王瑞那小子,就是不用功,考公务员考了几年,一开始就差三分,后来越差越远,我现在对他算是失望了。但接下去师傅的话似乎就另有所指了,他说,小于你还记得你才来上班时我找你谈的话吗?对于你们这些年轻人,我真的特别鼓励你们往更好的前程去奔,考公务员、考研,再或者在本系统里往上爬,多好,非常好,只要你们有能力、有本事,都考走了我才高兴呢,因为你们毕竟管我叫声师傅,是我带出来的,我脸上也有光。但我总觉得做事情不能太看重结果,过程更重要。你说呢,小于?
嗯。我点了点头。
师傅继续说,其实你现在的工作环境,你现在的经历,同样也是一个过程。我想,很多年后,你再回想这段你现在不喜欢,甚至很厌恶的生活时,他教会你的东西或许比你想象中多。

刘亚伟-《日记——夯墙》38×46cm 布面油画2011
见我一脸茫然,师傅又补充道,我直说吧,考研我支持,但本职工作要做好。——今天放风的时候刚好被我看到了,你不该那样对待那孩子,他们是犯人不假,但也是人。
师傅饶了这么大个弯子,原来竟是为了庄青——一个罪犯,一个强奸杀人犯,现在,他在为这个强奸杀人犯着想,为了他在批评我。
我一肚子委屈和不服,但我不可能起身反驳他。我没反驳,但我的不满全都写在脸上了,同时也被师傅看个通透。师傅说,小于啊,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是唯一跟犯人接触的人,也是唯一陪他们走完最后一程的人,你说难道我们不该抱着理解的态度去看待他们吗?他们是做了错事,或者说是大坏蛋,是人民和社会的敌人,可是亦敌亦友啊!你如果不能试着理解他们,走近他们,你怎么能做好一名狱警?你也知道咱们监狱现在人员的状况,一开始我就打算让你多看看心理学方面的书,计划让你兼做犯人的心理工作这块,可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
我被师傅说得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好像自己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跟那些犯人一样了。最后,师傅说,小于,你是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人很聪明,懂得多,学东西也快,其实很简单,你只差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一个认识的问题,只要想明白了,这点工作难不倒你的。在考研的同时,我希望你成为一名合格的狱警。
末了,师傅说,庄青这孩子最近有点问题,你抽空找他谈谈吧!
我?
对,难不成让我跟他谈?师傅说。
噢。
你也比他大不了几岁,他一定更愿意跟你说。对了,还有那个陈一河,也有问题。
噢。
我从师傅宿舍出来时,师傅又说了一句,对了,你以后不要上班的时候看考研书了,下了班回宿舍再看,休息的时候再看,要是嫌吵,我给你推荐个清静的去处,出了监狱大门往右走两公里,翻过山坡——只要你有那个胆量。师傅狡黠地说道。
4
我女朋友给了我两年的时间,她来信说等我两年,如果我考两次还没考到青岛,她就跟我分手。为此,那些闲班的白天,我经常会走出监狱大门向右两公里,翻过那座山,在另一面的山坡上看书。那一面的山坡相对平坦,没有成块的石头,取而代之的是相对柔软的细沙。那里海拔较高,阳光也更充足。人躺在沙子上,阳光照下来,天堂一般。唯一的缺点在于,从山坡向下望去,远处那片相对平坦的开阔之地,是一片坟地,依稀可见错落的墓碑横七竖八地散落其间。
墓地倒吓不住我,大白天的,总不至于碰见孤魂野鬼的。倒是师傅下达的任务几乎难倒了我,让我主动跟一个罪犯说话,还不仅仅是打个招呼,而是要挖出他的所思所想,帮助他们处理心理问题。怎么可能?
很简单啊!瑞哥说。你不是说庄青那天本来想跟你说什么来着嘛,这就代表他有跟你讲的欲望。你下次看管他们放风时,只要主动往他所在的位置走走,别总拉着个脸一脸凶相,让他觉得你是可以诉说的对象,就可以了。
哇靠,这么麻烦。我直接提审他到审讯室来问不可以吗?
情境!要注意情境你懂不?你像开会一样,他不一定会和你说。再者说,你不是很抵触主动跟他们说话吗?
嗯,也对。
我照瑞哥说的办了。
第一次,那是一个风很大的下午,犯人们在操场上劳动,我看庄青蹲在角落里擦栏杆,就晃晃悠悠地走了过去。我在他身后踱步,踱来踱去,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转头上扬看了我一眼,于警官好。
嗯。我瞥了一下他,好好干,那里那里,还有那里都要擦干净。我指手画脚,装作例行公事地停留了片刻,见他没反应,我只好再次踱步往回走。
来了来了来喽,哪里没弄好于警官?我帮他。大老远地,陈一河拎着一桶水跑了过来。陈一河是贩毒进来的,就等着宣判呢,他也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贩毒的那个量,枪毙他十次都不为过了。但每次见他,他似乎都毫无死相,是他们监室的乐天派,也是他们监室的头头。按说他这个年纪的人,该有几个同龄狱友围在身边,可偏偏每次见他,他都和庄青在一起。有庄青的地方,总有陈一河。陈一河胡子拉碴、体形魁梧,庄青则又白又瘦、一脸娇弱,这两个人形影不离地搭配在一起,就像老子和儿子。庄青对陈一河,也确实像儿子对老子一样,有几分敬畏。见陈一河过来,他赶紧往旁边让了让,腾出地方给他蹲。我想起师傅的话,从背后盯着陈一河看了一会,觉得他不像有什么问题。至于庄青?我突然想,有陈一河这么个老子罩着他庄青,他还能有什么心理问题?
第二次,他们在加工纸箱。他们有任务量,所以不敢懈怠。我走到庄青身边时,他正忙个不停,显然,他不擅长这个。一见到我,他竟有些紧张。这一次,我直言问道,庄青,你没话要对我说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他身旁的陈一河用胳膊碰了碰他,于警官问你话呢。
没有。庄青头也没抬,自顾自嘟囔着。
报告,他说他没有。陈一河说。
我听到了,不用你说。我气急败坏,站起身来。陈一河仰头狐疑地盯着我,我瞪他一眼,走开了。犯人们面面相觑。
真是不识抬举,问他也不说!这工作要怎么做嘛!我发着牢骚。
瑞哥说,别急,慢慢来嘛,时机成熟的时候他自然愿意跟你说。
愿意跟我说什么?我他妈怀疑他就是什么事也没有,故意耍老子玩,害老子挨领导批。
不至于吧!瑞哥说,他们这种人,没那心思找乐子,等死的人了。我听说庄青下个月就要执行枪决了。
“枪决”这个词从瑞哥的嘴里蹦出来时,我心里竟突然有一些不痛快。我管辖的那个监室,都是些重犯,死刑再正常不过。可把死亡安排在这个二十一岁的男孩身上时,我还是于心不忍了,我为他感到惋惜。我知道,他就要死了;我还知道,他有些话没对我说。
究竟是什么事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师傅说,就把他当成一个弟弟。可是弟弟是什么样的?对待弟弟又该是什么样呢?我不知所措。记得以前听父母说,在生下我的次一年,他们又怀了一个男孩,当时他们担心负担不起生活,打算晚几年再要,于是就做了流产。又过了三年,当他们计划给我个弟弟(或妹妹)时,却发现再也怀不上了。如果当初他们选择给予那个男孩生命,那么他现在跟庄青应该是同龄,如果那样的话,现在,当我面对庄青时,一定不会这么无措。起码,当我想到像对待弟弟那样对待他时,我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罢!
5
我是在会见室见的庄青。
那是第二天的晚饭后,别的犯人在例行公事看新闻联播,我单独把庄青叫了出来。
他推门进来时,右胯似乎扭伤了,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子前,扶着桌子缓缓坐在了我对面。他先是看了看屋子四周墙壁,又看了看我,神情似乎变得紧张起来。大概他还不大习惯屋子里只有两个人。
他定睛看着我,眼神里不再有第一次那种求助般的欲望和说话的热情,显出更多的苍白和麻木。
我最先开口了,庄青,现在你别把我当于警官,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属,现在我来看你了,监狱有规定,我们只有一刻钟的时间。还记得上一次家人来看你是什么时候吗?

刘仁仙-《繁花系列 1》 160×120cm 布面丙烯 2013
提起家人,他满脸失落,我知道我说错话了。听师傅说过,庄青进来后,他爸妈只来看过他一次,当时,他的妈妈激动地拿着电话说个不停,他的爸爸则自始至终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显然他爸爸被气得不轻,至今不肯原谅他。庄青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尤其他爸爸,戴着个眼镜,看得出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我让他们失望了。庄青终于开了口。看得出,他眼眶里的冰似乎在慢慢融化,融化成一包热情的水,他低下头,我分明看见泪水涌了出来。
他用袖子擦了一把眼睛。似乎要开口,又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门的方向。
没人。我提醒他,只有八分钟了,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他身体微微颤抖起来,趴桌子上呜呜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含糊其辞地说,于警官,第一次见你我就想到了我哥哥。我想跟你说话,想跟你做朋友,真的,你相信我。可我知道我没资格,我是一个罪犯,我就要被枪毙了,我,我他妈现在跟你说这些其实根本没有意义。但是,在我生命的最后关头,我想找个说话的人,我不想每天这么冷冰冰的,直到死,那样我在那边肯定会很孤单……
他似乎想表达的太多,一直说个不停,说得语无伦次,我根本插不上话。但每一句我都听得异常认真,并且也听懂了他的意思。说白了,他其实在忏悔,他带着悔恨,想到死亡时,他无疑不想这么死去,跟着监狱里的其他人一起这么死去。因为按他说的,到了另一个世界后,他身边也全是犯罪的人。
那一刻,我开始可怜他,可我救不了他,他是个犯了罪的人。同时,我也不可能陪他一起死,我想我能做的就是聆听他憋在心里的话,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给予他一些快乐。如果可以,我会跟领导申请送他上路。
他絮叨了十分钟后,终于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后,庄青对我说,于警官,我那次想跟你说的是,我看见自己的灵魂飞了出来,真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它飞了出来,在空中飘来荡去的。
哇靠,真可笑。我拍了下脑门,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个吗?
他狐疑地歪着头,那意思似乎在质问我,这不严重吗?
好吧,我得承认,最初,当师傅对我说他有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面临了什么现实困境,比如是不是狱友欺负了他,或者是不是他想见哪个亲人,可我万万没想到他跟我说这么虚头巴脑的东西。好吧,这是我的工作,我想起了师傅的话,我决定认真聆听,并且分析庄青这话的来源。
他继续说,我看见我的灵魂就在我前面,他用手指了指自己额头的前方,飘着。他向上翻着眼睛,人嗖地一下站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那一刻,似乎危险将立刻光顾我,我真怕眼前这个犯人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可显然这一次我判断错了,庄青并没有那个打算,他不好意思地退了回去,又坐了下来。
我整理下衣领,发现师傅说的太轻巧了,我真的没办法不把他当成一个犯人,他是人这不假,但他首先是个犯人,这是他区别于正常人的特殊性。
我问他,你别扯了,你能看见你的灵魂?他是什么样子的?
他是一匹马。庄青说。
一匹马?你是说你的灵魂是一匹马?
不,不是,好像又是一条龙,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挺大的一个东西,我只知道他是我的灵魂。庄青说。
你别装疯卖傻了,还一会马,一会龙的,你肯定是有眼疾,青光眼、白内障?反正是眼睛的毛病。我脱口而出。
他显然不大高兴,又一次沉默无声了,嘴里嘟囔着,你应该相信我。
可我怎么相信你?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的灵魂?我质问他。
他跟我说的。庄青答道,他在怨恨我,我把它弄脏了,他在怨恨我,所以他从我的身体里脱离出来了,我好脏、我好脏——呕、呕——,庄青越说越激动,他双臂抱在胸前,不住地做干呕状。
停,打住!我说,你用不着这样。你现在的意思就是你把你的灵魂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了,好比是另一个人,噢,不,不是人,是另一种事物,你觉得你玷污了他、对不起他、配不上他。可我问你,庄青,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强奸人家的时候,你——
我想说,你对得起你的灵魂了吗?可话到嘴边还是收了回去,庄青在瞪着我,充满了仇恨。我知道,作为一名警察,我几乎失态了。
他低着头,双臂夹着头,像头疾发作了一样,小声说,我错了,这是我该得的报应。他们都瞧不起强奸犯,他带头搞我,他想搞死我……
谁?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跟我说,我跟领导反映。
哧——,跟你说有什么用?你会信吗?他把他鸡巴放到我嘴里,跟着他下意识地扭了扭屁股,谁叫我干了那事,这就是我应得的报应!

刘仁仙-《繁花系列 2》 160×120cm 布面丙烯 2013
庄青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一下想到陈一河满脸的络腮胡子。
岂有此理,在我管辖的监区竟然能出现这种事。
你放心,庄青,这事交给我,这事如果查实,一定会处理他的。
处理?呵,处理得过来嘛!几个人架着你,轮流来……说着,两行清泪无声地从庄青绝望的眼睛里流出来,那双眼睛,绝望得能让人做恶梦。
他开始不信任我了,说,反正是要死的人了,反正已经不干净了,怎么死都是死。
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爱干净的男孩。这一刻,我突然发现他区别于其他犯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他的干净,出奇的干净,脸上皮肤光洁无痕,手臂白皙、手指修长,连同样的囚服,好像都比别的犯人干净得多。
跟庄青谈完后,我真恨不得冲进监室把陈一河押出来,好好提问他。可我又一想,这种事,还得从长计议,我怎么问得出口呢?更重要的是,陈一河那种监室一霸,凭我这么个乳臭未干的新狱警,我能对付得了他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
6
我和瑞哥要进县城的前一晚,师傅塞给我一个大信封,让我替他寄一下。递给我信的时候,师傅说,江月何年初照人啊?我的《春江花月夜》,就看你小于的手气了。
又参加比赛了?瑞哥问。
这次可是《人民日报》办的。师傅说。
哇,师傅威武!等获奖了一定要请徒弟吃饭哈?
一定一定。
要去海边吃海鲜大餐。瑞哥说。
对,咱去海边吃海鲜大餐。
大家都喜欢说海,都喜欢说到海边去看。好像海离我们很近似的,可结果……人人都知道。那段时间,我打听得知,那个叫刘刚的警察,也就是瑞哥的前辈,就是扬言一定要走到海边去看看,某一个晚上真的付诸行动,却从此消失,人间蒸发了。听说,那个叫刘刚的警察和现在在监狱执勤的武警是老乡,可瑞哥变着法问过那个武警好几次,他是不是回老家了?是不是真的跑到海边常驻、隐居起来了?那个武警却打死都不肯透露半句。
我们回到监狱时,已经快到次日了。还没睡个囫囵觉,就出事了。
事情应该是以我监室的一声惨叫开始的,只是我不在现场,不清楚当时惨叫的究竟是陈一河,还是庄青。在值班狱警正瞌睡的那个时间,惨叫声将狱警惊醒。狱警赶到监室时,庄青已经被揍得口鼻直冒血,被紧急送往医务室。第二天一早我在医务室见到他时,他两颗门牙均已脱落,嘴唇和脸都肿得老高,右眼的眼角也残留血渍,现在的他,跟干净一词完全沾不上边,他神情恍惚,但那股仇恨催生的狠劲还未散去。他嘟囔着,妈的,老子也是杀过人的,别把老子逼急了。
我走到他跟前,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张着嘴,胸此起彼伏的,呼吸浓重。
我没有继续问下去,静静地等他回答。
过了一会,他看了我一眼,先是一愣,慢慢地情绪稍微平静了些。他看我的时候,并无敌意,反而让我有种温暖感。瑞哥早就说过,他说庄青看你的眼神跟看别人都不一样。我当时还问过瑞哥怎么个不一样法。瑞哥说,他看别人时很冷,要么有仇恨,要么有蔑视,他是不合群的。但他看你时,他的眼神就跟正常人别无二样了。他相信你。
我想瑞哥说得没错。
庄青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嘴现在的样子说起话来很费劲,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他说,我把他咬了。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又对你——
妈的,看老子不收拾他。
我气急败坏,冲出医务室就往监室走去。我听到庄青在后面喊我,于警官、于警官——
我踹了几脚监室的门,值班狱警把门打开后,我看陈一河蹲在监室最里面,便直接冲了过去。他起身的同时,下意识地用右手捂着裆,很痛苦的样子,我的右拳就直接冲他脑袋抡了过去。
他被我打得火冒三丈,起身要回击。这时,值班狱警已经开始往外拉我了,别这样于哥,有话好好说,跟个犯人这样犯不着。
就是就是。后面有人应和着。
陈一河也已经被人架了起来,他的双手被其他犯人拽着,他试图用脚踢我,但够不到。
你疯了吗陈一河?值班狱警冲他吼,你还想反抗?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他的脚终于收了回去。可人还在气头上,你个嫩伢崽打老子?他冲我咆哮。
我说,你凭什么那么对他?
他个强奸犯,我那么对他怎么了?他咬牙切齿,所有人都该那么对他。显然,他知道我指的是庄青。
我说陈一河,我右手食指指着他头,你他妈也是当爹的人,你的小孩也就他那么大吧?你怎么下得去——手?我的“手”字几乎咽了回去,因为他下的不是手。太无耻了,变态!我往地上吐着。
老子不无耻就他妈不来这种地方了。他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
我说你这辈子就白活,你他妈就枉为人,你这种人就该去死。
他目瞪口呆,愣在那。其他犯人也目瞪口呆,愣着不说话。他们的眼里充满惊讶,在惊讶的同时,一种我这辈子从未见过的悲伤在那里闪动。
于哥,唉。身后的同事拽了我一下,松开了手。
陈一河的手也被松开了。但他并没有趁机会反击,只是愣在那。监室安静如刑场。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瑞哥说我说错话了,师傅也说我说错话了,对我的鲁莽举动,就连庄青本人也没发表过态度,虽然他是事情的导火索,我是在为他抱不平。
庄青伤好后,被关进了另一个监室,脱离了陈一河的魔爪,至于他还会不会陷入别的犯人的魔爪,我不得而知。因为陈一河已经把我搞得焦头烂额了,我真的没时间去想其他事。我连本职工作都做不明白。

刘仁仙-《繁花系列4》 120×160cm 布面油画 2013
那件事发生以后,陈一河对我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让我觉得他之前对我的言听计从,服服帖帖都是装出来的,不过是给我面子罢了。像他说的,我是个嫩伢崽,不识抬举的嫩伢崽。现在,在他的影响力下,当然我相信并不是他煽动的,而是犯人们自发的,总之,监室里的所有人都不再给我面子,一个个都在针对我、在与我消极对抗着。这种对抗,体现在工作中任何一处细枝末节,他们只针对我一个人,只要是我值班,我说什么他们都爱答不理,你往前推他,人家不仅不走,还在使相反的力。他们最习惯也最常用的对白就是大声冲着天花板,或者大声冲着操场喊,反正咱们这些人呢,也不算是个人,活不活的能怎么地呢?
我听着极其不爽,可又能怎么办,这话是我说出去的。
我现在越来越想逃离这个鬼地方。
7
出了监狱大门,右转步行两公里,然后翻过石头山。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件事我干的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庄青离开监狱后。有时我也会下了班去,只要天还没完全黑,只要还有光线让我看看书,哪怕没有光线,我也想在那里躺一下,脑子里想点事,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想。
有一次,我摸黑刚爬到山顶,距离我一百米外的地方就亮着一团火。吓得我一身冷汗,赶紧退到一块石头后面。
我背靠着巨石,不敢回头看。我闭着眼睛,甚至不敢睁开,就怕一旦睁开眼睛,那团火正飘在我眼前。我在想怎么办怎么办,这地方太晦气,你晓得有多少人从这地方走向死亡,保不齐哪个怨气大的又回到这里来了。
脑子里乱如麻,正待理清思路准备付诸返回行动时,石头后面依稀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刘刚,刚子,今天是你的忌日。不,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今天死的,权当是吧,我记得我是两年前的今天在这里捡到你的鞋的,我知道你肯定是寻了短见,我才不相信你去看海呢,哪里有什么海呢!今天兄弟陪你喝点,你要还记得兄弟晚上就给咱托个梦,告诉告诉咱你在那边咋样,连个尸体也没留下。
接着,传来了一个大男人吭哧吭哧的哭声。哭完,男人清了清嗓子,对着坟地的方向吼了一嗓子蒙古长调,接着传来浑厚的男低音: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啊,你在山下唱歌……声音再次哽咽下去。原来是瑞哥。
我走过去,他没发现我。
我在身后拍他肩膀,他吓得一屁股差点坐到火堆里。转身见是我,就也招呼我坐下跟他一起烧纸。纸是先前进县城他偷偷买的,还有蜡烛,还有蒙古高粱酒。瑞哥说酒是他找了好多地方才买到的。
我说,你这是何苦呢?
他说,人,总得信点啥才有奔头,哪怕是错的吧,否则成天看着一个个犯人拉出去枪毙,可怎么活啊?
我说你可以学师傅,找点爱好不好吗?
师傅,哧。瑞哥说,你以为师傅真的写一手好毛笔字啊?你见过他写?
见过啊,话一出口,心里早没了底气。
他说他获了这个奖那个奖的,谁知道真的假的呢!反正有一次我上网无聊,查他之前说的那个什么杯的书法大赛,结果根本就没查到有那个杯。
不是吧!
你爱信不信。
那晚,我和瑞哥在繁星密布的山坡上边抽烟边聊天,聊了很久。我和陈一河打架的事在监狱传开后,不仅犯人一个个成了刺头,师傅批评了我,就连其他同事也都对我另眼相看了。只有瑞哥,还会对我说说心里话。瑞哥说,小于,抽空给老陈道个歉吧!说着,他点着一支烟。
老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陈一河哇。
瑞哥对他的称呼让我一时不太习惯。
老陈也要走了,听说也是下个月宣判。这都月底了,没几天了。
瑞哥见我没回应,补充道,道个歉不丢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的。我想说其实我很后悔说出那样的话,可人在气头上,话收也收不住。但想了想,还是没说,有些话只适合放在心里。就像庄青临行前,我送了他最后一程,把他从监室送上了警车。临刑前,庄青整个人几乎崩溃,他被架着往外走,开了一道门,又关上一道门,又开了一道门,又关上一道门……他的双腿就像被抽出了骨骼,尿液从裤管里滴出来蹭了一路,但没有人笑他,犯人们都趴挤在监室门口,像送别任何一个朋友一样的送别他。他面如死灰,惊恐在眼睛里收也收不住。他以前问过我,子弹打在太阳穴上是什么样?会不会把脸弄得很脏、很难看?他甚至想让我违反纪律赐予他一个好看点的死法。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只能安慰他说,没有那些你担心的过程,也没有疼痛,总之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也看不到,你的脑袋套在布袋里,没人能看得到。
在他被拖出去的那一刻,本来准备好的一箩筐的话都不再有说的必要,我只是陪他走了从监室到监狱大门的那段路。
上车时,他颤抖着双唇,哆哆嗦嗦地对我说,于哥,下辈子见了,有下辈子,我们做朋友。我相信这句话他准备了很久。
我故作轻松地说,这辈子就是朋友啊!
事实上,送庄青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应该跟陈一河郑重其事道个歉。那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想这件事,想得失眠。迷迷糊糊中,我似乎听到了两声枪响,正奇怪怎么会响两声时,庄青走到了我梦里来。他穿的仍旧是那身囚服,只是被他穿得格外潇洒,他精气神十足,是笑着冲我走来的,从脸到脚,全身干干净净,看得人心情愉悦。他走到我面前一米处,停了下来。我试着抓他,抓不到。他安详地看着我,跟之前我见过的他截然不同,像是洞察世事,专等我开口。
我就把烦扰我的话讲给他听了,我说庄青,我要不要跟陈一河道个歉呢?
提起陈一河,他沉思了一会,然后神情又从凝重中恢复过来,我见他冲我竖起了大拇指。我问他,庄青,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他回答说,我找到我的灵魂了,他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我还想问他什么,他没理我,转身向前走去了。
我喊他,庄青、庄青,他只是回身冲我摆了摆手,然后,大步流星朝着前方的漆黑走去。
他是我亲自送的第一个犯人。我想,第二个会是陈一河。我希望我只有机会送他们两个。
报告!
进来!
我进师傅办公室时,师傅神色慌张,正顺手把一张报纸团了团扔进垃圾桶。
我问师傅你怎么了。
师傅问有什么事?
我说我想请示一下,跟陈一河郑重道个歉。
好!我来安排。师傅说。
离开他办公室前,我鬼使神差地问了句,《春江花月夜》怎么样了?江月照到你了没有?
他有些不自然地说,照到了照到了!改天请你吃饭。
嘿嘿。
我觉得哪里不对劲,于是回到办公室后,赶紧找出了当天的《人民日报》,获奖名单已经登出,但没有师傅的名字。
我呆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