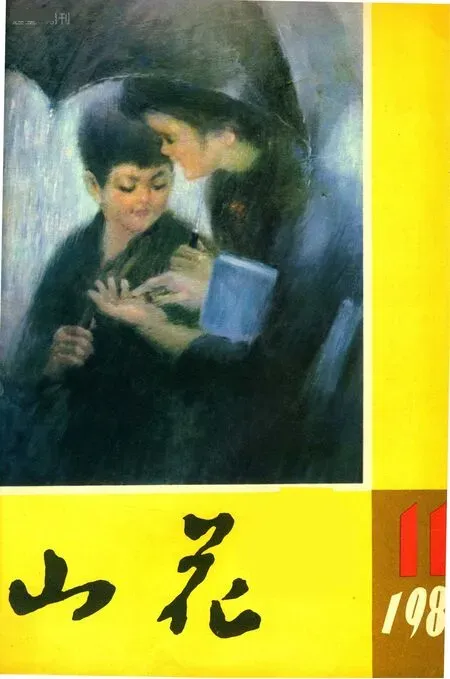陌上行
2014-12-02
雨
下雨。
回国正赶上中秋节,又是下雨。秋意盎然。不经意想起那首歌:
总归是秋天 总归是秋天
春走了 夏也去 秋意浓
......
雨意朦朦是我所喜欢的,好像喧嚣的世界突然停步了,我也可以安然休息。说穿了,就是可以不用斗志昂扬野心勃勃上蹿下跳了。睡觉,睡觉,像青蛙一样冬眠。
雨声分季节,好像也分地域。
大雨哗哗下起来的时候,真是惊天地的感觉。大雨如注,片刻不停,以为是大雨如柱了。窗前的白果树在风里撕扯,摇啊摇,像呐喊,蒙克的《呐喊》。
等下去捡白果吧,我叫着。
风停雨住,大地清新,空气里留下的是清冽。白果树上的果子像刚被雷劈了,炮弹炸了,一地碎果,青青的,还带着白霜,像绿色的葡萄,开花的葡萄。还没熟呢,就给雨打风吹落了。街上的行人也都像吹散的叶子四处飘零做鸟兽状,躬身弯腰,缩着脖子,快步行进着。
第二天雨接着下。小姜的补习老师来电话说,她家的后墙进水了,泥浆石块把玻璃砸碎了。不能来上课了。
停电。街上的救护车“呜呜”叫着跑过。
我的机票是第二天傍晚的,心底庆幸,坐飞机,不是火车,因为电视上讲铁路被冲垮,火车停运。所以把卧铺票退了,换成飞机票。
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正打理行李,手机响。告知飞机也取消了。窗外的雨“哗哗”还在下。心里震惊加好奇,为什么要等到临上飞机几个小时才告知取消,这让人如何做计划。
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弟弟在旁边插话道。
去凤城吧。当机立断,一车人立马打的去凤城。
凤凰城简称凤城,不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是110公里外的一座小城,从前的一个过站,如今变成了首发站。
三十年河东,这连三天都不到,我们从搭飞机的侠客变成无座位的游民。连火车票都没有,却要到另一座城市去搭火车。
雨还在下着。出租车跟蚂蚁搬家一样早躲起来了。一是下雨,再就是火车没了,乘车去另一个城市的人多了。弟弟好不容易截了一辆,还因为是熟人。上车,去凤城。
火车沿路的这些城市,名字熟悉,却都没去过,鸡冠山,凤凰城,宽甸,老虎岭,名字好像都很有故事。
车轮飞,汽笛没怎么响。路上几乎就没什么车,高速旁边的大桥墩都给雨水冲塌了。豆腐渣工程?脑子里闪过这些句子。暴雨连绵几天就成了这样,这么不抗冲,不是豆腐渣是什么。美国也会下大雨,大雨如注的那种。我住的那个地方也会有小小的水灾。因为地势使然。要不不下雨,要不下起来就吓人。可很少有公路塌方,停车停飞的情况。
之所以想到美国,是因为广义上中国的城市面貌已经很像美国了,不全米国吧,也是面国,米国的堂弟。
站在街头,马路对面就是麦当劳。小姜一指,说,我来过这里。
梦里吧。我想说。你怎么会来过这里?南朝四百八十寺,你以为是穿越呢,那么容易就多少楼台风雨中了。
可是我明白。
一面山应该是个小镇吧。小时候我总把“一”当成“移”。这山怎么会移动呢?还跟着我爸去赶集。坐火车赶集,因为没见过,所以稀奇,一定要去,赶集好像买了只鸡,大公鸡,红红的冠子,雄赳赳的眼神,黑得透蓝的羽毛,抱在怀里,有一种奔腾的挣扎。说是赶集,地方并不是很大,人也不是很多。有一个小高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那种高地。卖东西的小贩头披着围巾像鸟翼,露出的脸颊却像山里红。回家后,我妈早等不及地拉我去炕头。
快把手捂在被子底下,我妈催促道:冷吧?嘘寒问暖。可是冷却一点也不记得。小时候好像对冷是免疫的。
如今这个出租车带着我们一路飞奔着往凤城驰去。说飞奔,其实一点儿不快。司机说不敢开太快,下雨,路滑,安全第一。而且火车要到晚上才开呢,这才刚过中午,一个小时保准到。
趁着空隙,想起来也许火车站可以买票呢,不如先叫弟弟去询问一下。
我妈说,叫他也没用,自行车刚给偷了还得走去车站。
偷车好像都成了家常便饭。这辆自行车给人偷去了两次了,又给找回来两次。这是第三次了。倒像人间正道是偷车。第一次给弟弟自己看到了,在街角闹市旁。我的车怎么在这儿?他惊奇,上去打开锁,骑回来了。然后又给偷走了,又重复被找到。如今又给偷走了。自行车快赶上诸葛亮了,被人一顾再顾连三顾。上锁都没用,得绑在树上,门上。
到汤山城了。我爸指着窗外说。
汤山城有温泉,如今的温泉浴很有名。小时候来过这里。
那一次也是跟我爸出去玩,我爸大概想要个男孩的,结果是个女孩儿,就把这十八般武艺也交给女孩儿。我们去钓鱼。河水清澈,能看到脚底的石子沙砾,竟然抓到一只小螃蟹。我把它放到随身带的小竹篮里,还时不时加点儿水。旁边有人在炸鱼,“嘭嘭”地山响。我爸拉着我赶紧往岸上躲,匆忙间,小螃蟹跑了。鱼也没钓到,父女俩到旁边的小饭馆吃了午饭,然后坐到铁路边的枕木上休息。枕木油黑,阳光照出雾一般的沥青味。父女俩又坐马路边小憩,看人来人往。回去的路上,要经过一片苞米地。青纱帐一样,都是绿茸茸的影子,我呆在里面不肯走了。我爸吓唬道:再不出来,熊瞎子就来了。老熊最喜欢吃苞米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风吹大地,玉米秸沙沙响,仿佛老熊的脚步。我吓得比熊瞎子掰苞米跑得还快。

王 锐-《那山头》 145×123cm×2 布面油画 2013
也是这次钓鱼回来的路上,坐在火车上。凭窗远眺,一片广袤的土地。天尽头,绿油油的草地成片,有牛,羊在吃草。
这些牛羊好奇怪啊,很小,低着头只管吃啊吃。那么遥远又那么近,是迷你小牛和小羊啊。我兴奋地叫起来,嚷着指给我爸看。可是他正跟什么人聊天聊得起劲儿,怎么叫也不理我。所以呢,这个迷你牛羊真是死无对证。
他聊完了,我又兴致勃勃地提起刚才看到的那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小牛小羊。我爸只是嗯嗯着,并不当回事儿。儿时的眼光跟成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想,许许多多年后,那个场景还会在我脑子里游弋出现。扑朔迷离,似真似幻。不成比例的真实,仿佛那些天边的牛羊电影屏幕一样拉到眼前。可是它们确确实实在很远的地方啊。我当时的惊奇是觉得自己发现了小人国,里面的牛羊就该是这样的迷你而真实。
无论如何,每次离家都是坐着火车,只有这次是沿着铁路线坐出租车去那么远的一个城市。沿路的高速路牌也像美国指示路标那样高高地悬挂在路侧,只有时不时出现个大牌子在眼前晃过,大牌子上的字迹告诉你:这里是最好的地方,快来投资快来玩。仿佛确切地提醒你,是在中国,是充满变化契机的中国。
出租车进了凤城,看起来不像个小镇呢。旁边的高楼大厦跟我来的城市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城市像积木,摆的人兴致盎然,看得人盎然兴致。住的人呢,黯然吗?空气就不说了。饮食却不可避免。
发现国内的色彩很奇异。所谓奇异,就是颜色的特异好像跟原本的色系不是一个统一体。西红柿的红是紫红,摔打过的紫。胡萝卜像橡皮;三合面的馒头像肿胀的脸,黄的发亮。街上人的衬衫颜色也是奇异的,难以描述是哪一种颜色。不纯绿,不纯黄,不纯的扎眼。就像我在美国的街上看到那样的打扮,浑身肉滚滚的女人,手里牵着一条狗,黑色鸭舌帽下面露出一条火焰山样红彤彤的马尾辫。我想这就是文化震撼,文化差异的确切表现。
一行人风雨兼程到了车站,第一件事去买票。当然没有。站台票,当然不卖。
站台票怎么都不卖了?那怎么送人?不知道,但是不卖。
两个没票的人变成了双倍,我和小姜加上前来相送的姥姥姥爷。旁边的两个女子也跟我们一样。乘出租车跑到凤城,飞机票取消了,火车票也退了。老实讲如果那一刻有什么魔术可以一下子把我变成小飞侠那样飞走,我是愿意的啊。
发短信给同学,人回:Oh my god.Oh your god.上帝啊,求你的上帝吧。
时钟快转,各人买了一张到下一站的火车票。那两个女子也是各持短程车票一张。火车上才发现,这一个站地的火车票都成了身份证了,每人一张。怪不得不卖站台票。到下一站的无座车票也是一张站台票的百倍。
没有票的人笼中鸟状聚集在餐厅里,临近的车厢过道间。小姜坐在行李箱上,悠然自得,引得旁边的站客们一个劲儿地夸奖。我想说,一个小时以后还是这样才是真乖。
餐车像备用车厢,还没开里面已经坐了八九十来个人了。环顾四周,这里还真不错,白桌布亮晃晃,空调凉嗖嗖。如果是笼子也算是高端笼吧。一男孩说:餐厅越呆越冷,后半夜就冷得受不了了。
这男孩儿也是一无票游民,大家站在车厢间等卧铺,间或聊起了天。小姜首当其冲是话题,其中的两位拿到卧铺后更表示如果等下拿不到,可以带小姜去他们卧铺休息。还好大家都拿到了,而且还在同一车厢。
这大男孩上大二,父母是做生意的,他想读MBA,去加州。于是剩下的路途就一直跟我探寻米国探寻加州。小姜在卧铺上看Harry Potter(哈利波特),对面上下铺的母女俩是去西藏玩。现在的国人真是不同了。我还从没去过西藏呢。看那闲言说,月收入三万可考虑低端欧洲游,月收入一万到两万请选择东南亚游,月收入低于一万请选择国内游,月收入低于五千请选择省内游,月收入三千请选择郊游,低于两千请选择花生油,低于一千的请选择梦游。低于0至五百请选择地沟油。
梦游的好像比较浪漫吧。正胡思乱想间,男孩手机噶愣愣响。北京机场有人扔炸弹,他说。
我心里一跳,今天还不够折腾吗,飞机飞机取消,火车火车票也退了,还要无票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乘车。现在,又来了什么炸弹。
炸弹是谣言,好像说是什么人不满,放了一个比较响的爆破物。声音像炸弹,山寨炸弹。
接下来,还是听这大男孩讲他的理想,抱负。现在的小孩儿都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吧,你看他老早就计划好了,MBA读完就回国,接替家族企业。当然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就那么决绝。这期间的纠结谁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他说。
会有的。我向他坦诚,就像现在,包围在自己熟悉的语言中,眼前的景物,人物都是习惯的放松,那是一种非常惬意的享受尽兴。但是数小时之前,车站的奔波等待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乃至深恶痛绝的。这就是纠结啊。

王 锐-《一棵有叶的树》 140×100cm 布面油画 2013
吃在故乡
回国的早餐最令人兴奋。大街的早晨就像人生的盛年。街边的小摊旁蒸锅上的蒸气扑腾腾冒,掀开锅的一笼屉包子白白胖胖,座位上的人面前的鸡蛋饼金黄,小米粥喷香。小米粥还带吸管的,滑腻馨香。整条街都像是在叫:我要吃呀。
回国的时候,吃了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呢?这是朋友常问的问题。
午餐的一道茄子烧鲶鱼能让我想起好多故事。茄子烧鲶鱼,撑死老爷子。
小时候吃过的茄盒可以和潘多拉的盒子媲美,就是茄子切大片,中间夹肉,红烧,带一点儿汁,恰到好处。那情景里的大铁锅黑亮,茄盒在油锅里滋滋作响,我爸在炸茄盒,我在旁边转悠,闻一闻都是很香的。
茄子不见得一定要下油锅。凉拌茄子也一样入味,就是把茄子蒸熟,撕条,凉拌。蒜茄子要用刚下来的小茄子,黑黝黝的亮,腌渍好的蒜茄子也是同样的色彩。早餐就白粥一起吃,清爽下饭。
茄子,土豆,辣椒的三鲜。比较家常,像秋天南飞的大雁,可以预告季节。
新鲜茄子就是生吃也很好吃。要挑细长的,嫩嫩的,一咬脆生生,甜丝丝。多么健康的吃法,不用动用任何工具的色拉茄子。
茄子的英文名字厉害,egg plant双料。双料,蛋白质蔬菜都有了。
米国的茄子也是美的,圆的,大大的,滚滚的,切片可以,切块也可以,但是都适合炒熟。蒜茄子,算了。茄子是个多么有情意的蔬菜。
留影之际,道一声“茄——子”你就是不笑也是笑了。
茄子花开,很雅很淡,有一种丁香的紫雾,却没有丁香一般的忧愁。
茄子好像也是善于入画的,印象派的静物里,紫色的代表多半是茄子。不用说,Georgia O’Keeffe(欧姬芙)的茄子是最美的茄子之一。
说完了茄子的青春时代,想说点茄子的七八十岁。
就是茄子干。
晒茄子干。从前冬天蔬菜有限,茄子于是被切成丝,片,再晒成干。别小看这茄子干,烧肉,香到绝。
茄子的贬义好像只有一句,就是形容某人脸色不好,憋得紫茄子一样的脸。这,也就是顶级了。
回国吃的这些家常菜,茄子是其中的一种,每一种如果都这样讲,绝对可以写一本美食大全。
看佳肴漫山,食客遍地。
真是遍地。每到夜晚,夜幕降临,大街小巷烤炉如春笋,烟气袅袅,熏声吱吱,气味逼人。美其名曰:烧烤。
这种烧烤倒是真便利。我第一次看到也很惊奇。一个小炭火,三五人围坐,然后肉串,鱼串,串串都放上。人影幢幢流水淙淙,很快乐。
忧心忡忡——我却想到这个词。这是从前听过的一首歌名,大学同舍每天都要放的一首曲子,忧心忡忡。
忡忡何意?这是地毯式餐馆,没人管,什么人想开,都可以端了炉火开,在马路上,公园,小区门口,任何地方开,餐馆。
有人就在楼道下面摆了一个烧烤炉,火苗艳艳,人走过一股热浪袭来。女主人,立在旁边,刚下班?来这里守株待兔,愿者上钩。
It stinks。小姜说着,揪着鼻子,跑走了。
马路边有人在淘洗食物,大盆鲜红的肉类,屈身的背影和不远处的高牌子——糖尿病医治,脑血栓广告相呼应。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在现世的生活里遥远得仿佛不存在。
跳 舞
楼下的黄毛子,每天晚上吃过饭,穿戴整齐,出门跳舞。不要以为这跳舞是到哪个舞厅场所特别的地方。就在楼下的万隆广场。每天晚上七点钟,固定时间,大喇叭一响,舞步踏起来。一溜十行,横竖成行,偌大的广场总有五六十人排列跳舞。这跳舞其实是锻炼的一种,名曰:广场舞。
他们锻炼怎么还打扮得像逛街约会,裙子,高跟鞋。运动装都少见。我总要诧异。
黄毛子是指她的头发,烫了毛毛卷,又染成金黄。黄毛子女儿都结婚了。每日打扮光鲜,早晨去早市,晚上去跳广场舞。二楼三家就剩下他们一家是住家,其他的都成了做生意的铺子,补习班的场所。
每日的这个露天舞场很有磁力。高高大大的立体音箱立在地上,电源拉着长线接到广场旁边的小屋里。小屋像鸽子笼,门上招牌像大狮子——万隆招待所。发现如今国内的商店名字都吓人,只看招牌都能唬你一跟头:“环球车行”,“世纪婚纱”,“宇宙商场”,不怕大,怕不大。
“辽阔的天空白云朵朵,夕阳映照在晚霞中”这首歌,柔婉得十八转,听起来似曾相识,像是哪个电影里的插曲。跳得人更是二十八转的柔婉。
有个动作像是纺织,或者西施浣纱,两只手臂一上一下在胸前摆动,弯腰俯身再抬头远眺。多么优美的形象,女人摆,男人摆,老太太们摆,老头也跟着摆。站在音箱最近的这位就是个老头。不能算太老,瘦老,个子不高,有点像中晚年的台湾诗人余光中。白色鸭舌帽下面是一张古铜色的脸。浅色高尔夫衫,白裤子。这就是跳舞的服装了。
东西方舞蹈太不同了?还是东西方锻炼概念不一样。老美健身房那叫一个热、情、奔、放。不出汗是不可能的,舞曲不震天响也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大家都是一身运动行头,是真的拼搏,拼命三妹也。
中国式的舞蹈嘛,摇摇身子,摆摆手,再随着小曲,兜一圈,转两转。转两转?再转十圈也转不出一颗汗珠。所以眼前是轻纱曼舞,同舞们高跟凉鞋真丝裙。晃荡的舞姿。
当然晃荡并不等于敷衍。你看各个跳得多认真,前排领队的还是统一的服装呢。还有音乐,不知名的音乐,不知唱者,不知歌名。但是心悸一点儿也不少。这是谁唱的?缠绵感伤,像似曾相识的一种感觉。
国人跳舞跳的是消遣,跳的是回忆。情歌绵绵,情意长长。我常想东西方的情感理念真的不一样,而这跳舞又有多少不是在表现这种不同呢?
老美的舞蹈课,清一色的女子,女多男没有,偶尔的一两个男士出现也像突发事件。东方男人的情结,陪伴女人,哪怕是去跳舞。中国男人这一点上真得要大赞特赞一下。生如夏草愿伴红花一世。你看那给女人系鞋带,拎背包的男士都是贾宝玉的高生与门徒。老美男士吗?系鞋带,拎背包断然不可能的。
舞曲袅袅,看前后左右男丁壮士,伸手曲膝,弯腰展臂,动作质拙中的认真,像在品味凝望东方理念的千丝万缕。千层海浪千重山,千江有水千江月。
舞曲也是迥异的。老美的舞曲铿锵有力,情歌也是激情的,配激情有力的舞姿。国内的曲子正相反。一个小时的晨光里,除了那首柔软的“纺织娘”。剩下的一首又一首的歌里不是心疼就是肠断,情困,情问,情不堪。
看大家听也听了,跳也跳了,感伤多少不知道,憧憬不少,怀想应该也不少。
此话怎讲?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动作里的蕴意。
广 州
乘飞机去广州,机场跟地铁直接连着,下了飞机上地铁。
地铁好,很清晰,站名都是双语。路线由一小串灯光显示,走过的路程就变成红的,前方是绿的。这个很吸引小姜,他瞪着瞧,然后对站名。还有认识的中文字呢,东山。还有呢?天河。立马精神百倍高,南,我认识那个南字——广州南。小姜这么一路指指点点,坐地铁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广州的地铁,比上次来又多修出许多。上次是十年前,一出站口,就听到满耳的粤语声声,心情激动,仿佛清风吹过。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
我永远永远不能忘……
邓丽君《初恋的地方》回荡着。那时候,我站在街头,站在繁忙的远洋宾馆大道前,还能记起曾经走过的街道,见过的景色。
如今,这样的记忆模糊着,像隔世的朝阳。我使劲回忆着,是在这个有粉红色和天蓝色的地方吗?我走过一个斜坡,然后一大片一大片的沼泽地,你要飞过去,越过一个高墙,然后进入一个楼里,楼里有电梯,也有楼梯,进入电梯,来到一个阶梯教室。
这样的梦境一样的情形,实在是真假难辨了。闺蜜说,带电梯的楼梯吗,现在的住家都是带电梯的,还有三十几层大楼。不是说吗,如今的广州是最不像广州的城市。
最不像。
首先就是语言。满街的普通话,满街的行人,看起来南头北脑?
腐烂的水果气味,袒胸露怀卧在路边的民工。公交车经过的窗外,一树的青芒果。小姜叫着指着。想起当年宿舍外面的米焦树。
这是不能吃的,闺蜜的女儿菲菲说。这些芒果都是洗尘的,装饰还差不多,谁敢吃,全是废气灰尘,她说。
道具吗?我说,看那硬邦邦的青绿倒真有些假的了。
真的。菲菲说,但不是吃的。
然后是人。
在地铁上就注意到旁边站着的是印度人。印度人?对,说汉语的印度人。你道是张爱玲小说里的上海滩印度人吗?不知道,反正人家汉语说得很顺溜。印度人聪明啊,经济飞跃的触角。想起小姜象棋会社里面的那些印度小孩。
站名仍然是用粤语跟普通话交叉报站。除了这点儿,几乎都感觉不到是在广州了。上海人吵着说报站名也要用上海话跟普通话,说,看广东人为什么就可以,阿拉上海人做啥就勿兴。我倒是认为应该保有原始的文化。比如去到上海滩,大鸣钟叮当,耳边吴侬软语萦绕,该是多么地闲雅与适宜。
北 京
北京是个发轻功的好机会。不是让子弹飞啊飞的那样,是白日梦的那样凝思冥想。颐和园里,长廊下,晓风习习,你可以想象黛玉,小红们,在这里走过。故宫里面走累了,歇歇脚,去卖货的小柜买根棒冰。小屋矮旧,墙上漆皮剥离。窗户却是从前的格式,纸棱窗,红漆,太阳斜照着,时光老去,时光驻留,你还要什么?
颐和园的长廊里,你可以听得到衣鬓匆匆人影憧憧,有熏香逸过,有翠鸟啼鸣。哎,我是愿意在这样的宫殿里尝试一下古人的意味的。柳树也好,就那么漂着,随风逐影,湖里划一艘小船,你就到了“五四”的春天,男人女人们在湖中荡漾,谈论爱情,谈论生活。
五四的春天是张爱玲小说里的一个场景。小说里提到一干人在湖里划船,谈情说爱。男的大都已婚,却同女生们畅游。故事是想借此良宵美景反衬包办婚姻,也即讽刺那些男人借此开放。划船的那个场景很迷人,女学生的白衣长裙,男人的长衫白手绢,清风徐徐,此情绵绵,很有“五四”那个年代的色彩。
划船好像很能催情。划船和跳舞,恋爱催化剂?
想起一个同学,年龄小,个子也小。谁也不会想到她会恋爱,二八不到。有一天,说划船去了,她跟低一年级的大一男生去的。不久,就听说他们好上了。那个傍晚如画,他们划船回来。她跟他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的,讲述,划船。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可以隔一个船头。但那之间的引力,却是可以与地心较量的。
记忆里如果有北海划船会是多么独特。
这次去北海却没什么人,也许是阴天——天上飘着毛毛细雨。

虞 华-《孕夜-04》 160×150cm 布面丙烯 2013
没排队的,也没什么船,船都在桥头落叶一般挤在一起,湖中间只有一艘小船,倒是荡起双桨。我们也跃跃欲试,可是实在阴冷,我又不会划,小姜吵着,然后就只顾对着湖边的鱼草发功,说要找青蛙。
湖里的草很多,好像是树上掉下来的。有人拿着大笊篱之类的长杆子在捞,一层层移到岸边像过草地。
说到北京,想起好多片段。
如果一定要比喻,北京像盐,美味必不可少的佐料。就是中转中枢,来来去去总要从这里过。
也像袜子。每次来去匆匆,大多浮光掠影。袜子给人看到最多也就是裤腿跟袜腰那一段。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峥嵘呢就是机场了。安检,脱鞋吧,袜子显气派了。
所以我在北京换飞机,火车,就想到了袜子,然后想到火车。
火车上也是袜子的天地。
想起一段往事,读研的时候,火车上几个同学南下,三女一男,都是新科研究生,暑假后相约一起走。打牌消磨。坐对面的女生,打牌打得得意了,忘形了,鞋也脱了,脚就伸到了对面。她穿的丝袜,汗味,酸溜溜的一路飘摇啊。后来这女生去了英国,大有作为一番,可是我一想起她来,臭脚丫的记忆又回来了。
讲北京讲到臭脚丫,说明北京很有人情味的。
某年寒假回校,中转上车,人流水一样往前奔。手里的包重如山,心里对父母一百个不满。不是说我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还装这么多东西,比一百只鸡还重?
身后过来一个男子,我帮你拿吧,他说,哪个车厢,我就放门口。然后他匆匆拎起来就走了。
男人大概三四十岁吧,很高,不苟言笑。我愣着,直到看见我的旅行包静静地竖立在车厢过道中,还在想刚才的一幕是不是放电影。
下一次是暑假回家。我发愁,还是包,拎不动。这次可不能怨别人装多了。是自己打的包,自己装了一百只鸡。为什么要自己折磨自己,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因为说好了同学来接,可是先得找打电话的地方告知同学。拎着一百只鸡找餐馆还不如干脆就地百鸡宴算了。
座位对面的人说话了,你有同学的电话吗?我可以帮你打。我就住北京,家里就有电话,举手之劳。
不多久,同学就来了,拎起背包,说,走,去俺单位的食堂吃馒头,白菜炖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