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解放日报》在汉口路旧址的岁月
2014-11-24居欣如
居欣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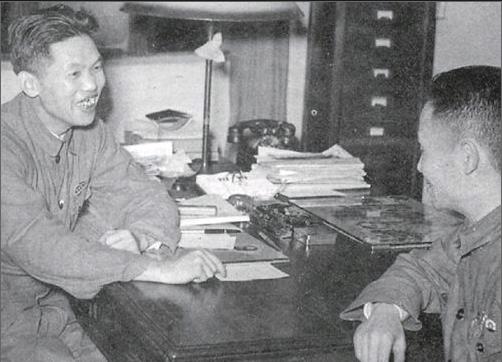
报街地标
沿着上海山东路,北起南京路、南至福州路,中间夹着一条汉口路,这便是一百多年前上海滩上十分有名的“旗舰街”——望平街,但见不足二百米的小马路两侧,先后集聚了包括上海滩三大最有影响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在内的数十家大大小小报馆。集散信息,名震中外。而最具历史地标意义的,莫过于鹤立在望平街与汉口路十字街口(现今汉口路309号)的《申报》馆了。这不仅因为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是中国报刊史上首开近代报刊集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及广告四大要素为一体之先河者,而且亦是中国著名报人史量才1912年接办《申报》之后、锐意改革的迁址大手笔之作:建造五层楼具有近代经典建筑意蕴的报馆大厦,同时引进最新式的印刷机器设备,从而使《申报》完成了近代报业的历史性转折。至1932年,其发行量已从当年的九千多份,猛增至十九万份。还先后发行《教育与人才》、《申报月刊》、《申报丛书》等杂志,并举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以及业余补习学校等,致力于开启民智、传播先进文化。直至1934年,史量才在浙江返沪途中被枪击遇害。申报馆即是这一段历史风云的最好见证。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入市区,让这座历史地标性报馆大楼见证了时代的新纪元。第二天,随军南下的范长江、恽逸群便带着进城前就配备好的《解放日报》编辑部人马来到汉口路309号大楼,与上海地下党同志会师。开会时,恽逸群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块带有木托的铜版报头,对大家说:“毛主席对陈(毅)军长说,现在《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了。中央以前用过的两个机关报名字,《新华日报》给了南京,《解放日报》就给你们上海吧!”从那天起,《解放日报》就作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入住了汉口路309号大楼。1960年《解放日报》和《新闻报》合并,解放日报社大楼又扩展到了汉口路274号。尽管后来这里相继就地改造新建了两座大楼,但汉口路309号大楼作为文物保护建筑依然完好。
党报光环
回想一个甲子的辉煌历史进程,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解放日报》四个字具有无上的神圣和荣光,而无数往事的发生和演绎又都离不开汉口路大楼。
我这一生,除了有二十年是在复旦新闻系从教以外,大半辈子都是在《解放日报》度过的。即便任教这些年,也经常带着学生到《解放日报》实习,亦借机参加一些编辑和采访活动。而从整体时间节点来看,我想大致是“三进”《解放日报》。正是这“三进”,让我铭记《解放日报》对我的培养之恩,铭记解放同人给我的友情和温馨,更忘不了在汉口路309号大楼的岁月。
记得首次进《解放日报》工作,是在1958年夏天。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杨西光奉上海市委之命调《解放日报》任总编辑,是他点名要我到《解放日报》的。我为能到党的机关报工作而深感荣幸。时人还介绍说,《解放日报》大楼是史量才建造的,他的办公室就在五楼,上下班还有保镖护送。这些话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将在史量才办报的地方上班。
然而,一到报社,迎面扑来的是热气腾腾的工作热情和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是志同道合的真挚友情,让我很快融入了党报这个大家庭。除了在总编办公室做些秘书工作,我在三楼的大办公室(时为工交部)也占了一个位置,坐在孟凡夏的隔壁,抽空就和记者一起去采访。
时值“大跃进”和向“解放十周年”献礼之际,报纸难免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和社会思潮影响,党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时的报社领导是心存疑虑的,但也难以实事求是,不得不被“运动”裹挟着跑。然而,客观来说,当时的记者、编辑还是很敬业的,在实际采访中也实事求是报道了不少经济发展、技术革新的新成就。比如,当年被称之为十面红旗的系列典型报道,还是起了很大影响。记得那时是王树人、夏华乙主抓工交系统新闻报道,记者出去奔跑了一天,回到报社已经晚上八九点钟,向领导汇报后,马上就提笔写稿,连夜完成。如,高肖笑、孟凡夏、王一鲁他们天天都是如此,从不叫苦。有时还要送审稿件,直忙到午夜才能回家;而第二天一早,照样赶来上班。那时,食堂里每天都有夜宵供应,一个馒头一碗粥。整个309大楼灯火通明,一派兴旺。
息息相通
更令人难忘的是,党委重视党的机关报的好传统。早在解放初期,华东局就专门成立了党报委员会,加强对《解放日报》的集体领导。由舒同、刘晓、魏文伯、夏衍、恽逸群(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五位同志组成,遇到重大问题开会讨论。
为了让党报的干部及时了解党的意图,《解放日报》社长(总编辑)可以列席华东局和市委书记的办公会议。华东局撤销后,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党报领导亦是列席参加的;还可以看到书记处的文件。不少绝密电报或重要文件只发《解放日报》,有些部委反而发不到。
历任市委书记对机关报的要求都很严格,但又特别关心。每天清晨,《解放日报》直送市委领导;早上七点多钟,我们总编办的红机铃声就会响起,传来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当天报纸的意见,或是表扬鼓励、或是批评关照。记得有一段时间,是由我接听并记录红机传来的书记指示,直接向总编辑汇报的。这些指示每天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在报社编辑部传达贯彻。
为了发挥党报的领头作用,当时还将上海新闻界各报(台)头头如陈虞孙、赵超构、王维、乐静、邹凡扬等组成一个小组,由杨西光定期传达市委一些精神,共同讨论,明确报道思想。遇有重大突出新闻和典型,书记市长亲临一线去视察,总会要求党报领导和相关条线记者一起随同采访;直接领会市领导的工作部署和意图,更好地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中加以体现。特别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经过总结整顿,吸取经验教训,《解放日报》上下意气风发、齐心合力抓思想、抓典型、抓言论,报道宣传了许多重大成就和先进典型。从“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拒腐蚀永不沾的旗帜,到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成功抢救大面积烧灼伤钢铁工人邱财康的报道;从王林鹤历经371次失败、最终试制成功一万伏高压电桥等电子产品填补国家空白的感人事迹,到吴佩芳以一个家庭妇女组织创办建襄小学的“鸡毛飞上天”美丽故事,都是通过《解放日报》而家喻户晓,至今仍被传为美谈。不少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大都是《解放日报》先发现报道的同时还配发了评论。可以说,《解放日报》以其思想性、新闻性和权威性在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干部群众中树立了比较高的威信。人家只要听说你是《解放日报》记者,都会刮目相看,肃然起敬。这促使解放报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历史浩劫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一场浩劫开始。十年“文革”,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这场内乱中《解放日报》也成了重灾区。造反派企图以《解放日报》作为打倒上海市委的突破口,由此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这一事件先是由上海大专院校造反派“红革会”挑起的,他们诬蔑《解放日报》发表了大量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在他们编印的第九期《红卫战报》上,写文章批判《解放日报》,并强行要求将这期《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送发给报纸订户。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报社领导严正拒绝后,红革会调动大批人马涌进《解放日报》汉口路274号大楼,强行占领报社,不准当天《解放日报》发行。
红革会强占《解放日报》的消息传开,成为全市市民关注热点。汉口路274号大楼前群众越聚越多,很多读者出于义愤,要保卫党报,要冲进报社,与红革会的人评理。双方严重对立,局势一触即发。红革会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压,一面给张春桥,陈伯达打电报寻求支持,一面便随意揪斗上海市委干部,甚至从医院里揪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12月12日“四人帮”掌控的《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夺取新胜利》的社论,肯定造反派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表现。这样,造反派气焰更为嚣张,甚至将《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总编辑马达关押在上海展览馆达一月之久。还把红革会制造的事端归罪于上海市委,诬蔑“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一手制造的。这就是颠倒是非、人妖不分的年代,留给《解放日报》在汉口路最突出的事件。
在“文革”期间,我也曾到《解放日报》评论部边工作边实践,为期仅一年余,那时办公室在汉口路274号三楼。在当时形势下也难以有所作为。
阴霾烟消
1976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以通栏标题和通栏图片刊出《上海百万人集会声讨揭批反党篡权者的反革命罪行》的报道,并刊出编辑部文章《誓同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斗争到底》,这时,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虽尚未公开,但大家传说纷纷,心知肚明。直到第二天,10月22日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定在全国各报刊登。人们拿着《解放日报》争相传阅,认为党报都说话了,绝对错不了啦!党报传达了党的声音,至今难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华社播发全会公报,报社同人读完公报,不由热血沸腾,三中全会明确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5月份《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三中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个凡是”的阴霾烟消云散。公报字字句句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面貌和报纸版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群众把《解放日报》看作自己可依赖的朋友。当时读者来信量非常大,一麻袋一麻袋的装,多的时候一个月要收到六千多封。群众来信《公物招领》放上了头版头条,从而引发了《公物招领》的大讨论,以群众自我教育的形式进行了爱护公物、加强管理、反对浪费、克服官僚作风的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实事求是说真话,实事求是宣传。1980年10月3日,《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文字,在头版头条通栏刊登,引发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广泛讨论。当天,上海所有零售报摊《解放日报》脱销,读者来电也很多,反应热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新形势下要求上海“在国家四化建设中发挥重要基地和开路先锋的作用”,“上海不仅是一个工业基地,而且应该是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应当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的、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根据这样的发展目标,报纸主要从几方面进行宣传:一是发展横向经济联系,发展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二是抓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三是搞活流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四是反映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地位。
我们除了发表经济理论家马洪、于光远、许涤新等有关论证上海战略发展的文章外,还发表了《上海应成为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上海应该成为多功能的中心城市》、《上海要发挥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等评论,同时还报道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以来的成就,如:《上海吸收外资突破九亿美元》、《全国客商云集上海争设窗口》、《上海电机公司下放72条权限、建立5个经济实体,从管头管脚转为搞好协调服务》、《上海个体户总数突破六万》等等。
同时,也通过一些典型,从政策高度,明确政策界限,作出回答。
重现辉煌
从1984年的战略大讨论到迈向21世纪的上海,问题集中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是否需要开放,城市向哪个方向拓展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解放日报》先后刊登《海盐衬衫总厂步鑫生树立改革创新榜样》的报道和《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温州模式”的报道。“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还配发评论《温州的启示》,在内容涉及闯禁区、绕地雷,有争议的情况下,最终肯定是一种改革实践,上了头版头条。
1985年在东海之滨,宝钢十三平方公里厂区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一号高炉点火,在我国钢铁生产史上揭开崭新的一页。对宝钢建设,当时议论颇多。小平同志在1979年7月在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时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后来又在一次会议上说:“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解放日报》认真报道了宝钢一号高炉点火,炼钢厂出钢水,初轧厂轧出各种钢坯等环节,特别介绍了宝钢人的拼搏、苛求、实干、创新和协作精神,还发表了大型通讯《二千五百个日日夜夜》和大特写《老钢铁逛新钢城》。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已由历史证明它的正确。宝钢一号高炉点火,才有今日的辉煌;而《解放日报》的记者们也以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记下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1991年周瑞金等几位同志所写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发表,在国内外,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对“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作了有力的 、正确的引导,消除疑虑,推进改革开放。
文明建设
党中央要求上海集中体现“上海水平、上海效率、上海风格、上海精神”,同心同德,振兴上海的任务就提到上海人面前了。市委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当时的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指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市委一开始就要求《解放日报》带头开展“90年代上海人”的大讨论。把讨论活动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推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动力和契机。
在新形势面前,上海人面对的是时代的召唤,难逢的机遇和历史的重任。上海人是怨天尤人、慢条斯理、按部就班,还是敢字当头、急起直追、埋头苦干?上海人是观望、埋怨、懒散呢,还是抓住机遇,励精图治、奋发向上呢?
1991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读者魏澜的来信,加发编者按。刊登读者来信,揭开讨论序幕,然后,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发动群众。历时一年有余,发表了二十八组高质量的讨论发言,参加的有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企业家、工人、青年、妇女代表、外商首席代表、外省市驻沪代表、机关干部、局级领导等。这次讨论,参与和发动面广泛,影响深远。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本质特征是“容纳、吸收、汇总、开拓,做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要“让思想冲破牢笼”,“敢闯禁区,敢创一流”,要实现第二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对推动上海人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创新,振兴上海”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接着上海的新闻媒体也参与了“90年代上海人”的大讨论。
献身报业
想起汉口路,始终忘不了汉口路274号五楼那层拥挤、凌乱的夜班编辑部。临窗的那张陈旧的写字台,那是夜班编辑部的顶梁柱陆炳麟的办公桌。夜班编辑部是报社的总装配车间,那里人才济济,许寅、金福安、钱存源、金尚俭、陆炳麟可称夜班编辑部“五虎将”的代表人物。陆炳麟每夜上班,人未到,嗽先闻。一坐下,先泡一杯茶,点一支烟。似乎漫不经心地将新华社稿和本报稿件翻阅一遍,就全部搞定。夜班有句名言:“陆炳麟当夜班,任何朝代的领导都可以放心睡觉。”记得1983年我刚来报社不久,就轮到我值夜班。我因长期从事新闻教育工作,要真刀真枪值夜班真有点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我专门请教老陆,要老陆示范,我跟班见习。他既不故作谦虚,也没有一点矜持、傲慢,而是诚诚恳恳、实实在在一口答允。我上完日班,就来夜编部。只见老陆将当天一厚叠新华社电讯稿,哗哗一翻,似乎一目十行,然后再将编辑部稿子看完,分门别类向版面编辑一一交代。倘有编辑粗心出错的,漏掉的,他都能一一看出。这样的功夫真了得!令我深受教育。平时,我写了什么文章,也乐意请老陆提提意见。他就会留条退给我,真诚而恳切。这种光明磊落的学者风度,把报社事业视作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一位老报人,令人敬佩,永不忘怀!而当时解放日报就有这样一批将事业看作比生命更重要的老报人。奉献聪明才智,办好党报。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这一个个高大而可亲的报人,让我对《解放日报》在汉口路的一段日子难以忘怀!它承载着《解放日报》曾有的辉煌,它记下了《解放日报》光辉的历史!在这里解放报人挑起重担,为党的新闻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献出了自己的热情,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谱写了一曲豪迈而高昂的共和国进行曲,激荡人心,回旋始终,永难忘怀!
(作者为《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殷之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