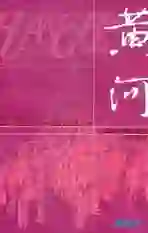梦里依稀上南山
2014-11-18杨晋林
杨晋林
“当童稚无邪的年代,我莫名其妙地向往两个地方:一处是口外的草地,一处是南山。”这是我的乡党牛汉在《南山》一文中的开场白,牛汉的南山正是小城的南山,也是我的南山。
——题记
小城对面的南山名唤居士山,又称七岩山,较之于国内那些名山大川而言,家乡的南山几乎没有一点可比性,高度不够,植被不够,名气也不够,除了山褶子里散落着几座不成气候的村庄外,也就剩下山名还算洋气。但你不知道,小城对面的南山也是有典故的,不说山脚下有个灵性十足的惠应圣母祠吧,也不说还有个与赵氏孤儿扯不断理还乱的藏孤台吧,单说山顶上四四方方一座小石阁就很让人浮想联翩。小城人称其为老松台,是一座实心塔,旁边还有个极风雅的去处——三间石砌的窑洞,据说是大诗人王维、王缙兄弟在一千三百年前秉烛夜读的书房,大概是乡人为了佐证这件事的合理性,甚至在石窑内立了一个字迹漫漶的神位:“唐居士王维神”。但我不知道,名盛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诗佛王摩诘本应是晋南蒲州人士,何以又出现在晋北的定襄小山上面,也不惧临崖百丈,风寒蚀骨。
上小学那会儿,母亲说我脑子笨得跟猪一样,只会加法,不会减法,功课差得要命,我经常选择逃学的方式消磨时间。我去的地方一般是村南一座大照壁,在大照壁的南面,越过油绿的青纱帐,能够看到淡淡的一线南山,南山横亘在遥远的天际,慈祥地向我投来慰藉的目光。
那天,父亲掮着一个草绿色的大提包从南面走来,他惊讶地问我,你怎么不上学,在这里做什么?我一时回答不上来,被父亲捉了现行,从不舍得动我一根指头的父亲硬邦邦地踢我一脚,说你太让我失望了。
父亲在几百里之外的太原西山煤矿工作,一年里难得有几次回家探亲的机会,见面少,我对父亲的印象就仅剩了敬畏。父亲从县城的火车站出来,扛着几十斤的包裹,大步流星往三十里外的村里赶,连一丝犹豫都没有,偶尔遇见村里的拖拉机在城里办事,也不主动跟司机打招呼,那年头的拖拉机驾驶员是有身份的,所以父亲很少能够把三十里的步行节省下来。中午下车,半下午的时候,身材高大的父亲才黑黢黢地出现在我家院子里,母亲把手里晾晒红薯干的簸箕放在檐台上,一边拍打围裙上的土,一边说回来了。父亲嗯一声,把肩头沉重的包裹咚地扔在地上,也不歇一歇,操起房檐下的扁担就去挑水。
说不来我为什么利用宝贵的逃课时间来眺望南山,也许是想把心中的郁闷向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南山默默倾吐吧,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有关于父亲与南山的一段渊源……我有一个本家三爷给生产队赶马车,三爷串门子时候喜欢讲家史,谈到我父亲的来历时特别说明一点,你爹是你奶去南山圣母祠的七娘洞里祈回来的,七娘洞里有个七宝池,池里有功德水,水里有花花绿绿的鹅卵石,坐不住娃娃的女人只要在水里能摸到一块小石头,就一准能怀孕,你奶三年去了三趟,最后一年才摸到石头。我固执地认为,就是在某个大月亮的晚上听了三爷的故事后,我才开始关注起南山的。
村子距离南山足足有六七十里路程,天晴的时候,站在村前大照壁旁能够看到南山白蓝相间的皱褶,被西斜的阳光分离出许多十分硬朗的线条,七岩山顶的老松台若隐若现,最高的山脊呈直线状无限延伸。有一年夏天的黄昏,南山上的桦树林着火了,火势从山脚一直蔓延上山巅,我们在村口惊奇地发现南山上倒竖着一条金黄的火龙,龙首颤栗着,龙尾分开两叉,一叉去了东边,一叉去了西边,只有龙身瘦弱着,不甚壮观。那场山火整整燃烧了一夜,第二天当我顺着木梯爬上房顶,看到南山上仍袅娜着股股青烟。我们老师说,南山上原本树就少,这下算剃光头了。
夜里,我却梦见南山顶上莲花盛开,清风吹过,暗香浮动……
我和母亲的关系像南山的浮云一样若即若离,这是我很小就能够感受到的,家里但凡有一点好吃的,母亲总是分出一多半给了姐姐,剩下的一少半还要对半均分,她一半,我一半。母亲对我说,你姐姐食量大,你让着点。这样分配食物的方法我也认同,习惯养成了自然。后来,赶马车的三爷偷偷告诉我,母亲是从邻村改嫁过来的,姐姐也是她带过来的,总担心父亲会亏待姐姐,临结婚前还让父亲写了约法三章……
童年的思维是无羁绊的,我开始着迷于遥远的南山。从童年到少年那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经常梦想着去爬一次南山,看看陌生的南山上有没有传说中的南天门,看看火柴盒一样的老松台上住没住着白胡子神仙。由于距离远,由于光线的不均衡,能够看到清晰的南山的日子很少,南山往往被厚实的云朵笼罩着,显出非一般的诡谲和迷离。曾经有许多次我萌生了独自去南山的念头,都想好了路上该怎么走,见了村里人该怎么搪塞,到了山脚又该怎么上山,可临出门却改变了主意。
我相信我是个缺乏主见的人。
南山的庙会固定在每一年的农历七月初一,民国版的《七岩山志》里有过记载,称七岩山古庙会又为“捞儿会”,自宋崇宁之初,惠应圣母加有封号,遂为本山之主神也,每至会期,商贾云集,人流接踵,香客远迄二州五县,明晋庄王朱钟铉无子嗣,仲夏携妻到此祈子,秋末果得子……古庙会因文革停办多年,1977年,回家探亲的父亲听说南山又要重开庙会,就打算带母亲一块去许愿。母亲是大队会计,又是共产党员,她不相信迷信,或者说压根儿就不想去,她打发我陪父亲去。一听说父亲要带我去南山,头一天夜里我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隔着一尺见方的玻璃窗数了一夜星星。
第二天没吃早饭就踩着露水上路了,父亲在挎包里揣了五个白面饼子,一壶温开水。我们村与南山之间间隔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还有一座小小的县城,一个公社所在地,这些村庄和县城都是我从未涉足的,我相信哪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地方都有为我所不曾预知的奇异景观……不善言谈的父亲却跟我扯了半路关于南山的事情,最多的是我三爷的见闻,因为三爷每年春忙结束就赶着生产队十几匹牲畜去南山上面的南坪梁放牧,三爷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有人说三爷在南山上的窑头村还有个小他十几岁的相好。
在我吃第二个白面饼子的时候,我们被一条湍急的大河挡住了去路。父亲说这可糟了,河里发大水了。那时,我和父亲用两大两小四只脚把五个村庄的大田和宅院都闪在了身后,我一心指望着在七岩山下的庙会摊子上吃一碗搁了三片五花烧肉、两颗肉丸子的大肉片汤,可是滹沱河翻卷着浪花,浑浊地阻梗在脚下。父亲用一根葵花杆试了试水深,两米长的杆子入水后竟探不到底,说,背河人也过不去了,咱回吧。我不舍得返回去,大河的南岸就是定襄城,我连定襄城北那座关王庙的五脊六兽都看见了,却只能望而却步。父亲沮丧地说,咱要住在县城就好办了。又说,其实庙会也没啥看头……endprint
一年后,滹沱河上有了一座跨度近百米的水泥大桥,河北岸的村民再无须望水兴叹,可父亲也再未提要去赶七岩山古庙会的意思。
自从滹沱河上有了大桥,我对南岸的小城不再陌生,曾不止一次坐着三爷的马车进城赶集。犹记得小城方圆不足里许,许多地方可以看到明显的古城墙的遗痕,城北的民房远高于路面,一座一座耸立在北城墙外的土坡上,破旧而凌乱。我不知道三套马车的胶皮轮胎碾轧过的地方正是一千多年前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修筑的古城街路,我不知道脚下这座由汉阳曲故城演化而来的定襄城,日后会与我的命运紧紧联袂在一起,不可分离,我只知道当年的县城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楼房,县城的制高点是建在南关梨市街的水塔,水塔不允许人随便上去观瞻,定襄有多大,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潜意识里没有任何明确的概念,直到参加工作,偶翻《定襄县补志》,我才弄清,从齐武成帝河清二年起,小城仅有“周四里七十三步,高四丈,池深二丈一尺,阔二丈七尺”的面积,而以后历代对小城的增补都没有太大的突破。
南山在小城之南缓慢地生长,它的上升的幅度与我的成长成正比。我猜想南山已经极其苍老,佝偻的脊背宛如一口生满铜锈的古钟;我又想,南山不该那么苍老,它应该很年轻,举止轻狂英气逼人;而更多的时候,我想象中的南山是一个智者,他很自然地肃立着,立出一种洞晓天下事的姿态,那种对人世间万事万物都满不在乎的样子也着实令人感动,不仅感动着天上悠闲的流云,而且感动着身边鸣啭的飞鸟,还有生活在南山阴影里的乡民们。
再大一点,我就很少坐三爷的马车了,马车太慢,耽误时间不说,坐在上面也不舒服。我或骑自行车,或搭乘村里的拖拉机,无数次地单独光顾小城,花几角钱在新华书店或街头知青流动车上买一本文学杂志,随手翻翻,交完钱,扭头就回。我把嘈杂的小城撇在身后,全然不去想它背负了两千多年的沧桑历史,我与身后的南山背道而驰。那时,我与南山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恒定的三十华里和七十华里之间。这是小城与乡村的落差,这是南山与我的梦想的直线距离。
1983年,我从小城火车站出发,去几百里之外的太原西山当煤矿工人。隔着低矮的车窗眺望即将作别的南山,心里涩涩的,别提有多难受,倒是觉得车轮下的小城与我没有半毛钱的瓜葛。火车越走越远,眼里噙满泪水,父亲塞给我一颗蒸熟的凉鸡蛋,大概看出我悒郁的表情,嘴里嘀咕一声,没出息。我相信在外漂泊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感情早已被一层厚厚的茧子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是顶替父亲参加工作的,我上班了,意味着父亲就该正式退休了。叶落归根,我对即将离开矿山的父亲没有一丝的眷恋,反而有种难以抑制的艳羡,从此父亲有大把的时间用来造访我无数次眺望过的南山,去爬我梦中常见到的乱云堆砌的老松台,去赶人头攒动的七月初一的捞儿会……而我却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面对色泽晦暗的矿山。
八十年代初期的西山煤矿尽管与市区仅隔数十公里,但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盘山路把数十公里延长到一个未知数。有一年冬天,天降大雪,通往山外的交通中断了,缺乏水源的矿区连吃水都成了问题。我和我的矿工兄弟们每天从井下出来,泡在脏兮兮的澡堂里,用手不住地从洗澡池里往外撩着乌黑的油渍,大声嚷着还让不让人洗澡了?管理澡堂的工作人员也是有苦难言,说不是不给换新水,是老天不眨眼啊,清水送不进山来。大约一个礼拜后的某个早晨,太阳终于钻出阴霾,一点一点溶解掉地面的积雪。当第一辆驮着大皮囊的运水车驶进矿区时,我和我憨厚的矿工兄弟们就像迎接新人一样夹道欢迎,每一张黝黑的脸上都洋溢着久违的笑容。或许是从那年冬天开始,我突然强烈地思念起我家乡的南山,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思念那座玲珑而繁华的小县城,甚至思念很少过问我的饮食起居的母亲。我觉得,家乡的南山绝不会把山民困在山上下不来。我给母亲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里面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问候她和父亲;二是山里的日子太苦焦了,没商场,没女人,一日三餐只有馒头稀饭,连见日头的时间都比老家短好几小时,想进一趟市区连公交车都没有;三是许多跟我一同上班的年轻人要么调进省城,要么调回老家,人心思动,只要有正常思维的人就必定有逃离矿山的想法;四是这里的煤山没有老家的南山好……母亲给我回信说,什么煤山南山乱七八糟的,调动工作谈何容易,咱家一没面子,二没关系,三没票子,你就省点心吧。
矿区周边的山有好多个名字,卧龙山、二龙山、九家背山等等,可哪一架大山都不是我梦中的南山。这里的山大多为土山,土山下面蛰伏着肥沃的煤田,土山上面除了灌木就是层层梯田,还有密匝匝的果园。无论山上山下都被细密的煤粉覆盖着,隐匿了原有的青葱。苹果成熟的季节,看果园的人背着猎枪,牵着猎狗鬼魅一样在山坡上逡巡。我和几个原平县的老乡趁着月黑风高夜爬上山去偷摘人家的苹果,被埋伏在草丛里的猎狗一阵狂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跳了悬崖,其中两个崴了脚,一个摔断了腿,我是仅存的一个手脚囫囵的人,也因这件事受了单位处分。
父亲从几百里外的老家来看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个不省心的货!我当了一辈子矿工没偷拿过矿里一块煤球,你倒好,来了没几年就瞄上人家的苹果了。”我不敢直视父亲,好在父亲训完话,又谈起另外一件事,说你三爷死了,去南山放牲口让雷劈死了……我本来心情就郁闷,听到三爷的噩耗,浑身激灵哆嗦一下,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三爷的音容笑貌,而是三爷再不可能在每一年的春夏之交,赶着生产队的牲畜徒步七八十里,去南山上放牧了……
一定是父亲怕我再出事,他回去后就耐心地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催她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终于从县里一个物资企业开出一份商调函。而这时候,我已经在矿山生活了整整五年。五年的时间并未加深我对这里的了解,反倒是一听说老家的工作有了着落,我破例花了一个月的工资——80元钱,在煤矿的小食堂里请那几个大难不死的原平老乡打了一顿牙祭,小炒肉、过油肉、鱼香肉丝……凡是小食堂里有的,我都点到了餐桌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鼻梁说,我这人有福气,要回去了,这儿不是我呆的地方,以后有空就去定襄找哥儿们,别的我没啥好招待的,我带你们去爬我老家的南山——那家伙,不比北京城的香山差!endprint
不是在吹牛,我想象中的南山的确要比香山好一百倍。
1988年夏天,我正式成为小城的常住居民。第一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城南一段古城墙的废墟前,驻足在那里长久凝注着“失而复得”的南山。尽管那天是晴天,却有一带青岚纠缠在南山的半山腰,我清楚地看到散落在山坡上的一些杂树和村庄,甚至看到一条牧羊人走出来的山径扭曲着伸上山顶,但山腰之上的景色被青岚映掩着,不甚分明。而我所处的位置,在七十多年前,一个叫牛成汉的脑后拖条小辫子的小男孩就趴在一丈多高的古城墙上挖甜根苗,他一边挖,一边提防从某个土洞内蹿出一条乌梢蛇。这个牛成汉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诗人牛汉,只不过牛汉那时的古城墙仍延续着汉城墙的雄厚宽广,一甲子的光阴倏忽而逝,高不过一米七的我已经很轻松地把急剧萎缩的古城墙废墟踩在了脚底,只有南山仍旧是汉时的南山。
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骑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进城来看我,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再不能像煤矿那样吊儿郎当了,能把你从太原超度回来,咱这普通人家,实在不容易呀。沧桑顺着父亲越来越显目的皱纹爬满脸颊,我喉咙里哽咽着,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在小城工作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总是回忆着死去的三爷,回忆着那个曾经赶着三套辕的马车把我一次次送进小城的三爷,想象着三爷年年要去的南山,还有南山上某个容颜渐老的女人……
九十年代初期的小城,建筑古朴,街道逼仄,车水马龙里唱主角的是两个轮胎的自行车,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多以自行车代步。我就是骑着一辆红旗牌加重自行车把小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个遍,于是我知道,小城的街巷多为东西走向,当然南北走向的也不少,每一条街道都不算长,一眼能够望到底。小城最宽的路叫新开路,古时又称傅家街,傅家街在明万历年间曾出过一位国子监祭酒傅新德。当年,著名的戏曲剧作家汤显祖的长子汤士蘧到南京国子监游学,受到傅新德和郭正域的赏识,“不谓翻然游太学,文章惊动两鸿师。”这是汤显祖对儿子的两位恩师由衷的赞誉。只是光阴老矣,风景不再,如今已找不到一处磨砖嵌缝的古宅院或是一座雕花门楼了。
小城曾有过东、南、西三个城门洞。久居小城的老人说起西城门来颇有些意味深长,说春秋列国时,孔丘带着他的得意门生乘坐牛车四处游说,走到西城门前遇见两个头梳髽髻的小儿正用黄土堆城池玩儿,子贡奉老师之命过去劝两个孩子让一让路,其中一个孩子对车上的孔子说,从来都是车绕城走,没听说过还有城绕车走的。孔子看看小孩脚下的土城不禁莞尔,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随后他让自己的牛车绕“城”而行……
但是,一些古老的街名诸如东门街、西门街、小南门街、花大门街、文庙街、财神庙街……至今仍被牢牢钉在小城那些长长短短的胡同里。它们不是一些简单的名字符号,而是相关这座小城历史的最直观描述。而南山呢?尽管近在咫尺,我仍未能身临其境。
南山,仿佛一扇久闭的门户,无须任何理由,把一个虔诚的信徒挡在门外。
偶翻古籍,看到一个叫张友桐的民国学者是这样记述我的南山的:“定襄南为丛蒙山,由丛蒙东折,巍然高者为七岩山,山距城十数余里,远可见百里外。层崖累上,阶数而七,故曰七岩。或曰山有七洞,故名。中一洞阔二十余丈,石罅出泉冽而清,渊然而井,曰惠泉,明邑侯王立爱所题也。洞祀惠应圣母,俗所传磨笄夫人者也”……从北魏起,历经东魏北齐唐宋元明清,诸多佛家建筑群落,譬如灵光寺、七岩庙、千佛殿、睡佛殿、文殊洞、仰光楼、梳洗楼等等如珍珠般散落在南山上下……沧海桑田,世事无常……曾无数次梦见我来到南山脚下,仰望金碧辉煌的大山,我只能以顶礼膜拜的方式诠释我浓浓的景仰之情。
父亲到底是矿工出身,七十多岁高龄了,仍健步而行。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让他去摆弄自行车,但他每天仍把大部分时间安排在临近村口的庄稼地里。村里像我父亲这种年纪的老人,大都在自家门前坐街,用慢吞吞的旱烟和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打发着所剩不多的时日,唯有父亲在不停地忙碌着。有一次我下班回村,看到做完农活儿的父亲把草帽垫在屁股下,静静地,石雕一样坐在渠堰上眺望南山,那种专注的神情与当年逃课的我如出一辙,我突然觉得我与父亲存在着冥冥中的某种契合。
母亲也在一天天衰老,但她对我的态度依旧不冷不热,最直观的表现是她带大了姐姐的两个孩子,而我的孩子她没带过哪怕一天,总说孙子太顽皮,管不了。
小城在不知不觉中变迁着,街宽了,楼高了,车多了,人挤了,都还是极表象的变化,尤其显著的是小城人慢条斯理简简单单的生活变得急促起来,丰富起来,有了动力,有了质感,看上去身边的人都在快节奏地往小康社会奔跑,人人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这人天生缺乏进取心,思维总比别人慢半拍,早让风风火火的时尚抛诸岸边,但站在岸边看旁人往家里扛钱袋子,也心有不甘,我也有自己的小小梦想,就是在小城的腹地拥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陋室,让爱人和儿子不再跟着我寄人篱下。
小城有高层建筑的历史并不久远,也就这一两年的事。在我乔迁新居的当天下午,年逾八旬的老父亲在我家阳台上鸟瞰小城街景,起初是出奇的淡定,只说县城不是以前的县城了,都快认不出了。我有些沾沾自喜,似乎父亲对小城的褒奖,正是对我工作与生活态度的认可。后来,父亲用拐杖指着对面一挂青山说,好家伙,那不会是南山吧?连山褶子都看得一清二楚,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赶七岩山庙会,碰上河里发大水,走了一半路,没去成?我点点头,父亲话锋一转,你该多关心一下你妈,心要放宽,不能老这么别扭着……我又点点头。
那时,阳光从侧面的玻璃窗透进阳台,父亲周身镀了一层朦胧的赭黄,这时的父亲像极了小城对面的南山,像极了南山的沧桑与淳朴,像极了南山的宽容和厚道,尽管父亲的脊梁已明显弯曲,但他对于我的伟岸是永恒的。
我从不敢轻易接近现实中的那座南山,正如我不敢与父亲对视一样,但我愿意让南山成为我生命中上下求索的制高点,成为我后半生的一个参照物,我静赏着对面的南山,一种坐看云起时的禅意纳入心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