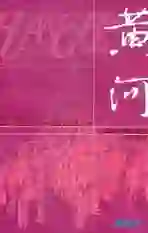家园意识的精神追寻
2014-11-18柴然
柴然
郭虎的中篇报告文学《右玉,不会忘记》,发表于《中国作家》,后选入该年度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写了右玉县威远城一个叫毛永宽的有志青年短暂却很不平凡的一生。
1968年,18岁的毛永宽开始任威远大队村干部,从大队会计、民兵营长很快干到大队主任、大队支部书记,聚10年之功,带领威远乡亲们植树造林,修路架桥,开渠平地,发展畜牧,在他28岁上,被活活累死了。毛永宽为右玉献出了青春壮丽的生命,30多年后,另一个右玉人郭虎为他立传,最后比照的,一个是保尔·柯察金,一个是我们山西的英雄诗人高君宇。
郭虎是县里的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民间身份,一为诗人、作家,一为右玉赤子。
尤在省城,郭虎出现在大家中间,皆“为右玉精神的鼓与呼”有关:找作家赵瑜、张石山和电视台的朋友谈编写及拍摄电视连续剧的事儿;找文学院院长张锐锋谈康熙蒙古大营,设立文学院创作基地;找《山西画报》的老师拍摄并报道右玉全县的绿化,让更多关注右玉的人看今日之杀虎口长城、古苍头河、西口、古堡等著名的塞上风光;泡在印刷厂激光排照室审定《西口文艺》的出片及印制情况,诸如此类,尽为此道。
现在,人们关注右玉,知其右玉精神已推广到全国,右玉精神的宣传工作已然纳入我们国家的主流话语霸权——外面大报、大电视台的记者蜂拥而至,实为他们必须去践行的新闻任务,而非右玉或者说凭借郭虎这样的右玉人的一腔热诚所邀请;而能完成这样一个大的跨度,除却右玉绿化本身的重大存在,其间正为郭虎这样的地方贤德不辞劳苦、四方奔走、无私奉献而取得。他们当然是右玉精神的代言人。
我以为,这正是郭虎的《右玉,不会忘记》能获得多方认可的一大前提。这也是他作家的质素。
在文学界,时下谈论报告文学的成功,除题材之外,更多谈论的还是采访或田野调查。郭虎也讲,为这部作品,他至少跑了有几十趟,用了几年时间,采访得相当地全面而深入。有评论家指出:“报告文学采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得大量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获得相应的体验,并由体验而感悟、而饱满作家的感情。”有所不同的是,郭虎的这一系列采访,却非从情感上更多进入自己的写作对象,他真正找寻(释放)的恰恰是一种我们共有的核心情感,所谓人的精神;本质意义,还在于对我们生命的重塑或者精神上的更新,完善。两个字,他在写:我们。
《右玉,不会忘记》在纪录毛永宽一生的同时,实质还指出一种重要的文学力量:与这块土地相依为命的强烈的命运感。对呀,并没有什么不离不弃,如年轻的毛永宽考取了教师资格、几乎就得到了到外面去上大学的机会、还有被提拔到上一级当干部的机遇,但几多争取,终究无果,右玉威远城也就真的成了他人生的终极。而与此相互依存的,则是那种战胜艰难困苦的现实力量,它就蕴涵在人民群众中间,和尘同光。
毛永宽生于1950年,比郭虎大13岁,他任威远大队干部的前后10年,正逢“文革”和学大寨运动对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轮番倾轧。在右玉,又加之风沙肆虐,毛乌素沙漠不断向前推进,家园大有被废弃的危险,那完全可以说是自建国以来他们所处的最艰难的一个10年。今天有不少到过右玉的人,因它的绿化超乎想象,绿化又为右玉人几十年而为,特别是年轻一代,便把右玉的过去简化为单一的绿化史,美化或者说弱化了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大小运动,甚或为某些运动涂抹上喜剧色彩;如我,也曾对“文革”中的右玉有过相应的误读,认为永不停歇地种树便是一贴阶级斗争的缓释剂。对于这一点,郭虎在《右玉,不会忘记》中虽隐晦曲折,但还是点了出来。是的,历史不能假设,如我们不能假设没有始自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文革”10年浩劫,年轻的威远大队党支部书记毛永宽的内心没有那么多争斗,因之而过早地撒手人寰。所以说,右玉境内的那一大片碧绿,最是饱含着人民群众痛苦牺牲的生命结晶。
这过去的年代,痛苦的年代,却是确立右玉能有今朝的血汗基础。这是最坚实的,对此,没有一个外人能比这位写作者更清晰、明晓。
和几位报告文学专家讨论此著,有朋友还借用了批评家雷达的话:“看一个作家深刻还是肤浅,首先要看他有无强烈的自主性。主体意识才是作品价值的立法者。”而郭虎这部报告文学呈现出的自主性及主体意识,也许就最值得我们留意并肯定。另一个观点:报告文学的业余写作虽无优势可言,但作者生活中积累的财富,反是一般职业写家所不具有的。郭虎则说他“不会写;不知道报告文学该怎么写;仅凭自己一腔情感的冲力”,而令其燃烧、沸腾。是为我们长此以往一直强调的一种粗粝的原创意义:与生存息息相关的朴素之美;初看简略,实不简单,掩卷长思,人物、事件、场景反而一一浮现于心壑脑海,久莫能忘。
是在有意也是在无意之间,通过毛永宽这一理想化身,郭虎在作品中完成了他们共有的灵魂塑造。
郭虎对毛永宽的认同是完全彻底的。如前所示,毛永宽其实还是一个新一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热爱文学,有着高远的生命理想,并不希望这一生全然被固定在右玉县威远城。是命运把他和威远城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直至不能分割,血肉之躯全部融入泥土,成为它的一部分——这土地上的绿荫与传奇。论年纪,奉献出青春与生命的毛永宽该是郭虎的长兄,郭虎在少年时,就曾被他的人生故事所深深打动,并始终被激励着。郭虎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种树,青少年时代更不例外,大学毕业后回到右玉,一边当教师,一边种树。全右玉人,也大凡如此,如工人在工余,如机关干部在节假日,在八小时之外,种树成了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常态。外来人也一样,如插队知青,首先学的就是种树。运动的同时也不能耽搁了种树。这边批林批孔,那边南山种树。当然,种树任务最重的还是农民,他们的父老乡亲。而他们所有人经年累月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仍然是:难得把树种活。那不能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如此的生命考验,第一就要他们做到不屈不挠,谈何容易啊,人在反反复复不能成活的事物前太容易气馁了,因此上,他们心目中则不能没有英雄。毛永宽卒于1978年12月,1979年10月,右玉县委县政府发出通知:“向优秀共产党员毛永宽学习,为绿化右玉大地不懈奋斗。”至此,毛永宽成为全右玉的一面旗帜,也驻扎在了郭虎这个少年诗人的灵魂之中。把毛永宽写出来,一定程度上,倒成了郭虎的命定。所以,毛永宽之于郭虎,实为一种自发的人物塑造,一种右玉精神的悲壮回归。而郭虎在令他心目中的英雄长存的同时,更值得首肯,是完成了右玉精神的人格化(拟人化)飞跃(这是文学家的任务):毛永宽上升为那个艰辛奋斗时代的符号与象征,记住毛永宽,也就记住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岁月;认识毛永宽,也就是更深地认识了右玉人和右玉精神。endprint
而揭示作品中最深刻的家园意识,在有限的视域里,能比照的是甘肃环县。2007年夏,我们一行到离县城60公里的山城堡采访,车向县北进发,那黄土已变白沙的群山,充斥着唯有死寂的悲号,压抑得人几近无法呼吸。大自然有时候就这么残酷:滚滚旱象,颗粒不收,寸草不生,人畜不见。但那山峁峁上却有一户人家,在挣扎、坚守。他们家中什么都没有,维持生命,仅靠一点扎了芽发了臭的土豆。那40余岁姓户的男主人,则接近于半疯癫状态。有朋友说,此中生存,人不变为半疯,又怎么往下活吗?这恐怕也是事实。返回来重忆右玉当年,那是他们如若不是及早地便展开自救,种树不歇,兴许比环县北部这白象似的群山,会完蛋得更早,漫漫黄沙,会以毛乌素沙漠的名义,统驭一切。
读郭虎这部作品,结合到塞上走得久了,感同身受,反而认识到,最终对这片土地取得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华夏民族古老的农耕文明之光。它贯穿在字里行间,例子很多,大家展卷即可发现。在这山西紧邻内蒙古的北大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连年征战,烽烟不息,鼓角相闻,马蹄声碎,这土地也一定是最早接受游牧文化,融合胡服骑射的,当然游牧文化的光辉在这里亦随处可见,并显出它勃勃的生命力;但说到底它还属于支流,不是决定右玉和右玉人的“道”——他们视土地为母亲,为一切,忽然就想起老祖母抱着你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教你牙牙学语: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不就是吾中华文明的基石家园?
作品中有一个细节,是说吃“钢丝面”的。那时毛永宽已经病入膏盲,在医院里,当他品尝到那一饭盒用玉米面压制的特别筋道的“钢丝面”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村中应该有这样一台压面机,让全威远人都能吃到“钢丝面”。
在种树之外,如毛永宽早早便带着大家兴修水利,搞粮食深加工,办养老院等等,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具体例子。
是离开这块与生俱来的故土呢,还是坚守,挣扎,挑战沙海,赢得一线生机,部分地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他们没有选择离去,而是留下来,选择了种树,一直种树,让家园和他们一同活着。
右玉人是赢得家园的人,有足够的底气与欣慰?因之郭虎脸上才有那样不倦的笑容?
2012年夏天,山西省报告文学创作会议在保德召开,会议伊始,著名作家赵瑜在向大家介绍山西省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情况时,特别点出“郭虎写右玉基层干部的《右玉,不会忘记》”,将其和鲁顺民的《送84位烈士回家》、陈为人的《唐达成风雨五十年》《马烽无刺》、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顺民、骏虎、黄风、玄武的《王家岭的诉说》、黄风和徐茂斌的《夕阳下的歌手》、王保国写抗日女英雄的《李林传》、聂还贵的《中国有座古都叫大同》一并提出,认为写得“扎实饱满,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是我省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成就”。
肯定作品,自不待言。倒有一事应记在后面。还是我拿到该作品的同时,郭虎向我讲:右玉人口10万左右,国家有政策,人口不足10万的县份将被撤掉。正因为如此,右玉县在人口普查时,一些村里在县上打工的人,因城里的临时户口,既顶着村里人,又顶着城里人。右玉县至今也存在着被撤掉的危险。当然了,天下从来也没有可供人类予取予夺的一寸土地。右玉自不例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