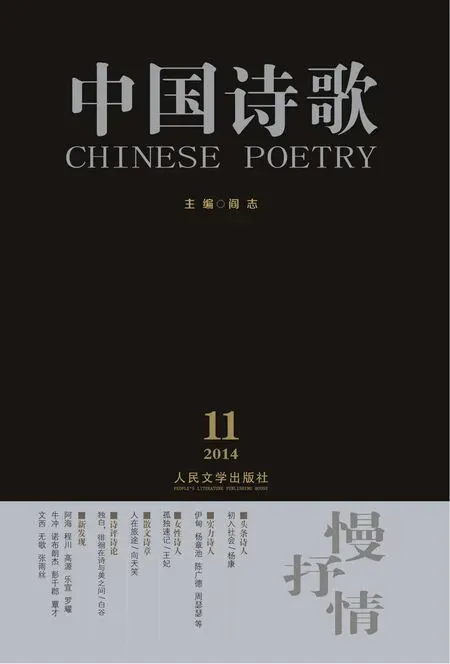杨章池的诗
2014-11-14YANGZHANGCHI
YANGZHANGCHI
杨章池的诗
YANGZHANGCHI
存在
我对一个人说过,我什么
都给你,除了精神
我对另一个人说过,除了精神
我什么也给不了你。
这两天,这两个人
陆续跨出我的身体,头也不回。
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人:
一个不存在的人。
寒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零度以下,汽车反复启动
有一家人低语着远方。
一阵风执意寻找它的情人。
钟楼含混地说,七点吧
破旧如它,依然原谅了生活。
你将怎样降临?眉眼暗淡的
敌人和罪人。
垃圾箱口,避孕套耷拉
多年前的欢愉此刻重现。
香樟树交头接耳
小广场一派胡言。
冰渍里的月亮,盛下
几则往事。七楼窗帘后闪过的一线光
冷得像个笑话。
是啊,呵气就是遗忘,咳嗽
代表健康。雾又起了
五米之内有一场革命。
一树繁花
它好像是直接从这平房中
长出来的。一朵又一朵
怔怔的紫薇
挤在枝头不愿醒来。
它就是家庭的一员,看护着
破损的屋瓦,瓦楞中的几根草。
木门紧闭,打工者陪着遥远的机床
而祖孙正冒雨赶往最近的小学。
没有心情思乡和怀旧了,枝桠间
还栖着零星争吵。
旁边卖豆角的婆婆秤杆高扬
她眼里也有一树繁花。
修辞
穿过荷塘的风叫荷风
长满藕的水面叫藕海
潜入莲心的脚步叫莲步
从一朵荷花中绽开一座观音
从一颗莲子中诞生无限菩提
谁能同时有节,虚心,有情
像身体的佛堂寄着一个远方?
谁愿香,净,柔软,可爱
“四德”和“十优”?
我只负责唤来一场暴雨,让
大珠小珠,落满碧盘,
让宏大交响,洗尽灵魂的忧伤。
河那边
河那边有不同的方言。稠密的树林
黄昏时分就黑作一团
像我远房的亲戚,至今不共往来
河那边的天亮得很早,公鸡很贱
它扯起喉咙,搅乱三千鸭子
而姥爷的晨鼾还飘在霞光中
河那边的伢子很危险,逃学者们
隔河跟我们打仗。他们唱:
“河那边的人,肚子疼,肠子掉了不省得……”
河那边的哨棚和渔筏都会赶路
我四年级时一船坐到县城,成了回不去的新江口人
我有时指着对岸讲给你听,也讲给自己听
河那边很远,像过去的三十年那么远
对岸的少年总在不停吹口哨,用网打鱼,用卵石
掷来高高的抛物线
手扶拖拉机
紧跑几步就能挂在拖厢上
手抓横沿,两脚蹬住挡板
书包拍打屁股,红领巾勒紧喉咙——
驾驶员从肮脏鼻子和耳后夹着的
香烟间,刮来一阵嫌恶。
转学第七天,从危险的城里孩子
那里偷来的技艺不比骑牛困难
他们并不总穿白衬衫
而姥姥做的布鞋
总是落单。
合唱《小小少年》的没有我
吹口琴和小号的没有我
连留校背“日照香炉生紫烟”的
也没有我。新结拜的七兄弟飞向
他们的花果山,车站路队走剩我一人。
它吭吭地走,赶上来从烟筒里
抽我一耳光。爬上又怎样?
它猛然加速,喷出浓烟变成
拦在校门口的教导主任。
仰面飘下,我进入
傍晚的电影:满天星星
拥抱了两个月的绷带
“它是欺生的,轻狂的,
满厢吱吱叫的木柴也在跳跃!”
这是我一口咬到今天的理由。
蝉蜕
我们每天做很多事,使自己
仍有价值。
我们背过脸吞下不同的空气和药
凑到一起何其快乐。
我们互称爸爸,妈妈,像两个易碎儿童。
我们小心嘲笑彼此的蠢,绕开各自痛点。
我们用无穷无尽的交谈来证明我们并非
无话可说。
我们每天在心里拔着河,与
世界的黑,时间的长。
十年,二十年
我们一点一点用尽了对方
剩下各自的壳
我之所爱
我爱的是“水果”的光泽和气息
而不是苹果,葡萄和梨
我爱的是“女人”这个词的温度
而不是特定的体臭和怪脾气
我爱的是“世界”而不是它的肢体
在我心里奔跑的马
和这匹白马没什么关系
我的光
深夜从屋顶亮瓦渗入的那阵月光是我的
它为我留住了半个童年
梦中从那摞作业本上溜进蚊帐的灯光是我的
母亲留在额上的抚摸让我睡眠更深。
正午从榕树的细叶间漏下的那线阳光
是我的,它健康,热烈,深怀使命。
除了这三种光,我真的
不再需要其他的光。
哆嗦
这老人站在傍晚公交站牌前
哆嗦:他平伸的双手
握着一个想象的马达。
电钻轰鸣,斜截锯嘶叫
振动棒敲打着砂石。身边
这座大楼眼看就要站起来了。
在它巨大的阴影之下,他的
哆嗦与佝偻互文:
一对因过分传神而失去本体的喻体。
路过他的人个个有匆忙的理由。
秋风起了,一片哆嗦的叶子
落到他的肩膀
又一个清晨
每天的嘉宾指点江山,电视
统治人类。鸟声恳切,玻璃外
有一个意思就要直接蹦出来
黑暗盘旋离开,厨房如此干净。
碟子盘子轻轻磕碰,妻子端来
素净早餐,脚步无声。
满院子的杜鹃花都同意了。
你的爱,多么突然
就如它当初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