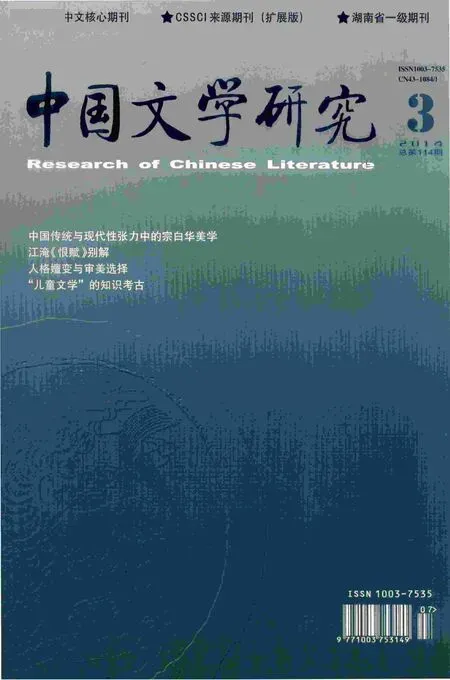南朝陈代辞赋初探
2014-11-14郭建勋
郭建勋 张 婧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清代严可均《全陈文》和《全隋文》共收录陈代辞赋32篇,单就数量来看,已居南朝四代之末,加之部分文人本由梁入陈,创作特色较梁代并无新变,故此前学者在述及陈代辞赋时,大多附于梁代之后一笔带过。如曹道衡先生的《汉魏六朝辞赋》介绍陈代辞赋不到二百字,且认为陈代辞赋没有脱出梁代萧纲、萧绎的窠臼,并未产生什么传诵之作。王琳先生的《六朝辞赋史》以“沈炯与陈代辞赋”为题单列一节,论述较曹著细致,但也承认:“辞赋在这个时期更加衰落,现存作品不过30篇,多为声色大开而兴寄莫存的咏物之作,基本是沿着萧纲、萧绎等前代宫廷文人的路子。”应该说,作为对陈代辞赋的基本评价,前辈学人上述看法并无不妥,只是容易造成陈代辞赋完全乏善可陈之感,与事实似不尽相符。平心而论,陈代辞赋虽继轨齐梁,重形式而轻内容,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易代之际文人的离乱之感、家国之悲,同时在骈赋技巧的运用上也多有进益,值得作更全面细致的考察。
一、咏物小赋
陈代咏物小赋共有17篇,按内容可分为三类。动植物类有陈后主《枣赋》、《夜亭度雁赋》,徐陵《鸳鸯赋》,褚玠《风里蝉赋》,江总《南岳木槿赋》,陆琼《栗赋》,张正见《衰桃赋》,周弘让《山兰赋》八篇;音乐歌舞类有顾野王《舞影赋》、《筝赋》、《笙赋》,陆瑜《琴赋》,傅縡《笛赋》五篇;服饰器物类有傅縡《博山香炉赋》,江总《华貂赋》、《山水纳袍赋》、《玛瑙碗赋》四篇。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自屈原《橘颂》开咏物兴寄的先河以来,后世文人无不通过自然物象来寄寓情志。这种兴寄手法尤见于陈代辞赋的动植物类题材。除《枣赋》、《栗赋》以单纯咏物为主外,其余都有明显立象尽意的痕迹。其中《风里蝉赋》、《山兰赋》是托物喻志。“终不校树兮寂寞,方复饮露兮光荣”,先借蝉声的起伏不定来感时伤事,再用蝉栖高饮露的生活习性象征自己超逸脱俗的风神气貌和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入坦道而销声,屏山幽而静异”,或侧重山兰甘愿寂寞,不求闻达的品性,抒发作者超拔绝尘的节操和渴望归隐的情怀。
《夜亭度雁赋》、《鸳鸯赋》则借物言情。前者如马积高先生所言,“把春夜的度雁与倡楼思妇的怨情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很鲜明的意境,特别是末段写怨情,层层推进,极见精思”。后者很可能是徐陵与萧纲、萧绎的同题唱和之作。二萧纯粹是借鸳鸯鸟喻男女恋情,而徐陵却站在更高的角度,将普通男女相思之情升华为人世间至真至纯之爱,传达出希望天下有情人“真长合会”、不离不弃的美好信念。故钱钟书先生以为:“结处以卓文君之孀居呼应山鸡、孤鸾之顾影无偶,较梁元之直言‘愿学’,更为婉约。”〔6〕(P432)
《南岳木槿》、《衰桃》二赋是以物喻人。有所不同的是,《南岳木槿赋》刻画木槿盛开时的艳丽妖娆,是为了引出和衬托红妆女性的风姿绰约,“以物譬花,以花譬人,花人映衬,极为艳丽”。而《衰桃赋》则是借衰桃喻女子容颜的衰老。用桃花盛开时的尽态极妍和衰败时的惨烈幻灭形成强烈比照,发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感慨,看似是衰桃之叹,实际是女子之叹。
再来看音乐歌舞类。古代文学作品中关于舞蹈场面的描写可追溯到《诗经·邶风·简兮》,枚乘《七发》也出现了对音乐场景的刻画。但辞赋中真正将音乐和歌舞结合起来却肇自《楚辞·招魂》。以此为基础,音乐歌舞类题材衍生为以写乐为主和以写舞为主两类。在陈代辞赋的此类题材中,集中写舞的只有顾野王《舞影赋》。辞赋中舞蹈题材颇多佳作,然顾氏却独辟蹊径,巧妙地将角度转向“舞影”,用新的视角展现舞女们的轻盈舞步和曼妙身姿。从听觉、视觉、嗅觉着手,将舞女之影写得惟妙惟肖,颇有新意。
集中写乐的赋作有四篇,分别刻画一种乐器,即顾野王《筝赋》、《笙赋》,陆瑜《琴赋》,傅縡《笛赋》。其中,《筝》《笙》二赋皆为六句,篇幅短小,作者并未对乐器多加展开,只侧重于音乐曲调和演出效果。《笛赋》因有所兴寄,格调高雅。傅縡通过写竹笛材质的耐寒、声音的嘹亮,讴歌了坚贞高洁、卓尔不凡的君子人格。陆瑜之作或受嵇康《琴赋》崇尚哀乐的影响,而带有明显的悲怨色彩。因琴身世凄凉,故琴音难免愀怆,所以能引发听者去国怀乡的悲愁之感。
在服饰器物类的四篇辞赋中,唯有傅縡《博山香炉赋》值得一提。此赋言简意赅,作者寥寥数语便将香炉的产地、制作、外形一一道出。赋尾的七言诗句“制作巧妙独称珍,淑气氛氲长似春。随风本胜千酿酒,散馥还如一硕人”,更刻画出香炉味道馥郁,香气袭人的妙处。其他《华貂》、《山水纳袍》、《玛瑙碗》三赋皆为江总所作。前两篇的创作缘由是为了“仰铭恩泽”,“奉扬恩德”。《玛瑙碗赋》虽未言明,但从题材内容来看也大同小异。作赋是源于政治上的颂扬而非个人情志的抒发,这对颇有才华的江总来说不失为一种遗憾。这类辞赋,和陈代其他应制类辞赋,如江总《劳酒》、《辞行李》、虞世基《讲武》、顾野王《拂尘筿》、陈暄《应诏语》、《食梅》等赋一样,没有多少文学价值。
二、纪行抒怀之作
除咏物小赋外,陈代还有一些纪行抒怀之作,这些赋更多地融入了作者真实的生命体验和创作激情,有的还形象勾勒出当时国家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的历史画面,刻画出颠沛流离、悲欢离合的情感生活,因此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价值。
其中首推沈炯《归魂赋》。这是一篇纪行赋,其源头发端于屈原的《涉江》、《哀郢》。后世文人多继承其以行踪为线索的创作手法,或咏史抒怀,发思古之幽情;或借古刺今,寄针砭讽谏之意;或羁旅行役,抒一己之感慨,创作了如刘歆《遂初》、班彪《北征》、蔡邕《述行》、潘岳《西征》等一批优秀的述行赋作。在这些“大赋”映衬下,《归魂赋》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与之后庾信《哀江南赋》相较,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及表现技巧方面也有所不及。不过,能在梁陈宫体之风弥漫,作品多注重形式精巧、缺乏真情实感之际出现这样一篇情真意切、反映时代声音的作品,《归魂赋》便显现出其存在意义。
该赋真实记载了沈炯在梁末丧乱中被掳西去、由魏东归的一段经历,带有自传性质。此赋取名《归魂》,很可能受屈原《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九章·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和《九章·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等句的启发。从魂牵故国、狐死首丘这一情感层面来说,屈原可谓沈炯之先导。
整体而言,该赋既体现作者国破家亡、骨肉离散的悲痛欲绝:“肌肤之痛何泯,潜翳之悲无伏。我国家之沸腾,我天下之匡复。我何辜于上玄,我何负于邻睦”;又有羁旅异国、举目无亲的黯然销魂:“去父母之邦国,埋形影于胡戎。绝君臣而辞胥宇,蹐厚地而踞苍穹。抱北思之胡马,望南飞之夕鸿。泣沾襟而杂露,悲微吟而带风”;更有魂归故国、去魏返乡的喜极而泣:“至诚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殒而魄散,忽魂归而气旋……泪未悲而自堕,语未咽而无宣。”全赋紧扣“归魂”这一主题,将去国之悲、乡关之思、归国之喜紧密结合,情感有起有伏、情节一波三折。
另外,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手法,通过对一些重要事件的回顾与叙述,抒发情感,渲染气氛。如描写被掳西去和由魏东归的两段景物描写:
履峨峨之层冰,面飀飀之岩雪。去莫敖之所缢,过临江之轨折。矧今古之悲凉,并攒心而沾袂。渡狭石之攲危,跨清津之幽咽。
于时和风四起,具物初荣。草极野而舒翠,花分丛而落英。鱼则潜波涣濯,鸟则应岭俱鸣。随六合之开朗,与风云而自轻。
一幅是西去之沉痛,一幅是东归之欢欣。两幅画面悲喜对照,苦乐相衬,作者移情入景、物我情融,使作品具有非常震撼的艺术感染力。陈寅恪先生有言:“今观《归魂赋》,其体制结构固与《哀江南赋》相类,其内容次第亦少差异。至其词句如‘而大盗之移国’,‘斩蚩尤之旗’,‘去莫敖之所缢’,‘但望斗而观牛’等,则更符同矣。”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归魂赋》与《哀江南赋》差可比拟。
江总《修心赋》则流露出其圆滑老道的生存哲学。此赋是侯景之乱时江总避乱于龙华寺所作。尽管在序中抒发了山河破碎的伤痛,但在面对这种惨淡的现实时,他却选择消极隐世,试图用佛法义理作为心灵苦痛的解救之方,以达到宠辱不惊、遗荣忘累的超脱境界。曹道衡先生认为“这完全反映了南朝后期高门士族在动乱中虽有悲愁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心理”,这也正是江总生逢乱世却巧避风险、游刃有余的生存智慧之所在。
释真观《愁赋》围绕特定情感作赋,从取材立意来看,是借鉴江淹《恨赋》与《别赋》。忧愁是人生的一种复杂情绪,飘忽不定、难以名状,作者先用山岳、沧溟、烟雾、玉叶、金波等自然物象喻愁,构思新颖别致,再用历史典故对“愁”加以铺陈渲染,有去国辞乡之愁、怀才不遇之愁、贫苦窘困之愁、荡子思妇之愁,使读者对愁情有了全方位的体验和理解。他的《梦赋》是假借主客问答的汉大赋形式,阐释佛教义理,表现了作者“无为无欲,何惧何忧”,希望超脱世俗的士人心理和虚无人生观。
综上所述,尽管尚未脱离梁代“金声玉润”、“绣错绮交”的浸淫,但陈代辞赋已开始呈现出创作结构小品化、语言风格浅易化的趋势。由于朝代短暂,辞赋家们还来不及作深刻体验与沉淀反思,作品柔靡空乏。就咏物赋而言,以体物小赋为主。虽有所兴寄,但题材内容多因袭前朝,缺乏新变,呈现出狭窄单薄的特点;就抒怀赋而言,作家多站在个人角度抒发情志,表现个体生命体验,欠缺壮阔情思。尽管其中也有触动心弦的感伤之作,但不足以代表陈代辞赋的主流。
三、陈赋的诗化
程章灿先生将赋的诗化分为“赋末乱辞”、“赋中系诗”、“诗赋合一”三个阶段。若从诗歌句式考察而言,赋的诗化起于引骚入赋,西汉枚乘《七发》始用“歌曰”衔接七言骚体句式。为求新变,张衡《思玄赋》、马融《长笛赋》“从民间歌谣中吸收了七言句式”。赵壹《刺世疾邪赋》还在篇末系上两首五言诗。至此,引诗入赋的基调已得到确立。到了南朝,赋的诗化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出现谢庄《怀园引》、《山夜忧吟》、沈约《愍衰草赋》这样亦诗亦赋之作,诗、赋这两种抒情文体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梁代不少辞赋都显露出诗化的痕迹,但主要集中于庾信、萧纲、萧绎等人所创作的咏物艳情赋,而陈代辞赋的诗化则有推波助澜之势。陈后主、徐陵、江总、沈炯、陈暄、傅縡等都不乏引诗入赋的实践。
陈代辞赋主要以四言和六言句式为主。在此基础上,辞赋家们借鉴前人,引骚入赋,继承楚骚抒情传统。比如陈后主《夜亭度雁赋》:“从风兮前倡融,带暗兮后群惊。帛久兮书字灭,芦束兮断衔轻”;徐陵《鸳鸯赋》:“飞飞兮海滨,去去兮迎春”;褚玠《风里蝉赋》:“愁人兮易惊,静听兮伤情。听蝉兮靡惓,更相和兮风生。终不校树兮寂寞,方复饮露兮光荣”;陆琼《栗赋》:“金盘兮丽色,玉俎兮鲜光”;陆瑜《琴赋》:“飞青雀兮歌绮殿,引黄鹤兮惨离筵。吟高松兮落春叶,断轻丝兮改夏弦”等,这些骚体诗句为全赋增添了摇曳的风姿和清美的情韵。
据马海英先生统计,“陈代五言诗的声律、篇制、对偶已非常成熟”,“七言诗总体格律化不如五言诗,但也有趋势表现出来”。赋的诗化是多种原因所致,但诗歌体制的成熟和创作的繁荣,无疑会造成其对辞赋强有力的渗透,所以陈代不少辞赋都留下五、七言诗句的痕迹,具体表现为赋末系诗与赋中系诗两种情况。赋末系诗如沈炯《幽庭赋》:“于是起而长谣曰:故年花落今复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长绳系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陈暄《应诏语赋》:“欲同吃如邓士载,欲作辩似娄君卿。为首为相并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傅縡《博山香炉赋》:“制作巧妙独称珍,淑气氛氲长似春。随风本胜千酿酒,散馥还如一硕人”。这些口语化的诗句作为赋的补充,增强了抒情意味,弱化了骈俪效果,既有民歌风味又有宫体色彩,雅俗共赏。
赋中系诗如徐陵《鸳鸯赋》,七言与五言相互杂糅,几乎占去整篇大半。黄庭坚《题画睡鸭》将徐赋中“山鸡映水那自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两鸳鸯”之句一变为诗:“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和,两凫相倚睡秋江”。陈后主《夜亭度雁赋》则包含三、四、五、六、七言相互交杂的句群,明显受到谢庄《怀园引》、《山夜忧吟》的启发。郭维森和许结先生在论述南朝诗赋合流时也提到陈代辞赋的诗化现象,认为江总《南岳木槿赋》“既有七言诗句,又有五言之歌唱,诗句作赋已成风气”,徐陵《鸳鸯赋》中“五、七言诗间出,且用口语,富有民歌情调”。
可以看出,陈代辞赋中四、六言句式与骚体“兮”字句相互杂糅是常见现象;赋中所引的五、七言诗句大部分单独拿出即可构成一首完整的五言或七言诗;引诗入赋不再局限于某位作家或某类题材,而在辞人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发展;从赋末系诗到赋中系诗,诗句作为赋的补充不再固定出现在赋的末尾,可自由发挥,从而使情感抒发得更加淋漓尽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赋作中,只有《幽亭赋》和《南岳木槿赋》在诗前系有“谣曰”、“歌曰”进行连接,其他几首都直接由赋过渡到诗,体现出诗赋合一的圆融境界。
四、陈赋余波
诚如马积高先生所言:“一个王朝开始建立和巩固的一段时间内,其文风多沿袭前朝,这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学发展中带规律性的现象。”作为陈代后继,隋唐两代文风难免受其影响。一方面,陈代灭亡后,很多旧朝遗臣归顺隋文帝,比如江总、虞世基等人,依旧在新朝为官,从而延续了其在陈代形成的辞赋创作上的风格特征;另一方面,一些由北入隋的文人在隋统一前还曾出使过陈朝,颇受梁陈文风熏染。其中如薛道衡之作甚至令南人折服,《隋书》本传称:“江左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咏焉。”薛道衡喜欢追仿梁陈藻绘缛丽、靡妍精工的骈赋,其《宴喜赋》“刻画之细腻,对偶之精工,音韵之和谐,与南陈当时赋家如江总实不相上下。”初唐时期的君主同样爱好文艺。尽管此时辞赋在辞采富艳、用典繁密方面不及陈代,但旧臣的流入、宫廷生活的相似、君主的喜好等因素共同促成了南朝赋风在初唐的赓续。
也正因为如此,太宗时期的一批应诏类辞赋,如杨师道《听歌管》、虞世南《狮子》、李百药《鹦鹉》、许敬宗《欹器》、《掖庭山》等赋作,无论是风格的秾丽,语词的雕琢还是创作的意图,都不由让人联想到陈代江总、虞世基等人在宴席闲咏时的奉承感恩之作。而虞世南原本就是徐陵的得意门生,入唐后又受到太宗青睐,衣钵因此得以相传。此外,陈代辞赋追求新奇、构思纤巧的命题方式亦为唐代文人所效法,程章灿先生即指出,陈后主《夜亭度雁赋》、顾野王《舞影赋》、褚玠《风里蝉赋》“开了唐人命题之先河”,王勃《寒梧栖凤赋》、《江曲孤凫赋》、《涧底寒松赋》、张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等便属于这种情况。
相比之下,陈赋对入唐以后赋体文学新变的影响似更值得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歌行体辞赋,二是律赋。
如前所述,梁陈两代文人辞赋创作大量引入五、七言诗句,进一步发展了赋的诗化倾向,这直接影响到初唐赋家的创作。如王勃在《春思赋》中便大量运用五、七言诗句,其中七言诗句甚至成为该赋的主体。还有骆宾王《荡子从军赋》,以五、七言诗句为主干,间杂以四、六言骈体句式,将古诗与骈句相结合,既有歌行体的遒放宕逸,又有骈文的精工婉丽。刘希夷所作《死马赋》,虽题为赋,但全篇皆为七言,和骆宾王《荡子从军赋》一样构成初唐歌行体辞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陈代文人引诗入赋的大量实践对后代长篇歌行辞赋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律赋的形成也不例外。律赋与骈赋之承续关系,前人早已指出,如元代祝尧《古赋辩体》称:“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也说:“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依马积高先生之见,律赋的特点是“篇幅短小,开头就要破题,除基本上通体俳偶外,还限定几个字作为韵脚”。同时,“律赋是从骈赋中蜕变出来的,如果我们把限韵这一点略去不计,则通体对偶的短赋在体制上即与律赋没有区别”。骈偶的运用在整个南朝辞赋中原属常见,而陈赋则将这一特点推向极致,甚至达到了句句皆对的地步。如张正见《石赋》被李调元称为“通章无句不对,实开律赋之先”。其他如《舞影》、《筝》、《笙》、《拂尘筿》、《栗》、《贞女峡》、《云堂》、《华貂》、《山水纳袍》等也都是通篇对偶。这已然在对偶方面为律赋的出现作了充分的准备。再从篇幅方面来看,陈代辞赋以小赋居多,呈现出小品化的趋势,这也与律赋体制相吻合。概而言之,尽管唐代律赋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但陈赋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虽然整体而言,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陈代辞赋均难媲美此前宋、齐、梁三代之作,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且构成了由南朝辞赋向唐代辞赋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故理当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
〔1〕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王琳.六朝辞赋史〔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陈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三联书店,2001.
〔7〕(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哀江南赋〔M〕.北京:三联书店,2001.
〔9〕(唐)姚思谦.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0〕曹道衡.论江总及其作品〔J〕.齐鲁学刊,1991(1).
〔11〕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2〕马海英.陈代诗歌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13〕(宋)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4〕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15〕(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韩晖.隋及初唐赋风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7〕(元)祝尧.古赋辨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9〕(清)李调元.赋话(续修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