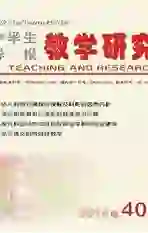弃婴岛问题与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
2014-10-21李小元
李小元
摘要:在我国,“婴儿安全岛”的设置和运行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广泛讨论。本文认为“婴儿安全岛”只能是维护婴儿权利和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要做到真正满足包括婴儿在内的儿童需求、维护儿童权利和合法权益,必须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致力于完善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儿童大病医疗保障制度,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共担和共同努力。
关键词:婴儿安全岛;儿童福利制度;责任共担
一、婴儿安全岛
弃婴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均存在,是一個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为了保护弃婴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维护婴儿的合法权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对其予以保护,严格禁止弃婴并且严厉惩罚弃婴行为。此外,许多国家还建立了弃婴接收和保护设施,旨在使那部分已经被丢弃的婴儿得到及时的保护,这体现了生命至上和儿童权利优先的原则。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弃婴设施最早于1188年出现在法国,称为“弃婴轮盘”;后来,意大利等欧洲多个国家以及欧洲之外的俄罗斯、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国家也设置了类似的弃婴保护装置。[1]
与国外相比,针对弃婴设置保护设施对我国来说还是新兴事物。2011年6月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弃婴保护装置——“婴儿安全岛”,用来收容被遗弃的婴儿,并给予他们及时的照顾和救治。经过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先行试点,民政部于2013年7月26日发布通知在全国各地开展试点工作,以保护弃婴的生命健康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人们对是否应该建立弃婴收容装置和设施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肯定者认为这些装置有利于及时的为弃婴提供保护和照顾,避免弃婴遭到其他一些因素的伤害,是对婴儿生命健康权的尊重和保护;反对者却认为弃婴岛的设立违反了法律禁止弃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弃婴行为的变相纵容和容许。正如柳华文所说的,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既涉及预防和打击遗弃未成年人犯罪,又涉及儿童权利保护,还涉及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以及运作。”
二、“婴儿安全岛”折射出的问题
(一)弃婴岛只是诸多服务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设立弃婴岛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及时发现弃婴并为他们提供保护和照顾,避免他们遭受第二次的伤害,确保弃婴的基本生命健康权,这体现了政府以弃婴为中心的儿童福利理念,也体现出国家和政府对儿童权利的重视和保护。这显示出设置弃婴岛的初衷是好的、无可厚非的。但是,对弃婴的救治不仅仅只是设置弃婴岛这么简单,而是需要一系列相关服务链条和环节紧密衔接和配合。具体包括:收留弃婴的福利机构须配置具备医疗、康复、教育等功能的基础设施和器械,须配备相关的专业护理人员,须与医疗救治机构等建立良好的联系和转移制度和机制,须与公安机关联合做好弃婴的户籍登记和联合打击恶意弃婴现象,须与民政和财政部门建立好联系以获得相应的补助资金等等。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和不完善都会使婴儿的合法权益受损。
因此,我国在开展试点工作的过程中应该格外注重对弃婴岛的相关配套设施、制度、机制和部门的完善,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使弃婴岛发挥好其最后一道保障线的作用。
(二)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父母的缺位
婴儿被遗弃的主要原因是生理上的缺陷,目前,我国各类福利院收养的弃婴中患病和残疾的人数占很高的比例。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首属群体对一个人而言是最重要的群体,其对个人的社会性和独立性的形成有基本的影响,而家庭就属于首属群体,主要包括父母和其他亲人。[2]孩子的治疗和成长,除了治疗资源的保障外,也离不开父母的关心和呵护。而且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家庭是不可或缺的主体,福利院不能取代家庭的作用。这也是导致弃婴岛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即父母应不应该完全放弃自己对孩子的抚养责任和义务,而把责任完全推给国家和社会;父母在这部分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缺位会不会对儿童健康人格和心理的形成造成影响。
(三)弃婴数量激增折射出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不完善
广州“婴儿安全岛”是全国首个叫停试点的城市,因为其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接收了262名弃婴;山东省济南市婴儿安全岛从6月1日设立到10日这短短的11天时间内就接收了106名婴童,且有百分之八十是重度疾病患儿。从这些设置“婴儿安全岛”后出现的弃婴数量激增的现象来看,被遗弃的主要是患有疾病或残疾的婴儿,其中不乏设置弃婴岛的初衷被有些父母恶意利用,但是,本文认为这只是少数,大多数父母都是因没有能力给孩子治病而选择把他们放在婴儿安全岛,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救治。这反映出我国对患有大病的儿童和家庭的救助和支持制度的缺失或不足,弃婴岛中婴童数量的激增恰恰折射出人们对这一儿童福利和保障制度的需求。
因此,本文认为不能单纯的讨论弃婴岛是否应该存在,而是应该透过“婴儿安全岛”折射出的问题,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注重从源头上入手去维护这些婴儿的合法权益。
三、儿童福利制度与弃婴救助
(一)儿童福利制度
儿童福利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作用,儿童福利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儿童福利针对的是全体儿童的普遍需求,体现的是一种预防性和发展性的取向,包括提供给儿童本身的直接福利和提供给儿童所在家庭和社区的间接福利;狭义的儿童福利针对的主要是特殊儿童的特殊需求,体现的是一种补偿性取向,如针对残疾儿童、弃婴、受虐待的儿童等的福利制度。对弃婴的救助就属于狭义的儿童福利的范畴。[3]
总的来说,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如,高华俊(2013)认为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表现出以下不足:制度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和行政机构缺位;儿童社会服务组织数量少且面临发展所需的资源短缺困境;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规模和金额不足;困境儿童所需的相关福利服务短缺等等。[4]
具体来说,2013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5%,这部分儿童及其家庭有着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满足。婴儿处于儿童的早期阶段,是最脆弱的群体,尤其是其中的患有先天性疾病和生理缺陷的婴儿,这部分婴儿及其所在家庭的需求没有得到的满足。虽然我国国家民政部、卫生部于2010年6月出台了《关于开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的意见》,但是这次试点工作的范围只是农村儿童,所涉及的病种也很有限,不能满足更多儿童和家庭的需要,进一步折射出我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缺失和滞后的。
(二)完善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需多主体责任共担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由于先天生理缺陷或患有大病而可能被丢弃的婴儿的救助,为了减少弃婴和救助这部分患有重大疾病的婴儿,我们应该积极促进我国相关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宣飞霞,王玥(2013)和劉继同(2013)。[5]因此,本文主要侧重的是儿童福利制度中的一个方面即儿童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完善。由于目前关于婴儿安全岛的相关学术研究很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探讨多见诸于报纸、网络等,本文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只是在笔者自己思考的基础上的一些不成熟的探索。
在完善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强调责任主体的多元化,即实现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共担,其中的主体是政府,但具体的运作需要家庭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共担责任。
第一,就政府而言,其作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主体应该积极致力于完善我国的医疗救助制度,尤其是儿童大病医疗保障制度。政府应该在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的基础上,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定和方案,积极听取各方的意见和需求,进一步扩大试点的范围和救助的病种,把更多的儿童与病种纳入医疗救助的范围;应该加大对儿童尤其是婴儿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的投入,确保这一救助制度能够持续运作下去,以减轻有患有重大疾病婴儿家庭的压力。
第二,就社会力量而言,这里主要指的是非政府组织。建立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和儿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仅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应该鼓励致力于儿童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对儿童重大疾病救助及其家庭的服务中来,发挥其优势,充分调动其社会资源,努力为患有重大疾病的婴儿及其家庭提供资金支持、专业的医疗服务支持、生活服务支持等,使更多的患病婴儿能够得到救治、其所在家庭的压力和负担能得到减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吸引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第三,就家庭而言,好的家庭福利是儿童福利的重要支撑,因为家庭是儿童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因此,政府在完善儿童社会福利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增进家庭的福利,如建立家庭津贴和家庭收入维持制度,以支持和促进儿童福利,尤其是对患病婴儿及其家庭的救助和支持。[6]同时还应该倡导树立儿童福利和救助责任的国家、社会和家庭共担的价值理念,使家庭在面临患有重大疾病的婴儿和儿童时时不至于束手无策而做出丢弃婴儿的举措。
此外,我们在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的同时,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以降低婴儿出生缺陷率。一是学校应该注重对青少年学生的性教育,减少意外怀孕和生育而导致的弃婴和有缺陷婴儿的出生数量;二是通过多种渠道宣传、鼓励新婚夫妇进行婚前体检和孕前检查,做好早期的预防;加强孕期的指导和检查,提高健康婴儿的出生率。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医院、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为这些措施的推进提供相关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柳华文.设立弃婴岛与儿童权利保护[J].人权,2014,(1):36-41.
[2]王瑞鸿.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90.
[3]宣飞霞,王玥.国外儿童福利模式及孤儿、弃婴救助经验评介[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8-44.
[4]高华俊.中国儿童福利的制度转型与政策设计[J].社会福利,2013,(6):15-17.
[5]刘继同.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构建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6):4-12.
[6]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3(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