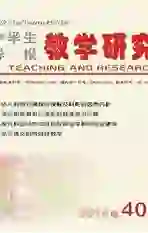在人群中若即若离
2014-10-21向泽莉
向泽莉
人穿行于象征之林,
那些熟悉的眼光注视着他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同爱伦·坡、雨果、巴尔扎克、恩格斯笔下的巴黎相同。第二帝国的巴黎,人群、橱窗、赌场……一切在跳動而混乱的煤气灯光下,被绘出点彩派般光怪陆离的平面效果。煤气灯亮起来了。司灯人穿过拱门街挤满建筑物的通道和夜游症的人群,把幽暗隐晦的街灯点亮。玻璃顶、大理石地面的通道,豪华的商品陈列、赌场、玻璃橱窗……人群的面孔幽灵般显现,他们焦灼、茫然、彼此雷同,拥挤得连梦幻都没有了间隙。
本雅明深层挖掘了波德莱尔作品中有关巴黎的文化构建与想象,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深刻的理解。人群是波德莱尔着重的意象,本雅明注入了更多理性的思考。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开始了它第二真正的工业革命。在本雅明的理论话语外衣之后,挽歌式的哀叹和眷恋无奈的怀旧伤感随手可拾:渐次熄灭的煤气灯、把人被迫固定在土地上的住房牌号、日渐堕落成商品生产者的专栏作家……
“注视”是这首时代挽歌背后隐性的关键词,本雅明作出了诗意的阐释。
人群、人群中的人、诗人,甚至包括作者本雅明自身,都被卷入这种既离且合的多重注视关系之中。注视作为一种能力,是为人群作出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群(Les Foules)在本雅明笔下,是一个含混而暧昧的意象。它消灭个人痕迹于拥挤和雷同之中,又使个人的孤独感成倍地放大;它是游手好闲者窥视的对象,也是赋予诗人们安全感的隐遁场所。可以说,人群是屈从于工业化商品社会的残余意象之一,是另一个后来被文化研究置于中心地位的研究对象——“大众”(乌合之众,mass)的前身。城市人群的注视功能被明显地剥离开来,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所应具有的“看”的后继能力。
“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地表现在眼的活动大大超越耳的活动。公共交通手段是主要原因。在汽车、火车、电车得到发展的十九世纪以前,人们是不能相视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而不攀谈的。” 有交通工具衍生出来的公共空间迫使人们无辜的相互凝望,人们逐渐的倚重用眼睛判断他人的内心。因此,盲人比聋子会更加恐惧。
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人群目光的功能却退化了,他们能注视,但却不能捕捉。他们被动地滞留在某种日趋机械化、工具化的状态。就像古时鬼魅附身的神话,人群似乎也被某种东西附上了灵魂,能看、能动,但行为却越来越外在于他们自身。本亚明在这一点上认可了马克思的分析:人,在资本主义的流水线之前,变成了游走的“商品本质”。工人、律师、财会……,对于他们,日常劳作更多关注的是物,在流水线、帐本、货币、商品建构的物质世界里,“他者”逐渐丧失了合法的地位,或者说,在他们的目光里,他者也被物化了。通过对他者的审视而确定自己,是他者存在对于人自身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人确立自我形象与个性的一个前提条件。在机械化和技术化的时代,人被机器工具化、变成了具有商品本质的劳动力。渐渐丧失差异和分歧,丧失了个性存在的一切可能性,同化使主体与他者不再能够得到恰当区分,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人”的消失、“人群”的出现。
人群成了一个吞噬个人的庞然大物,但是,反过来说,它也成为一个寻得庇护的最佳场所。于是,在对波德莱尔作品的分析之中,又一个意象从乌合之众背后浮现出来,那就是:人群中的人(I homme des foules)。
人群中的人。他们在人群中游荡、窥视,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冠以他们的各种所指和标签:密谋者、波西米亚人、拾垃圾者、游手好闲者、妓女……持有这些身份的人有着共通之处:他们是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单数的人。他们不仅是诗人的描述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可以说,他们是前工业时代的最后一批幸存者。
人有着和“人群”不同的注视能力。他们与后者始终处于一种窥视与被窥视的关系之中。街道与玻璃橱窗则是他们的道具。“在‘游手好闲者身上,看的快乐是令人陶醉的。” “人群中的人”是与“人群”不同的、还没有失去东张西望能力的那一些;但是,和纯粹看热闹的人不同,他们又充分地保留了自己的个性。他们注视中的他人形象没有被完全物化,是因为他们自身并未完全被挤压入这个拥挤而嘈杂的物质世界。
但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游手好闲者”又不等同于诗人的自画像。“真实生活中的波德莱尔并不像一些人描绘的那样‘心不在焉。”人群的陷落引发了他自我意识更深重的警觉。诗人的世界,对外部有选择地关闭或敞开。“诗人享受着既保持个性又充当他认为最合适的另外一个人的特权。他像借尸还魂般随时进入另一个角色。对他个人来说,一切都是敞开的;如果某些地方对他关闭,那是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地方是不值得审视的。”在这种关闭和敞开的过程中,人群成为诗人隐蔽的意象,“他人”在注视的目光之外,成为一个个可代入、可置换的符号。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很少能够找到对“大众”的描述;相反,倒是富于象征意味的个体在按照诗人的主观理解而被夸张扭曲后形成诗歌里的一个个意象,比如充满衰败意味的“小老太婆”,比如作为捕捉不到的爱的表现的“交臂而过的妇女”。
面对人群,波德莱尔反而退避回自己的内心,“注视”,成为一个指向内在世界、而非外部秩序的行为。在此意义上,诗人完成了一次自我意识的强化,这种逆世而行的对抗建构了一个隐遁于人群,又把自己于人群中剥离出来的特立独行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