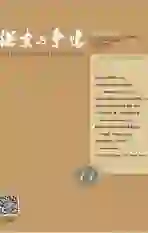文化翻译的“飞散性”:一种超越的文化逻辑
2014-10-21周宣丰
内容摘要 受“二元论”的影响,翻译中弥漫着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衍生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文化结构。然而,昔日的中心—边缘的文化政治格局已被文化多元化格局取代,文化的混杂性和飞散性是当代的文化特征。鉴此,译者应跨越二元对立,以超越的文化逻辑,从“飞散”视角重新思考文化翻译的作用和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
关 键 词 文化翻译 二元结构 飞散性 超越的文化逻辑
作者 周宣丰,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广东江门 529020)
文化翻译中的二元结构
作为跨学科研究,翻译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元论”和“同一性”思维可以说是衍生弥漫在翻译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过度迷恋“等值”神话的始源。就文本意义观和文化价值观而言,“同一性”思维的遗产则是呼吁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和权威性,文化价值标准的终极性、文化身份的本真性,排除文化相异性、意义的多元性、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而哲学思想说到底是由二元论决定的。[1]二元对立思维渗透到翻译研究中,使翻译学科充满了无数二律背反命题。其中,对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有着浓厚的“二元对立”情结。
从后殖民视角来看,这种“二元对立”情结具体体现在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敌对”状态上,为了挑战和反对殖民时期和权力关系不均衡引起的翻译的帝国(文化霸权)立场,一些后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过分强调其翻译的民族(文化抵抗)立场,片面强调民族文化的不可译性和本真性。然而,这种非黑即白的对文化的看法与文化的本质是相冲突的。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文化的民族性也只有放在世界文化的蓝图中才能被界定。另外,这种认识论也无益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只有与世界文化互动才能保存活力。翻译在民族文化之间所起的协调和互动作用越来越不可替代,好的翻译应该是民族文化延续和创新的结合。这正如美国学者韩南(2004)所言:“译文之间的差异一般都能用游离于两极间的总括性的词语加以描述,即一极是对所有方面的保留,而另一极则是对所有方面的同化。”[2]
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关系在强烈的文化身份诉求的驱使下显得更为紧张,特别是在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资本累积出现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当一方支配表征系统而另一方失去自我表征权力的情况下,“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尤为突出。而生活在特定文化结构下的译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着特定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代理人和代言人,在处理和表征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差异时,往往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二元倾向性(要么呈现出“自我”中心,要么呈现出“他者”中心)。然而,昔日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中心-边缘”世界文化格局体系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巴别塔”的世界,来自不同种族、有着不同宗教信仰、文化背景、说着不同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文化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随着文化互动所带来的“混杂的文化”(hybridized culture)使“纯真的文化”(purified culture)成为一个逝去的“神话”。基于这种境遇,我们对跨文化交流、对语言文化和翻译的“飞散性”应该有一种全新的认识。那么,在文化全球化和混杂化的气候下,译者能否超越自我/他者的二元分野, 拥有一种超越自我、宽容文化“他者”的胸怀呢?能否真正做到“出入于多种文化而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文化”的精神层面上的“飞散者”或者两种文化或者多种文化的“文化中间物”(cultural intermediary)或者文化亲信(cultural repository) 呢?
文化的“飞散”
从词源学来看,“飞散”(diaspor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diaspeirein”。后来,“飞散”成为文化研究的关键术语,它的意义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衍变。[3]
本文所用的“飞散”,专指特定文化实践的体验和思维方式,即具有“飞散意识”的文化实践。从后殖民视角看,“飞散意识”与殖民意识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文化和文化身份观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殖民意识和狭隘的民族意识下的文化和文化身份观是本质主义的,两者的核心命题是文化是本真的,文化身份是凝固的,而“飞散意识”强调的是文化的混杂性、异质性、文化身份的碎片化和建构性。因此,“飞散”已成为能指丰富的一个符号,用来思考文化知识生产的“混杂”模式,文化身份的多元“建构”模式,是对二元文化观和凝固的文化身份观的强有力的反拨。而二元文化观和凝固的文化身份观是殖民时期殖民权力代理者为了服务建构一个处于文化结构上层的“自我”,而将“他者”进行“他者化”表征的权力话语策略。与帝国主义话语实践相伴而生的民族主义话语实践(民族翻译也是一种民族主义话语实践)在特定历史时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消解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文化政治效应,但往往呈现出历史局限性,特别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例如,冷战后地方主义、种族主义引发的暴力冲突。所以,后期后殖民研究针对前期后殖民研究“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反思,认为“民族主义有固有的支配性、是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是破坏性的”[4]。
虽然“飞散”具有跨民族性、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无根性。“飞散者”只是从跨民族视角来审视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性,认为“民族性”与“本土性”是在“跨民族”关联网中实现的,是流动的、指向未来的。所以,与文化守成不同的是,“飞散”视角中的民族文化强调的是其跨民族性、繁衍性和可译性。“飞散视角”具有双重特征,即“抵制文化同化,同时又以跨民族的眼光和文化翻译的艺术进行新的文化实验和实践”。[5]来自霸权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仍然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叙事得以存在的逻辑起点,然而跨民族的世界格局、民族身份的跨民族性和混杂性,以及飞散的文化需要重新定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跨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画地为牢的文化界限[6]。
“飞散意识”是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与不同文化进行碰撞和对话而生成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时代,与文化“他者”发生碰撞和冲突是必然的。但是,文化全球本土化已成为一种共识,单一视角和凝固文化身份观下的文化和意义生产模式显然已经与当今的文化特征和复杂的国际政治文化语境有很大出入,而且文化的二元认识论也是开展跨文化对话的障碍。而飞散意识既是对文化边界的跨越,也是对单一视角下的激进的身份观的超越,“自我”与“他者”互为主体。也正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张力关系中,“飞散者”才会带回丰富的养料滋养民族文化,使得民族文化保持活力,故有“不译则死”的说法。
一种超越的文化逻辑
然而,随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我们进入了各民族各文化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时代。在这种充满张力的“后”时代,从单一视角来认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是不对的、危险的。“互主体性”、“对话”才是对殖民话语中的“自我主体性”和对“他者”进行“他者化”表征的一种理性的、超越的文化逻辑。其实,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一切文化可以说都是被翻译的文化、跨民族的文化。当然,我们强调文化的飞散性、翻译性和跨民族性的真正意义在于突出文化协调的可能性。因此,从文化的“飞散”特征来看,好的翻译应该让源语语言文化处于 “飞散”状态,让译语语言文化适当优化。相应地,译者作用也发生了变化,译者应超越 “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从文化政治代理者转变为文化搭桥人、文化协调者或者文化中间物,通过文化翻译更好地进行文化互动和文化价值的外传和民族文化的创新。
“飞散”视角下的翻译除了具有跨民族、跨语言与跨文化性之外,还具有“再生性”和“繁衍性”。借本雅明的话,译文是原文的来世,翻译不仅是意义的传递,更是一种生产性的书写。民族文化的民族性也只有在跨民族的关联过程中才能实现,也只有这样民族的文化记忆才有延续的希望。既然这样,译者既不应该是文化殖民的帮凶,也不应该只是文化抵抗的角斗士,不能将“异质性”过度归化或异化,而是以文化飞散者和文化协调者的身份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适当引进异质文化生成一种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或在译介民族文化时,坚守“民族性”,但以灵活变异的方法让民族文化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从而进入世界文化体系,参与文化对话和文化协商。因为“译”者易也,即换言语使相解也。所以,作为“飞散者”的译者要有文化自觉,在世界文化体系下对民族文化重新定位,既要反对“同一化”的文化霸权,又将“民族性”用另一语言文化再现出来,使之具有可译性和可传承性,形成跨民族性。当然,如前所言,飞散的民族文化不是无根的,译者既要坚持民族立场,敢于挑战以同化目的为主的国家文化实践,又要超越狭隘民族立场,坚持跨民族立场,参与跨民族文化实践,将民族文化置于飞散状态使之繁衍。在霍米·巴巴看来,文化翻译是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族裔文化繁衍生息的文化政治话语策略之一,译者要通过文化翻译在“间隙”处,在“第三空间”和“中间位置”创新,所以文化翻译意味着一种“新颖性”,它出现于不同社会和文化意指系统所导致的经常性的抗争与流动之域。它作为一种被动的反抗性替代物能够自主地发挥一定的文化政治效用。[7]
因此,文化翻譯的“飞散性”要求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从二元对立的思绪中摆脱出来,以一种超越的文化逻辑重新认识文化翻译的身份和译者的主体身份。翻译的身份是多元的,除了参与文化殖民和文化抵抗之外,还要发挥“桥”的作用推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译者的主体身份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一名世界公民,要抛开因权力差异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偏见以及惧怕“同一化”的文化心理而导致的文化排斥,推动文化融合。因为语言文化的多元之美才是众望所归。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9.
[2]韩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10.
[3]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An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1-2.
[4]Laura Chrisman. Nationalism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in Neil Lazarus(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2004:183.
[5]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中国比较文学,2005(3).
[6]Margaret Connell Szasz. Between Indian and White Worlds:the Cultural Broker.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4.
[7]Homi Bhah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4.
实习编辑 高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