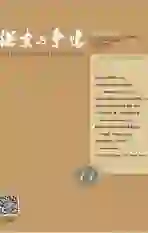以新普遍主义建构世界秩序
2014-10-21苏长和
内容摘要 共生是一种智慧。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普遍主义思想,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政府与政府乃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这种普遍主义从关系、共通、联系角度看待和完善上述关系的共处和共生问题。那种认为适用于自己的法则同样也可以推及他者、干涉他者甚至改造他者的西方式普遍主义思想,已经成为阻碍文明间和谐共生的消极思想力量。新的普遍主义有助于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在寻找共通共鸣中实现和谐共生的秩序。
关 键 词 共生理论 合解/分解 关系/理性 两种普遍主义 世界秩序
作 者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对两篇商榷文章的感想和回应
共生是一种生活智慧和政治智慧。
笔者的《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与任晓教授的《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两篇文章,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一定的关注和讨论。近年来,主要是在上海国际关系学界以及胡守钧、杨洁勉、金应忠等学者的推动下,“共生”这个词在中国社会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引起讨论。《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4期刊登了陈雪飞的《中国应建立文明导向的世界秩序观》(以下简称陈文)和熊李力的《共生型国际体系还是竞合型国际体系》(以下简称熊文),对笔者和任晓的两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其中,陈文将拙文解读为是建立一种利益导向的国际体系观,笔者觉得误读的成分多了点,可能是因为拙文没有阐述清楚造成了误解。其实,拙文阐述的“共生”与陈文主张的文明导向的世界秩序恰恰是接近的。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一回事。当然,关键是对“文明间关系”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会在后面讨论。
熊文集中讨论东亚是共生还是竞合体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出十个理由来证明东亚是共生型体系,同样,熊李力先生也可以找出十个理由论述东亚不是共生型体系而是竞合型体系或依附型体系。这样的讨论因为没有聚焦将很难深入下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学者站出来说,东亚是西方政治学中的霸权体系,或者是朝贡体系,或者是均势体系。坦率地说,其他的概念都为我们理解亚洲秩序有所帮助,拙文也只是为人们理解世界秩序和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中国本土的概念,且笔者愈来愈坚持认为,中国要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首当其冲的是要用自己本土的概念逐步替换、覆盖、遮蔽掉来自西方的概念。学术争论要么是因为价值问题,要么是因为概念问题,而一旦涉及到概念问题的争论,恰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名学”,所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
笔者以为,当我们形成了一个关于“共生”理论的共有知识背景时,才能够在共生这个理论上逐步形成对话平台,发展它,完善它。作为学术辩论,此文的目的不是去证明陈文和熊文哪里不对,而是要在他们的质疑下努力完善笔者对共生问题的看法。辩论集中在谁是谁非上,一定要争出个你对我错,这本身就是二元对立,不符合“共生”哲学。所以,笔者先对两篇商榷文章中的误解做个解释。
第一,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在共生论中,笔者坚持从中国传统中庸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矛盾和冲突因素一直存在,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来。没有矛盾的世界是和谐世界的最高阶段,和谐世界的初级阶段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换句话说,乌托邦自由主义者幻想世界是个真空之幕,或者有一种方案能将世界彻底变成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这是空想学说,或者浪漫主义学说。生活世界或者国际关系中如果没有矛盾了,那要政治家和我们这些学者做什么呢?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叫科斯,指出世界不存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转换成矛盾论话语来说,其实就是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所以,科斯只是说出了一个常识而已,这个常识谁都明白,并不是多大的理论发明。
第二,共生理论向来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依为伴的,共生论反对二元对立,不主张多元冲突。共生理论中有一个核心概念是“关系”,它与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理性”恰恰形成了对照。在“关系”中,更重视相互依存;在“理性”中,更重视因果改变。因为理性是与个体能力提高结合在一起,并假设个体能力的提高会对他者产生一种动能,从而改变相互间关系状态。在这里,当我们习惯了“理性”这个概念时,就会习惯认为干涉是正当的,因为干涉可以形成新的平衡。但是,当我们习惯“关系”这个概念时,就不太会认为干涉是一个必然正当的做法,因为在一个共生体系中,干涉往往会破坏共生体系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来将不干涉视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在西方理性政治文化中,一直强调将干涉视为一种天定责任。
这就又引出了与“关系”和“理性”相关的另外一个政治学概念,即“权力”。美国政治学有一个对权力的经典定义,就是让别人做其不想做的事,或者不让别人做其想做的事。在这个概念里,“权力”与力量是联系在一起,也即权力一定能够产生施动或者吓阻效应才是“权力”。所以,这种权力其实与因果理性关系很密切,是因果性权力。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但是,对熟悉共生环境的人来说,权力则不能从因果联系上去理解,而应从关系网络去理解。在一个生态共生系统中,讨论老虎重要还是老鼠重要是没有意义的,两者都是生态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但是如果习惯了西方权力概念,一定会认为老虎因為力量大,所以更重要。在一个政治生态系统中,我们要讨论君主重要还是人民重要。按照西方权力理论,君主权力更大,当然更重要。但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中,荀子说“水舟共生”,当代政治中认为党和人民是鱼水关系,相依为命。
因此,在共生理论中,在“关系”之中,一方不因为力量大、能力强,就一定居于支配地位。进一步说,在一个共生体系中,各方都处于互相依靠的关系之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共生体系中,由于相互依靠的关系性,大和小的区别往往失去意义,你不能说大一定就会支配小,也不能说小一定就屈从大。或者说,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大国和小国是相依为命的关系。一旦我们按照这个相互依靠的关系性概念去理解东亚国际体系,就能理解东亚国际体系中大小国家之间关系并不是依附的、朝贡的,而是大小共生、相依为命的关系,小国不因为其力量小就不重要,甚至有时比力量大的国家更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关系在西方因果权力支配的国际体系进来之后,被破坏了。正如孙中山先生曾经准确预测的,日本由于学了西方的战争扩张的术,丢了东亚和平的道,对东亚和平必定是个威胁。
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认为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由于关系性权力而不是因果性权力发挥作用,所以大国和小国能够接受共生状态。当然,熊文指出东亚因为存在一个强大的国家,维持了共生体系,而近代西欧则是竞争关系。拙文也揭示了西欧体系是按照均势原理来组织的,而东亚体系则是依照大一统来运转的,尽管在历史上中国分裂时期有例外。但笔者不认为共生只是可以解释东亚体系的理论,实际上,西欧国际关系中也有共生成分,美国一度出现所谓“仁慈的霸权”理论,其实也是想形成一个共生体系,但是很困难。因为“仁”不是美国和西欧政治文化的基因和主流,就如同“私”不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道理一样。
同样,拙文在阐述公道的时候,并没有将“公”和“私”对立起来。共生哲学最大的智慧不在于对立对抗,而是在对立对称对等中求统一。记住这一点对理解共生理论很重要,二元对立对抗本质是一神教文明的基因,中国和谐文明中一直重视的是二元、多元中求统一。熊文更多是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例如利益、私、个体、竞争等,来分析东亚。用别人的概念体系分析东亚有一定道理,笔者尊重这种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也就是任何一个共同体必然首先建立在“公”之上,才可能形成秩序。所以,公义、公理、公道、公意等等,都是共同体建设必须要考虑的内容。
笔者不太赞同斯密和哈耶克的个体主义之上的秩序,“私”有其积极意义,灭“私”也不是笔者的看法,但是循“私”或者以“私”为主导来建设社会和世界,已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与其带来的进步几乎一样多,而且,“私”的活动必须服从更大的公义。从西方一路而来的政治思想看,在漫长的宗教神学统治期间,欧洲“存天理,灭人欲”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一般将这个阶段称为黑暗的专制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将个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是“私”力量的释放,但即便在这释放期间,主权这一公意也是私不能对抗的,而是要服从的。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问题是,“私”一旦流淌到外界和国际社会以后,应该如何对待他者?西方自己也对他们历史上的扩张、侵略、屠杀、种族灭绝进行反思,但不能求解。当代国际政治中这种扩张表现为对西亚北非等地野蛮的干涉。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国际政治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国际政治思想而不是西方国际政治思想中,尽管后者不乏国际秩序的理想。当然,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如果能够吸收更多“公”的思想,则另当别论。
合解还是分解:关于共生的哲学问题
为了普及“共生”理论,或者我们在讨论“共生”问题时,还需要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基本共有知识背景,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谈谈中西社会科学的分野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理解共生理论或者共生思维的一个重要背景知识和辅助知识。
人类碰到的许多问题,解决之道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从解决思维来看,有两种,一是合解或合析;二是分解或分析。共生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合解的思维,认为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相通的关系。这与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分解的思维恰恰形成对照。我们熟悉的韦伯的社会科学著作,格外关注类型学。将事物解剖成一块一块碎片,再作分析,应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论著很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利在于将细致的地方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其弊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分”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除了常说的文史不分,其实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分,其中孕育的是合解思维。现在我们经常抱怨我国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过多,专业性刊物少。静心下来想一想,其实综合性刊物的优点是可以使读者全面了解自己学科之外的动态,而不是只拘泥于自己学科之内看问题。沃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抱怨专业之分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戕害,以及现在流行的跨学科研究,其实都是要打破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分解、分门、分析的弊端。我们的社会科学如果将自己合解的优秀传统丢掉了,一头扎进西方已经意识到的社会科学分解的弊端之中,岂不是丢了自己的西瓜,撿了别人的芝麻,自己找弯路走?
回到事物的属性来看,在分解分类思维下,当我们将任何一个整体用概念分为不同部分以后,一定会产生类型的不确切地方。概念是“名”,古人说“名可名,非常名”,一个含义是当我们给事物属性一个名以后,这个名一定因为不能概括对象的全部属性,从而与对象存在抵触的地方。比如,当我们说“东亚国际体系是共生型国际体系”时,你一定可以找出它存在不共生性的例证出来;当我们说西方构造的国际体系是“寄生型国际体系”时,也可以找出其国际体系存在互惠的一面。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反思,也就是一旦我们确立一个概念来定义和研究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的研究结论必然存在“非常名”所带来的不精确性。而如果我们再沿着这一不精确的概念作推导,其结论必然存在局部精确与整体不精确的矛盾之中。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非常重视命名,对比起来,中国社会科学不太重视命名,因为命名会损害对研究对象内涵的认识。两者各有利弊,从个人的研究感受来看,笔者更倾向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科学智慧。笔者也曾经试过用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分析问题,但是觉得那不是出路,似乎也找不到出路。西方社会科学现在的一大窘境,就是为“名”所累,各种五花八门的概念层出不穷,中国社会科学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时候,也逐步接受了其好用概念的分解思维,基于这种思维去处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碰到的许多问题,产生的效果不见得很好。
到分无可分的时候,人们会意识到合解的意义。要学会合解的思维,就需要对话。对话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找不同的地方,也不是找完全共同的地方,而是找共通共鸣的地方。现在流行的儿童启蒙书,其中不少是“找不同”游戏。如果一个人习惯找不同了,那么他/她会很难与打交道的人或物形成友善的关系,找不同等于是将自己与人或物区别、区隔开来,极端的时候就是分离孤立起来,因为人与人或物是不同的。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见人三分熟”这样的人,这种人之所以“见人三分熟”,是因为其很快就能与对方找到相似、接近的话题。因此,我们的教育,既要让小孩找不同的地方,也要更多教会他们一些找共通的游戏,这应该有助于他们成年后与人、物、社会、国家甚至其他文明,建立牢固的共同体和团结意识。
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同容易,找共通难。伟大的中国人,古时产生的许多智慧,都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寻找到共通的交集以后,形成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思想和智慧的。古人说,性相近,习相远,前句道出了“通”,其实应该说,习也不远。既然“共”是个核心字,那么就需要在各个事物之间找到能够使它们共同团结在一起的方法。完全相同当然最理想,现实的办法是找共通的普遍联系。因此,作为合解之道,关键在于找“通”;每个个体彼此之间形成共通共鸣的意识,共同体才有可能,它比单单依靠法律维系的共同体要更加牢固、持久和有韧性。
这里笔者只强调一种找共通的办法,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能在同义异名和同名异义之间学会转化转换。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少都会为“名”或概念所累。五花八门的“名”或者概念,正在淹没着社会科学;按照“名”的分类所造成的区隔,妨碍了我们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共通或者普遍的联系。世界上许多现象,虽然不同文明可能对其有不同的命名,但是该现象本来的意义却是一样的;世界上还有很多现象,尽管不同文明对其有相同的命名,但是其含义却可能是不同的。前者如墨子讲的“兼爱”,印度人说的“不害”,老子说的“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西方人说的“上帝要讓其灭亡,必先让其先疯狂”。后者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名同但义不同。此类现象很多,不必列举。总之,对同义异名的现象发现得越多,越有助于我们在被人为概念分割的世界中找到普遍联系和共通的地方,从而树立整体的共生意识,而不是对立对抗的意识。
两种普遍主义与世界秩序
我们最后回到共生和世界秩序话题上,主要谈两种普遍主义及其对文明共生与世界秩序的意义。
在同义异名或同名异义中寻找共通,简单地说,从事物的普遍联系角度看世界,代表着另外一种普遍主义。我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读到的普遍主义,主要是一种建立在地方经验基础上的法则,这个法则被认为是适合所有地区所有文明的法则,而将其上升到外交政策上,可怕的结果就是以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知识,去讨伐、改造其他不符合这个国家和这个文明标准的地区,从而引起野蛮的干涉,而干涉是侵犯他者自由的。因此,西方人讲的普遍主义,主要是指适用于一个地方的原理,也可以推己及人,适用于所有其他地方。这一点,基辛格是少有的认识比较清楚的人。他说,西方的政治思想一开始其实只是从很小的一个地方生长出来的,西方强大后要将这些思想推广到其他地区,必定会引起干涉问题。中国政治哲学讲普遍主义的时候,更主要是从普遍联系和共通的角度,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政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性和共通性。这代表着另外一种普遍主义。
假如我们按照这两种不同的普遍主义政治思想来看世界政治和国际秩序,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现在世界的问题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为什么文明之间会出现不共生,或者出现有的学者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命题?或者,为什么当美国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个命题时,在中国却遭到不认可?
在从孤立走向交流的过程中,人类文明之所以没有能够向更高阶段迈进,形成一个更大的文明共同体或者秩序,很重要的原因是一种强势文明总是试图将别的文明变得同自己一样,以一种文明来代替另外一种文明,或者以一种文明改造另外一种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以“一”改造“多”。这种思维是本文所说的第一种普遍主义思维,也即信奉适应于一个地方的文明法则同样应该适应于其他地方。这种政治思维会促使产生这种普遍主义土壤的地区,无论是崛起还是衰落的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在崛起的时候它会改造别人,在衰落的时候会担心被别人改造,这就是文明冲突的宿命。因此,按照这种普遍主义逻辑,并不能够解决文明间共生问题。如果我们换一个逻辑,也即第二种普遍主义逻辑,更多地是从异中求通,那么对话、欣赏、互鉴、依靠、共生等就会成为文明交流的主旋律。按照“通”的逻辑,文明交往才可以逐步到达一个化的境界,从而在多元中形成新的文明结晶。第一种逻辑只能使文明走向绝境,人类文明要向更高阶段迈进,形成全新的文明共同体和秩序,需要更多地从第二种普遍主义出发,来思考文明的当下困境和前景。
最后,“共”这个词,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关键词,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关键字,是国际关系和平的关键字。总体上看,我国传统和当代政治文化、政治思想中,关键词之一也是“共”,在对外交往中,这个词衍生出像共享、共赢、共处、共生、共荣、共和这些词。国与国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彼此能够找到更多共通共鸣的地方,天下则可百虑而一致,殊途同归。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