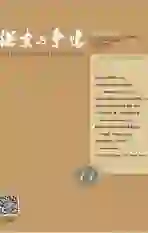平庸守成埋下亡国伏笔
2014-10-21叶书宗
叶书宗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俄国整体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短暂时段,应当把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历史,放在苏联历史、俄国历史,乃至世界整体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考察和定位。基于这样的基本思考和认识,《苏联史》第八卷《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以下简称《十八年》)围绕两条平行线展开:
第一条平行线是:在尽最大可能客观地展示勃列日涅夫當政时期苏联历史真实面貌的基础上,着意阐述勃列日涅夫何以能平稳当政18年。
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通过宫廷政变式的密谋上台。在苏联74年历史、八任领袖中,相对而言,他被公认为是不爱学习、懒于思考、基本上不动笔、缺乏领袖魅力、喜欢过平静生活的平庸之辈。历史事实表明,这也确是他的真实写照。尤其是从1974年起,由于几度中风,他几乎丧失了正常工作的健康条件。但是,他不仅平稳地当政18年,而且还能把苏联推上鼎盛,圆了俄国称雄世界之梦。
第一,勃列日涅夫根据自身的条件,以及权力交接的这种方式,在斯大林模式体制内构建新的权力中心时,特别谨慎地解决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以及杜绝发生自己当政方式重演的可能等两方面问题。他既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搞“大清洗”的资本,也不具备借助历史惯性运动,搞清除“反党集团”的条件。他采取常态化的方式,逐步地、平静地一一解决,使政坛水波不兴。对坚定拥护赫鲁晓夫的,如伊利切夫等一些领导人,他的做法是逐个“调整”。对于威胁到新的权力中心地位的谢列平等人,则是分几步:先提升稳住,或者提职务、降实权;继之刨去他们的根基,使他们完全孤立;再逐步降职,层层削权;最后将异己逐出苏联政坛。
第二,勃列日涅夫能审时度势,直面现实,调整权力结构,力求使权力结构保持均衡化,借以保持自己作为权力中心的稳定地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结束了创建苏维埃国家的老近卫军当政年代,开始了新的、后革命精英掌权年代。在老近卫军年代,苏联领导群体基本上是根据各人在革命过程中的资历,所表现出的能力和特长来组合、构建的。后革命精英年代,在架构新的权力结构群体时,他着眼于保持权力结构群体的均衡化。
在当政前期,勃列日涅夫能以比较客观的态度看待自己,对待别人。他有时也表现出浓浓的人情味,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以至于有了“勃列日涅夫式的吻”之说。他对人也常会表现出温和、关怀的一面。在苏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中,他安排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放手让葛罗米柯主持外交工作,任命安德罗波夫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后革命精英当政年代,可谓知人善任。在他的干部网络中,还有一个以与他有特殊关系的亲信们所组成的、无形的圈子,被称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但是,他构建的这个无形圈,又是有分寸的,在一些关键岗位安插这些人,也是适度的。
对于一些突发性事件,包括针对他的暗杀活动,勃列日涅夫基本能依据相关法规,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不搞政治运动。他也相对尊重党章关于党内生活的有关规定,大小事情的决策体现出“集体领导”原则。赫鲁晓夫以激烈的言词批判斯大林的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在形式上都做了改正。他的这些做法,不仅适合维护、巩固斯大林模式的新需要,而且为他个人当政也赢得了一定的信任度。
第三,勃列日涅夫接受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收获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提升苏联的综合国力,构筑支撑他平稳地当政18年的经济基础。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虽然在改革缘由和改革诉求等方面,与柯西金就有分歧,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接受由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相对出色地完成了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进一步壮大了苏联的经济基础。由于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接近斯大林模式的底线,它所遇到的阻力超出了柯西金的意料。本来就对新经济体制改革有所保留的勃列日涅夫,受到“布拉格之春”的刺激,立马从有限度的支持,转向完全反对。新经济体制改革停止之后,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经济,日显颓势。不过,勃列日涅夫抓住了国际市场上石油提价之机,扩大石油以及石油产品的出口量,积累财富,终能支撑住停滞不前的苏联经济。
第四,勃列日涅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凭借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坚决实施提升农村社会生活质量的“三化工程”,提高各民族共和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并且着力打造苏联的世界霸国地位,为他平稳当政18年构筑国内民心基础。
苏联自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后,农民受到国家无孔不入的控制,到上世纪50~60年代,与西欧社会的一般农村相比,苏联农村社会生活质量极为低下。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虽然原封不动地坚守斯大林创立的农村社会和农业生产体制,但是凭借国家已有的雄厚经济实力,不仅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更有时代性意义的是以有力的行政措施、巨大的财政投入,基本上实现了全国农村的电气化、燃气化,以及硬路面道路网络化,使农村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上升到新台阶,整体上改变了俄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上世纪70年代末,占全国总人口近40%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几乎接近城市水平,城乡社会呈现相对和谐的局面。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勃列日涅夫也有所收获。苏联是一个拥有150多个民族的特大型多民族国家。斯大林对待尖锐的民族矛盾,基本上就是使用暴力镇压。这使得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社会,民族关系就像被绷得紧紧的弦。赫鲁晓夫当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由于种种缘故,效果并不好,有的甚至事与愿违。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凭借国家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以有力的行政措施,在基础设施、基本建设等方面,向各民族共和国、特别是边远共和国倾斜,提升各民族共和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全苏联境内各民族共和国之间的差距,同时提倡、鼓励民族同化。
勃列日涅夫凭借较为雄厚的综合国力和先进的军工技术,以发展核武器和建造海军远洋打击力量为重点,打造世界级霸国地位,终于成就了苏联的霸业,满足了俄罗斯人几个世纪以来的企盼。
由于采取了上述做法,勃列日涅夫为自己坚守斯大林模式,平稳地当政18年,构筑起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因此,勃列日涅夫的“平庸”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以比较务实的态度,固守斯大林模式,为自己创造新的执政资源。作为斯大林模式的守业型领袖,他确实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既实现了斯大林的遗愿,也让斯大林模式释放完它的全部历史潜能。
另一条平行线是:《十八年》在展示勃列日涅夫当政期内“稳定”的基础上,着重厘清、阐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内在的、深层的、渐进式的变化。
《十八年》以历史事实阐明,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稳定”,是相对于列宁时期的革命与创业、斯大林时期的激荡、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以及后来的剧变而言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稳定”并不是铁定。实际上,这段时期苏共和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在不停地变化,只是这些变化是深层的、内在的、细微的、渐进式的,有时甚至是不被人注意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有机的过程:原因是结果的原因,结果往往又成为原因的结果,环环相扣。勃列日涅夫死后不到十年,苏联就发生剧变了。“剧变”不是无源之水,“剧变”是“渐变”的积累。《十八年》首先以历史事实阐述苏共自身的嬗变。
苏共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也是一党专政、党政一体的苏联国家的执政党。苏联社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展方向,都由党决定。苏共是苏联社会和国家的决定因素。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里,苏共在慢慢地、无声无息地蜕变,即从最初代表俄国工人和被压迫阶级利益的革命党,蜕变成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代表。
“特权阶层”,按俄文原意,应当译做“在册权贵”较为贴切。出于习惯上的使用,勉强被称作“特权阶层”。
关于“特权”这一概念,并无明确的、统一的界定。《十八年》认为:所谓苏联社会的“特权”是指社会中一部分人,拥有超出苏联宪法以及其他一些专门法以外的特殊权利,是凭借超经济的行政权力所获得的特殊权利。特权阶层凭借行政权力,不仅在日常生活消费品短缺性危机常态化的苏联社会,始终过着相对的贵族式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享有规定的,以及虽然并无明文规定,但是习惯上形成的各种特殊权利。
苏联社会中一部分人拥有特权的现象,作为一种非常现象,产生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当时,产生这种现象确有某种历史合理性。可是,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这种非常现象逐渐被常态化、制度化了。尽管没有上升到体制层面,但赫鲁晓夫确是朦胧地意识到特权的存在对苏共和苏联国家存在潜在危险。赫鲁晓夫多少还是采取过一些限制特权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并无实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反对特权而得罪了社会上的特权群体。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以“稳定”为口号,批判、取消了赫鲁晓夫一些隔靴搔痒的限制特权措施。勃列日涅夫当政以后,打着“马克思主义”“稳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等不容置疑的旗号,堂而皇之地鼓励、维护特权。经过这番努力,在他当政时期,社会上一部分拥有特权的群体,终于演变成苏联社会稳固的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形成的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在于:它不是由苏联共产党或苏联政府内的某些人来反映他们的利益和声音,它本身就是党政一体的苏联共产党自身的各级官员。之所以由最初的少数拥有特权的人群,演变成特权阶层,乃是苏共始终实行以党代政、党政一体的结果。可以说,特权阶层是苏共所建立的体制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是苏共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特殊地位的体现。而特权阶层也只能依附于苏共体制而存在。自然,特权阶层就成为苏共所实行的体制的、理所当然的坚定维护者。如此一来,任何触动这一体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会危及特权阶层的权利,都会遭到特权阶层的抵制和反对。勃列日涅夫宣布苏共是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利益的“全民党”,虽然从逻辑上说是合理的,却是苏共为自己以党代政、党政一体寻找合法性的自封。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共已无可挽回地滑向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代表,演变成深受俄国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社会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
特权阶层的形成和苏共的蜕变,使得苏联社会蔓延着一种对于苏共来说既可悲、又可怕的现象,即苏联一般公民,尤其是青年一代,提到苏共,几乎都是冷眼相向。
其次,《十八年》以历史事实展示苏联社会人本主义意识的不可抑止的强化,以致汇聚成以要求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主流的新政治觉醒运动。苏共虽然以暴力镇压了这场运动,但是人本主義意识已在全社会扩散,既深化了全社会的信仰危机,又强化了人的法律自主意识。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解放,是人本主义的完美和最高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批判过19世纪人本主义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是人本主义的替代学说。发轫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是现代法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立足点。18世纪以来,俄国的先进人士曾为宣传人本主义做出重大努力,产生了一批人本主义的杰出思想家。由于沙皇专制政府的镇压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因素,俄国终未能发育成适合俄国国情的俄国人本主义。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人本主义实际上是否定的。斯大林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是以国家主义取代人本主义,本就先天不足的俄国人本主义意识,也成为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革命和专政的对象。斯大林对具有人本主义意识的人,即使是老布尔什维克、苏共党内高层领导人,也必从精神到肉体,予以残酷迫害和杀戮。即便如此,在苏联的整个历史时期内,人本主义意识始终存在,并不时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在有关苏联问题的西方研究著作中,经常看到“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表述。按照俄文原意,这两个词应当译做“持异议者”和“持异议者运动”。《十八年》并未将这个词译作“人本主义”,只是认为在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人的法律地位主体化,已成为支撑现代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持异议者”以及“持异议者运动”,从根本上说,都是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对斯大林模式、对俄国历史选择更为理性的思考。在他当政时期,苏联各界对苏共执政方面的诘难,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批评,从思想观念上说,都是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呼声和表现。因此,《十八年》将“持异议者”或“持异议者运动”,都归为苏联社会人本主义的某种声张。
相关苏联历史研究著作,将萨哈罗夫、罗伊·梅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等三人,分别看作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西方派”“民主社会主义派”“俄罗斯派”的代表。《十八年》认为,他们三人各有不同的出身、经历、社会地位和专业研究领域。萨哈罗夫是核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曾经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他是通过研究自然科学而成为人本主义者,因而比较直线式地呼喊天赋人权。梅德维杰夫是历史学家,属于苏联社会的中等知识分子层。他的家庭出身、经历和学术追求,促使他从学术良心出发去探究“革命为什么要吞噬自己的孩子”。因此,梅德维杰夫是理性地反思斯大林模式,从揭示斯大林模式的历史真实,转向强烈要求建立法治社会。索尔仁尼琴由于他那坎坷的人生,把苏联社会的种种苦难概括为人性的扭曲和泯灭,从而致力于呼唤被扭曲、被扼杀的人性,发出列·托尔斯泰式的呼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萨哈罗夫、梅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尽管所表现出的人本主义意识各有侧重,但是他们一致把“天赋人权”“法治”“人性”,谱写成苏联社会人本主义的主题歌。
面对人本主义思潮的涌动,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不是以发展的眼光去主动疏导,将之作为改革斯大林模式、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契机,反而把人本主义看作是和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当作颠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思想核弹”。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把宣扬人本主义的人和活动,定性为“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刑事犯罪,制定新的刑法条文,动员一切司法手段,镇压人本主义思潮。勃列日涅夫的认识和做法,虽然维持了他自己当政时期的稳定,但是却给苏联社会连续不断地积存爆炸物。
《十八年》表现了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积郁与抬头。勃列日涅夫以行政手段,强行扶持各民族共和国,首先招致苏联主体民族俄罗斯族的普遍不满,导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愈来愈强烈的、不愿做“奶牛”的抱怨;二是由于倡導俄罗斯化,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倾斜”政策,不仅是各少数民族普遍不领情,反而增加了新的怨恨;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养了新一代民族精英,致使民族分离主义抬头。可悲的是他不仅察觉不到这些,反而沾沾自喜,大吹特吹“新的历史共同体”。
勃列日涅夫上台的时候,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变动时期,历史也为他提供了触手可及的发展机遇。而且勃列日涅夫也无需承担推行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责任,可以选择阻力较小的道路,采取可行的步骤,除旧布新。可是,勃列日涅夫却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胸无大志、鼠目寸光、贪图安逸,是个不堪大任的庸才。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稳定”,最终葬送了苏联。
实习编辑高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