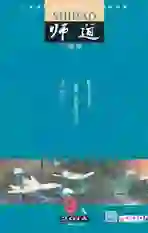不留恋与不必追:生命通达的一种方式
2014-10-10陈彦米
陈彦米
这是一篇纪念文章,王开岭把它编在心灵美学卷里。而我,在这年节打开了它。
本来,王开岭与史铁生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史铁生的一篇文章《我与地坛》,王开岭体验到了他的心境,对他怀有了敬意与亲切,因此,即使是在大过年的,“我”(王开岭)还是会为他的过世感到“空荡,陌生”——毕竟也与他“相识”甚久了,在地坛里。
地坛有着历史的味道,它是历史的沉淀物,也是王开岭探索史铁生的一个方式。在一番修整之后,地坛原来保存、收纳的全不复存在了,它虽整洁、端庄了许多,但已失却了早时那灵性的启示,可考究的价值,因此作者王开岭才感慨道:“其实我不该来”,“它变肤浅了”。
史铁生因写了《我与地坛》而得名,他在地坛中饱受“生死”思想斗争的折磨,以至于他的母亲都不敢去打扰他,又怕他想不开,于是尾随他去地坛,随时观察他的一举一动。那是一种心病,孤独、漫长、坚忍却又安静,它似生命中的一个考验,只有精神乐观、内心通达,才能通过考验,最后存活在世上。这某种程度上像极了犹太人,他们一把孩子生下来就将他们扔进水里,让他们懂得自生自灭的道理,只有在非凡的环境里存活下来的人才能行走在世界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的原因吧,他们洞悉了宇宙与人类之间的一种默会关系,从而学会正确地生存。
史铁生在 “生死折磨”中默默多年后,终于想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我与地坛》里,他这样写道。这种豁达的人生观,让史铁生生前多次向人重申,自己在失去救治意义时赶快放弃,死后只要有用的器官能救别人就全部捐献,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他在这样想通后的十几年,生活得跟正常人一样,甚至对生命的认识更加通达,超越。2012年的新年,史铁生平静离开人世。
这个新年,是通达的史铁生归向透明的另一个世界中去解脱的时候了,那么,就让他好好上路吧!
生命的长短是人不可控制的,正如我的生病的父亲,谁也不知道他将在哪一年中的哪一天病逝,只有到了他走的时候,人们才会去意识到他的挣扎与痛苦,才会去细细回顾他生命中一点一滴的美丽的成分,并去留住他的美好,给自己一个纪念。他,我的父亲,曾在世上给予我安好的生活,他势必也走过一个漫长的心灵路程,一如史铁生。王开岭的这篇纪念文章写于2012年,而我,也恰是在这年看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去探索了他心中的生与死。或许命运就是如此巧合,那书,是父亲推荐我看的,这难道预示着我也将面临这一切的对于生与死的拷问吗?
王开岭为什么要把这文章编入心灵美学卷?他从史铁生那里读懂了什么?又想向我们的心灵传达什么?掩卷,我默默地想。
如今,父亲过世已过百日,我也渐渐明白了,正如电影《可爱的骨头》中说的,一个亲人的离世还将带来更多婴儿的出生,所以,借来龙应台对待孩子的一句话:对待逝去的亲人,我们“不必追”;活着的人,好好地活着,即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我的父亲,史铁生,在你们要走向天蓝色的彼岸之前,你们一定回来看过,看过我,看过自己最亲的人,以及整个你们曾经恋恋不舍的世界,但是生命必然如此,向死而生是生命体必然的命运,也是此生安好、珍惜存在的密码——这便是我们所称的各安天命。父亲,史铁生,祝愿你们安心地走在自己的路上,不必留恋旧有的前尘往事;我们,也不必去追回那业已逝去的旧影,将来,我们都要相安在各自的世界里。父亲,安息,史铁生,安息。
(作者单位: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八(3)班)
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