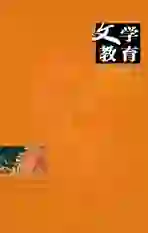纪录片《沙与海》的叙事手法与视听语言分析
2014-09-30刘姝媚
刘姝媚
内容摘要:作为我国早期的纪录片作品之一,《沙与海》在叙事手法的运用和叙事主题的选择上在当时的纪录片领域里可谓独秀一枝。该片巧妙地运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在两个相隔千里、素不相识的普通家庭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展现出这两户家庭在生活状态上的遥相呼应和相似性。在此基础上,纪录片中富有感染力的镜头语言和引人深思的解说词进一步地将这种偶然的相似性升华为普遍的相似性,将关注视角由两户家庭的生活规律升华到人类生活的普遍规律上,体现出创作者对平凡生活的细致观察、深入思考以及人文关怀。
关键词:《沙与海》 平行蒙太奇 主题升华 人文关怀
《沙与海》开拍于1989年,由康建宁和高国栋两人联手创作。影片荣获1992年“星光杯”特别奖和第28届“亚广联电视奖大奖”,是中国首部在亚广联上获此殊荣的作品。
该片记录的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沙漠边缘的牧民刘泽远和位于辽东半岛一座孤岛井洼岛上的渔民刘丕成两家人的生活状态。刘泽远一家靠在沙化的土地上种植粮食、牧养羊群、用骆驼驮运货物维系生计,年收入低时不足五千元;刘丕成一家承包家门前的一片海域养殖海产,据说已有三四十万的年收入并在城里买了房子,生活相对富足。虽然两个家庭素不相识,其生活环境也不同,但他们有着极为相似的生活状态: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都忍受着孤独;他们的生活牢牢地被大自然所左右,时刻面临着被摧残的威胁;同时他们都顽强地在艰苦的环境中建立家业。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残忍的生存规律:人生在世,在哪儿活着都是件不容易的事。
一.主题探讨
整部纪录片记录的刘泽远、刘丕成两家人的生活情况,但影片中很多生活场景、影片所反映的生活规律和人类品性引发了笔者良多感触与共鸣。该纪录片是采用由点到面、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反映成千上万普通百姓生活状态中的共同特性。在笔者看来,纪录片反映的主题有以下两方面:
(一) 对生活的深思:人生在世,在哪儿活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管是沙漠中的刘泽远一家、孤岛上的刘丕成一家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家庭在生活中都会面临很多矛盾和困难;不管我们生活在哪里,不管我们家境富裕与否,生活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张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棋局,只有足够地勇敢坚韧,并懂得包容谦让,我们才能“见招拆招”,用心地把这一盘棋下好。人生在世,在哪儿活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沙与海》反映了以下三方面我们在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矛盾:
1.人与自然的矛盾:不论在哪生活,我们都无法挣脱自然环境所固有的某些束缚,。我们应该怀着包容谦让的心态去顺应自然,与其和谐共处,并在此基础上以求新的拼搏与发展。
2.两代人不同思想观念的矛盾:父母希望孩子留在身边,继承家业;而孩子往往不甘孤独,向往外面的世界。他们与孩子间的这一观念冲突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位家长与子女间的矛盾冲突呢?年轻人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走出原有的小圈子,去更广的世界里尝试新的生活;而老一代人出于牵挂等诸多原因,往往想把孩子留在身边,舍不得让孩子走太远。
3.向往新世界与眷恋家人故土之间的矛盾:这在纪录片中主要表现在刘泽远的大女儿身上,导演在片中对她的面部表情用了长达一分多钟的特写,来变现她内心的纠结与伤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恋乡情结,都会在“闯四方”与恋乡情节上纠结不安,不管最终我们是选择远行还是选择守护故土,我们内心的这么一对矛盾都会一直存在。
(二)对人性美的讴歌:谦逊忍让,坚韧顽强
纪录片还赞美了在自然不可抗的残酷与毁灭力量面前,人类所具有的忍让和谦逊,以及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坚韧不拔之美。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刘泽远和刘丕成选择平静的加以对待,并在顺应的基础上顽强拼搏,建立家业以求发展。他们在逆境面前所表现出的极大的包容与坚韧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折服。他们用谦逊忍让和坚韧顽强谱写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命华章,而事实上,我们也用这些优秀品质在生命中谱写着属于我们的诗篇。
二.视听语言分析
作为一种视觉艺术,纪录片的价值和感染力是由其视听语言来传达。《沙与海》片长虽然不足三十分钟,但其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十分出彩,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运用平行蒙太奇实现巧妙衔接与相辅相成
导演巧妙地在刘泽远、刘丕成两家人相似的生活场景中运用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将两种相隔千里的生活交织连接,共同展现出人与自然、父辈与子辈的矛盾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谦和与顽强。是平行蒙太奇的运用使得两个家庭在生活状态上遥相呼应、相辅相成,两个生活场景彼此相互印证、相互解释,有助于强化受众对纪录片所要表达的主题的的感受和认同。
(二)场景切换时景别的运用
《沙与海》的拍摄人员在切换场景时镜头运用上可谓匠心独运。纪录片在由一家人的生活场景切换到另一家人的生活场景时,多采用前进式叙事。比如纪录片开头在介绍刘泽远一家时先在刘泽远家房子的外边用远景展现周围荒芜的沙漠和刘泽远家低矮的砖房,继而以刘泽远家的鸡鸣声为引子,慢慢将画面转移到房屋内,用中近景、特写表现人物及其间的关系。这些镜头语言的作用在于:对于观众而言,在了解了人物所处环境后再倾听人物故事,能够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当事人的境遇,引发更强的感触与共鸣。同时,对人物所处环境和事件发生环境的交代,也增强了纪录片的真实感和生活感。
(三)经典的特写突出细节、表现人物的表情和复杂的心理活动
特写用来表现细节,突出表现人物或事物某方面的特征。《沙与海》中有多处特写镜头堪称经典。比如在前文提及的对刘泽远大女儿面部表情长达一分钟的特写运用。
此外,片中还有两处特写在笔者看来堪称经典:一,在沙漠的大风过后,镜头对骆驼残骸的逐一特写和紧接着对刘泽远一家面部的沧桑和茫然的特写,极富震撼力地表现出沙漠的对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的残酷与无情。二,对打枣刘泽远面部、拾枣的动作的特写,从这些特写中,我们能体会到镜头语言的灵魂所在。刘泽远满是皱纹的面部给人以饱经风霜的印象,沙子从他粗大的手指间漏过刻画出他对于沙漠中长出的果实的爱惜,也表现出这位沙漠中的牧民如同沙枣树般坚强不屈的品性。
(四)现场声和音乐的恰当使用
对于现场声和音乐音响,《沙与海》进行了恰当的处理,以实现物尽其用,各显神通。该片注重用现场声反映生活,的呼啸声、海浪的咆哮声、人们在各种场所生活工作时的谈话声等。大漠上狂啸的风声给我们一种荒凉感,咆哮的海浪让人毛骨悚然,渔民们的口号声、炒菜声、吃饭的笑声等则表现出人们为在这片土地上坚强地活下来所作的努力。刘泽远在沙漠中挖地时粗厚的喘息声和锄头从沙地中拔出来时刺耳的吱呀声让人深刻体验到在沙漠中耕作的不易与艰辛,对在这样的环境下顽强生存下来的牧民们谁能不致以敬意?
据资料显示,《沙与海》整部片子的背景音乐只运用了一支曲子,通过控制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同一段音乐能产生的不同听觉效果。如在表现刘泽远大女儿面临向往沙漠外新生活和不舍离开家人故土的矛盾心理时,创作人员用较小音量的高潮部分,配合女孩儿脸部悲伤的神情,传达出一种悲凉的感染力。而在展现刘泽远拾枣这一画面时,创作人员用的是大音量的高潮部分,配合散落满地的鲜红的沙枣,表现出刘泽远收获的喜悦心情,同时也演奏了一曲对同沙枣树一般坚韧顽强的劳动人民的赞歌。
(五)画面纪实与访谈相结合
整部纪录片以画面纪实为主,在必要的时候拍摄人员会主观介入,向被拍摄者提问以引导其讲述画面所无法表现的细节。如为了解沙漠中年轻人的心理状况和对沙漠以外的世界的向往度,拍摄人员以交谈和提问的方式采访刘泽远的二儿子,揭示出客观的纯画面纪实所无法表现的信息:沙漠中的年轻人无法忍受沙漠生活的封闭和孤独,他们迫切地渴望走出沙漠,去尝试新的生活,进行新的冒险。如果仅是拍摄记录刘泽远他们在沙漠中的生活状况,则很难向观众表达出这些信息。
三.思考
除了上述优点和精彩之处外,笔者认为《沙与海》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介入式访谈和主观色彩较强的解说可能有损纪录片的客观性。之前讨论了运用介入式访谈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提问者在提问过程中往往根据自己的思路和意图来引导受访者回答,所以,这种扮演“空中飞舞的苍蝇”而非“墙壁上的苍蝇”的作法很可能有损纪录片的客观性和写实性。
纪录片中,沙漠里的刘泽远与孤岛上的刘丕成在生活状态上遥相呼应,但仔细想想,我们中的每个人不都是纪录片中刘泽远或者刘丕成吗?
我们同样被各种束缚所捆绑,同样试图在妥协和适应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与构建。我们畏惧命运和变数,但每次我们都鼓足勇气,试图与命运谈判以求和谐相处。
我们经常身陷困境、遭受挫折,但迈过那道坎后,我们依旧笑的很灿烂,甚至若干年后我们会忘了当初我们经历过怎样的挫折与难堪。
我们都向往外面的世界,像小猴摘西瓜,总觉得下一站会有更多精彩,而往往忽视了身边的美好。我们都有爱我们的父母和家人,他们希望我们过得更好,同时但又舍不得放开手中的那根线。
正如曲婉婷所唱,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哪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