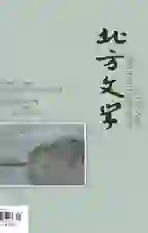苍凉背后的火光——迟子建散文中的隐喻意象赏析
2016-11-10李思颖
李思颖
摘要: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中最具影响力的散文家之一,迟子建的作品以清新丰润的文风笔触,细腻温婉的情感述求准确还原了生活中的自然和本真。在其作品唯美的艺术形式背后,是真挚醇厚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显,也是哀愁博大的艺术气质的流淌。而这一切主要是通过其散文作品中丰富的隐喻意象得以抒发和彰扬。在她的散文作品中,有两类隐喻意象最为突出,一是生命体喻象,二是气象喻象。通过对她作品的分析可见,生命体隐喻主要体现了人文关怀与伤怀之美,而气象隐喻主要体现了天人合一观和人性温暖。
关键词:生命体隐喻;人文关怀;伤怀之美;气象隐喻;人性温暖
迟子建是中国当代文坛中的一朵奇葩,以女性作家特有的丰润笔触和细腻情感表达对世界的看法,用朴素而高贵的作品勾勒出一个属于她, 也属于读者的纯美清新的精神世界。她是国内唯一一位获得三届“鲁迅文学奖”,两届“冰心文学奖”,以及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还获得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迟子建的作品引人注目,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坛。这一不争事实不仅代表着其个人作品的成熟,也是女性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成熟。《迟子建散文精品赏析》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评介,“在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报告文学、戏剧等文学诸多样式中,女性在散文创作上似乎有着天生的亲和力。相对于男性,女人更富于感性”[1]。女性作家流露的敏感天性和独有的审美追求,的确是迟子建散文作品的一大亮点,但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其最主要的部分。迟子建在接受《文化访谈录》栏目专访时曾谈到,她认为朴素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人性的本善,当如温泉一直贯穿作品的始终,即使现实中的苦难会“让作品长一点皱纹”,但忧伤的背后不是绝望,而是温暖与本真[2]。
苏童对迟子建的作品做过这样的评价,“迟子建的小说构想几乎不依赖于故事,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个人的内心感受折叠而来,一只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心中,因此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3]”。相比给她带来盛誉的小说,迟子建的散文毫不逊色,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洋溢着率真自由之风。另一位女性作家顾艳写道:“她的散文透着大自然与人物和谐之美的气息,气息中那些个忧郁的灵魂,宛如唱着一首首凄伤优美的歌。迟子建有很好的艺术感觉。诗思中的宁静,仿佛让我们看到一幅北国雪天的风情画。冷色调中,有着融融的暖意”[4]。可见,在其作品唯美的艺术形式背后,是真挚醇厚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显,也是哀愁博大的艺术气质的流淌。这一切主要是通过其散文作品中丰富的隐喻意象得以抒发和彰扬。
一、生命体隐喻体现的人文关怀与伤怀之美
迟子建的语言独具伤怀美感,饱含深切的人文关怀,用忧伤而不绝望的笔触准确还原了自然与本真。其作品中选择关注的对象多为细小的昆虫和鸟类,以及与人类共处的家畜,如鸡鸭、猫狗等。比如《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雾月牛栏》中因为初次见到阳光、怕自己的蹄子把阳光踩碎了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以及《北极村童话》里的那条名叫“傻子”的狗。通过人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之间的生命体互喻, 她把人们生活中自觉不自觉的感悟实现为感性的文字。
这些生命体隐喻的喻象可以细分为三类。首先是以人的精神和情感喻指低等的动植物属性。比如《鹤之舞》中的丹顶鹤,其寿命大抵与人类相等,在作者笔下,它与我们一样能感受世间的荣辱和兴衰,也因此成了“最具沧桑感”的鸟。一只鹤去了,另一只绝不再寻觅伴侣,这就体现出它们“对爱情格外忠贞”。它们甚至比人类还要来得高明,“它们才是大平原的主人,而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5](21-22)。《动物们》中的家狗黑子,长得丑,而且走路一瘸一拐,所以在作者笔下,它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残疾”,但它的心并不丑,总用一条腿帮回家的鸡顶住小门,颇有“绅士风度的样子”。黑子死后,作者慨叹它就像“旧时代的小媳妇,即使遭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会忍辱负重地陪伴主人过下去” [5](81-83)。
与之相对,迟子建散文中也出现了大量以低等动植物的生物属性喻指人类行为的意象。最典型的是散文《废墟上的雄鹰和蝴蝶》, 从标题上看即蕴含高度凝炼的比喻,通篇饱含生动鲜明的喻象。“废墟”具有双重涵义,既喻指墨西哥旧文化,也映射女画家卡洛伤残的身体,为整个文章奠定绚丽而苍凉的基调和背景。“雄鹰”喻指里维拉,这位诗人又高又胖,和他娇小玲珑的妻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被人形容为“大象和鸽子的结合”。为了复兴墨西哥文化,他“像雄鹰一样在旧文化的废墟上翱翔,以强健的翅膀,搏击出一片幽深广阔的艺术蓝天”;而卡洛如“轻灵的鸽子”,又如“凄美的蝴蝶”,用画笔把自己残损身体的废墟“血淋淋的解剖开来,坦然而醒目地呈现给世人” [5](51-52)。
除此之外,作品中也不乏低等动植物之间的互喻,通过对它们之间共同的生物属性和共通蕴含的剖析,营造出新奇独特的修辞效果,也提供给读者全新的认知体验和视角。在《年画与蟋蟀》一文中,蛐蛐儿待在阴湿的水缸旁边,入夜后的响亮鸣叫,是“像夜莺一样亮开歌喉” [5](98)。《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受到香气的吸引,一次一次试图爬上佛龛,可总是循环往复地失败。最惨的一次它从两尺来高摔了下来,它在地板上打滚,触角乱抖着,“像被狂风吹拂的野草”。
迟子建散文中生命体隐喻的大量使用,不仅是为了客观描摹自然界万物的形态,更有对自身情感和主观世界的剖析。如她本人所说,童年中围绕着的,除了亲人,最多的就是动物和植物。迟子建自认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而来的。比如从衰亡的动物植物身上,看到生命的脆弱,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从这些人和事物身上,作家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这几乎决定了她成年以后的世界观。哲人曰人类无一例外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万事万物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类也不例外。迟子建通过对各种生命存在体的互喻诠释了这一新的世界观,这种强烈的物我一体、物我合一的价值诉求,鲜明的万物有感、万物有灵的生命论,使她的散文作品充满了对人世间生死情爱的关照,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漫溢着对自然界的崇尚敬畏和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寻和肯定。
二、气象隐喻体现的天人合一观和人性温暖
迟子建的文字并不总是徘徊在记忆的后花园中,对于现实她也给予一样热情的关注。她的诸多散文游记,不仅使人领略到了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而且往往从简单的现象透析出人生的哲思。她“以文学的方式将个人的经验融化到大千世界之中,超越了冰冷的道德判断,让我们在光明和温暖中获得了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和认识” [6]。
除了各种生命存在体,在迟子建散文中出现最多的是自然气象。文如其人,文风大气沉着的迟子建有着北方人爽朗率真的个性,她每年都有几个月要回到漠河北极村,沉浸在故乡的山林雪原中,远离都市喧嚣。她的作品中记载了故乡种种奇异的风景,譬如劈天盖地的大雪、轰轰烈烈的晚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了花朵的土豆地、秋日雨后繁星一样多的蘑菇、在雪地上飞驰的雪橇、千年不遇的日全食等等。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以及雨雪风霜,都是作家笔下最钟情的描摹对象,使她的写作洋溢着丰沛的活力和激情。
最频繁进入作家关注视野的是故乡的风雪。这雪不是常人眼中的寒冷、僵硬和冰冻的代名词,而是北方黑土地的魂魄。在《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一文中,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描写霜雪:季节已是春天,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哪怕白天走了,逢到寒夜又回来,直到四月底才“彻底丢了魂儿”[5](1-2)。在《上个世纪的飞雪和溪流》中,作者感叹大兴安岭的雪是一年比一年小,风是一年比一年大,通过两个老者的交谈回忆起上个世纪雪是多么的频繁,多么的“恋人间”,常常是“闷着头下了一夜”。在她看来,冬天要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样子,风霜雨雪交替而来,那才叫好日子,所以在作家的心里渴望政府能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备受摧残的林地,幻想在新世纪的曙光中,飞雪能“带着重回人间的喜悦,妖娆地起舞和歌唱” [5](130-132)。无独有偶,在《风雨总是那么地灿烂》中作者描述了与母亲的回乡旅游,在途中她体会到“其实风雨也是上苍赐予我们的甘霖,它可以升华苦难、化解悲伤,教人以慈悲心对待尘世的荣辱。人生哪有一路的晴朗?波折起伏,最能修习心性;动荡颠簸,才会大彻大悟 [5](58)。”
自然界的天体,尤其是日月和星辰,在迟子建的笔下也饱含着温情和诗意。在《雪山的长夜》中,作者描写在故乡失眠的冬夜里,大自然抚慰了她失去爱人的痛苦,“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也是熄灭在光明中”[5](34)。而《萨尔图落日》里北方荒原的落日,则带着凌厉的气势和一股豪情,趁它“在人间最后的舞蹈”,把通身的光华都爆发出来,“落得朝气蓬勃、激昂澎湃,欣然与黑暗赴约”!彼时作家和爱人在列车厢里沐浴着暖融融的夕照,就仿佛被泡在蜜中一样。只是在不久后,爱人因事故永远离去,荒原上的落日,就深深地埋藏在了心底。“那不朽的落日,宛如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我最美的岁月”[5](23-24),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生活总是以残损的形式表现出与理想状态的距离。好在作家以温情的笔触,以及以不屈构筑起的勇气和信念,让我们在苍凉晦暗之中读出了对人性的悲悯和对神性的渴望,让我们看到了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精神的光辉。
作家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她的故乡、与她所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对这些所知所识的事物的认识,常常是喜忧参半。自然界的风云变化,潮起潮落,在她看来既象征着悲伤和苦难,也喻示着升华和化解。只有以慈悲心对待尘世的荣辱,才能领略风雨中的灿烂。迟子建笔下的温情和诗意,并不是对残酷现实的软弱回避或是简单的诗情画意,恰恰表现了作家的人性关怀和写作伦理。迟子建作品中的哀愁,不是颓废、腐朽的代名词,也不是被苦难丑恶推向白热化的戏剧冲突,相反,“真正的哀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可以让人生长智慧、增长力量的”[7]。而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身处“贫乏时代”的人们正是从她的作品中去感悟天人合一的精神栖居,以及追求自然本真的人性温暖,这些闪烁着光芒的东西,比批判针砭更能够给予人们挣脱阴郁的希望和勇气。
刘熙载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8]。作者以物作比,把悲伤的情意融合在特定的自然物象中,使之成为感伤情怀的载体,写景与抒怀浑然一体,凝结着作者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深刻思考,使抽象的天人合一观和伤怀之情表现得具体可感。
三、结语
哲学家洪堡特曾这样论述语言、世界与人的关系—“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和把握世界。语言记录下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存在于世的经验,加之又有自身的组织和规律,于是它逐渐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一个相对于使用者的客体,或者说,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具体的语言都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它源于人,反过来又作用于人,制约着人的思维和行动”[9]。
正如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所评价的一样,她的作品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这位来自极地的黑土地的女儿,选择了她作品中最常见的生命体喻象体现人文关怀与伤怀之美,气象隐喻体现天人合一观和人性温暖,“运用联想、想象作为刻画形象的主要手段,使之成为形象思维翱翔的翅膀,以具体可感的画面的描绘,多方面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因素。写透事物所蕴含的本质意义,对理性美进行探寻、升华”。正是凭藉丰富的隐喻意象,她的散文抒发和塑造了哀愁博大的艺术气质和精神境界,一如苍凉背后的火光。
参考文献:
[1][4]顾艳选编.迟子建散文精品赏析[M].学林出版社,2006:1-5.
[2][7]迟子建专访.中央三台《文化访谈录》,2010,1,4.http://space.tv.cctv.com.
[3]苏童,迟子建:一种叙述的信仰[N].羊城晚报,2007,2,16.
[5]迟子建.迟子建散文[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4.
[6]梁海.诗意与温情——读《迟子建散文》[N].人民日报,2009,12,24.
[8]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2.
[9]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商务印书馆,199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