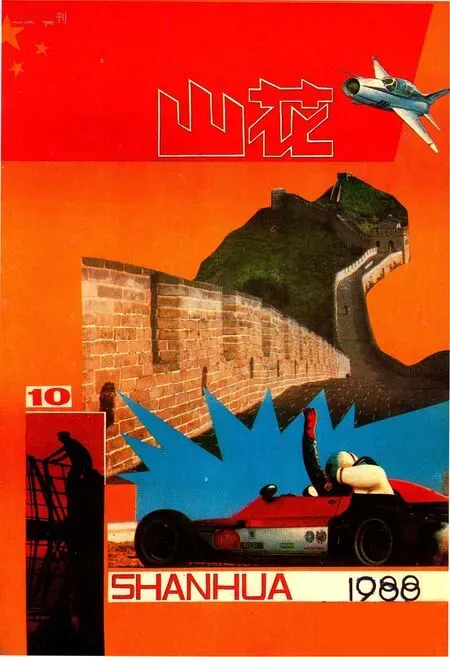废名诗化小说的形成及价值意义
2014-09-16
作为“京派”代表作家的废名,在鲁迅乡土文学的影响下,开始以家乡黄梅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但他的乡土叙事与鲁迅等乡土写实性作家的“揭示痛苦,引起疗救”的主题迥异。他在吸收西方莎士比亚、哈代等创作技巧的同时,沉入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冰层以下,执着而又寂寞地走上了一条乡土诗化小说的道路。废名的个性化创作得到了周作人、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汪曾祺等作家评论家的欣赏和肯定,也影响了后来的乡土小说,尤其是他在小说的抒情化方面的尝试,为诗化小说在小说界奠定了一席之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驰骋着一位文有奇气、特立独行却一生寂寞的非主流作家——“僻才”废名。废名的诗化小说以独异而强烈的抒情色彩,个性化的前卫性,实验的探索性在文体的叙事、立意、结构等方面的摸索和创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
废名,原名冯文炳,字蕴仲,湖北黄梅县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次年出版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9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与人创办过文学杂志《骆驼草》,后创作过短篇小说集《桃园》、《枣》,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等。
当鲁迅擎起新文学的大旗,揭示社会的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时候,废名对他除了欣赏的几部短篇小说之外,尤其对他倾心杂文创作并不表示格外的崇敬。在鲁氏兄弟失和后,他主动地拉远了与鲁迅的距离,赞赏周作人的“人格的健全”。然而,抗日战争时期,废名对恩师周作人却保持了远离的态度,回乡教学著书,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人格节操。鲁迅先生对废名的评价可谓准确:“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面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1]对于废名,鲁迅先生对于他前期的“哀愁”,还是给予肯定的,这些“哀愁”可以说就是废名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婉曲隐晦的反映,虽然经过了他的沉淀过滤,但我们透过作品平和诗意的表层,就能看到废名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以及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严肃思考。
作为“京派”代表作家的废名,在鲁迅的乡土文学的影响下,开始以家乡黄梅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但他的乡土叙事与鲁迅等乡土写实性作家的“揭示痛苦,引起疗救”的主题迥异。他在吸收众多西方大家,如莎士比亚、哈代、塞万提斯等的创作特点的同时,也深深地扎入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底层,坚定而又孤单地踏上了一条“诗化”的乡土小说之路。废名的这种富有个性化的创作得到了周作人、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汪曾祺等众多作家评论家的欣赏和肯定,也影响了后来的乡土小说,尤其是他在小说的抒情化方面的尝试,为诗化小说在小说界奠定了一席之地。
废名对乡土田园的书写范式,“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他的小说像诗又极具散文化,诗意浓郁,韵味悠长,富于美的气息,这种风格被称为“废名风”。同时,他的作品又简约晦涩,充满着佛理禅思、文化底蕴。读他的作品就如同品尝被江南人称为“青果”的橄榄,初入口不免苦涩,慢慢就有一股清香从舌端升起,甘美无比,久久之后竟连它的硬核也舍不得吐掉。
同时,废名的叙事结构也堪称独创,他把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打通,界限模糊,他用散文写诗,用散文写小说,用禅写诗,他的独创性得到了一些知音的欣赏。废名的作品中恬淡静谧的绿色田园,深沉质朴的乡土风情,柔婉美丽的女性形象,跳跃简洁的叙事风格,冲淡质朴的语言魅力,主观个性的自我体验,都深深吸引着读者。废名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操守,他不会向流行献媚取悦读者,没有甘当时代弄潮儿的勇气,创作成为他怡养性灵的修行。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废名的小说是耐读的,不仅耐得住不同的阅读空间,也耐得住不同的阅读时间和阅读对象。”[2]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发出灼人的光芒,使后来的知音品味和叹赏。
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废名向来以作品的晦涩难懂著称,不大受读者欢迎。但废名始终执着于他的诗化小说,坚持着自己的审美追求,他对乡土与传统的诗意回眸,使他的小说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文化的底蕴。更重要的是,有废名如春水秋月的才情,深会自然的真趣,用隐逸的身影铺展开一片诗画般的化境。
一直以来,在现代文学史上,废名的文学成就往往很少提及,甚至人们连废名与冯文炳的关系都搞不清楚。但随着“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高涨,文学的审美价值得到了高度重视。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废名终于被人重新发现,他的这种清新素朴、冲淡平和的文风,吸引了一部分欣赏者。
先是受鲁迅的影响,然后沉浸于乡土诗话小说中的废名,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他依然不改初衷,不去取悦献媚,不去追逐时尚,落寞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真谛。
在这之后,沈从文开始以湘西农村为写作背景,开始了他的乡土小说创作。沈从文先生对于废名是深有体会的,他说,“(废名)只是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3]。沈从文也公开表示,他受到了废名小说的影响,自称他的风格在现代中国作者里面与废名最相称,“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是因为农村观察相同;二是因为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于是从同一方向中,有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4]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我们会发现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在意境的组合与转换、流动与发展来完成的。在宁静恬淡的自然风光里融入人们质朴细腻的身影。显然,两人都在自己所编织的世外桃源的梦里追求、寻找着美好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去追寻,创造着一种健康而自然的精神世界,并与现实生活的迥异对抗着。“京派”作家除了以田园牧歌风格著称的废名、沈从文等,还有在审美理论阐析的朱光潜,在废名之后,影响了萧乾、芦焚(师陀)、李健吾、俞平伯、卞之琳之外,还有凌叔华、林徽因以及后来的汪曾祺等。他们虽然没有结社,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创作精神、审美追求,淡化政治意识,增强艺术的独立精神,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他们往往追寻过去,从平凡的人生命运中细加品味,提炼生活的诗意,寄托一定的文化理想。他们大大发展了抒情体小说,作品注重形式感和可读性,往往能体现出和谐、圆融、静美的特征。
周作人对废名的小说从来不吝赞辞,对废名褒奖有加,几乎篇篇废名的作品都由他写序,“冯文炳君的小说是我所喜欢的一种”[5],“我所喜欢的第一是这里面的文章”[6],“但是容我诚实地说,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7]废名的作品,自成一家,以其田园牧歌的风味和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别具一格,他的小说也往往被称为“乡土田园小说”。在秉承鲁迅等人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废名在他的作品中更加注重主观个性的展示,融入了真善美,使乡土风情雅化。
直接师承沈从文的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的婉约、灵性,那么从创作特点来探究,显而易见的对废名的学习、参考更要突出一些。汪曾祺也多次说过:“……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8]在20世纪80年代时,汪曾祺依然这样说“我确实受了他的影响,现在还能看得出来”。[9]在小说创作的诗情画意方面,废名对汪曾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真实地表达着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宣泄着生活中的的真实情感,具有突出的写意特征。作为受废名影响的小说家,汪曾祺同样把目光投向了氤氲水气中的故乡江苏高邮,相对于废名的温情中时时透露出的冷寂,汪曾祺在这方面更多地表现出温婉与欢悦的风格。理念的不同,造就了品味的不同,从而使得汪曾祺对中国抒情小说的影响远大于废名,将中国抒情小说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废名不仅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京派作家产生了影响,也对其他作家有一定影响。冯健男曾指出:“从‘五四’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有可以称之为以写实、以写意的抒情小说,鲁迅的《故乡》、《社戏》开其端,废名有意地在这路径上进行开辟、营造、前行,在废名之后,沈从文、萧红、师陀、孙犁、汪曾祺等也专走这个路子,于是这一路小说好看煞人,其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小说不同程度地诗化和散文化,而不论其哲学背景和政治倾向的异同。这一路风景实好,废名先行。”[10]新时期的文学,许多有成就的作家,深受废名的影响,在汪曾祺之后,何其芳、梁遇春、阿城、何立伟等作家在审美取向上也受到了废名的影响,着意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参透融入小说创作当代意识。
理解废名并不是一件易事,李健吾曾经说:“废名先生表现的方式,那样新颖,那样独特,于是拦住一般平易读者的结识……无论如何,一般人视为隐晦的,有时正相反,却是少数人的星光。”[11]汪曾祺曾经说过:“废名的价值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地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12]朱光潜先生也认为:“它通得我们要用劳力去征服,征服的倒不是书的困难而是我们安于粗浅的习惯。”[13]读者只要有了旧学的功底,逐渐地去参透反观生命活力的艺术世界,深悟废名的作品,就会对自己充满“情”、“意”、“味”的感知世界作出反应,看到自己的富有创造、审美的生命价值,是自己的视野拓展到作品以外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愉悦地徜徉。
虽然,废名注定在生前身后都不免经历孤独寂寞,一度连名字也被人忘记了,但他依然以自己非凡的才情以及对生命的感知和体悟,不断地影响着乡土抒情文学的发展,他的诗化和散文化小说对20世纪许多中国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废名在小说文体创新‘先行’之外,其田园归因情节这种反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追求也是‘先行’,这就是废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14]汪曾祺在为《废名短篇小说集》写的序中就指出:废名的“这种影响现在看不到了,但是它并没有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汩汩地流到地上来的”。[15]在整个社会越来越看重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废名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在不同的阅读空间、阅读时间、阅读对象经受一代代人的考验,而且会越发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4.
[2]严家炎.废名小说艺术随想.冯思纯.废名短篇小说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10.
[3]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1982-1985:99.
[4]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1982-1985:100.
[5]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止庵校订.苦雨斋序跋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1.
[6]周作人.桃园·跋.止庵校订.苦雨斋序跋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3.
[7]周作人.《枣》和《桥》的序.止庵校订.苦雨斋序跋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7.
[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5.
[9]汪曾祺.谈风格[J].文学月报.1986,(6).
[10]冯健男.梦中彩笔创新奇.艾以,等.废名小说(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21.
[11]刘西渭(李健吾).读《画梦录》[M].周立民.文季月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281.
[1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56.
[13]朱光潜.桥.朱光潜谈读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43.
[14]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2.
[15]汪曾祺.万寿宫丁丁响·代序.废名短篇小说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