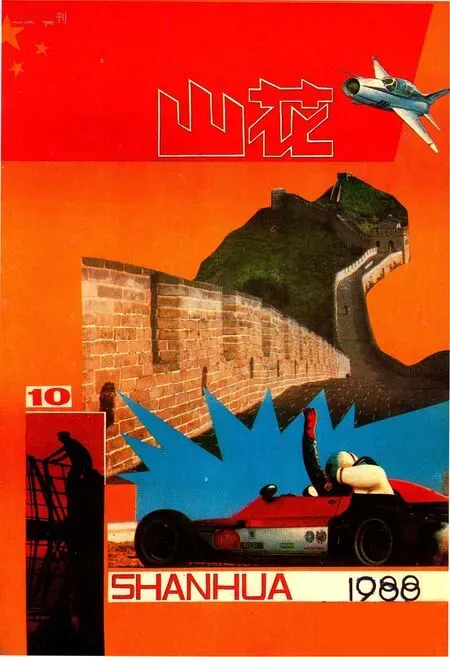被悲痛击中的命运——漫读曾蒙的几首诗
2014-09-16赵卡
赵 卡
“我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好人。但是我很有原则。我要做一个有原则的好人。”曾蒙说。我认为尽管他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努力,但这和他的诗没有多大关系。
在提到诗人曾蒙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攀枝花这个地名和他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齐奥朗晚年出版的《笔记选》中以怪异的口吻表达对波德莱尔的那种敬意,“我已经有许多年没读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我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攀枝花像个因陋就简的边缘村落,似乎有着与周遭世界截然不同的气质。“气质”一词用在这里有些怪诞。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气质,诗人广子曾问过曾蒙,攀枝花在他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曾蒙下的定义有点像咒语,“时代的产物”和“怪胎”。而且,曾蒙认为自己一直是攀枝花诗歌的边缘,而攀枝花又是中国的边缘,他不满但无奈地反问,“你说我咋说,能说什么呢?”所以,换个角度看攀枝花,就像德里克·沃尔科特观察特立尼达岛卡罗尼平原边缘的费利西蒂时那么说,“这个村名取得确实有道理”。
攀枝花在曾蒙的话语里是体制的(普遍)产物,隐含着反讽,就像曾蒙在一首献给柏桦的诗《体制》(2004年8月25日)中写到的那样,“童年和疾病,在蔓延”,缺乏自信和欢乐,失落而清晰;或者像埃科那样归入“中世纪象征主义”的象征和寓言。但攀枝花和柏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柏桦看上去有点模糊,难以定义,他是风格的也是效果的,他的形式机巧但也装饰过度,甚至是寓言性质的“形而上象征”,“呵,体制,我再一次,再一次仰膜你的高度。疾病在减轻,诗人柏桦在限制”。曾蒙对柏桦的热爱,如同布罗茨基对奥登的景慕,“多少年后,我来到你生活的周围”。谦卑,诚挚,优雅的称颂。
对曾蒙来说,“70后”或许也是一种奇怪的体制,这个物理意义上的代际概念曾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好多观点又是错误的),因此,“70后”诗人五花八门的出牌方式在曾蒙的视域里属于“这是一群在路上的诗人”。他们各自的终点不明,呈现出来的面孔也随之屡遭诟病,不妨说“70后”诗人有一种没被确切限制的自信的快乐,这一代人表现出来的祛魅和忠诚,绝对是解过毒的,如此,“70后”诗人区隔了象征的和寓言的诗人,差异性仿佛第一次确立了起来。这样,我把曾蒙放在“70后”这个体制里来观察便省事多了,就像他曾说过的,“在攀枝花,我可以说我很孤独,然而在诗歌中的我,并不孤独”。
如果逐行逐句像布罗茨基对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一诗细读那样,你肯定能从《压抑住悲痛》(2000年3月26日)中读出一只“被悲痛击中的蚊子”的孤独。在这首诗里,曾蒙展开了对一只蚊子的飞翔的想象(非分之想),然后描述了一只蚊子的命运,“不是吟叫,而是血液在对着前方游走”。血液的诱惑足以使蚊子致命,专注于自我的不计后果的摧毁,蚊子变成了的血液本身,如同词改变了性质(质量、重量、浓度、气味、症状、习惯等)。一只与他针锋相对的蚊子,软弱却野蛮的蚊子,像一把利斧意外地劈开了他麻木的肌肉,曾蒙的诗意表述为,“我可以把一只蚊子的命运,描述成停泊在码头上的船只,没有鱼群,浪花和桅杆,没有联想翩翩的童年,只有冥界中的气温在测量着,木棉树、鹌鹑的高度……在冷漠中逼视,那日照东墙的阴影,在川西的竹林中响成一片”。
返回来再说攀枝花,“攀枝花不是一般的冷,像铁片飞,像石头飞。雨一定在下,风一定在吹,在夜晚,在下午,你无法提供准确的地理位置”。(《又下雪了》2014年1月20日)这个地方在行政上属于四川毫无疑问,但人们总是忽略攀枝花属于四川这一事实。由此我又联想到曾蒙本人也很有意味,曾蒙的诗你怎么读都读不出川渝诗人的味道,如他认知的那样,镀金体式的巴文化的尖叫态势(语调)和蜀文化的繁复、华丽以及逍遥自在。这个问题造成了一种困惑,是诗人本身的困惑,而不是读者的困惑——一个温和的曾蒙,叙事的曾蒙,避让宏伟的曾蒙和缺乏野心的曾蒙,所以,曾蒙说,“我想多写点短诗,训练对日常性事物的及物性书写,隐退到能指上的写作”。
《雪的意境》(1992年1月9日)是曾蒙的一首旧作,有点沧桑感。那个时候他已然显露出娴熟的技艺。虽然,如他在诗中所言,“那时我还很年轻,我不知道事物的本质在等待死亡”,但他有一种对应的遍及全身的不祥预感,曾蒙在那个年代就为自己定下了一种哀歌式的调子,他在风格上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小传统,类似这样的表达,“遇见雪,我不知道春天的危机近在咫尺”;还有像在《明天的事情》(1992年3月7日)里的例句,“我听到风吹铁片的声音,明天的事情像风吹铁片”。曾蒙对自己的风格给予顽固的信任,他绝不牵强,如同史蒂文斯对他诸多关于诗歌的格言那样,目的尚未达成,风格却大获全胜。
《重庆素描》(1997年6月12日)和《成都记事》(1997年7月27日)这两首诗的氛围潮湿而杂乱。曾蒙对这两座城市的诗意描述是相面师式的——重庆“咆哮”,(“一个人的语境被语境所困,他的困惑如同咆哮的雄狮。”)成都“悠闲”,(“360度的高温呀,那坐在茶馆里翻报纸的人多么悠闲。”)无须揣摩他人的感觉,即使如戏剧般热闹(市民绝非演员,情绪发自自然),曾蒙仍对他写下的每一个场景的瞬间深信不疑。日落接着日出,市民的确在粉墨登场,扮演戏剧的情节中的自己,或是“离我们最近的生活,有一个害着感冒和高烧的青年”,或是“一位老年妇女,戴着无产阶级袖章,拿着小旗旗,引导人行道”,散漫而确凿。曾蒙的语气看上去是赞颂的,却又像挽歌,怀旧式的,描述性的,这种基调不仅表现在《重庆素描》和《成都记事》里,也持续地困扰于他的其他早期的诗篇中,如《不要轻易去触动》、《潮流》、《在呼吸中冥想》、《血》。
除了《太阳又出来了》、《瑞丽》、《海塔》、《青春》、《预言》,最近少量的几首诗似乎一反曾蒙过去的风格,变得凶狠和口语起来。说到口语,我必须强调一点,我不太明白曾蒙何以对口语化的诗写产生偏见(但他并不全盘否认口语诗),可能是他觉得口语入诗有其野蛮和粗陋的一面,让他感到遗憾或悲哀。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与冯尧谈诗》(2014年1月14日)里,曾蒙似乎站在了崇高的对立面,带着自我贬损的态度,“最近写了啥子?我要写诗了”。“冯尧,我们都过四十了,谈这些个是不是很矫情?”他的口语特征是显著的,但他的处境也是两难的,矫情何以抵达崇高?至此,曾蒙的诗不再连贯,但又要和谐一致,于他而言,不知道这种不安是不是有种自我强迫的况味。不管怎么说,曾蒙绕过了他之前的某些小传统,他变得狡黠了,随意了,但更狭窄,更刻意,更难以驯服。比如《魔鬼》(2014年1月15日),这首诗是自传性叙事的,恶习在他身体里驻扎下来并发生作用,但他流露出来的却更像赞美,怪诞的、有点波德莱尔的感觉,“我身体里驻扎着两个鬼,一个凶鬼恶灵,住在上半身。一个色鬼满天,住在下半身。他们平时相安无事,和气生财,井水不犯河水”。《孔子不要笑我》(2014年1月23日)以修辞的热情道出了一种灵魂战的场景,我仿佛听到了曾蒙内心撕裂的“嘎吱”声,“孔子不要笑我”,他寻找(自省)的东西远大于标题本身,或者说,他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发现自己的好奇心。特别需要强调的一首是《高黎贡山》(2014年2月11日),读后便觉出一种老于坚的味道,他绝不迁就对于景物的简单描摹,也绝不收敛奔向天堂(地狱)的速度。
在我的印象里,曾蒙应该属于一个向沉默妥协的人,在一个靠轶闻流传诗篇的时代里,他显然缺乏耀眼的章句和肉感挑逗的意味,这样一来,他因缺乏情调不免显得有些墨守成规了。川籍诗人的镀金体传统技法似乎离他很远,他的风格和意象也是松松垮垮,他不擅建设狂谵,更不会滑入狂热,大约唯此,曾蒙得以对自己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效果性辩护,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被悲痛击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