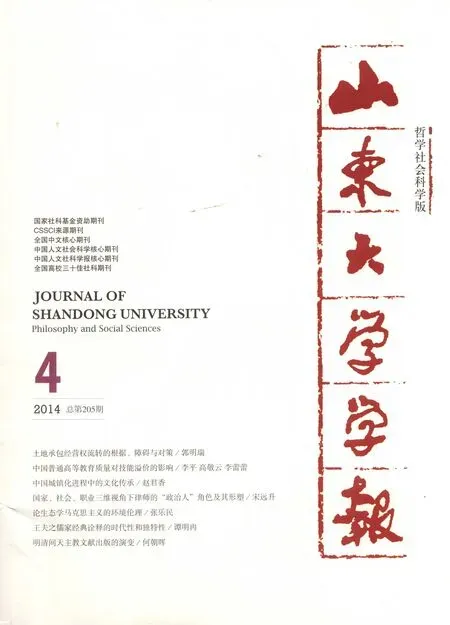明清间天主教文献出版的演变
2014-09-14何朝晖
何朝晖
明清间①本文所说的“明清间”指从晚明到鸦片战争前。这一时间概念此前学界已多有使用,大抵指晚明到清中叶这段时间,与本文所论时间范围基本重合。例如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计文德:《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台北:汉美图书公司,1991年;谢和耐、戴密微等:《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耿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等等。,基督宗教第三次进入中国。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的主要是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②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还有沙俄东正教,本文不涉及。,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关于西学和天主教教义的出版物。此前学术界在整理、汇编这些文献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③较早的有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等。近几十年来的汇编和影印成果主要有《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东传福音》、《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等等。,并对这些文献在传教史、思想史上的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以文本为中心,注重对文献内容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出版和传播的角度研究明清天主教文献④如钟鸣旦、杜鼎克:《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史林》1999年第2期;张先清:《刊书传教:清代禁教期天主教经卷在民间社会的流传》,见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141页;潘剑芬:《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穗澳地区的图书出版活动(15811840年代)》,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宋巧燕:《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刊刻与流传》,《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6期;张淑琼:《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粤刻印书籍述略》,《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2期;等等。著作方面有邹振环:《晚明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伍玉西:《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但从出版史角度对明清天主教文献所作的梳理仍然还很不够。明清天主教文献出版的主体及各自特点如何?明清天主教出版活动在各个不同时期如何发展演变?这些基本脉络仍有待于理清。没有这样的宏观梳理,我们很难对明清时期的天主教文献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本文所论天主教文献①实为沿用学界的习惯表述,如《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等,这些汇编文献中既包括宗教文献,也包括西学文献。指的是明清时期因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活动②葡萄牙势力较早进入澳门并建立传教基地,其天主教文献出版情况与中国其他地区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笔者所论暂不涉及澳门。亦不涉及台湾。而产生的文献,其中不仅包括有关天主教教义的宗教文献,也包括大量介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的西学文献。宗教文献又可分为宗教理论文献和宗教日用文献两类,前者指关于宗教信仰、教会史、辩教护教等理论层面的著作;后者则是指神职人员和普通教众从事日常宗教活动所需的实用性书籍,比如教会的各种规章制度,各种宗教仪式的仪轨,各种供念诵用的经文、诗歌等等,属于日常实践层面。关于“出版”,这里指的是以印刷方式出版的天主教文献。除了像《四库全书》这样地位重要的著作外,本文并未将以写本或抄本形式存在的天主教文献纳入考察范围③据统计,在产生天主教文献最多的17世纪,约出现了590种天主教文献,其中460种以上有刊本,因此对刊本的考察大致可以反映明清时期天主教文献的传播情况。见伍玉西:《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第140页。。
明清间天主教文献的出版者,不仅包括教会,还包括从皇室、士大夫到民间书坊主的各个阶层。这反映了天主教和西学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广泛影响。各个参与到天主教文献刊印中的出版主体,有其各自的考量和出发点,其出版物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点。明清间天主教文献出版的盛衰是与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运沉浮相始终的,笔者在此将其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以下分述之。
一、晚明士大夫刊布西学文献的热潮与教会出版事业的发轫
晚明时,天主教耶稣会士率先进入中国。耶稣会特别重视修士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修士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重视利用书籍传教。另外,耶稣会在传教中有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的传统。耶稣会远东地区巡察使范礼安在耶稣会进入中国内地的关键时刻,下令摒除“欧洲人文主义”,放弃对中国教徒的“葡萄牙化”政策,而要使传教士“中国化”④参见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 6页。。在这种传教思想的指导下,传教士由“僧”而“儒”,主动向中国文化及其主要承载者士大夫阶层靠拢。这种策略取得了成功。就天主教文献的出版而言,在传教的最初阶段,在教会出版机构普遍建立起来之前,天主教文献的刊刻传播主要是藉由中国士大夫之手实现的,士大夫的出版活动对于天主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有着重大的贡献。
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士居所——肇庆仙花寺里,罗明坚和利玛窦有意识地通过展示西方的图书和器物来吸引中国人的注意。这种策略颇有成效,肇庆知府王泮对悬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王泮的要求下,利玛窦将此图译成中文,王泮于万历十二年(1584)出资刊刻,名为《山海舆地图》⑤参见邹振环:《晚明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3739页。。这是中国士大夫刊刻西学文献的滥觞。此后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先后被应天巡抚赵可怀、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锦衣卫官员李应试等人不断修订、刊刻,在明朝士大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⑥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 62页。。王泮还刊刻了第一部用中文阐述天主教义的著作——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广为散播⑦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2页。。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到达南昌,明朝宗室建安王朱多 遇之甚厚,利玛窦有感于此,撰写了介绍西方人友谊观的著作《交友论》,甫一问世,即在士大夫中不胫而走。英德知县苏大用在利玛窦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江西宁都将此书刊刻出来,万历二十九年(1601)冯应京在湖广按察司佥事任上再次翻刻,足见此书在中国士人当中受欢迎的程度①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3840页。。利玛窦还在南昌士人面前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并在巡抚陆万陔的要求下撰写了介绍西方记忆术的《西国记法》。利玛窦后来又编撰了西方格言集《二十五言》,在士大夫中流传亦广。世界地图、《交友论》、《西国记法》、《二十五言》等西学文献的刊刻出版,传教士至少表面上扮演了被动的角色,中国士大夫则显得积极主动。这正是传教士的高明之处。一方面,他们要潜移默化地让中国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主动接近来自西方的异质文化。中国士大夫首批刊刻的主要是西学文献,没有多少宗教色彩,这反映了传教士循序渐进的传教策略。另一方面,耶稣会士对教会书籍有一套严格的出版许可制度,以免偏离教会的正统思想。最早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在中国出版书籍需要获得远在印度果阿的耶稣会东方省批准,十分不便,有了中国士人的出版热情正好可以借力行船。传教士不必亲力亲为,就通过中国士大夫刊刻的书籍把西学和天主教的影响传播四方了。
此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本土天主教徒,著名的有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以及王徵、孙元化、山西绛州的韩氏兄弟和段氏兄弟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因各种原因未能入教,但倾心、同情西学和天主教的士人,如冯应京、毕拱辰等。在他们的积极推动和参与下,晚明出现了刊刻天主教文献的高潮。这一时期士大夫刊刻的文献既有西学方面的,也有宗教文献。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偕二三同志,刻而传之”②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58页。,又将熊三拔《泰西水法》收入其编纂的《农政全书》中。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多部西学著作,并先后刊刻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交友论》、《天主实义》、《同文算指》、《辩学遗牍》等著作,崇祯元年(1628)刻傅汎际《寰有诠》,又刻孙学诗、杨廷筠《圣水纪言》③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7198页。钟鸣旦、杜鼎克主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8册《圣水纪言》李之藻《刻圣水纪言序》,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于崇祯二年(1629)辑印了影响巨大的《天学初函》。杨廷筠与艾儒略合撰《职方外纪》,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编刻《绝徼同文纪》,天启三年(1623)刻艾儒略《职方外纪》,还刻了庞迪我《七克》、熊士旂《策怠警喻》④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99100页。王美秀编:《东传福音》第2册《七克》,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卷端题署。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9596页。。冯应京虽最终未能入教,但与利玛窦为莫逆之交。他刊刻了利玛窦的《交友论》、《天主实义》、《四元行论》、《二十五言》和《世界舆地两小图》⑤伍玉西:《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第166页。。王徵与邓玉函合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又于天启六年(1626)刊刻了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⑥《东传福音》第11册《西儒耳目资》,牌记题“了一道人良甫梓行”。按:“了一道人”为王徵道号。。韩云、韩霖、韩霞兄弟和段衮、段袭、段扆兄弟是明末山西首批信奉天主教的士人,积极从事天主教书籍的刊刻活动。韩云刊行了罗雅谷的《天主经解》,韩霖、段衮刊刻了高一志的《童幼教育》,段衮、段袭兄弟还刻了艾儒略《三山论学记》⑦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5页。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童幼教育》韩霖“序”,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年。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16217页。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1册《三山论学记》段袭“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山东士人毕拱辰刊刻了邓玉函《泰西人身说概》,又刻高一志《斐录答汇》⑧钟鸣旦、杜鼎克、蒙曦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4册《泰西人身说概》毕拱辰“序”,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2册《斐录答汇》毕拱辰“序”。。此外,晚明时瞿汝夔、郑怀魁、熊士旂、袁升闻、许胥臣、朱宗元、汪元泰、武位中等许多中国官绅士人都曾参与天主教书籍的出版⑨参见伍玉西:《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第163、169页;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225、294页。。
晚明是中国出版史上商业出版急剧爆发的一个时期。在天主教文献的传播中,书商也起了一定作用。天主教文献不仅有思想、学术价值,也可能具备商业价值,因为这些承载着异域文化的文字,对晚明深受尚奇好异风气影响的中国读书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世界地图、《交友论》、《西国记法》、《二十五言》、《五十言余》等书,新奇而典雅,非常适合中国文人的阅读趣味。引介西方科学的著作也有一定市场。有些书坊主一方面从中看到了商机,一方面也可能向往天主教,于是加入到刊刻天主教文献的行列中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徽州书商。晚明徽州汪姓书商在出版界十分活跃,汪姓书商中刊刻天主教书籍可考者,有汪汝淳、汪应魁。汪汝淳本为徽州歙县人,生员,字孟朴,后到杭州开设书坊燕贻堂①《天学初函》之《天主实义》前有汪汝淳《重刻天主实义跋》,末题“新都后学诸生汪汝淳书”,同书李之藻“序”称其为“汪孟朴氏”,《天主实义》卷端题“燕贻堂较梓”。参见李之藻辑:《天学初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第356、375377页。另参胡金平:《晚明“汪汝淳”考》,《基督教文化学刊》第23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5242页。,与李之藻、杨廷筠等天主教士人交往密切。实际上,李之藻所辑《天学初函》中的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二十五言》、《天主实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撰的《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庞迪我的《七克》,书版均应为汪汝淳所刻②《重刻畸人十篇》卷端题“后学汪汝淳较梓”,见《天学初函》第117页;《重刻二十五言》卷端题“新都后学汪汝淳较梓”,见《天学初函》第331页;《天主实义》有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汪汝淳《重刻天主实义跋》,皆显示该书为汪氏所刊,参见《天学初函》第351357、373376页;《同文算指》目录后题“新安汪汝淳、钱塘叶一元同较梓”,参见《天学初函》第2788页;《圜容较义》据李之藻序,为汪氏所梓,见《天学初函》第34333434页;《七克》卷端题“武林郑圃居士杨廷筠较梓”,据汪汝淳《七克后跋》则似为汪氏所梓,参见《天学初函》第717、11251126页。。这些书很可能在市面上发售,比如《天学初函》除分赠友人之外,还“公开发售给百姓”③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第434页。。徽州书商汪应魁,从王徵那里得到了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初刻本,在他经营的广及堂加以翻刻出售。崇祯四年(1631),另一名徽州书商西爽堂主人吴氏再次翻刻《奇器图说》,更名为《新制诸器图说》④邹振环:《晚明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306307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0页。,可见这部充分展现欧洲人“奇技淫巧”的书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徽州制墨商、出版商程大约与利玛窦相识,从利玛窦那里得到《西字奇迹》一书中的《圣母怀抱耶稣之像》、《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闻实即舍空虚》、《淫色秽气自速天火》等四幅《圣经》故事西洋铜版画。程大约请名画家丁云鹏摹绘,由徽州著名的黄氏刻工雕版,刻入万历二十三年(1595)出版的《程式墨苑》中。该书是一部供客户看样选购的墨锭样式图谱,这四幅从题材到形式都具有浓郁欧洲风格的版画作品,盖可成为吸引读者和买家的一大亮点。这可视为天主教文献通过书商得到传播的又一例证。
除了借助中国士大夫和书商刊刻传播天主教文献之外,教会自身的出版活动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罗明坚于万历八年(1580)年进入广东,三年后得以在肇庆定居,他撰写了第一部中文天主教书籍《天主圣教实录》,于万历十二年(1584)在广东出版⑤参见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此书初版书名为《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书中作者自称为“天竺国僧”。后经教会修改审定,去除佛家用语后于崇祯十年(1637)重新出版。详见《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方豪《影印天主圣教实录序》。。利玛窦第一部用中文撰写的天主教著作《天主实义》,或认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初版于南昌,或认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才在北京首次出版⑥邹振环:《晚明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108页。。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进入北京,将住所作为耶稣会会院,尽管条件简陋,但已开始刊刻《天主实义》、《二十五言》、《要理问答》等书籍⑦利玛窦:《利氏致德·法比神父书》,见罗渔译:《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下),台北:光启出版社;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5279页。此信写于1605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金尼阁代表在华耶稣会士到罗马向教宗申请用中文做弥撒,诵念日课,翻译《圣经》。获得批准,传教士乃更积极地用中文出版教会书籍。与此同时,在华教会书籍的出版在管理体制上也进一步理顺。万历四十六年(1618),耶稣会中国传教区成立了中国副省。大约从1620年代开始,耶稣会中国副省获得了出版传教书籍的核准权①伍玉西:《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第134135页。,而不必从远在印度果阿的耶稣会东方省获得出版许可,从此中国天主教书籍的出版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天主教堂逐渐在各省建立起来。这些教堂不仅是传教中心,同时也是教会文献出版中心。金尼阁回到中国后对出版教会书籍十分积极,泰昌、天启年间他在绛州、西安、杭州均设立了印书工场,每年出版书籍甚多②费赖之编,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1页。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3页。。现存明清间各地教堂刊本以清代版本居多,明代出版物相对较少,有些出版物则难以辨别是明刊或清刊。为叙述方便起见,各地堂口的出版情况集中放在下一节考述。
耶稣会士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他们一直试图获得官方的认可,若能使最高统治者皈依天主,则可以带动整个国家信仰的转变。在这一方面,传教士远不如他们对中国士大夫所做的那样成功。利玛窦在广东、江西、南京等地时,与众多地方官员和明朝宗室有交往,但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与利玛窦交往的,并不代表官方。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进入北京,将西洋礼品进献给万历皇帝,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始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但并不意味着对传教事业的支持。明朝皇帝感兴趣的只是西洋自鸣钟、铁弦琴、世界地图等新奇之物,以及传教士所拥有的铸炮、修历等实用性技能,对天主教本身则始终缺乏热情。传教士虽然未能使皇帝本人皈依天主,但却成功地使得一些明朝宗室、后宫嫔妃和太监受洗入教。南明时,几个小朝廷试图借助西方势力抵抗清兵南下,永历政权的皇太后、皇后、皇子和朝廷重臣也纷纷加入天主教,官方与天主教的关系可谓达于顶点。但南明政权很快在颠沛流离中覆亡,在传教事业上并没有什么作为。
晚明具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出版物仅限于历法方面的著作。崇祯初年,徐光启受命修订历法,与李天经、传教士罗雅谷、汤若望合著《崇祯历书》进呈御览。这部书不久就被刊刻出来,题“明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杨惟一梓”③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45页。,杨惟一应是具体负责出版事宜的官员。著名的奉教太监庞天寿于崇祯六年(1633)刊刻了范中圣的《天主圣教小引》,这是宫廷中刊刻天主教读物的一个证据④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75页。。
二、清前期教会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宫廷中刊刻的西学文献
这一阶段指的是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五十九年(16441720)。清前期传教士进一步取得官方认可,统治者对天主教较为优容。顺治皇帝尊称汤若望为“玛法”(满语“爷爷”),关系十分亲密。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从此西洋传教士垄断这一职位长达近两百年之久。康熙帝对西方科学兴趣浓厚,亲自学习西学知识。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下达了著名的“容教令”,通令各省允许天主教传播,“不必禁止”。受益于这种良好氛围,此期传教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各地教堂数量、教徒人数都有很大增长。
这一时期天主教徒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入清以后士大夫阶层对天主教的热情逐渐消退,清代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趋于严厉,晚明时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不复存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清初儒家知识分子在整体心态上相对于晚明呈急剧收缩态势,对天主教的态度发生很大转变,从好异慕新、宽容包纳转而回归程朱理学,排斥异端⑤参张先清:《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另一方面,耶稣会之外的其他修会陆续进入中国⑥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于1630年代进入中国内地。奥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均在17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入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等托钵修会的传教策略与耶稣会有很大差异,注重在社会下层发展教徒。此消彼长,使得教徒中来自普通百姓的比重大大增加。新增教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甚至有许多是文盲,他们对书籍的需求大为降低。
晚明士人对天主教书籍的刊刻出版盛极一时,但随着明清易代,这一势头嘎然而止。清代士人刊印天主教文献的数量大为减少,而其中又以宗教理论著作为主,罕有西学书籍。清初奉教士人在教案频发、官民反教情绪日趋浓烈的情况下,撰写了一些辩教、护教著作,如张星曜的《天儒同异考》、《圣教赞铭》、《祀典说》①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8册、《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0册。《东传福音》第3册《天释明辨》牌记题“敕建天主堂绣梓”。方豪以北京东堂顺治十二年(1655)蒙受钦赐,似认为此书为东堂所梓。按:北京北堂亦为康熙敕建,故未便确定究竟为何堂所梓。见《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1册方豪《影印天释明辨序》,第13页。,严谟的《天帝考》②也有学者认为,应作《帝天考》。参褚良才:《从儒家经典到天主教教义——解析严谟〈帝天考〉如何为“上帝”正名》,见李炽昌主编:《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5186页。、《祭祖考》、《木主考》、《辩祭》③参见《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1册。,这些著作很多都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其中原因除了士大夫阶层逐渐远离天主教之外,也因为晚明知识界译介西学的高潮已经过去,大量西学著作已经得到翻译出版,西学文献逐渐从天主教文献出版的中心淡出。
如果说在前一个阶段士大夫与教会是天主教文献出版的两大力量,那么在这一时期教会就成了天主教文献出版的绝对主力。随着传教事业的持续发展,各地教堂及其所属出版机构比较普遍地建立起来,刊刻了大量书籍。清顺治十六年(1659),卫匡国在杭州建立圣母无染原罪堂,刻书的版片价值超过2000两银子④参见赵殿红:《清初耶稣会士在江南的传教活动》,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4、18页。。康熙三年(1664)出版的李祖白《天学传概》中说,教会“成书三百卷:有经,有史,有超形性学,有形性学,有修学,有天文学,板藏京师、江南、浙、闽、秦、晋各堂”⑤李祖白《天学传概》康熙三年许之渐“序”,见《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1067页。。可见当时各地教堂刻书之盛。现存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康熙十三年(1674)至康熙十五年(1676)在常熟传教的账本显示,书籍印刷方面的开支在传教活动的各项支出之中占据了最大的比例⑥参见[比]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赵殿红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500514页。。
对各地教堂的刻书机构,以前未见系统研究。兹根据已经公布的各种目录、提要,尤其是近年来影印出版的大批天主教文献等资料,对各地教堂的刻书情况作一初步梳理。此前关于明清间各地教堂数量和分布的研究⑦如汤开建、赵殿红:《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汤开建:《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所据基本上是一些宏观的统计报告,对各地堂口的具体名称则语焉不详。国内外现存天主教著作刊本中的题记,或可弥补这方面资料的不足。
北京是最重要的天主教文献出版中心。在得到万历皇帝的默许立足于北京之后,传教士就把北京作为全国的传教中心。北京刊刻的图书占了明清间全国天主教刻书总量的70%⑧宋巧燕:《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刊刻与流传》,第97页。该文统计依据为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北京先后建有南堂、东堂、北堂、西堂四大天主教堂,以南、北二堂刻书最多。南堂或又名领报堂、京都始胎大堂,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苏霖《圣母领报会规》、利玛窦《畸人十篇》,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畸人十篇》,乾隆二十年(1755)刻《总牍汇要》,龙华民《圣教日课》,嘉庆三年(1798)刊庞迪我《七克》⑨参见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01、34、354页。邹振环:《晚明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127、130页。《畸人十篇》作“金台圣母会”刊本,盖即圣母领报会。。北堂又名救世堂,所刻书籍又署“首善堂”、“仁爱圣所”。刻有冯秉正的《盛世刍荛》、《圣年广益》、《圣经广益》、《朋来集说》、《圣体仁爱经规条》,佚名《思正恩言》,又于乾隆十八年(1753)刻孙璋《性理真诠》⑩参见《东传福音》第2册《盛世刍荛》牌记。《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4册《圣经广益》牌记;第12册《朋来集说》牌记;第20册《圣体仁爱经规条》牌记;第22册《思正恩言》牌记。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40、413页。。北京还有署“敕建天主堂”刊杨廷筠《天释明辨》⑪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8册、《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0册。《东传福音》第3册《天释明辨》牌记题“敕建天主堂绣梓”。方豪以北京东堂顺治十二年(1655)蒙受钦赐,似认为此书为东堂所梓。按:北京北堂亦为康熙敕建,故未便确定究竟为何堂所梓。见《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1册方豪《影印天释明辨序》,第13页。,署“北京天主堂”梓行利类思《超性学要》、《司铎典要》,署“金台景教堂”刊刻的罗雅谷《天主经解》①参见 《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超性学要》牌记;第19册《司铎典要》牌记;第21册《天主经解》牌记。《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3册《唐景教碑颂正诠》牌记。,具体堂口均不详。梵蒂冈图书馆藏清初入华传教士叶尊孝《字汇拉定略解》后附有几份书目,上列明清时期北京教会出版的书籍达123种②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186页。 钟鸣旦、杜鼎克:《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尚扬译,第58页。梵蒂冈图书馆藏的叶尊孝书目作36种,小有差异。见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186页。。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一份书目则列出212种③钟鸣旦、杜鼎克:《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尚扬译,第58页。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8册《圣洗规仪》牌记。。由此可见,北京教堂刻书之多。
山西绛州是北方传教活动活跃的地区之一。现存署“古绛景教堂”刊高一志《修身西学》④《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修身西学》牌记。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5册《善终诸功规例》书末题“建武日旦堂重梓”。按:建昌、建武皆为江西南城一带旧称,五代南唐置建武军,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改名建昌军。《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7册《天学蒙引》卷端题署。《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天主教要》页12b题“日旦堂梓”。。山东济南在明清之际有两所重要的教堂,即耶稣会士建立的西堂和方济各会士建立的东堂。西堂康熙三年(1664)刻有利安当《天儒印》。东堂正式名称为天衢堂,刻有石铎禄《启蒙指要》,康熙三十七年(1698)刊利安当与尚祜卿合著《正学镠石》。署“补儒堂”的石铎禄《默想神功》,署“圣路堂”的《圣教总牍经文》,亦为东堂所刊⑤《东传福音》第2册《天儒印》尚祜卿序末题署。《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1册《启蒙指要》卷五页53a题“济南府天主天衢堂梓”。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第1册《正学镠石》牌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潘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05107页。参见《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天主圣教四字经文》牌记;第12册《本草补》刘凝序末题署。《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8册《告解四要》卷末题署;同册《领圣体紧要》卷末题署。。东堂还刊行了利安宁的多部著作,如《五方圣方济各祷文》、《圣伯多禄亚甘太辣祝文》、《圣人文度辣赞圣人安多尼祝文》和《圣若瑟七苦乐文》⑥参见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92页。。
徐光启的家乡上海是天主教重镇,有“云间敬一堂”。敬一堂于康熙十四年(1675)刻有柏应理《四末真论》、毕多明我《显相十五端玫瑰经》、阳玛诺《圣若瑟行实》。“云间天主堂”梓罗雅谷《求说》。苏州有大原堂,刻过佚名《真福八端》⑦《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4册《四末真论》柏应理序末题署。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637页。《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5册《圣若瑟行实》牌记;第21册《求说》牌记;第14册《真福八端》书末题署。。
杭州是又一个重要的天主教文献出版中心,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中的李之藻、杨廷筠皆为杭州人。第一部汇刻天主教文献的丛书《天学初函》即出版于杭州。杭州有慎修堂,刊有毕方济《灵言蠡勺》,又刻有王丰肃《教要解略》⑧《东传福音》第2册《灵言蠡勺》卷端题署。《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教要解略》卷端题署。。昭事堂,曾刊汤若望《进呈画像》⑨《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进呈画像》书末题署。。超性堂于崇祯二年(1629)刻高一志《圣意纳爵传》、《圣方济各沙勿略传》,顺治十八年(1661)刊潘国光《天神会课》,又刻《与弥撒功程》⑩超性堂□刻”。《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0册《天神会课》卷末题署;第17册《与弥撒功程》版心刻“超性堂”。。“武林天主堂”于崇祯十七年(1644)刊《唐景教碑颂正诠》⑪参见 《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超性学要》牌记;第19册《司铎典要》牌记;第21册《天主经解》牌记。《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3册《唐景教碑颂正诠》牌记。。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一份书目上,列有杭州天主堂刊刻的图书40种⑫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186页。 钟鸣旦、杜鼎克:《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尚扬译,第58页。梵蒂冈图书馆藏的叶尊孝书目作36种,小有差异。见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186页。。
湖广武昌府有“郢都天主堂”,刊穆迪我《圣洗规仪》⑬钟鸣旦、杜鼎克:《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尚扬译,第58页。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8册《圣洗规仪》牌记。。江西有建昌日旦堂,刊伏若望《善终诸功规例》,“周志于道甫”《天学蒙引》,佚名《天主教要》⑭《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修身西学》牌记。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5册《善终诸功规例》书末题“建武日旦堂重梓”。按:建昌、建武皆为江西南城一带旧称,五代南唐置建武军,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改名建昌军。《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7册《天学蒙引》卷端题署。《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天主教要》页12b题“日旦堂梓”。。江西又有“钦一堂”,清初刊艾儒略《天主圣教四字经文》。江西南安府大庾县有“横浦翼翼堂”,刻过石铎禄《本草补》。翼翼堂又刻有《告解四要》、《领圣体紧要》,都是一整张便于普通教众携带阅读的问答体传教宣传品⑮《东传福音》第2册《天儒印》尚祜卿序末题署。《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1册《启蒙指要》卷五页53a题“济南府天主天衢堂梓”。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第1册《正学镠石》牌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潘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05107页。参见《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天主圣教四字经文》牌记;第12册《本草补》刘凝序末题署。《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8册《告解四要》卷末题署;同册《领圣体紧要》卷末题署。。
福建是又一个教会出版活动十分兴盛的地区。福州“钦一堂”于天启六年(1626)刻艾儒略《西学凡》,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艾儒略《圣梦歌》①邹振环:《晚明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225页。《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6册《圣梦歌》书末题署。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391392页。。在梵蒂冈图书馆保存的一份书目中,有福州“钦一堂”刻书55种②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185-186页。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书目作51种,见钟鸣旦、杜鼎克:《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尚扬译,第58页。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186187页。。福州又有“怀德堂”,刊颜珰《天主圣教要理》;“玫瑰堂”,梓行罗森铎《圣女罗洒行实》;“三山景教堂”刊罗雅谷《圣记百言》③《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5册《天主圣教要理》牌记;第15册《圣女罗洒行实》牌记;第23册《圣记百言》牌记。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39252页。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536页。。晋江有“景教堂”,于崇祯八年(1635)刊杨廷筠《代疑续篇》,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纪略》④《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6册《代疑续篇》牌记及卷末题署;《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4册《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书末题署。。漳州的“清漳景教堂”明清之际刻有庞迪我《天主实义续篇》⑤《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1册《天主实义续篇》牌记。方豪所撰解题认为,刊于天启五年(1625)至南明永历八年(1654)之间。。“闽中景教堂”刊高一志《十慰》、《则圣十篇》、艾儒略《涤罪正规》,崇祯二年(1629)刊艾儒略《弥撒祭义》。⑥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4册《十慰》牌记;同册《则圣十篇》目录末题署。《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4册《涤罪正规》牌记。《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6册《弥撒祭义》牌记,又有崇祯二年艾儒略序。南明唐王政权时期,“敕建闽中天主堂”于隆武元年(1645)刊龙华民《圣若撒法始末》,隆武二年(1646)刻艾儒略《性学觕述》、《五十言余》⑦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5册《圣若撒法始末》牌记及卷端题署。《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6册《性学觕述》牌记。《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第1册《五十余言》牌记。。福建教堂的刻书数量仅次于北京。
广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广州大原堂”,康熙八年(1669)刻南怀仁《妄推吉凶辩》、《妄占辩》,康熙十九年(1680)刻高一志《圣母行实》,又刻朱宗元《天主圣教豁疑论》⑧参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6册《妄推吉凶辩》目录后题署;同册《妄占辩》目录前题署。《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第3册《圣母行实》牌记;第2册《天主圣教豁疑论》卷末题署。。广州杨仁里有方济各会士建立的“福音堂”,曾刻利安当《万物本末约言》⑨《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万物本末约言》卷末题署。、恩若瑟《圣父方济各行实》、利安定《成人要集》、文度辣《圣教要训》⑩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391392页。。广州“朝天路教堂”亦为方济各会建立的教堂,刊卞芳世《进教领洗捷录》、利安定《永福天衢》⑪邹振环:《晚明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第225页。《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6册《圣梦歌》书末题署。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391392页。。梵蒂冈图书馆藏的叶尊孝书目中有“广东书版目录”14种,大约是耶稣会出版物;同时列有广东方济各会刻书23种⑫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185-186页。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书目作51种,见钟鸣旦、杜鼎克:《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尚扬译,第58页。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第186187页。。
关于教堂与出版机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发掘,以作深入探究。一些重要的传教地点和知名教堂,如南京的“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杭州的“圣母无染原罪堂”,在现存版本中尚没有发现刻书活动的踪迹。另一方面,同一所教堂刻书时使用多个名号也较常见。总体来看,北京、杭州、福建、广州、绛州是全国范围内几个最重要的天主教文献出版中心。在来华各修会中,以耶稣会的出版活动最为兴盛。其他修会传教策略与耶稣会有显著不同,在出版成就上远不及耶稣会。其中,方济各会也刊行了一定数量的传教书籍。
这一时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对传教士的恩宠和对西学的浓厚兴趣,宫廷中刊刻了一批重要的西学文献。《崇祯历书》入清后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书》,经汤若望修订,由钦天监于顺治二年(1645)、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二十二年(1683)多次刊行⑬《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5册《天主圣教要理》牌记;第15册《圣女罗洒行实》牌记;第23册《圣记百言》牌记。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39252页。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536页。。康熙十三年(1674),内府刊刻了南怀仁的《新制仪象图》①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第35页。。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刊行了汤若望的《民历铺注解惑》②《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6册《民历铺注解惑》,书前列数十官员衔名“共参”,应为官刻。。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圣祖任用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以西洋技术测绘全国地图,编制成《皇舆全览图》,现存康熙五十七年(1718)、六十年(1721)木刻本及康熙五十八年(1719)由传教士马国贤主持以西洋铜版印刷方法印制的版本。康熙五十二年(1713),马国贤又以铜版印刷法印制了《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康熙后期从全国征召了方苞、梅瑴成、明安图等一批著名学者,与传教士合作编纂融汇中西数学、历法、音乐成果的《御制数理精蕴》、《御制钦若历书》、《律吕正义》,传教士张诚、白晋、戴进贤、徐日升、德理格等皆参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以上三书皆有康熙内府铜活字本③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概述”,第38、59页;“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第8 9、35页。。白晋、张诚还用满文撰写了《西洋药书》,书中记述了曾治愈康熙疟疾的金鸡纳(奎宁)等西药④朱赛虹:《从守望到会通——康熙和路易十四时期的中法科技文化交流》,见胡建中、马季戈主编:《“太阳王”路易十四》,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7283页。。
康熙末年爆发“礼仪之争”,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导致教会与清廷的关系恶化。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帝谕令传教士必须持有朝廷发给的“信票”⑤实际票面上称“信票”。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332页收有传教士伊大任所持信票影印件。官方文书中则作“印票”,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84页。,声明遵守尊重中国传统礼仪的“利玛窦规矩”方可传教,否则将被驱逐出境。此后双方的关系虽趋于紧张,但康熙并无意全面禁绝天主教,各省的传教活动仍在继续开展。但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直接阻绝了中国士人的入教之路,此后天主教徒中几乎不再有知识分子。
三、禁教期的天主教文献出版:两极化
这一阶段从康熙六十年(1721)到鸦片战争前。经多次与教廷交涉无果后,清圣祖于康熙六十年明确下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雍正、乾隆、嘉庆对天主教的态度变得更加严厉,各地教案频发,传教士和教徒遭到搜捕、迫害,教堂被毁弃、没收,传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
此期天主教文献的出版呈现出两极化的特点。一方面,宫廷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刊行西学著作,同时天子脚下的北京教堂也在继续出版天主教书籍;另一方面,外省各地的教会出版机构遭到全面破坏,但民间顽强地存在着一股刊刻传播天主教文献的潜流。
雍正、乾隆虽然不再像康熙那样热衷于西学,但宫中仍留用了大量传教士从事修历、地图测绘、翻译、医药、钟表修理、绘画、铜版印刷等工作。宫廷中继续刊刻西洋天文历法、测绘、地理、艺术等方面的著作,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高潮。康熙后期的陈梦雷编成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雍正继位后命蒋廷锡编订,于雍正六年(1728)以武英殿铜活字刊行,其中收入了《西洋新法历书》、《职方外纪》、《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西学书籍的内容。雍正二年(1724),将康熙时成书的《御制数理精蕴》、《御制钦若历书》(更名《御制历象考成》)、《律吕正义》合编为《御制律历渊源》,内府雕版刊行。乾隆七年(1742),武英殿刊刻出版敕纂《御制历象考成后编》,传教士戴进贤、徐懋德参与纂修。乾隆十一年(1746),敕修《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成,武英殿以朱墨套印形式刊出,传教士德理格、魏继晋、鲁仲贤参与了该书的修纂。乾隆二十一年(1756),武英殿刊行《钦定仪象考成》,主要编纂者中有传教士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①参见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第9、35页。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其中收入的西学书籍有《御定律吕正义》、《御制律吕正义后编》、《职方外纪》、《坤舆图说》、《泰西水法》、《乾坤体义》、《表度说》、《简平仪说》、《天问略》、《新法算书》、《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御定历象考成》、《御定仪象考成》、《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数理精蕴》、《天步真原》、《天学会通》、《同文算指》、《几何原本》、《奇器图说》等数部;存目部分有《西儒耳目资》、《别本坤舆外纪》、《西方要记》、《辨学遗牍》、《二十五言》、《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西琴曲意》、《交友论》、《七克》、《西学凡》、《灵言蠡勺》、《空际格致》、《寰有诠》、《天学初函》等多部。从上述书目可以看出,《四库全书》全文收入的都是西学类著作,其中又以历算书籍占绝大部分,仅在子部杂家类存目部分收入了数种天主教教理和宇宙论著作的提要。雍正、乾隆年间,还任用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蒋友仁、傅作霖、高慎思等人以西洋技术测绘中国地图,先后出版《皇舆十排全图》(《雍正十排图》)、《皇舆全图》(《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十三排图》),前者有木刻本,后者有铜版本②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第3031页。。乾隆时还在郎世宁、艾启蒙、王致和等传教士主持下,完成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台湾得胜图》、《平定安南得胜图》等多种西洋风格的铜版战图的出版③其中《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是送到法国制版的。参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内府刻书概述”第3537页;“清代内府刻书总目录”,第3738页。。
禁教期间,各地教堂大都遭到破坏,但北京南、东、北三堂由于皇帝的特许得以保留,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还出资为自己当皇子时的教师德里格新建了西堂,北京的传教士仍然可以继续撰写、出版著作④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北:光启出版社,1992年,第122125页。。在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所列的书籍中,刊于康熙六十年(1721)禁教令之后的就有24种,基本上是在皇帝卵翼下的北京出版的⑤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477478页。。
在北京之外,虽然朝廷明令禁教,但传教活动仍在不少地方顽强地开展,著名的传教社区有塞外西湾子、湖北谷城磨盘山“教友谷”、浙江衢县麻蓬村等。禁教初期教徒人数有所下降,但到禁教后期反而持续增加⑥1703年中国有教徒近20万,1740年减到12万,但到1815年则升至21.7万。参见Nicolas Standaert,ed.,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Leiden:Brill,2001,p.383.。由于传教被迫转入地下,向乡村转移,教众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下层百姓⑦道光二十一年(1841),江南教友至少有48000人,大都为农民、渔民。参见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北:光启出版社,1992年,第216页。,传教出版物更趋向于通俗化、实用化。教理书籍、经卷、瞻礼单、通功单、图像等宗教读物,在民间秘密刊行⑧参见张先清:《刊书传教:清代禁教期天主教经卷在民间社会的流传》。。外省传教士还利用北京的特殊地位继续刊播传教书籍。嘉庆十年(1805),清仁宗发布禁止天主教堂刊刻书籍的上谕,其中透露北京“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民人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在京传教士德天赐“妄行刊书传教”,“用汉字编造西洋经卷至三十一种之多,……所造经卷,系刊刻汉字”。这一年对北京教堂进行了一次搜查,打破了北京地区长期以来的相对平静,查获“清汉字书一百七十三种”,可见当时刊版之多,其中可能有禁教之后各地教堂抢救性地转移到北京教堂的书版。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四所教堂才被全部关闭。然而道光二十年(1840),北京官员又一次查获两千余本天主教经卷,刻书版片1512块⑨参见邹爱莲、吴小新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38、839、845、1266页 。。可见,官方的禁教远未使天主教文献的出版彻底断绝。
结语
明清间天主教文献的刊刻传播,有皇室和官方、士大夫、教会、书商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士大夫和教会。官方所重者主要是其中的西学器用部分。明清帝王对传教士的态度,可谓重其“器”,而摒其“道理”。明朝皇帝看重的是传教士进献的西洋珍奇及其铸炮、修历技能。乾隆皇帝则借四库馆臣之口道出了对西学的看法:“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朝廷的政策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四“天学初函”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361137页;卷一百二十五“寰有铨”条,第1081页。。这充分反映在官方刊刻书籍的倾向上,即仅出版历算、地理、音乐、工艺美术等实用性西学文献,对宗教文献则十分敏感和排斥。晚明士大夫刊刻西学著作的成就突出,同时也刊刻了一部分宗教文献,对西学和天主教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入清以后,教会成为天主教文献出版的主要力量。教会所刊基本上是宗教文献,其中也有少量像《西国记法》、《二十五言》、《西学凡》、《本草补》这样对传教有促进作用但与教义并不直接相关的文献。一部分天主教文献流行很广,风行一时,具有商业价值,成为书商藉以谋利的工具。
为了从量的方面考察明清间天主教文献的演变,笔者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②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名表》(第473478页)、崔维孝《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在华出版神学著作统计表》(第391392页),按本文分类标准统计。徐著表中的一些书并不见于提要正文,提示在如今可见资料大为扩充的情况下,亟需一部更为完善的明清天主教著作目录和提要。崔著表中有25部著作,其中2部为抄本未计入,刊本中出版时间不详者,则根据作者在华活动时间或生卒年断定该书所属阶段。统计了各个时期天主教书籍的出版情况,制成下表。中,宗教日用文献的比重在后两个阶段显著上升,显示思想文化层面中西对话与交锋的高潮已经过去,传教工作走向常态化,日常宗教活动中对实用文献的需求大大增加。在这方面,耶稣会士利类思有杰出的贡献,他在顺治、康熙年间花了24年时间将各种宗教礼仪用书译为典雅的中文①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156157页。。即使是宗教理论文献,以士大夫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深奥教理著作的比例也在减少,而以普通教众为对象的宗教启蒙读物不断增多。不少宣传天主教教义的著作以语体文或问答体的形式写作,以适合于基层教众阅读。

天主教在华出版中文文献分类统计表
实际上,教会在华出版物中还包括一些西文著作。如天启六年(1626)金尼格将中国儒家典籍《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出版;殷铎泽、郭纳爵等以拉丁文译《大学》、《中庸》,分别于康熙元年(1662)、康熙六年(1667)刊刻于江西建昌和广州②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24、331页。方豪:《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见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90191页。。这些出版物属于“东学西渐”范畴,与本文主旨不甚相关,故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