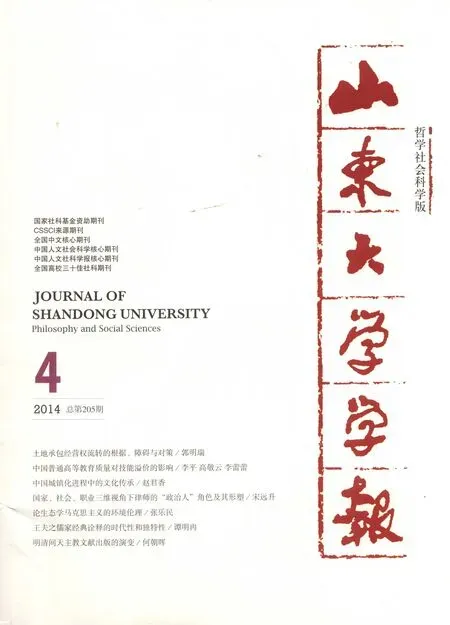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根据、障碍与对策
2014-04-05郭明瑞
郭明瑞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根据、障碍与对策
郭明瑞
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一项用益物权,完全流通性是其应有的属性。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法律和政策上的根据。然现实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认识上的模糊、权属不清、改变土地用途等障碍。为保障规范有序地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厘清思想上的认识,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确权,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搭建交易平台,强化政府的服务、监管职能。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障碍; 对策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根据
众所周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完善而出现并确立起来的。最初,土地承包经营权仅指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一方依承包合同享有的权利,并不具有对第三人的物权效力。学者称其仅有债权效力。当时,由于承包权仅被看作为基于承包合同享有的合同权利,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因此,对于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予以严格限制的,承包权人不能自主进行流转。1999年7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4条就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人同意,转让承包合同,转包或者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这表明承包方以任何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都须经发包人的同意,否则即无效。
至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颁行,法律上开始确认承包方对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为物权,也确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流通性*郭明瑞:《也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兼与刘保玉教授商榷》,《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如该法第16条中明确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的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当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还是予以一定限制。如该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编以专章(第十二章)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并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一项用益物权。依《物权法》第125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业生产经营者为种植、养殖、畜牧等农业目的,对其依法承包的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占有、使用其承包的土地的权利,在他人占有其承包土地时有权要求返还;有自主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其收益的权利,对于他人对其收益的侵占,当然有权要求返还、请求赔偿损失。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利。作为财产权利,除法律另有特别限制外,当然具有流通性。从法理上说,为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财产权益,发挥土地的效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当然有权依法自主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流通性,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应有的属性。可以说,自从《物权法》明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流转就不应存在法理上的疑问。
有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以家庭承包方式设立的承包经营权和以竞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者的流通性不同。只有以竞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承包经营权才有流通性,而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具有完全的流通性。其根据是,《物权法》第128条中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而第13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依此两条规定,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入股、抵押,只有以竞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可以入股、抵押。的确,《物权法》对于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以竞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的规定有所不同。这一不同规定源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这不能成为否认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具有完全流通性的理由。
首先,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是《物权法》的这种区别对待的规定是有局限性的。在《物权法》立法中对于是否赋予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完全的流通性就有争议。即使在《物权法》通过后,一些学者也强调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动性。如张新宝教授在对《物权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评价中提出:“合理平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社会保障功能与资产功能之间的关系、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动性、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优化配置、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无疑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张新宝:《土地承包经营权》,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名家讲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7页。。崔建远教授在谈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精神实质时指出,以竞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代表了农业用地权利的发展方向,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化,……现今以家庭承包方式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模式就得变革,向类似‘四荒’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模式发展。”这也就是说,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具有与以竞争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同的流通性*崔建远:《物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其次,从立法者关于《物权法草案》的立法说明中可以看出,法律之所以作区别对待的规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全国范围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完全放开的条件尚不成熟,待条件成熟时即可实行完全放开。这大概是担心一旦规定完全放开,各地就会不顾条件的以各种方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第二,为今后修改有关法律和有关政策留有余地。这里所提的“留有余地”正是指为完全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通性留有余地。因此,尽管《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而未规定采取“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并未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作出禁止性的规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兆国在向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中,作了以下说明:“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能否放开的问题。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现在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为了维护现行法律和现阶段国家有关土地政策,并为今后修改有关法律或者调整有关政策留有余地,物权法草案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此说明的理解请参见郭明瑞:《也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兼与刘保玉教授商榷》,《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因此,从立法者的立法意旨上说,立法上也是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通性的。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属于私法问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依私法上“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规则,只要法律未作出禁止性规定,权利人就可自主决定是否流转以及以何种方式流转。另一方面,《物权法》第128条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虽采取列举法,但这一列举并未穷尽可以采取的各种方式,而是用了“等方式”的用语。这里的“等”既可作为是对前述方式的概括的解释,也可作还包括其他方式的解释。采取后一种解释,并不违背法律的精神。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以扩大解释的方法认可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具有完全流通性。
再次,如果说,我们不能通过扩大解释认可《物权法》上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全流通性,那么,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以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通,就属于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事项。《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依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活动就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自《物权法》实施后,国家政策一直在致力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例如,2008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要求:“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抓紧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2012年12月3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再次要求:“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指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必须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是强调如何依现行法的规定予以限制,而是强调如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保障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主地按照自愿有偿原则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自愿有偿原则,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可由权利人自主流转的财产权*郭明瑞:《也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兼与刘保玉教授商榷》,《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并且,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许多地方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试点工作。
综上所述,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完全流通性,既是该权利的属性使然,又是深化改革的趋势要求,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凡与此不相应的观念和作法应予以纠正,与此不相符合的法律法规亦应作出相应的修改。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障碍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让与他人,受让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让与人则不再享有该权利。这也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取得方式。广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仅将经营权转让给他人而自己仍保留承包权,此种流转方式的结果是受让人取得对土地的经营权,而让与人仍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物权法》中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广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既包括转让、互换,也包括转包、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尽管如上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各种方式流转,是有基本法上的依据的,但是,现实中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有序流转上仍存在许多障碍。
(一)观念上的误区
在对待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流转观念上主要存在两方面的误区:
一种观念认为,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享有的社会福利,是保障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全放开,允许以各种方式流转,甚至可以抵押,就会使农民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土地。这种观念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视为农民的一种福利和生存保障,在最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观念已经与现实不符。一方面,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范围在日益扩大,“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发展完善,农村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渐居于次要地位”*刘凯湘:《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另一方面,改革和发展是让农民增加收入,富裕起来,而不是仅仅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一项财产权利,而并非仅为生存的基本条件。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流动起来,虽可让农民有地种,但也仅仅是能解决农民自家的吃饭问题,而不能更多地增加收入。现实中农民的收入越来越主要的并不是靠“经营”家庭承包的土地,而是靠其他收入。有学者指出:“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量结构中,非农化、多元化的特征更为鲜明。与上年相比,在农民纯收入的增量中,农民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即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的纯收入增量占比,2004年为64.7%,2011年下降到27.3%。农民来自于非农产业的纯收入增量占比,2004年为25.8%,2011年增加到55.1%”*姜长云:《中国农民增收现状及其中长期影响因素》,《新华文摘》2013年第17期。。许多地方的农村,留在家中种地的只是一些老年人,而一旦这些老人不能种地了,或者无老人种地,又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只能撂荒。这显然既不利于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这种观念认为,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完全流通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会完全流通。这是一种误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完全放开,并不等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会在各地全部流转,这只是为农民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决定是否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以何种方式流转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流转问题上,农民会有自己的利益衡量,并非许可流转就会不顾一切盲目地将其承包地流转。以争议最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为例。我们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并不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一定用于抵押。是否能够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还至少决定于两方面:一是农民有融资的需求且愿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二是金融机构经过风险评估愿意接受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如山东《寿光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借款暂行办法》中就规定:“本市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因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向金融机构申请货款时,可以依照本办法规定,以其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抵押担保。”“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借款,原则上不能超过家庭承包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依照本办法开展货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按有关规定对贷款人的资信进行审查,保障按期收回货款。”可见,允许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借款,仅是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担保权能,为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借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至于农民是否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借款,金融机构是否接受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借款的申请,则是另一回事。抵押借款为一种市场行为,当事人双方均需也会对其风险作出评估的*需要说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是存在一定法律障碍的。因为,依《物权法》第184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除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外,属于不得抵押的财产。这一规定与中央关于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权能的政策不符,应予修正。。
另一种观念认为,既然中央提出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推进城镇化建设,政府就要下大力气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动起来。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有的地方将有多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一个考核指标。特别是在发展所谓特色农业,搞“一乡一镇一业”时,当地政府更是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促成承包地流转,有的甚至带有强制性,忽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流转主体地位。如“一些地方以流转比例和流转规模论英雄,逼得基层干部采取多种方式诱导推进,违背农民真实意愿”*刘奇:《农村土地的现实困境》,《财经》2014年第7期。。这种观念忽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市场行为,是通过市场对土地资源重新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应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应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
(二)权属不清
产权清晰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只有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清晰的前提下,明确谁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谁有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谁可以通过流转取得对土地的经营权以及所取得的土地经营权有何效力,土地承包经营权才能有序有效地流转。从理论上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清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现实并非如此。这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可流转土地的权利主体不明确。现实中对于农业用地的占有与占有人是否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将其流转,是存在诸多疑问的。例如,有的人特别是农村干部利用权势占有了相当多的农村土地,他们能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到期,但并未续签,原承包人还能否享有权利?有的农民长期在外打工,承包地由他人占有使用,权利归谁享有?有的承包方全家迁入了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业户口,但未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其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诸如此类问题若不解决,无论是认可现实对土地的占有人有权流转,还是不认可现实占有人有权流转,都会引发群众的不满,使土地权利的流转陷入混乱。
其二,受让者的预期权益不明。没有人能依法流转土地权利,土地权利就不能流转;没有人愿接受流转的权利,土地权利也不可能实现流转。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受让人决定是否受让当然是从受让是否有利于自己上考虑。只有在受让后的预期利益明确且于受让人有利时,受让人才会接受流转。但现实中受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权益并不都清楚。例如,依《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采取各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物权法》第126条规定了不同农业用地的不同期限,如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这一期限从何时算起?是从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还是从《物权法》实施之日起算呢?此并不明确。若从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算,相当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剩余期限已经不长了,而作为受让人受让的权利期限若过短,受让人就不会对土地的利用有久远的计划。特别是希望通过流转取得更多的土地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为职业的,若通过流转所取得的经营权没有长期的稳定性,就不可能实现其理想。因此,受让权利的期限不明确或者过短,就难以有经营者愿意受让流转的承包地的经营权。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就难以实现。
(三)承包地的用途被改变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方面可使承包权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其他职业并取得转让收益,另一方面可使土地相对集中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依《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然而,现实中有的通过流转方式(转让或出租等)取得承包地的使用权,未经批准就擅自改为建设用地,用来建场、建房。有的虽未将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用于非农建设,但“非粮化现象严重,一些大户圈占土地后,主要从事苗木、花卉、蔬菜等经济作物生产,粮食安全问题难以保障”*刘奇:《农村土地的现实困境》,《财经》2014年第7期。。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对策
为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地正常流转,必须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首先要从理念上认识到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性,解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完善的模糊认识。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应是利于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益,能使农民更多地从土地上解脱并从中获得相应的利益,而不是使农民不脱离土地。无论是保护农民财产权益,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经营,还是实现城镇化,使城乡一体化发展,都绕不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其次,笔者认为,至少还应采取以下必要的对策,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一)对农民的承包地进行确权
这里的确权并非是指确认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权利属性,因为《物权法》对于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的规定是明确、清晰的。确权是指确定农民具体享有的土地权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确权可以是确认权利股份,但就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应确认农民对哪宗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哪块土地又归何人享有土地权益。确权应公开、公正,必要时需经农民集体的全体成员评议,以做到群众无疑义。笔者认为,对于利用不正当手段多占地的,应明确其对多占的土地不享有权利;对于不应收回承包地而发包人予以收回的,应确认原承包人仍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仅外出打工或就业而未在城市落户的,自应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在城市落户的农民,是否可享有土地承包经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3款规定:“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承包方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依此规定,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承包方,不能享有原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今天看来,并不妥当,应予修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其一项重要财产权利,也可以说是其作为农民积累的一笔财富,即使其迁入城市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被剥夺。而应允许其保留该项权利,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以取得收益,以便以此作为其在城市安家置业的资本。城镇化会使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但不是让变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失去原享有的权益。
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物权法》第127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对某宗土地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记载为准呢?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学者对此就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属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应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也就是说,未经登记的,尚不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物权法》未采取这种观点。《物权法》第127条第1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第129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依此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互换、转让,并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仅具有对抗效力,登记与否为当事人的权利,而非当事人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要件。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登记,登记机构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办理设立或变更登记;当事人未要求登记的,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权利。即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未经变更登记也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而不是不发生变更的效力。这里的善意第三人应是指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例如,甲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未经登记,乙仍取得受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若甲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又转让给丙,而丙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已转让给乙,则丙可以取得受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乙不能以其已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抗丙。但如果丙知道甲已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或者应当知道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转让给乙(例如,丙知道该承包地已为乙占有使用),则丙不为善意第三人,不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确权并非以发证为主,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仅是对权利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形式上的确认,是权利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证据,但不是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事实。当事人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依是否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中规定:“承包方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即以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请求确认该流转无效的,应予支持。但非因承包方原因未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证书的除外。”这一规定将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前提条件,似有将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作为是否享有权利的根据之嫌。笔者认为,这一解释并不妥当。。实务中,有的实际承包的土地范围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不一致,如,依土地承包合同和实际利用土地的状况,甲地为某人承包经营权的客体,但甲地却登记记载在他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当事人要求确认权利的,应如何处理呢?有的法院仅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确权依据,而作出相应的判决,这种判决理由是不正确的。由于原告实际上是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不正确,而认定自己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因此,法院应当对其是否有享有权利的事实根据进行审查,而不应仅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记载就认定原告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在法院作出原告事实上对涉案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裁决,原告才可以以法院的有效裁决为证据请求登记机构更正登记的错误。因为对于不动产的登记错误,权利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但在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变更或者登记机构认为申请人尚无足够证据证明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不能办理更正登记。于此情形下,权利人只能提起诉讼,由法院判决其享有不动产权利,而后根据法院对其权利确认的判决,申请登记机构办理更正登记。如果登记错误,权利人要求法院确认自己的权利,而法院在审理时又以不动产登记为确认权利的根据而作出裁判,那么,权利人岂不陷入登记机构与法院相互推卸的怪圈,而无法得到救济?
其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如上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有重要意义,若期限不明确或者期限过短,难以展开流转。笔者认为,为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应于确权中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永久性。《物权法》第126条第1款规定了承包期限,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笔者建议,对于该条第1款关于承包期限的规定,不应视为强制性条款,而应看作为法定的最短期限的规定*梁慧星教授负责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461条规定:“农地使用权的期限为五十年。既存的农地使用权,其期限短于五十年的,延长为五十年。”在对该条说明中指出:农地使用权的期限,应为法定期限。当事人在设立农地使用权时,不可短于法定期限而约定具体农地使用权的存续期限(见《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414页)。这一观点可供参考。。另外,国家应作出规定,承包期届满的,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外,土地承包权人继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严格遵循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原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的原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这些原则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条件。笔者认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务中特别应注重以下几点:
其一,坚持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私法上的交易行为。私法主体地位平等,私法自治是私法的核心原则,等价有偿则是价值规律的体现。因此,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上,必须坚持平等自愿原则。自愿原则体现为交易的双方依自己的意愿平等地协商流转的相关事项。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何时流转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流转,完全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自主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不得诱导当事人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各级政府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上可以发挥引导作用,但不能起主导作用。农民自治组织可以协助当事人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不能代当事人决定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其二,坚持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现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不能发生土地所有权性质的改变,但却常发生土地的用途的改变。现行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笔者认为,这一限制必须坚持,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农业用途的范围极为广泛,而限制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只能保障不使农业用地擅自改为建设用地,而不能保障基本粮田和粮食生产。一般来说,种粮较之从事其他农业生产,收益要低。现实中相当多的流转土地是用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受让人是为从事其他农业生产而非粮食生产流转土地的。因此,为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基本粮田的规模,应对“农业用途”作必要的限缩解释,明确:土地为基本粮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粮田用途。另一方面,国家应采取相应的补偿政策,保障种粮户种粮的积极性。
其三,坚持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依《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者,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其他用益物权在主体上的区别。因此,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也只能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能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特别是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会进入这一领域,有的仅是为圈占土地以伺机牟利,并不利用取得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有的则根本不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因此,对于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让土地权利的,须予以一定限制,一方面,受让者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另一方面,受让者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以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仍能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客体,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三)建设农业产权交易市场,强化政府的服务、监管职能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市场行为,但不能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应强化其服务和监管职能。
政府服务职能的强化主要是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创造安全、便捷的条件,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公开、公平、公正。以政府为主导建设农业产权交易市场,是一项强化服务的重要措施。如山东省滕州西岗镇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就建立起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服务中心负责制定土地流转规划、收集发布土地流转信息、进行土地收入评估、规范土地流转程序、指导办理流转手续。这一举措健全了交易体系,使土地流转进入有序、公开便捷的轨道,推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政府监管职能的强化主要是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不破坏生态环境等。
四、结语
[责任编辑:林 舒]
The Basis,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Land Contracting Right of Management Circulation
GUO Ming-rui
(Law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as a usufructuary right, full circulation is its attribute. There are legal and policy basis for transferring the contracted land management rights. But in reality, the land contracting right of management circulation has some problems on vague, unclear ownership, land use change and other obstacles of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ensure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land contract and management rights orderly, we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thought, verify farmers’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adhere to the land contracting right of management circulation principle, build a trading platform, and strengthen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regulatory functions.
circulation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obstacle; countermeasures
2014-05-12
本文系山东大学社科重点项目“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私法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郭明瑞,山东大学法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烟台264000)。